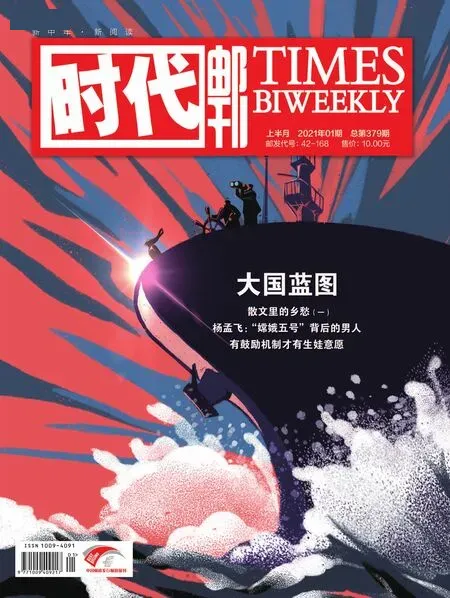我的主治醫生
王主任作為我的主治醫生,已經三年了。
在遇見他之前,我先后問診了其他醫院的幾位醫生。相對他們的冷傲,他可算是十分親切接地氣。第一次咨詢,他跟我說:“小姑娘,你這個年紀,腫瘤一般不會是惡性的,就算是惡性的,發現得早,也不會有什么大事,別害怕,我給你盡快安排手術。”因此,我對他印象頗好,之后的治療方案全交由他做主。他說什么,我都說好。可能我也是他遇到最好說話的病人,他忍不住問我:“怎么我說什么你都說好?”我答:“你是醫生,我是你的病人,當然聽你的。”
某日復查,他給我開驗血的單子,開完之后想起來,問我吃飯了沒有,我說吃了一塊巧克力。他說那不多,讓我去驗,有人問起來就說空腹。我點頭說好,那一刻,我們瞬間結盟。
病理檢查結果出來得很戲劇化。第一份病理報告說沒有問題,于是我喜滋滋地跟獵頭聊下一份工作的事,結果兩日后又接到醫院電話,說還有一份病理報告也出來了,是惡性腫瘤,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癌癥,讓我去醫院找王主任。
王主任在他常用的診室。他所在的婦產醫院當時管理秩序不算很好(現在好了),經常上一位患者還沒看完,下一位就已經擠進診室了。我進去看病時,幾位阿姨也這樣進來了,都是五六十歲的樣子。王主任看著我,嘆了口氣說:“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壞消息是惡性的……”身后的阿姨們頓時紛紛感慨:“天啊,這么年輕就……”王主任接著說:“好消息是沒有擴散,選擇放療就可以了,不用化療,不用擔心掉頭發。”阿姨們又齊齊感嘆說:“真好真好,不嚴重就好……”那場面頗覺喜感。
每月至少開一次藥,三個月一次復診,如此頻繁的接觸,我和王主任迅速建立起“革命友情”。前兩年,我去時偶爾會帶些零食給他,清明的青團、平安夜的蘋果、隆冬里的柿子餅,我想這是日常里人對人的一點甜。今年疫情來了,我便不再帶吃的,問他口罩可夠用,他說醫院一天只發一個。我下次去就給他拿一些。
王主任年紀沒有我父母大,但我媽每次見他都再三強調說我一個人在北京,平時父母不在身邊,恨不得他把我當成自家孩子。媽媽說的當然是虛詞,但也可見我這種情況,病人和主治醫生的關系是緊密的,才會聊到這些。
他是態度謙和、說話又實在的醫生,給人許多信任感,這對于病患和家屬來說尤其重要。現在,我成了他的義務宣傳員,每次排隊看病時都會安撫其他病人,推銷王主任。
朋友不明白,那么多選擇,我為什么要去那么遠的婦產醫院——因為那里,有一個與我有緊密關聯的人啊。我去那里,倒像是去見一位老朋友。他問我好不好,我問他好不好。作為病人,我是否不適,作為醫生,他是否辛苦。
手術之后,我休養了一段時間。他讓我鍛煉,說我體質太虛。我問他,傷口不怕扯到嗎?他說不怕,扯不到傷口,該咋活動就咋活動吧,多活動。每次復查拿片子,他一邊看一邊說:“你恢復得很好,各項都很好。”我又說:“我有個肺部片子顯示有問題。”他淡然地回答:“我肺部片子也有問題,這都不影響,不是什么病。”
他的那種態度,豁達又樂觀,讓人平添幾分信心。真希望每一位病人都能因此得到安慰,在病痛中少一些擔憂和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