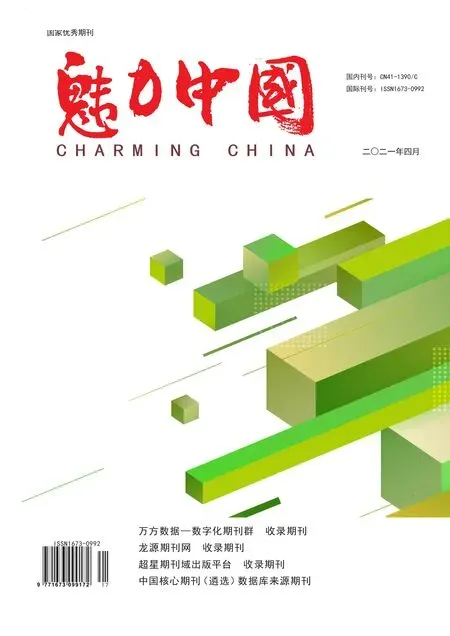知識產權法基本范疇中的特殊法理分析
秦萌
(呼倫貝爾學院法學院,內蒙古 呼倫貝爾 021008)
通過傳統范疇理論對價值、本體等范疇框架的預設,能夠發現知識產權中的特殊法理
一、研究知識產權法基本范疇中確定特殊法理的標準
(一)具有對知識產權法特有規律的揭示作用
對于知識產權而言,其內生產以及內容等方面均能夠表明該權利具有民事權利屬性,為此,其屬于民事權利家族,在具備家族共性的同時,還兼備客體的無形性。為此,對于知識產權而言,特殊法理應對客體無形性引發的特殊規律進行揭示,即揭示民事權利“知識版”的獨特規定性。與此同時,知識產權與市場主體競爭優勢、人的生存發展等方面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因此,知識產權呈現的并非是單一維度下的利益,而是以立體化的方式存在,主體具有多元化特點,而特殊法理應當揭示這種獨特的權利呈現方式。基于知識產權的特有規律,知識產權法在規則設計和基本原則等方面也具有較強特殊性,展現著特殊法理。對于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而言,知識產權客體是起點,如何將抽象的財產形態轉變為能夠被法律調整的實體,這其間的法理是獨特的,無法與有形財產實現法理共享[1]。
(二)能夠對知識產權法特有學理進行明確闡述
學理能夠闡釋知識產權法基本范疇的特殊法理,即學說。以知識產權法價值、概念等范疇為核心存在較多學說,例如信息產權理論以及人格權理論等。此類學說雖然能夠對知識產權法特定范疇進行闡釋,但這些學說主要來自于其他學科,例如哲學,其視角并非出于知識產權法內部,為此,此類學理闡釋屬于交叉學科意義上的闡釋。因此,知識產權基本范疇內的特殊學理應滿足以下標準;第一,以知識產權法內部視角對其基本范疇進行闡釋;第二,特殊學理應具有與知識產權法相契合的時空特性。
二、分析知識產權法基本范疇中的特殊法理的體系化表達
知識產權法基本范疇中的特殊法理并非零散存在的,能夠以體系化方式對其進行表達,進而形成規范的法理體系。具體表達如下:
(一)有關客體的法理—基石性特殊法理
由于知識產權法面向的客體對象具有多元化特點,為此,在對知識產權客體進行考察、表達特殊法理時,應著眼于體系內部。第一,知識產品形態。知識產權的根本屬性是知識產品的無形性,無論是知識產權法的特質還是知識產權制度的構造,均以產品無形性為基礎。因此,通過對“知識產品無形性”法理意義進行發掘,能夠掌握私權體系中知識產權的定位,進而為民法與知識產權法的制度體系協調提供有效引導。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私權類型高度細分的背景下,知識產權雖然屬于私權,但并不意味知識產權可以與民事權利劃等號,而應該以客體范疇變動性和客體特征無形性為基礎對私權類型進行精細界定,從而實現民法與知識產權法的合理銜接。具體而言,擺正對知識產權法的認知,避免共性問題與特殊問題的混淆,同時,提高知識產權在民法理論和制度體系中的定位以及融合問題的重視程度,立足于知識產品無形特點,將知識產權制度與物權制度之間的相通之處控制在制度原則和理念方面,讓知識產品的無形性法理能夠為民法與知識產權法的制度協調提供幫助。第二,知識產品承載的正當利益。一般情況下,“勞動價值論”能夠對財產正當性進行解釋,但無法對知識產品“創造性”進行妥善解釋。對于知識產品而言,其受到保護的根本原因是產品的創造性,可以說知識產權法保護的客體是“特定主體的、新的創造性貢獻”,當“新的創造性貢獻”沒有在無形財產中體現出來,那么該財產不屬于知識產品[2]。因此,應以“知識產品具有創造性”為基礎對“公有領域”和“私有領域”進行劃定。
(二)“權利塑造”相關法理—特殊法理的構建
第一,塑造知識產權支配性。支配性是知識產權存在于私權體系的方式,也是知識產權“合法壟斷”的外在表現。目前,人們主要使用“排他權”、“專有權”等方式對知識產權支配性進行解讀,在知識產權客體無形性的前提下,法律在塑造知識產權支配性時,實質上就是以“排他性”權利對“非排他性”的知識產品進行權利塑造,相較于物權,知識產權支配性的塑造對法理的依賴性較高。在對特殊法理進行構建時,應落實“以簡馭繁”的權項設置方式,并在合理限度內對知識產權支配性進行塑造,避免“合法壟斷”變為“非法壟斷”。
第二,知識產權法定性的品格。以法律規定為基礎對知識產權進行制度建構是知識產權法的必然選擇,不僅能夠明確權利內容,還能夠以法定的方式實現知識產權法對“創造性”的合理識別。因此,知識產權法具有“權利法定”基因,在注重知識產權法定意義的同時關注其功能,克服知識產品的模糊性。
三、結論
綜上所述,特殊法理蘊含在知識產權法基本范疇的本體以及價值等框架內,對知識產權法特有規律具有揭示意義,發揮著奠定制度基石、調節利益關系以及制度架構的塑造作用。因此,應以傳統法學基本范疇揭示特殊法理,從而為特殊范疇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