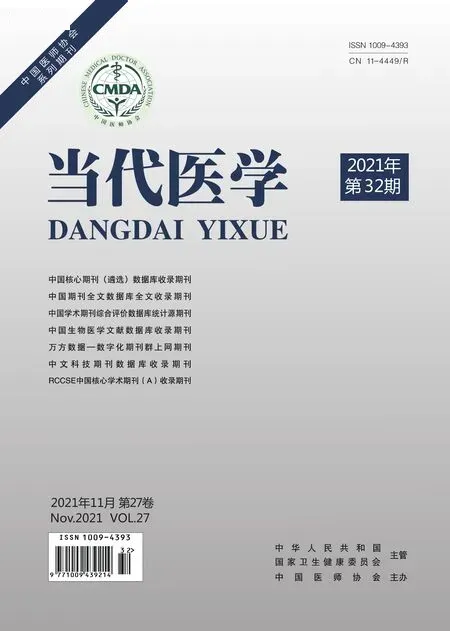抗菌藥物預防性應用預防老年腹股溝疝患者術后切口感染的臨床研究
呂華新
(廬山市人民醫院普通外科,江西 九江 332800)
老年患者因肌肉萎縮、腹壁變薄,致使其腹股溝區更加薄弱,因而發生腹股溝疝的風險更高,若不及時給予治療,將會增加腸梗阻、腸穿孔等并發癥的發生風險,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目前,臨床上針對老年腹股溝疝患者多行腹腔鏡下腹股溝疝修補術進行治療,該術式因具有創面小、易恢復等特點,逐漸被患者青睞[1]。但該術式仍存在一定的術后切口感染風險,而臨床關于行腹腔鏡下腹股溝疝修補術患者是否需應用預防性抗生素以降低術后切口感染的發生風險尚未達成共識[2]。基于此,本研究選取2018年1月至2019年6 月于本院行腹腔鏡下腹股溝疝修補術的老年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抗菌藥物預防性應用預防老年腹股溝疝患者術后切口感染的臨床價值,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18 年1 月至2019 年6 月于本院行腹腔鏡下腹股溝疝修補術治療的老年患者60 例,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兩組,各30 例。對照組男27 例,女3 例;年齡60~79 歲,平均(69.74±4.18)歲;體質量65~87 kg,平均(76.25±4.66)kg。觀察組男28例,女2例;年齡60~80歲,平均(70.11±4.07)歲;體質量64~87 kg,平均(75.89±4.72)kg。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患者及家屬均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腹股溝疝符合《外科學》[3]中的相關診斷標準者;單側初發疝;凝血功能正常者;精神、智力發育正常者。排除標準:復發疝、嵌頓疝、雙側疝、絞窄疝者;心、肝、腎等臟器功能重度衰竭者;合并免疫缺陷性疾病者;合并惡性腫瘤者。
1.3 方法 兩組患者均行腹腔鏡下腹股溝疝修補術,將10 mm 或12 mm 的套管經臍下緣通過腹壁切口進入腹直肌后鞘前方空間,并將臍孔至恥骨上中間部位的腹膜前間隙進行鈍性分離,于恥骨聯合與臍部連線的2/3處,置入5 mm套管,在恥骨聯合與臍部連線的中心位置置入另一根5 mm套管,腹膜前間隙進一步游離后,將疝囊進行回納或橫斷后,使恥骨肌孔充分暴露,并用16×10.8 cm的補片整個覆蓋,并應用可吸收縫合線縫合切口。
1.3.1 對照組 對照組在術前30 min給予0.5%氯化鈉溶液100 mL,靜脈滴注。
1.3.2 觀察組 觀察組在術前30 min給予0.5%氯化鈉溶液100 mL+1.5g 的頭孢呋辛鈉[國藥集團致君(深圳)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9990005],靜脈滴注。兩組患者術后均不給予抗生素。兩組患者均于術后隨訪6個月。
1.4 觀察指標 ①術后3 d,采集兩組患者空腹狀態時下的外周血5 mL,離心處理后,應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廣州東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型號:DP-280)測定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含量。②比較兩組患者術后6 個月內出現的淺層切口感染、深層切口感染、血腫、發熱、血清腫情況。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n(%)]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白細胞計數及中性粒細胞含量比較 術后3 d,兩組白細胞計數及中性粒細胞含量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白細胞計數及中性粒細胞含量比較(±s)

表1 兩組患者白細胞計數及中性粒細胞含量比較(±s)
中性粒細胞(%)72.30±5.05 71.48±5.17 0.622 0.537組別對照組(n=30)觀察組(n=30)t值P值白細胞計數(×109/L)7.81±0.73 7.75±0.77 0.310 0.758
2.2 兩組患者隨訪6 個月內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術后隨訪6個月內,兩組淺層切口感染、深層切口感染、血腫、發熱、血清腫發生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n(%)]
3 討論
臨床上將腹股溝疝分為腹股溝斜疝和腹股溝直疝兩種,在老年腹股溝疝患者中,腹股溝斜疝較為多見,臨床認為腹股溝疝的主要病因是腹壁肌肉強度降低、腹內壓力增高,該病患者的臨床癥狀多為腹股溝處有突出體外的包塊,站立時包塊自行突出等,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4]。目前,臨床上針對該病癥患者多行腹腔鏡下腹股溝疝修補術治療,具有創面小、易恢復等特點,但也存在一定的術后切口感染問題。因此,圍術期內是否需要應用預防性抗生素來預防術后切口感染也成了臨床上討論的熱點。
術后切口感染是外科手術中較為常見的一種并發癥,臨床上將切口感染分為淺層切口感染及深層切口感染兩種,其中淺層切口感染與常規的軟組織感染并無明顯差異,大部分患者在經過換藥、引流、追加抗菌藥物等措施干預后,即可痊愈[5]。而深層切口感染多為腹股溝疝補片發生感染,即使經過換藥、清創、引流等措施干預后,其切口仍存在遷延不愈的風險,此時需要將補片取出,進行再次手術才能提高切口的愈合速率,加重了患者的痛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6]。而抗菌藥物的預防性應用的目的在于通過在手術切口形成足量的血藥濃度,增強機體對病原菌入侵的抵抗力,進而有效降低術后切口感染的發生風險[7]。然而抗菌藥物的應用雖能有效的抑制病原菌的生長、繁殖,但對患者機體內的正常菌群也會起到抑制、殺滅的作用,破壞正常菌群的穩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感染的風險[8]。此外,不規范、合理的應用抗生素,也會增加病原菌的耐藥性,為后續治療增加難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者的經濟成本。本研究結果顯示,術后3 d,兩組的白細胞計數及中性粒細胞含量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術后隨訪6 個月內,兩組淺層切口感染、深層切口感染、血腫、發熱、血清腫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明術前應用預防性抗生素與不應用抗生素并無實質效果,臨床上無必要應用預防性抗生素用于預防術后切口感染。
在臨床上為控制及降低老年腹股溝疝患者術后切口感染的發生風險,圍術期內嚴格遵照無菌操作流程是關鍵。對術中的相關操作及手術器械進行嚴格的無菌要求,能有效降低術后感染的發生風險。進行腹腔鏡下腹股溝疝修補術時,應選擇具有抗感染作用且組織相容性良好的補片進行手術,當病原菌入侵補片表面時,可以有效形成一層保護膜,進而有效阻斷機械、化學、免疫等對病原菌的供給途徑,有效的清除病原菌,降低術后感染的發生風險。此外,在進行切口縫合時,應盡量選擇尼龍線進行縫合,其對病原菌的藏匿效果較差,可以有效降低病原菌入侵機體的風險[9]。而過多的組織分離,易引發出血,進而為病原菌的生長及繁殖提供營養支持,故臨床上在術中應盡量減少電刀的使用,提高止血效果,對于已經發生感染的患者,應盡量暴露切口,避免其向深層切口感染發展[10]。
綜上所述,預防性抗生素在老年腹股溝疝患者術后切口感染中并無實質效果,故臨床并無必要應用預防性抗生素用于預防術后切口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