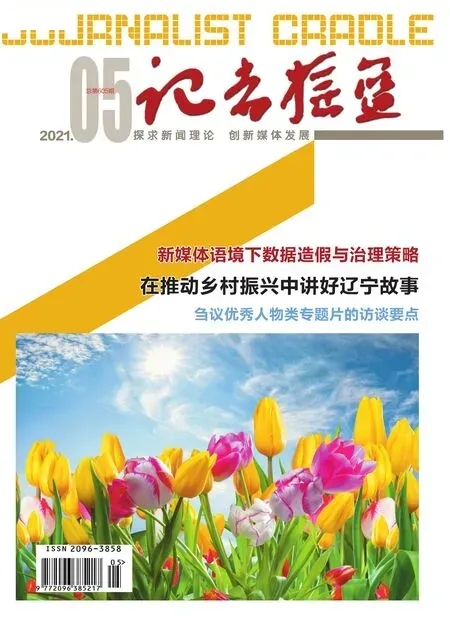談談播音降調問題及對策
——以電視專題片解說為例
□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廣播電視播音中一度出現“不喊不革命”“調高情亦高”的現象和思潮。進入改革開放后,那種空喊大話、聲嘶力竭的現象明顯減少了。但隨之也產生了“調降情亦降”“聲虛氣亦虛”的現象,為降調而降調。
那么如今,降調問題還存在嗎?還有必要重提降調問題嗎?
觀察和收看當今一些節目,尤其是許多電視專題片的配音解說,調子確實降下來了,而且降得不可謂不徹底,但給人感覺故作低沉、平淡無味、窒息壓抑,有的像是在自然自語,有的像是在說悄悄話,令受眾不得不屏住呼吸、豎起耳朵,才能大概聽得清。這樣的降調,這樣的播音,其傳播效果還會令人滿意嗎?
下面筆者就播音降調問題展開論述,結合當下播音現狀和自身播音實踐,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如何應對降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一、播音降調應該做到“無一字無依據”
播音作品的成敗與否,最關鍵的就是要看是不是從稿件的內容出發。要以稿件的內容為依據,以稿件的主題為表達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一些人播音時“睜眼看稿不動腦,張嘴念字不動心”,只顧自己機械式地播音,應付差事,哪里還有什么好的播音表達效果呢?
正像中國播音學學科體系創立者張頌教授指出的那樣,“為降調而降調的表現之一,就是脫離了內容,失去了依據”。
許多初學播音者,為了努力向成熟播音者靠攏,或者為了顯示自己的老練持重,不管什么樣的稿件,都是用厚重低沉的聲音、不緊不慢的語速。哪怕是令人歡欣鼓舞的捷報、使人興奮的喜訊,他們也是使用如此低調低速的方式進行表達,至于播出后的傳播效果如何,好像與他們沒有任何關系,這恐怕就很難令受眾滿意了。
二、播音降調應該做到“無一處無變化”
毛澤東同志曾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這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
有聲語言的有效表達和有力傳達,也離不開把握思想感情的曲折性和聲音形式的波浪式,因為只有曲折性和波浪式,才能使訴諸聽覺的有聲語言表達更生動、更精彩、更靈巧、更自然。
縱觀當今的廣播電視播音和主持,絕大多數在堅持和實踐著這樣的有變化有波浪的有聲語言表達方式。但那種自始至終都是一個低沉的調子,無精打采,毫無變化,和尚念經式的播音,也不時地出現在廣播電視節目尤其是電視專題片的解說中。調子是降下來了,可聽起來是那樣平淡,感覺是那樣呆板,語調也是那樣僵直……這種無聲音變化、無感情起伏、無語調錯落的播音,在那些旅游風光類、歷史考古類、科普知識類、人文地理類等的電視專題片的解說中非常普遍。要知道,如果沒有精彩畫面烘托和屏幕上的字幕提示,這樣的配音解說絕不會讓受眾專心地、心情愉悅地靜下心來傾聽的。
有句話叫“文似看山不喜平”,有聲語言表達也是這樣,沒有起伏變化的平淡僵直的語言,是不會產生積極的動人的表達效果和理想的傳播效果的。
三、播音降調應該做到“無一言無對象”
張頌教授在談到播音降調的問題時,針對播音缺乏對象感的現象,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了降調而降調的播音,往往失去對象感……降調而無對象,猶如自言自語,聽眾會覺得你的話與我無關。”這可真是說到了“痛處”,戳中了這類播音方式的“軟肋”。
試想,你的配音和解說作品,如果完全不顧受眾的感覺,從頭到尾好像都是在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就完全疏遠了你和受眾的距離,從而形成了“我說我的,你干你的”這樣一種令人難堪的傳播窘境。播者與受眾之間好像隔著一堵墻,從而形成了互不相干的“兩張皮”,這與當初播音表達目的和傳播預想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想真正避免這種播音與聽眾之間互不相干的“兩張皮”現象,克服掉這種沒有對象感的播音陋習,就要做到“心中有人”;把每句話既能送到受眾的耳朵里,又能送到受眾的心坎上,進而打動受眾的心弦,觸動受眾的心靈,那么這樣的降調才能真正煥發活力,才能切實取得理想的傳播效果。
四、播音降調應該做到“無一處不清晰”
當今的一些播音,尤其是一些電視專題片的配音解說,不但降調降得夠低,而且用氣發聲嚴重“脫實向虛”,既像是有氣無力的呻吟,又像是故意不想讓別人聽清的悄悄話。他們播音解說的清晰程度,大多時候竟然不及專題片里被采訪對象——普通人說話的清晰程度,這實在是有失專業播音工作者的身份,使人生厭,令人反感。
我們之所以主張不要為了降調而降調,其中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課題,就是由過度降調而導致的語言清晰度下降、嚴重影響有效信息傳達的問題。
五、結語
一部好的播音或配音解說作品,不但語調適當、感情充沛、邏輯感強,而且還要讓廣大受眾即使是在不看字幕的情況下,也能較為清晰明了地接收到完整的播音語言信息。
“降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只是為了更好地為宣傳目的服務,只是為了‘使人愿意接受’而被我們賦予了存在的價值。”對此,新時代的播音主持人員應該牢牢銘記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