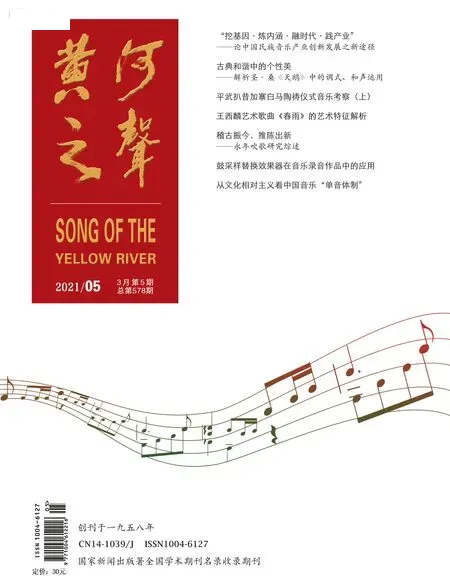拉威爾鋼琴作品中的新古典主義風格與器樂化音響效果的演奏法
——以《高貴而傷感的圓舞曲》為例
閆鶴文
在和聲的體系當中,拉威爾積極進行了嘗試,在音樂色彩層面上,也始終堅持個性化的氣質,不僅對家拉莫和庫普蘭的典雅風格進行了繼承,也對浪漫時期的柏遼茲所具有的絢爛色彩進行了發展。在此基礎上,拉威爾對相關的曲子進行了改變,呈現出拉威爾獨特的風格,展示出耳目一新的效果。
一、新古典主義的風格概述
(一)拉威爾與新古典主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拉威爾和與斯特拉文斯基正式開啟了新古典主義的浪潮,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在20 世紀的初期階段,歐洲古典的樂壇掀起了對上個世紀德國的浪漫主義風潮予以反對的浪潮,以勛伯格為典型代表的群體開始對無調性與序列的音樂風格進行宣傳。但是以拉威爾以及德彪西為典型代表的印象主義派創造出了法國特殊的和聲語匯體系。拉威爾還把奏鳴曲、組曲等相對古典的形式融合到印象派的和聲體系當中,由此可知,新古典主義并不代表一種風格的回歸,這是由于曲目的創作方法并不會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對現代化的音樂語言進行了運用。例如在高貴并且傷感的曲目當中,拉威爾將圓舞曲的節拍、和弦等元素進行疊加。以上創新性的和聲形式都是建立在圓舞曲自身節奏特征的基礎上產生的變化,這使得人們逐漸對這類音樂作品著迷。
拉威爾所創作的最為關鍵的新古典主義音樂作品是《庫普蘭之墓》,其創作于1920 年,也是最后一首鋼琴獨奏曲,其對上個世紀的羽管鍵琴組曲風格進行了借鑒,然而在此之前,其很多作品都涵蓋著清新與純凈的古典元素。在拉威爾的自傳中,他表示高貴而且傷感的圓舞曲對應的風格是相對簡單與清晰的,和聲部分會更為堅硬,旋律和線條更為突出。將高貴且傷感的圓舞曲作為時間分界線,在這一時間節點前,其所創造的作品風格基本上能夠分為回歸古典傾向與印象派傾向。在他的作品當中,呈現出印象派特征的曲目標題基本上是描述性的詞匯與語句,而與古典主義相悖的作品標題基本上都是以體裁進行命名的[1]。
(二)循環的曲式和調式
拉威爾所創作的作品所具備的結構是堅實的。《高貴而傷感的圓舞曲》是由8 首風格完全不同的圓舞曲所組成的。前七首圓舞曲都各自具備自身的風格,速度對比相對鮮明,對段落的劃分比較清晰。第八首是對曲目的匯總,由前七首中的每個主題組合而成的。事實上,第八首是易于被人們所忽視的,當然也是最為神奇的一首曲目。作曲家借助這樣的形式來對曲子尾聲進行了創作,將風格以及形式各異的旋律片段在一首作品當中進行穿插,對圓舞曲對應的速度以及風格進行有效提示。由此可知,這一首音樂作品的曲式結構對古典樂派當中的循環曲式進行了延續,關鍵是拉威爾對這一曲目的調性也進行了相同的安排。
(三)古典曲式的運用
《高貴而傷感的圓舞曲》是對維也納古典圓舞曲所具有的風格進行了借鑒,同時逐漸回歸到古典曲目當中。圓舞曲的Ⅲ與Ⅴ均是使用了相似度比較高的主題材料的ABA 三段體,第四以及第六首都屬于風旋二部的曲式。相比較之下,第四首和聲關系更加復雜。圓舞曲VII 屬于有前奉的ABA 三段體,A 段涵蓋著2 個打情以及雙劇化的內容,無論是在和聲還是在織體上,B 段都與A 段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對比,織體更為輕盈,站在和聲角度上進行分析,雙調性這一特征表現得更加明顯。所以,站在整體結構上進行分析,這一曲目更像是延伸拓展的圓舞曲目。
圓舞曲Ⅰ與Ⅱ都是采用的奏鳴曲式,第二首的曲式結構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拉威爾在進行設計的過程中運用了呈現出利都奈羅特點的小奏鳴曲式,句子的結構是運用了八小節分句。
利都奈羅的每一次出現都是被用作八小節的前置句子,對主題性的后置句子進行引導。顯示部的中一與主題問所形成的對比、主調到屬調所進行的和聲轉換過程都對奏鳴曲的典型特征進行了遵循。盡管第二主題一在初始階段處在轉調階段中,并未以屬調D 的大調形式呈現,再現部的2 個主題都逐漸回到了主調上[2]。
二、演奏效果和方法
拉威爾音響世界呈現出五彩繽紛的狀況,其非常關注配器所呈現出的音響的效果。站在配器的角度上進行分析,他不斷進行研究與探索,創建出了個性化的管弦樂配法,從而使得不同樂器所具有的表現性能進行充分彰顯。拉威爾具備自身獨特的構思與技巧,所使用的音色主要是和,思想呈現出協調一致的狀態,和節奏是相對應的。拉威爾個人的管弦樂作品都具備著相對豐富的想象力,能夠對精美多彩的音響效果進行表達,在《高貴而傷感的圓舞曲》當中,所使用的樂器有雙簧管、小號、長號、三角鐵等。在聆聽樂器的演奏時,豐富多彩的顏色與變換性的音效能夠為作品的演奏帶來一定的想象與啟示,對于鋼琴家而言,對樂隊效果進行模仿具有一定的挑戰性。
(一)器樂化的彈奏效果與方案
拉威爾所創作的管弦樂類的作品廣泛運用木管這一樂器,一般情況下,其被賦予特殊的使命。四舞曲的中段由英國管、雙簧管以及長笛等進行演繹,時而哀傷、時而明媚。魔法性的色彩能夠為不同聲樂音色的處理提供出更多的想象空間。圓舞曲II、III、V 對應的主旋律是由雙簧進行演奏的。圓舞曲II 呈現出“音樂意”的狀態,雙簧管這一樂器的演奏旋律能夠傳達出纖細與精巧的風格。借助連音與雪音結合的方式,對傳統三拍子的節奏特點予以改變,需要在極弱力度中才能夠模仿出類似的音色,運用短促的腕部動作來對兩個連奏性的四分音符進行表現。右手的第三拍上具有的跳音與票音更加關注指尖上的短促有力的波動,需要強壯收支與切分的踏板積極進行配合。在對踏板進行切換時,腳下力需要輕,每次釋放四分之三,并不是全部進行釋放,這樣的演奏形式能夠與曾樂中所具備的平緩綿長氣息更為接近,實現更加理想的音色表現效果。
雙簧管所表現出的音色為第二首圓舞曲賦予了神秘同時吸引力極強的力量,所表現出的淡淡憂傷深入人心,在平靜中彰顯出精巧細膩的音樂畫面,拉威爾對主鵬和插段進行了標注,賦予作品更加緩慢以及自由的節奏,旋律開頭在C 音上捧,彰顯出更為哀傷的情感,長笛所具備的透明音色所表達的情感往往更加自然,裝飾音與四分音符兩者之間所進行的過渡需要借助手腕部的輕盈柔和動作進行呈現,從而傳達出細膩的音符。
在長笛這一樂器的支持之下,第四首圓舞曲的主題得以被牽出來。跨越小節對應的附點節奏借助弦樂器當中常見的演奏法進行表達,鍵盤樂器在進行敲擊后無法表現出漸強減弱的效果的強狂下,內心需要具備更強的張力對并連接音與音的聯系。右手借助輕弱的演奏對優美旋律進行演奏,觸鍵深而柔軟,樂齊奏呈現出低聲部符合節奏的特征,能夠提供強大的推動力,在3/2 拍與3/4 拍共同出現時,雙手獨立更為關鍵。在進行演奏的過程中,左手需要保持平衡,從而進行精準演奏,右手旋律可以自由地進行處理[3]。在八首樂曲當中,這首華爾茲的風格作為浪漫,拉威爾曾經為其起名為“威尼斯的圓舞曲”,無論是在風格上還是在節奏特征上,其與拉威爾在晚期所創作的圓舞曲《鮑羅丁的風格》有著異曲同工的相同之處。圓舞曲VII 的主題對另外一種具有著弦樂技巧的演奏方式進行了模仿,與跳弓相似弓子觸弦后,借助其彈力跳起之后離開琴弦,速度不可以太快。手指在與鍵盤接觸之后輕輕彈起,在空中形成一個拋物線,使得余音或者是泛音能夠在空中逐漸飄散開來,手腕放松之后自然下伏。
(二)樂隊全奏的效果與演奏的方法
在第一首圓舞曲的開頭,樂隊運用了大齊奏的演奏方式,音主要是被放置在第三拍上,在對樂器進行敲擊的過程中,所傳達出的聲音相對明顯,有時會尖銳和刻耳,為了追求這種演奏效果,在進行彈奏時,需要準備直接性的力量,和弦需要安排整齊,力量需要順暢無阻,音色需要強而不粗,堅實而不硬,所以右手的小手指需要突出自身的線條,力量逐漸朝著小手指進行靠攏,勾勒出一條旋律線條,在重音第三拍不能對踏板進行踩踏。
在進行輝煌開場之后,樂隊借助弦樂所演奏出的悠揚旋律過渡句進行音色表達,柔和有致,不同的聲部逐漸減弱,旋律短暫隨著音階逐漸上行,這時需要借助手指來對連貫性的樂句進行彈奏。隨著手指的不斷移動,手腕會帶動著手臂,觸鍵相對柔和,左手輕輕進行點綴,演奏出弦樂撥奏這樣的感覺。之后旋律能夠被第二主題素材節奏所打斷,之后樂句能夠呈現出漸強的效果,開始時,樂隊當中融入了三角鐵、鈴鼓,精巧可愛。右手對觸鍵緩慢進行接觸,呈現出清晰明亮的音色效果,中間聲部時,左手和弦音能夠被優雅唱出,節奏比較精準。盡管樂隊當中所敲擊的聲音不容易被模仿,但是也需要對律動的關鍵性與重要性進行提示,右手會跟隨著左手變化逐漸增強下鍵力度與速度,三個非常果斷和干脆,有力量的和弦能夠將音樂逐漸帶入到高潮部分。隨著音樂的發展,便是呈現出令人驚悚的音樂,逐漸拉開新的畜牧,這一次所進行的強奏會比開場時的輝煌更勝一籌,尖銳的小號聲會逐漸沖破耳膜,氣勢相對浩大,所以,和弦體系的第一個音需要借助腰部進行發力,運用大臂力量使得左右手一齊呈現出驚人力量。圓舞曲VII 借助循序漸進的形式逐漸達到高潮部分,也呈現出了一樣的音效[4]。
三、層次與對比
在《高貴而傷感的圓舞曲》中,無論是旋律還是伴奏,這幾首圓舞曲都呈現出一定的對比性,這也是其層次更為鮮明,使得聽眾產生耳目一新的感受,更加享受音樂所營造的氛圍,對《高貴而傷感的圓舞曲》進行深入分析會發現背后所蘊含的音樂價值與效果。
(一)旋律與伴奏
拉威爾更加關注旋律體系的作用與價值,其曾經表示在音樂體系當中,都具備了含蓄的旋律與輪廓。所以,拉威爾作品的旋律呈現出功能式的狀態,句子長度相對較長,呈現出古典主義的特征,具有相對明確的節奏以及清晰的結構。例如,在第五首圓舞曲當中,右手所演奏出來的清幽的旋律往往帶著美妙的情思,在整個音樂作品演奏過程中,其對旋律體系的處理相對微妙,借助輕微的半音變化來對樂句進行移調,色彩呈現出明暗相間的效果,左手運用持續以及半音色的不協調伴奏形式實現和聲延留的效果,所以,在小姐內不可以對踏板進行切換,需要對和聲效果進行保留,全曲略帶著惆悵與隱晦,緩慢分解和弦,創造出誘惑力更強的氛圍,對歌德時代進行了回憶。
(二)鮮明與朦朧
拉威爾對鮮明與朦朧進行了強調,呈現出明與暗對比的效果,第二首以及第五首圓舞曲都呈現出色調相對暗淡、朦朧與鮮明的旋律。第二首圓舞曲導奏是籠罩在朦朧色彩當中,具備著拉威爾所特有的冷峻,導奏呈現出不和諧的效果。運用圓號進行演奏時,左手聲部會比右手更加惆悵,多了一份鎮定的色彩。色調時明時暗,在進行演奏時,對這些變化進行處理的過程中,需要具備色彩想象力,意識到色彩的變化。第七首圓舞曲對應的導奏呈現出遲疑的效果,是對問句進行了反復,程度逐漸減輕,語氣逐漸加重,觸鍵比較輕,音色相對柔和與夢幻,整個作品的導奏就像是在襁褓當中所存在的物體,呈現出朦朧平靜的效果,直到優雅圓舞曲破繭而出,逐漸將人們帶入到明亮世界當中[5]。
第七首圓舞曲所表現出來的獨立性比較強的主題旋律和前幾首圓舞曲當中所具有的相對鮮明的形象互相交織,就像是對記憶片段進行了充足,在不同人物以及回憶當中進行穿梭。此外,拉威爾也對持續性的低音進行了設置,這使得整首樂曲都具備了記憶的面紗。由于拉威爾意識到僅僅借助有限的和聲,鋼琴所創造出來的氣氛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為了實現更為鮮明的效果,就需要進行創新。在譜曲當中,對延音踏板進行了標注,其指的是對音用的踏板進行適當延長。拉威爾所選擇的第七首圓舞曲當中的主音A 呈現出持續低音的狀態,在經過轉調后,第四十一小節能夠到達樂曲的主音G,在一切新加入的音色當中,低音G 持續在曲目當中存在,無論是和聲還是在結構上,所表現出來的起承轉合的效果是非常優異的。在進行演奏的過程中,需要在彈下低音之后再繼續將延音的踏板踩下去,在對低音的色彩進行保持的基礎上襯托出其他聲部對應的主題。
結 語
拉威爾所適應的音樂詞匯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狀態,音響的效果也是充滿變化的,和聲語匯相對奇幻,與傳統意義上的調性以及旋律進行了脫離,是獨特的思維形式。《高貴而傷感的圓舞曲》是拉威爾所創作的古典性質的音樂作品,彰顯出來拉威爾的個性,在其中,拉威爾進行了很多的嘗試。通過分析作品對應的結構曲式會發現,器樂化音響效果、和聲色彩、音色層次變化呈現出來鮮明的對比性,這些研究活動的進行有助于相關學者對作品風格進行正確把握,對演奏的靈感進行激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