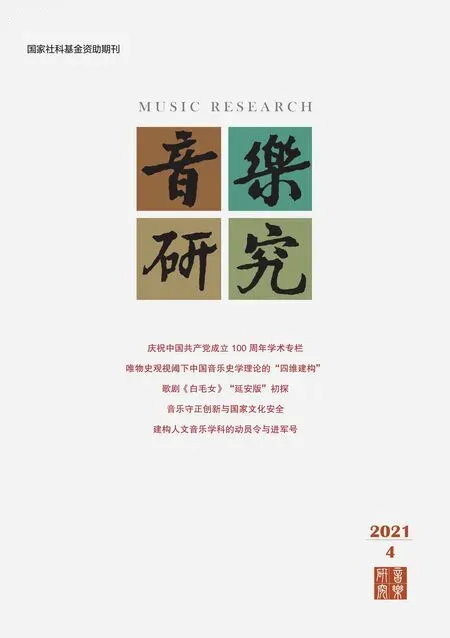建構人文音樂學科的動員令與進軍號
——郭乃安先生《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再讀有感之一
文◎秦 序
音樂學前輩郭乃安先生(1920——2015),曾撰《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一文,發(fā)表于《中國音樂學》1991 年第2 期。從1985 年創(chuàng)刊起,郭先生一直擔任該刊主編,閱稿無數(shù),此文系先生有感而發(fā),針對性很強。先生強調:“音樂,作為一種人文現(xiàn)象,創(chuàng)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樂的意義價值皆取決于人。因此,音樂學的研究,總離不開人的因素。……人是音樂的出發(fā)點和歸宿。”①郭乃安《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中國音樂學》1991 年第2 期,第16 頁。郭先生還列舉許多具體事例,說明當下某些音樂學研究,見樂、見音樂形態(tài)、見律調譜器,也見物,但未能見人,未能深入關注人,難免片面、偏頗乃至失誤。如單靠純物理量的測試分析,不知必須與人相聯(lián)系才能理解其本質,或忽略人耳聽音的模糊性,以及聽力范圍局限等人的因素。又如,以指孔位置數(shù)據(jù)簡單判斷簫笛類管樂器的音律,不考慮具體演奏實踐中人的主觀能動因素,忽視口風、岔口、半開口等技法指法影響,其結論當然“不怎么可靠”甚至“大錯特錯”。郭先生還指出,有些音樂學論著中常用一定篇幅敘述音樂產(chǎn)生的歷史、時代背景材料,但背景歸背景、音樂歸音樂,彼此掛不上鉤,也看不出相互間的必然聯(lián)系,正是“忽略了它們之間重要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即人的積極作用”。
郭先生批評音樂學研究中的“就事論事”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能聚焦透視于音樂的主體即人,忽略人的因素、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等,切中時弊。他登高而招發(fā)出的呼吁也極富啟發(fā)性,引發(fā)廣泛關注。發(fā)表迄今,已近三十年,學界仍不斷有回饋反響遙相呼應。比如趙書鋒不久前發(fā)表的《民族音樂學為何要研究人》,希望民族音樂學研究也要多多關注人、研究人;筆者兩年前也“東施效顰”,模仿郭先生發(fā)出了《音樂學,請把目光也投向表演》②秦序《音樂學,請把目光也投向表演》,《中國音樂學》2019 年第2 期。的呼吁。
最近再次拜讀先生大作,受益良多,引發(fā)許多思考。談幾點粗淺感想,與學界朋友們分享,并祈指正。
一、郭先生呼吁系向“音樂學”界朋友們發(fā)出
對郭先生“請把目光投向人”的呼吁,也有不同意見或不以為然者。有人認為無非老生常談,不過是眾人皆知的常識;也有人覺得普通聽眾或一般音樂愛好者,接觸、欣賞音樂,所謂“好讀書,不求甚解”,足矣。這些看法不無道理,我們先談談后一種看法。錢鐘書先生幽默地反對別人去關注在大量作品和論著背后的他。錢先生說:“雞蛋好吃就行,何必非要見到下蛋的雞呢?”吳冠中先生大聲疾呼,說中國當下“美盲”多于“文盲”!大千世界,蕓蕓眾生,辛苦勞作之余,愿意抽空聆聽音樂或關注各類藝術作品,隨性徜徉于藝術海洋,有所感受共鳴,已是音樂界、藝術界的幸事!若能喜歡或判斷音樂之“蛋”新鮮與否、味道如何,或進一步關注作者及音樂本體等問題,對音樂家而言更是望外收獲。這也是有關部門近來強調“加強學校審美教育”的重要緣由之一。
音樂屬于時間藝術,訴諸聽覺,自身無形無影又轉瞬即逝。相比宗白華先生所說的“目所見的空間中表現(xiàn)”的建筑、繪畫、雕塑等造型藝術,以及“同時在空間時間中表現(xiàn)的擬態(tài)藝術”,如戲曲、舞蹈等表演藝術,③參見宗白華《美學與藝術略談》,載《藝境》,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版,第8 頁。當然音樂更為抽象、縹緲,更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的“非物質”特性,④當然,音樂也不是“非物質”的存在,音樂同樣離不開物質基礎,離不開聲波這種物質載體。也更難把握分析。一般人說自己“不懂音樂”“不是干這行的”,不足為怪。所以,周海宏等學者要反復解釋“音樂何須懂”,請各界朋友放下心理負擔,音樂欣賞的規(guī)律雖然獨特,但音樂藝術本來就是屬于每一個人的,并不難體驗感受!
不過請注意,郭先生“請把目光投向人”的呼吁,本向“音樂學”即音樂學家、音樂學人發(fā)出,專門投向研究音樂的同行們,并不針對普通大眾和一般音樂愛好者。專門從事研究的音樂學家(或其他門類藝術的專門研究者)當然應有比一般聽樂群眾更高的要求。對某一具體作品,音樂學者不僅要“感其然”“體驗其然”,還要“知其然”,以及進一步“知其所以然”“明其所以然”。既要相當深入地體驗、了解,把握作品本體,探悉其創(chuàng)作過程,包括作曲家、演奏家創(chuàng)演該作品時的情感心態(tài)、思想精神及藝術創(chuàng)造的心路歷程;還要了解藝術家個性、身世、經(jīng)歷、家庭、教育、藝術和風格追求等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不僅如此,還要能“知人論世”,即不僅分析了解“這一個”作品或作者,還要與其周圍同人、朋友、社群、流派相聯(lián)系,與同代文化藝術思想政治大背景相結合,掌握該藝術門類及體裁之由來和發(fā)展趨勢,聯(lián)系相關文化藝術傳統(tǒng)的積淀(李澤厚語)等進行研究。
就體驗觀察和研究分析的方法而言,也有許多講究,比如點面結合、多方面多層次甚至多學科有機綜合;比如有針對性地結合運用音樂學的多學科(如歷史音樂學、體系音樂學等)多方面,還可以拓展到人類學、民族學、心理學、社會學、傳播學、文化學、歷史學、政治學、哲學美學和經(jīng)濟學等鄰近學科,廣泛吸收、借鑒它們的理論和方法,以深化和拓展音樂學的研究。
李澤厚先生《走我自己的路》曾希望研究要“多層次、多側面、多角度、多途徑、多目標、多問題、多要求、多方法,互相互補,互相完善”,即走出單面思維、平面思維的局限,努力實現(xiàn)立體思維、多向度復合的全面綜合的思維,這也是我們音樂研究的努力方向。
法國藝術史家丹納的《藝術哲學》,從種族、環(huán)境和時代三大因素出發(fā),結合思想感情、道德宗教、政治法律和風俗人情,深入分析研究藝術(美術),成就突出,影響很大。但后人仍有批評,說他雖考察了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所揭露的時代與環(huán)境仍局限于“上層建筑”,“忽略了或是強調不夠最基本的一面——經(jīng)濟生活”⑤〔法〕丹納著,傅雷譯《藝術哲學》“譯者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年版,第4 頁。。而且,批評者也說丹納的研究在目光投向人方面,尤其是關注具體的個人方面,也有不足。可見,藝術的研究存在非常廣闊、深邃的空間,需要多方面、多學科、多層次展開,但也極不易達到完美。關鍵和核心之一,則需要把“目光投向人”,牢牢把握藝術主體、文化主體的“人”。
二、郭先生為何提出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
由此,不免想起音樂研究所的一段往事,與郭先生發(fā)出的呼吁或有某種聯(lián)系。
20 世紀50 年代,曾任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系主任的古琴家查阜西先生(1895——1976),也兼任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今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前身)研究員。他主持整理、編輯《琴曲集成》和《存見古琴曲譜輯覽》等重要琴樂文獻,還與幾位古琴音樂研究者一道,到全國各地實地采訪、搶錄大批極其珍貴的古琴音樂遺產(chǎn)。此外,還領導幾位研究者廣泛搜集資料編寫了《歷代琴人傳》等諸多著述,為傳統(tǒng)琴樂的繼承發(fā)揚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當時一位大學剛畢業(yè)的年輕人,對編寫《歷代琴人傳》不理解,說我們應關注的事,是音樂,為什么去關注琴人呢?查先生的回答非常精辟,他說,“關注事當然應關注人呀,‘事在人為’嘛!”也就是說,沒有人之為,哪來音樂的行為、事項和音樂藝術本身呢?
年輕人認為要關注事,不必關注人,也并非毫無道理。當時盛行讀《居里夫人傳》,里面有一段趣事:居里夫人發(fā)現(xiàn)放射性元素鐳并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轟動世界。但居里夫婦極其低調,各國記者到處追蹤,好不容易才在巴黎一個不知名的鄉(xiāng)下,找到農(nóng)婦打扮的居里夫人。不料這位女科學巨星不僅拒絕拍照、采訪,反而諄諄告誡記者:“在科學上,我們應該注意事,不應該注意人!”⑥〔法〕艾芙·居里著,左明徹譯《居里夫人傳》,商務印書館1984 年版,第219 頁。
確實,科學上應該注意的是事,不必過多注意人。但在音樂藝術上和文學上,恐怕就大不一樣。如前引郭先生文章所闡明,人在音樂藝術中的地位極其重要,作品的創(chuàng)作、表演,以及共同欣賞傳播和共同再創(chuàng)造,都離不開人。
這個重要看法,當然不是郭先生首先提出,過去許許多多哲人和文學藝術大師,都曾發(fā)表過類似的意見。例如,席勒在18世紀末就明確提出“美育”概念,主張“審美游戲說”,主張藝術起源于“游戲”,并用“游戲沖動”指稱“審美的創(chuàng)造形象的沖動”。他說:“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它才完全是人。”席勒所說的“游戲”,即藝術。葉朗先生換用另一說法:“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審美;只有當人審美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葉先生還指出,柳宗元早在《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一文中,就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美學命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于空山矣。”按,右軍即王羲之,沒有他(人)的關注,蘭亭的清湍修竹,也不會成為審美對象,說明美離不開人的審美體驗,美感是人的體驗。“一個客體的價值正在于它以感性存在的特有呼喚并在某種程度上引導了主體的審美體驗”,所謂“主體”也就是人。⑦葉朗《美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404、405 頁。有關席勒話語出自席勒《審美教育書簡》“第十五封信”,葉先生采用的是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中的譯文。而人這一主體的美感體驗,是創(chuàng)造,也是溝通,是王陽明所說的“我的心靈”,是與“天地萬物”的欣合歡暢、一氣流通,也是王夫之所說的“吾心”與“大化”的“相值而相取”。⑧葉朗《美學原理》,第43 頁。
尼采說:“只有作為一種審美現(xiàn)象,人生和世界才是有意義的。”⑨〔德〕尼采著,周國平譯《悲劇的誕生》,三聯(lián)書店1986 年版,第105 頁。在他看來,人生的意義不在真理中,而在藝術中、在美之中。可見美感、審美活動和藝術創(chuàng)造,是人實現(xiàn)精神自由、實現(xiàn)人性完滿的絕不可少的條件。沒有人就沒有文學藝術,也沒有審美活動,人也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人與藝術的關系,對人對藝術都無比重要,所以,研究藝術、探討審美,決不能忽略人,不能忽略人的相關思想與各種社會、文化藝術活動。
文學界早就高舉“文學就是人學”的大旗。錢谷融先生說這句話含義極為深廣,可做理解一切文學問題的總鑰匙!誰要想深入文藝的堂奧,不管創(chuàng)作好,理論研究也好,非得掌握這把鑰匙不可。離開了這把鑰匙,理論家無法解釋文藝上的一系列現(xiàn)象;創(chuàng)作家忘記了這把鑰匙,就寫不出激動人心的真正的藝術作品。他還說,文學作為人類所獨有的一種語言藝術,如果撇開了“人”,何以安身立命?⑩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5 月5 日。
因此,“文學是人學”早已深入人心,早已成為一種基本的文化常識。?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據(jù)說是周作人在其著名文章《人的文學》中第一個提出“文學是人學”。筆者認為,藝術學、音樂舞蹈學、戲劇學等,與文學一樣,一刻離不開人這一主體,故毫無例外也都是“人學”,是人文之學。沒有人,這些藝術和相關研究學科,也同樣無法安身立命,故不能不關注人,既關注人的集體,也關注個人(個性及藝術風格各不相同的人)。
郭先生向音樂學界發(fā)出“請把目光投向人”的呼吁,是常識,也有“事在人為”的辯證前例。但今天回頭看,筆者認為先生的呼吁不僅有重要的具體針對性,還有更深遠的思想和文化內(nèi)涵,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歷史文化意義。因為,“把目光投向人”,是郭先生向音樂學界發(fā)出校正現(xiàn)有航向偏差、回歸人文學科廣闊正道的呼吁;是建構包含科學音樂學在內(nèi)的,更深、更廣也更全面的人文學科音樂研究(或音樂學科研究)宏偉大廈的動員令和進軍號!
茲事體大,也相當復雜,當專文深入論證,這里約略勾畫幾個要點。
三、科學的音樂學與人文學科的音樂之學
首先,要看到并承認音樂學、藝術學研究具有科學性,看到科學在這些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音樂學藝術學的基本立足點,是科學或科學的研究。可惜這一點不僅一般人不太了解,就連音樂學(及藝術學)領域眾多師生,即所謂“局內(nèi)人”,也不都十分清楚,予以高度重視。比如,歸國應聘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的著名畫家陳丹青,幾年后,卻宣布辭去所有職務,并公開承認自己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美術學”。
為此,幾年前筆者曾專門撰文探討音樂學的學科性質,?秦序《音樂學學科性質再認識——讀何兆武〈歷史與歷史學〉劄記》,《中國音樂學》2015 年第2 期。并著力推介中央音樂學院俞人豪先生編著的《音樂學概論》(以下簡稱《概論》),指出它是我國較早的且非常重要的音樂學基礎教材。該書第一章第一節(jié)開宗明義指出,音樂學是“有關音樂的科學”,“音樂學”這個詞在歐洲最早見于米茨勒1738 年在德國成立的團體名稱“音樂學協(xié)會”(Socictact der musikalischen Wissenschaft),這個德文詞的意思為“音樂的科學”。俞先生還說,確立這門學科的人應是德國音樂學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其1863 年編撰的《音樂學年鑒》不僅使用了“音樂學”這一名稱,還明確指出,“音樂的研究,特別是歷史的研究,應該提高到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中長期采用的那種嚴肅而精確的標準上來”;克里桑德還主張音樂學應與當時呈上升趨勢的“實證科學”相聯(lián)系,“應成為受到尊重的、完全意義上的科學”,并且,“不應該逃避最嚴格的要求”。?俞人豪《音樂學概論》,人民音樂出版社1997 年版,第4 頁。
要音樂學研究聯(lián)系和學習的“實證科學”是什么呢?法國孔德(Auguste Comte,1789——1857)首先提出“實證主義”,認為自然科學的各個部分都已進入實證狀態(tài),唯獨人文科學仍游離于外,所以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實證科學體系,用自然科學來說明人類社會。英國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則是實證史學最重要的代表,將歷史看作自然科學,借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尋找歷史規(guī)律。還說這個過程中,自然科學的思想與方法是歷史學成為科學的關鍵,強調“離開了自然科學,歷史學也不成其為歷史學了”?張廣智《西方史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孔德觀點見第221、222 頁,巴克爾觀點見第224 頁。。因此,一般所說的“音樂學”,應屬近代科學體系中的藝術學分科之一。《概論》進一步說它應屬“人文科學”或“精神學科”?“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系德國哲學家狄爾泰提出,其范圍包括我們通常講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參見張汝倫《現(xiàn)代西方哲學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100 頁。范疇,還指出我國音樂學專業(yè)多設置于音樂、藝術院校,而在西方“音樂學系則普遍設置在綜合大學的人文科學學院之內(nèi)”?同注?,第11 頁。。
但在拙文后面部分,對音樂學是科學的這一基本屬性定位,已經(jīng)有所修正和發(fā)展。強調音樂學與藝術學、歷史學等學科一樣,具有突出的人文特性及人文評判價值,顯然不同于科學。所以,音樂學、藝術學等不全是科學,也不全是“人文科學”,應是人文學科。這是受何兆武先生《歷史與歷史學》等論著啟發(fā),而得到的一點新認知。
何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實證主義史學過分強調科學至上的觀點,是片面的,它忽略了人文學科和科學(自然科學)的巨大差別。”何先生還指出,多年來存在“一切都要以科學性為唯一準則,一切論斷都須從科學出發(fā),以科學為唯一的歸宿”,是一種“唯科學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歷史學理所當然應該是科學,完全地而又徹底,有如柏里(劍橋大學教授)聲稱“歷史是科學,不多也不少”一樣。但何先生明確指出,歷史不同于一般科學,因為“歷史學并不是一門實證的科學,你無法進行可控的實驗來證實它或者證偽它”?何兆武《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載《歷史與歷史學》,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25 頁。。
何先生還以歷史學為例,多方面深入論證科學與人文學科兩者的差異和不同。比如,歷史學研究的是人文史而非自然史,人文史之所以成其為人文史,則端靠其中自始至終貫徹著人文思想。比如,“沒有人的思想,也就沒有人文史。都是人的思想賦給了歷史以活的生命。假如沒有理想、熱望、感情、德行、思索乃至貪婪、野心、狂妄、愚昧和惡意等,也就無謂人的歷史了。這一點是人文研究有別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地方。”又如,“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研究的主體是人,人是有思想的生命;而其所研究的客體則是沒有思想的乃至沒有生命的自然界。而在人文研究中,研究的主體是人,研究的客體也是人,是人在研究他自己。所以它那研究的路數(shù)和方法就自然有別于自然科學的。”再如,“自然科學的對象是沒有思想、感情和意志的,所以研究者對它的態(tài)度是價值中立的、超然物外的……歷史歸根到底乃是人的有意識的、有意志的(而非單純自然的)產(chǎn)物。”
所以,歷史的研究既有其科學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學的一面。或者說,它具有科學與非科學、自由與必然的兩重性。?何兆武《歷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2 頁。所以,歷史學既需要有科學性,又需要有科學性之外的某些東西。沒有科學性,就沒有學術紀律可言,歷史也就不能成為一門科學或學科;但僅僅有科學性,還不能使它就成其為歷史學。?同注?,第3 頁。
何先生指出歷史學既是科學,同時又不是科學。史學(作為一種人文學科),是科學的,所以它不是反科學的;又因為它是非科學的,所以它就不是或不完全是科學的,這兩方面的合成,才成其為歷史學。何先生還說,歷史學不僅是一種科學,同時還是一種人文學科,這一點好像連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都還不曾意識到。所以,“凡是認為歷史學是科學或應該成為科學的人,于此都可以說是未達一間,正如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所表現(xiàn)的那樣。”?同注?,第3 頁。
受此啟發(fā),可以認為音樂學、藝術學與歷史學等學科一樣:一方面是科學(近代意義的科學),必須發(fā)揚科學精神、嚴格遵循科學研究的規(guī)律和規(guī)范,相關研究成果要符合科學標準;但另一方面,它們又不全是科學(不是反科學),而是有別于科學的、獨具人文特質的“人文學科”。所以,常用的“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等概念,僅僅強調其科學的屬性,是不能充分涵蓋和指代音樂學、藝術學及歷史學等人文學科的基本特性的。
何先生還就歷史學的學科定位問題,發(fā)出了非常重要的、富于建設性的呼吁。他說:
歷史學的世界是外在世界和內(nèi)在世界的統(tǒng)一體。我們對外在世界(客觀存在)的認識需要科學,我們對內(nèi)在世界(主觀存在)的認識還需要有科學之外的某些東西。這里的“某些東西”,即我們對認識歷史所需要的那種心靈體驗的敏感性,那實質上有似于藝術的敏感性。我們對外界的認識要憑觀察,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還要憑人生的體驗,否則就做不到真正地理解。這一點或許可以說是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為避免與科學一詞相混淆,我們姑稱之為學科而不稱為科學)的根本分野之一。[21]同注?,第4——5 頁。
何先生提出,為了避免人文“與科學一詞相混淆”,避免將歷史學等學科統(tǒng)稱“人文科學”,應將歷史學(科學)改稱“歷史學科”,以示區(qū)別,即不再稱“科學”而改用“學科”這一新稱謂。這一稱謂的改正,意義深遠。雖然歷史學,人文各學科各方面都離不開科學的研究,但也容易發(fā)生同樣“與科學一詞相混淆”的問題,而遮蔽了、淡化了自己的最重要的人文特性。因此,人文學科各學科各方面研究,理應清楚、自覺地了解學科人文本質及歸屬,認真建構人文邏輯基礎,認真構建自己人文學科的相關“元理論”,才能真正地將目光投向人,凸顯自己學科人文特性和人文價值的依歸,全面實現(xiàn)以人為本的學術思想目標。
四、20 世紀西方思想文化潮流突出人文學科的價值與意義
明確人文學科、突出人文價值,也是20 世紀以來世界文化、思想發(fā)展的新潮流。工業(yè)文明占統(tǒng)治地位之后,隨著科學技術高速進步,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浪潮洶涌澎湃,極大地改變世界的舊貌,極大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但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也猶如雙刃劍:既造福世界,也能造成危害。人類的實際歷史進程表明,科技騰飛的20 世紀并沒有實現(xiàn)人性的真正的、自由全面的發(fā)展,反而普遍異化、動亂不已。文藝復興以來的啟蒙理性,本是為確立人對自然的無限的統(tǒng)治權,使自然成為屬人的存在;但人征服自然的結果,也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破壞,導致自然對人類的報復。而在被技術理性完全統(tǒng)治的世界中,不但人與自然相異化,人與人也相異化;人還普遍物化,在普遍異化的世界中相互沖突,甚至相互廝殺。[22]衣俊卿主編《文化哲學十五講》“第九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184 頁。
正如韋伯等學者所批評,在科學主義、理性至上思潮,尤其“技術理性”[23]韋伯提出“技術理性”概念,指在近現(xiàn)代科學技術呈加速度發(fā)展背景下的一種新理性主義思潮,其立根于科學技術的無限潛力和無限的解決問題的能力之上,其核心是科學技術萬能論。西方很多學者認為西方現(xiàn)代理性文化危機,其根源離不開技術理性的異化。參見注[22],第180 頁。統(tǒng)治的現(xiàn)代,科學、理性和技術的發(fā)展,并沒有像啟蒙先哲們預計的那樣,不斷增強人的本質力量,實現(xiàn)人的普遍自由。技術本身反而成為自律的、自我發(fā)展的、總體性的統(tǒng)治力量,成為扼殺人自由和個性的異化力量,成為一種比傳統(tǒng)政治統(tǒng)治力量更強大的力量。同時出現(xiàn)了英國學者C.P.諾斯所說的“兩種文化”,即“文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與“科學文化(scientific culture)”[24]〔英〕C. P.斯諾著,紀樹立譯《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4 年版,第3——4 頁。,彼此漸行漸遠,甚至發(fā)生日益尖銳的對立。所以,哲學家馬爾庫塞[25]〔美〕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德裔美籍哲學家、美學家和社會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譽為“新左派哲學家”。特別提醒人們,以科學技術飛速發(fā)展為背景的相對富裕的消費世界中,技術理性形成新的統(tǒng)治體制,讓人們陷入一種新的異化的和物化的生存方式。人作為一種自由的、創(chuàng)造性的實踐存在,理應具有的否定性、超越性和批判性,卻被技術理性所消解。人成為失去了超越維度和批判維度的、與現(xiàn)存認同的“單向度的人”或“單面人”,而“單向度的思維”或“單面思維”,則成了缺少否定維度的主導性的社會意識。[26]〔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fā)達工業(yè)社會意識形態(tài)研究》,重慶出版社1988 年版,第21——31 頁;參見注[22],第184——186 頁。
因此,鼓吹人文精神、人道精神和“人學”,反思科學主義、理性尤其是技術理性(也叫工具理性)的弊病,成為20 世紀以來西方思想文化潮流的重大核心問題。
旅美學者林毓生20 世紀80 年代回國,即強烈感到國內(nèi)人文研究包括學科名稱“呈現(xiàn)非常混亂的現(xiàn)象”。他在《中國人文的重建》一文中批評很多人不清楚什么是“人文”,甚至把“人文學科”(humanities)叫作“人文科學”,“好像不加‘科學’兩字就不覺得這種學問值得研究似的。”他強烈表示:“人文學科”絕對不能叫作“人文科學”,因為事實上“人文學科”與“科學”,有很大的差別。我們是“人”而不是“機器”,因為是“人”,所以有特別對自己的要求;因為我是人,所以要肯定人的價值,找尋人的意義。[27]林毓生《中國人文的重建》,載《中國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8 年版,第3——4 頁。該文原發(fā)表于臺灣《聯(lián)合月刊》第14 期,1982 年9 月。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國內(nèi)文學、歷史學,以及音樂研究、藝術研究的學科性質,也逐漸發(fā)生從“社會科學”到“人文社會科學”的變化,繼又從“人文社會科學”進一步分化出“人文科學”及“精神科學”等概念。更加突出人文特質的“人文學科”概念,正逐漸取代“人文科學”“精神科學”等稱謂。比如,何兆武先生在早幾年論著中,還常用“人文科學”概念,或與“人文學科”相混用,后來不僅明確改用“人文學科”一名,甚至提出上述以“歷史學科”取代原有“歷史學”的重大主張。
其實,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 年中文版《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其中就只有“人文學科”(humanities)條目,而沒有“人文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詞條。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國外很早就加強和提升了對人文學科文化價值與學術意義的重視。[28]此《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是根據(jù)美國1975 年版《不列顛百科全書》翻譯編寫的。
更早,20 世紀50 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唐君毅就連連著書,大聲呼吁中西人文要返本開新,重建人文精神。他指出:“人是透過人文去看世界,從科學哲學去看世界的條理與秩序,從文學藝術去看世界之美,從道德去看世界之善,從宗教去看世界之無限的神圣莊嚴。但是,世界的迅猛進步,世界人文的巨大進化,反而出現(xiàn)巨大的混亂和矛盾。”這種矛盾,先是因西方近代人文中,科學一支特別發(fā)達,人們只依從已有的科學結論去看宇宙人生,以及科學技術運用得“不得其當”的影響。其次,是人們忘記了自己在人文世界;也就是說,科學之發(fā)達,竟致使人忘記了他們本來是在人文的世界,“而自以為處在一陌生世界、物質世界,而迷失了自己的道路”,不僅如此,還相反地“從事于人文之毀滅”[29]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1 頁。。
唐先生反復指出,科學只是人的學問中之一種,“它亦不能在人的學問世界中高居一至高的指導一切之地位,并由之以說明人的學問之全與其次序應當是什么,及人的學問與今日之人的存在問題之關系。”[30]唐君毅《中國人文與當今世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60 頁。他還說,自己理想的世界是人文的世界,在這個理想之世界,其實科學亦自必需發(fā)達。我們反對的,只是以科學凌駕于一切人文之上。所以“要知道人文涵蓋科學,科學不能凌駕人文。”[31]同注[29],第22 頁。他希望提高科學以外的人文領域地位,并將人的生存置于科學態(tài)度、科學真理之上。因為科學之外的其他人文領域,“自具其真理、理想與價值。而人生存在自己,亦有超于科學之真理以上之理想與價值。”他還說,“我們固當講人文世界的科學,但不必講科學的人文主義”[32]同注[30],第63 頁。,不是科學涵蓋人文學科,而是人文學科應該涵蓋科學,也就是說,不是科學文化高于、大于人文文化,而是因為人文學科本來就高于、大于科學,人文文化也應高于、大于科學文化(當然科學也需發(fā)達,也需重視)。[33]比唐君毅更早,與梁啟超1918 年一起考察戰(zhàn)后歐洲、后赴德國專攻哲學的張君勱,1923 年發(fā)起“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就指出西方文化,或稱科學、物質文明,并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解決世界乃至中國的問題。參見張君勱《明日之中國文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3 頁。
人文學科努力擺脫“科學主義”、技術理性至上等束縛,走出“人文科學”“精神科學”等相對狹隘的定位,擺脫將人文藝術研究等同于純科學研究的偏頗失誤,已是20 世紀以來世界文化思想新的發(fā)展潮流和基本趨勢。因此,我們應該反思,如何盡快實現(xiàn)我國現(xiàn)代人文學科發(fā)展的“入流”和“預流”(陳寅恪語),充分發(fā)揚人文學科獨特品格和價值魅力,向絢麗燦爛的“人文學科”新天地邁進。開拓更為深廣宏大的“人學”“人文研究”新疆域,應是我國學術思想和文化發(fā)展(包括藝術研究、音樂研究)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結 語
何兆武先生強調,一切人文價值——自由、平等、博愛、生命權、財產(chǎn)權與追求幸福之權,以及英明遠見、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乃至一切精神境界與道德情操,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從科學里面推導出來的結論。它們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觀給定的事實和規(guī)律。他還說,展望現(xiàn)代思想文化前景,首先將是一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是一個多元化或多極化的世界,統(tǒng)一性要求并且包括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個性。其次,除了科學的進步,還必須努力保持人文學術的同步發(fā)展,沒有人文學術的健全、發(fā)展,科學(知識就是力量)一旦失控,不但不能造福人類,反而很可能危害人類。[34]何兆武《歷史兩重性片論》,載《歷史與歷史學》,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33 頁。唐君毅先生的理想的人文世界,與此相類似,也是強調人文和科學的共同攜手共同進步的。
將郭乃安先生當年發(fā)出的呼吁,放到當今和未來音樂、藝術乃至世界人文學科發(fā)展的歷史大潮流、大背景中重新審視,其深遠內(nèi)涵和意義,可以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受郭乃安、何兆武、唐君毅等先生啟發(fā),我們需要進一步認識藝術學、音樂學的人文學科本質屬性,明確其“人學”品格。為厘清易與“科學”一詞相混淆的“人文科學”“精神科學”等稱謂,我們建議不妨改用“藝術學科”“音樂學科”(或略嫌煩瑣啰唆的“人文學科藝術學”“人文學科音樂學”)這類新稱謂,取代“藝術學”“音樂學”之類名稱。這樣的命名,可以同所謂科學的“藝術學”“音樂學”等相對狹隘的概念,能夠涇渭分明,其人文學科的概念和定位,也更準確、更合理,其實也更科學。
為此,可以認為郭先生的呼吁,是校正現(xiàn)有音樂學、藝術學的航向偏差,回歸人文學科研究廣闊正道的動員令,也是建構包含科學的音樂學在內(nèi)的人文學科音樂研究的進軍號!我們要與時俱進,主動參與現(xiàn)代人文學科發(fā)展的澎湃新潮流,認真反思、明確音樂學的人文學科的根本屬性,果斷走出科學主義、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至上的束縛和困擾,堅持將目光投向人,堅持以人為本,高度肯定和凸顯中國的人文音樂研究的民族個性與獨特價值。
緣此,建構包括科學音樂學在內(nèi)而具有真正人文特色的“中國的藝術學科”“中國的音樂學科”(或中國“人文學科藝術學”“人文學科音樂學”)的宏偉大廈,此其奠基之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