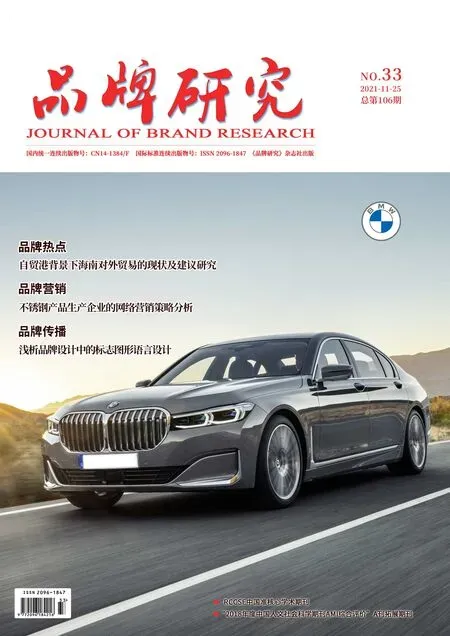淺析二次創作短視頻中的“合理使用”
文/左娜(濟南廣播電視臺)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高速發展,媒介形態不斷更新迭代。短視頻因其制作門檻低、社交屬性強、用戶參與度高等優勢迅速崛起,成為新型表達媒介。當然,在持續火爆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發展亂象。由于原創作品費時費力,某些短視頻制作者在利益驅動下,奉行“拿來主義”,未經授權即搬運、切條、剪輯他人原創視頻,進行所謂“二次創作”,從而達到迅速吸粉、流量變現、增加用戶黏性的目的。該種行為不僅侵害了原創者的權益,而且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破壞短視頻行業的健康生態,因此引發了諸多著作權侵權糾紛。
雖然眾多被告在抗辯時普遍引用《著作權法》第24條有關“合理使用”的規定,認為自己的行為屬于介紹、評論作品,不構成侵權。但從判決結果來看,大多數案件以被告敗訴告終。究竟何為“合理使用”?二次創作短視頻是否構成“合理使用”?其亂象應當如何治理?筆者將在下文中詳細闡述。
一、二次創作短視頻的定義及分類
根據2021年5月12426版權監測中心發布的《2021年中國短視頻版權保護白皮書》的定義,“二次創作短視頻是利用已有作品的視頻素材進行創作,常見為影視綜、動漫、體育及游戲等作品素材制作的短視頻,簡稱二創短視頻。主要分為六類,即預告片類、影評類、盤點類、片段類(CUT)、解說類、混剪類”。筆者認為,在此基礎上,根據使用目的、對原作品的引用比例、二次創作程度(即轉換性高低)等標準可以劃分為切條搬運類、速看類、評論說明類、混剪重構類及其他類。關于二次創作短視頻的侵權可能性,需要基于上述分類并結合具體場景進行類型化認定。
二、合理使用的法律規定及認定標準
(一)合理使用的法律規定
2021年6月1日起實施的新《著作權法》第24條對“合理使用”做了新的規定:是指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使用作品時,“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稱、作品名稱,并且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其中,二次創作短視頻涉及該條第二款規定,“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
(二)“三步檢驗法”和“四要素”標準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中有關“合理使用”的規定,著重參考了伯爾尼公約及TRIPS協定中的“三步檢驗法”。“三步檢驗法”是指認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合理使用”需要進行以下三個步驟的檢驗:(1)“合理使用”只能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適用;(2)不能與原作品的正常使用相沖突;(3)不能損害原作品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
我國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法院也頒布了相關司法政策,在上述檢驗方法基礎上制定了“四要素”標準。所謂“四要素”標準,是指判斷被訴侵權行為是否屬于適當引用的合理使用行為,需要考慮以下四個因素:(1)被引用作品的性質,即是否是已經發表的作品;(2)引用行為的目的,即引用作品是否為了介紹、評論或說明問題;(3)被引用內容的數量和程度,即被引用內容在被引用作品中以及被訴侵權作品中所占比例是否適當;(4)引用行為對被引用作品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即引用行為是否影響被引用作品的正常使用或者損害其權利人的合法利益,造成實質性替代。以上四個因素具有很強的參考價值和實務操作性,筆者將以此為依據,對幾類典型的二次創作短視頻的侵權可能性展開分析。
三、二次創作短視頻侵權可能性分析
(一)切條搬運類短視頻
切條搬運類短視頻是指未經著作權人授權,直接將綜藝節目、影視電影作品甚至是體育賽事等視聽作品進行剪輯切斷、配以標題并傳播的短視頻,其剪輯出的通常為作品中的精彩片段。這類短視頻無論是從引用目的和篇幅,還是從對被引用作品潛在市場的影響方面分析,都無法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合理使用”,屬于典型的侵犯原創權利人著作權的行為,主要涉及信息網絡傳播權、復制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等幾項權利,應當予以嚴厲打擊、制止。
(二)速看類短視頻
速看類短視頻是指對影視綜等視聽作品進行剪輯、提煉,截取主要片段并配以解說,概括整部作品的主線發展,從而讓觀眾快速了解作品的短視頻。典型代表是“谷阿莫X分鐘看完一部電影”等影視作品解說短視頻。與切條搬運類短視頻相比,其旁白解說、剪輯拼接手法等體現了創作者對于影視作品獨特的理解和審美,具有一定的獨創性。但按照“四要素”標準分析,該類短視頻依然存在較高的侵權風險。首先,從引用目的角度分析,速看類短視頻通常截取正片視頻的主線情節,該做法明顯超出了“介紹、評論、說明”的合理需要和必要限度。其次,從引用比例角度分析,雖然被引用內容累計只有幾分鐘,在被引用作品中所占比例很低,但適當引用的比例標準不應當采用簡單機械的量化標準,而應當結合引用目的、必要性等綜合判斷。如果被引用部分成為新作品的主體甚至是全部內容,原作品的藝術價值和功能沒有產生較高的轉換性,則不應當認定為引用適當。在“圖解電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案的判決中,北京互聯網法院就持上述觀點。[1]最后,該類短視頻使得觀眾無須再觀看被引用作品即可了解故事核心內容,構成實質性替代,嚴重影響被引用作品的發行、傳播和正常使用,損害權利人的合法利益。
(三)評論說明類短視頻
評論說明類短視頻是指對他人作品中的劇情、人物等進行分析、評論,或者圍繞特定主題、引用多部他人作品進行說明的短視頻。如果該類短視頻是以“介紹、評論、說明”為目的引用他人已發表作品,引用時指明了作品名稱及作者的姓名或名稱,被引用內容在新作品中占比較小,且具有新的價值、功能,引用行為不影響被引用作品的正常使用,新作品與被引用作品之間無競爭、替代關系,符合“四要素”標準,則可以考慮認定為“合理使用”。
(四)混剪重構類短視頻
混剪重構類短視頻是指以一部或多部作品為素材,通過剪輯、配音、重構劇情等手法,表達與原作品不同的新內容、新思想的短視頻。該類短視頻能否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合理使用”,目前存在較大爭議。支持者認為,該類短視頻往往能夠滿足不影響作品的正常使用、且不會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的前提要件,以及蘊含在“適當引用”條款中的價值追求。[2]因為很多觀眾是在看了混剪短視頻后,才去觀看相應影視作品的,這類短視頻對于作品的傳播具有積極作用,全面禁止反而會影響著作權人的收益。反對者則認為,這類短視頻的作者在未經原作品著作權人授權的情況下,篡改、歪曲原作主旨,對其作品進行編輯、修改并通過網絡傳播,侵犯了著作權人依法享有的復制權、改編權、保護作品完整權、信息網絡傳播權;如果混剪的短視頻以惡搞、反諷等手段歪曲原作中的演員形象,還可能涉嫌侵犯演員的表演者權。
筆者認為,雖然混剪重構類短視頻存在侵權風險,但從促進文化繁榮、關注公眾表達自由和表達需求的角度分析,其具有存在的意義,不能一刀切式地全面禁止,而應探索合法的便利許可機制來平衡著作權保護與鼓勵創作的關系,達到影視作品著作權人、短視頻平臺、二創作者之間的利益共贏。
四、二次創作短視頻亂象的治理建議
當前,短視頻領域亂象叢生,通過“三步檢驗法”和“四要素”標準分析,很多二次創作短視頻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規定。
雖然國家鼓勵創作、倡導文化繁榮,但也不應以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為代價。因此,筆者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對二次創作短視頻領域的亂象予以治理。
(一)樹立版權意識,提升原創能力
二創作者應當牢固樹立版權意識和規則意識,尊重他人知識產權,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開展創作,規避侵權風險。同時,強化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學習,不斷提升內容原創能力,主動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
(二)壓實主體責任,強化監管職責
除了二創作者本身版權意識匱乏外,二次創作短視頻亂象與短視頻平臺之間惡意競爭、拿“避風港規則”作擋箭牌、信息審查的主體責任未壓實有很大關系。
短視頻平臺應當切實履行法定義務,充分運用技術手段加強對侵權內容的過濾、刪除,提升治理效能。同時,相關部門要完善法律法規,進一步壓實短視頻平臺疏于履行審查、刪除義務的法律責任,強化監管職責。
(三)建立新型便利許可制度和利益分配補償機制
一刀切式禁止、限制二次創作并不利于作品的傳播和利益最大化。原創作品的著作權人、短視頻平臺和二創作者應當積極探索互利共贏的合作方式,使一些不構成“合理使用”、應當取得著作權人授權的二次創作短視頻獲得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1)建立低價的視頻素材交易平臺。由平臺方與著作權人開展影視作品的授權使用合作,再通過低價的打包授權、包月授權等方式許可二創作者使用視頻素材,使其能夠在合理的成本下獲得合法授權,從而解決其單獨獲得許可成本高、效率低的難題。
(2)引入CC許可協議等新型許可模式。新模式下的作品并未進入公有領域,只要公眾遵守相應的許可協議,便不必單獨經過著作權人的許可,享有按照協議規定的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權利。[3]
(3)健全利益分配補償機制。通過技術手段精準篩選、測算二次創作短視頻中引用他人作品的數量,針對不同的影視作品制定相應的利益分配及補償機制,實現各方利益最大化。
五、結語
當前,我們已經進入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創作者。短視頻的崛起為人們的表達需求提供創作空間的同時,也伴隨著諸多法律問題。對于二次創作短視頻中“合理使用”的認定,應當結合實際情況分類確認,避免一刀切式簡單處理。
同時,也應拓寬思路,積極探索新型合作模式,兼顧版權保護與短視頻創作產業發展,實現社會主義文化繁榮。
注釋
1北京互聯網法院(2019)京0491民初663號民事判決書。
2張吉豫.“二次創作”短視頻中 的 合 理 使 用[EB/OL].https://weibo.com/ttarticle/p/634332684746999.2021-05-07/2021-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