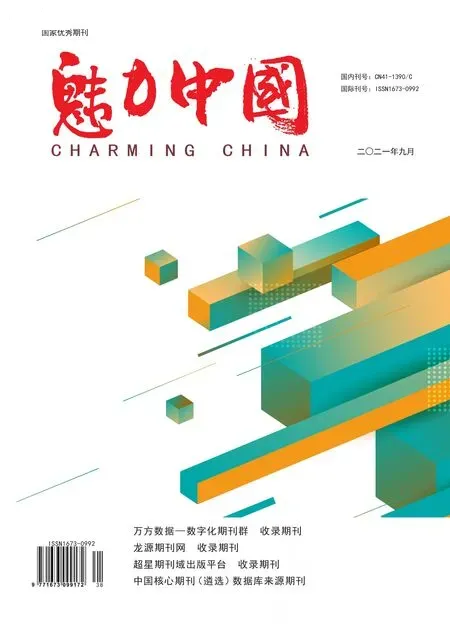淺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間造物精神
任軍君
(湖北經濟學院藝術設計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中國民間造物歷史是中華民族披荊斬棘、開拓創新的發展史,其源遠流長、生生不息,是一支鮮活而厚重的中華文脈。中國民間造物精神是中華民族創新精神的基石和源頭活水,在新的歷史時期,國家提出“鄉村振興”“設計創新”“綠色和諧”等發展戰略,實施《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系列政策,旨在挖掘、保護和傳承中國民間優秀的文化資源,促進傳統工藝的創新性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凸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必須要筑牢民間文化創新的基石。
一、中國民間造物概述
中國傳統造物按社會階層可分為官營工造、士族文人匠作和民間造物三大類。官營工造主要是為皇室貴胄、官宦等統治階級所營造的器物,他們利用其特殊的經濟政治統治地位,在器物等制作中往往不計成本,正如王琥先生在《設計史鑒》中所言“舉國之力而御于一人,是官作的本質”,官作造物體現了當時社會的最高水平,是集材料、技術、藝術之大成者。官作器物除了使用功能之外,更多的是用來彰顯社會等級的傳統“禮制”,如始于西周的“藏禮于器”的青銅禮器,就有嚴格的制作標準和使用規范,通過器物來強化、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威,《公羊傳·桓公二年》中記載“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可見禮器是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不同層級不可隨意僭越。
士族文人匠作造物則往往會疏離沉冗繁雜、等級森嚴的官營工造方式,在“不逾禮”的前提下追求本我的內心情感和審美情趣。孔子說“君子不器”,體現出士族文人對器的態度,他們雖極少參與具體的造物實踐活動,但善于通過器物來抒發個人情感,諸如以“梅、蘭、竹、菊”等植物造型來彰顯“君子氣節”,以“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來體現出“以玉比德”的觀念等,他們“寄于器而高于器”處世哲學,追求“器以載道”的思想境界。歷史上孔子、孟子、墨子、莊子、老子、荀子等先賢們,對中國傳統造物活動進行了深刻地思辨,形成了中華民族獨特的“天人合一”“道器合一”“致用利人”“重己役物”“道法自然”等造物哲學思想。
民間造物則是最廣大的勞動人民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立足于本土民風民俗文化和生產生活實際,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所創造出的物質器具,其涵蓋了“衣、食、住、行、用、娛、祭”等諸多方面,又因地域性、民族性的不同而呈現出風格迥異的特征。民間造物活動遠離了國家公器,沒有等級森嚴的宗法壁壘束縛,也不像士族文人對造物所追求的超凡脫俗之意境,其在注重實用功能的前提下,具備天然、健康、自由和生活的樸實特性。
中國有關造物文化記載的歷史典籍眾多,諸如《考工記》《天工開物》《長物志》《木經》《髹飾錄》《營造法式》《園冶》等,大多是立足于官營工造、士族匠作的領域,歸納總結了中華民族的造物文化,它們是中華民族造物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中華文明之瑰寶。從造物本質上來看,官營工造和士族文人匠作的造物主體仍然是普通勞動者中杰出的工匠代表,因此可以說廟堂之器的制作、士族文人的造物思想均來源于民間的造物實踐,廣博而豐富的民間造物文化、創造精神孕育造就了中華民族璀璨的造物文明。然而對中國傳統的民間造物文化、藝術卻鮮有典籍文獻的知識傳承,大多依靠口傳心授的經驗傳承,處于自生自長、自存自滅的狀態。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在社會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傳承民間造物藝術和文化,充分發揮民間造物思想的創造力,是對我們民族文化自覺自信的考驗。
二、中國民間造物的精神特征
1.“無中生有”的創新精神
民間造物活動是對自然環境的認識、開發和利用。早在公元前7000年前的上古舊石器時代,華夏族人“有巢氏”就教人構木為巢,以避野獸侵害,正如《莊子》所載:“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有巢氏為了適應惡劣的生存環境,通過觀察、模仿自然界中鳥類生存方式,帶領族人創造性地構建木式巢穴居住,開啟了偉大的巢居文明,也為后世輝煌的中國傳統木結構建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陶瓷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之一,早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公元前5000 年-6000 年),我國先民就創造出陶器,這是人類最早利用化學變化改變物質天然性質的開端,標志著人類社會由舊石器時代發展到新石器時代的標志,極大改善了人類生活條件,也造新了中國舉世聞名的陶瓷文化。這些劃時代的人類創舉,得利于我國先民善于認識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在造物過程中體現出“從無到有”的創新精神。
2.“敬天惜物”的節用觀念
墨學是最廣大勞動人民的造物智慧的杰出代表,他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志向,在《墨子·節用》中明確提出他的“節用之法”,涵蓋了日常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如對衣物倡導“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輕且凊,則止”;對宮室建造認為“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對車輛制造提出“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圣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于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墨子站在底層勞動人民的角度,提出“諸加費不中民利者,圣王弗為”,勸誡統治者要愛惜民力,這種“敬天惜物”的節用造物思想造就了中華民族勤勞簡樸、節儉自律的優良傳統。
3.“格物致知”的科學思想
宋代理學家程頤認為“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認為認知事物是從逐漸積習到深入領會貫通的過程,總結出“致知在格物”的科學認識觀。
中國傳統民間造物文明是古人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時代,對科學技術不懈追求的結果。例如:遠古時期人們利用榫卯結構制作出堅固耐用的建筑和家具;發明了陶輪成功運用了機械能,極大地提升了陶瓷的生產效率和質量水平;初步掌握了熱傳導學原理,將大部分陶質炊具如甑、鬲、鑊、鼎做成開叉的三足造型,有更大的腹身范圍受熱可使食物更快煮熟;通過杠桿力學原理,創造出了汲水、灌溉農業生產工具桔槔、戽桶,極大地節省了人力;通過杠桿平衡原理,創造出衡器工具桿秤、天平;通過水流、風作為動力來代替人力、畜力,發明出水轉筒車、水磨、水碾、舂米機、風車等;……。中國古人們“格物致知”的科學思想,通過“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勞動智慧,不斷地創造出先進的、科學的生產生活器具,極大地提高了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造就了中華大地上下五千年的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的史,極大提升了中華文明的世界影響力。
4.“致用為本”的功能理念
明末著名科學家宋應星在《天工開物》指出器物應“效用于日用之間”,講究日常生活中“致用”、“實用”的器用之道。
中國民間的造物從一開始就具有“功能主義”的特點,即“有用性領先的合理性原則”,利用“天時、地利、材美、工巧”創造出生產生活中所需要的器物。“天時、地利”是造物的原始本源,在農耕時代勞動人民需要對“天時”、“地氣”進行仔細觀察和深刻了解,逐步掌握“春、夏、秋、冬”不同時段,“東、西、南、北”不同區域,以及地勢地貌等生長環境對自然材料的影響,順應“天時地氣”是“材美”的前提,是器物能否滿足使用的物質條件,最后利用人們長期技術經驗積累的“工巧”為技術手段,創造出優良的器具。如在《考工記》《天工開物》中詳細記載了車輪的制作,車輻通常用槐木,車軸用檀木、棗木、梨木等硬木,這樣選材所制作出來的馬車、獨輪車、水車、風車等,才能保證其優良的使用功能。
5.“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
先秦《考工記》至明末《天工開物》等典籍中都提到“天人合一”的造物理念,強調人與自然的共通、共融、共生,體現了中國傳統造物“和諧共生”的文化精髓,強調人類所有活動都應在順應自然規律基礎上,再發揮人的主觀創造性,達到“生生不息”無窮盡的自然、人、物之間的和諧狀態。
中國傳統民間一切造物材料都來源于自然又回歸自然,通過主觀創造發揮出自然材料最大的利用效率。民間造物的傳統材料如黏土、木材、石材、竹材、藤材等,人們都會貫徹“窮盡其用”的造物思想,譬如竹子可以制作家具(竹凳、竹椅、竹床、竹架、竹席等)、生活用具(傘、扇子、勺子、筷子、牙簽、吹火筒、竹筐、背篼、扁擔、菜籃、籮筐、篩子等)、樂器(笛子、簫)和武器(弓箭、長矛)等;人們就地取材制作出各式各樣簡易實用的生產生活用品,如葫蘆可以用來制作水瓢、裝酒水的容器;老絲瓜瓤可以用來清洗洗炊具、餐具;草可以用來編織草帽、草鞋、草墊、草席、掃帚等;蒲葵、棕櫚可以做蒲扇、棕繩、蓑衣等,羽毛可以做成除塵的撣子;……。以上種種不勝枚舉,這些器物制作都以自然提供的材料為基礎,人們根據生產生活所需加以合理而充分地利用,使自然的生命變得雋永,平凡的事物有了情感。器物達到自然使用壽命后又回歸自然懷抱,這種“周而復始”的可持續發展觀,正是中國民族尊重自然、尊重生命最本質的造物精神。
6.“樂觀祥和”的生活精神
中國傳統民間造物藝術,即是生產的技藝,也是生活的藝術,是以生產和生活為基礎,對物用功能、材料技術、審美情趣、倫理習俗的融會與綜合呈現。民間造物都是大眾化的、平凡而普通的物品,是老百姓每天都要使用的器具,具有鮮活的生活形態,是勞動與美的交融、技術與情感的融合。“勞者自歌”折射出人們在辛勤的勞作中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在日常生活用具的制作中非常注重“紋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表達,通過象征、隱喻、諧音等手法,創作出豐富多彩的裝飾圖案,例如在建筑和家具上雕刻松、鶴、鹿、金魚、蝙蝠、喜鵲、蟠桃、牡丹、葡萄、石榴、金銀花、蓮花、菊花等等,來表達人們對身體康健、延年益壽、子孫興旺、平安祥和、幸福美滿、五谷豐登等樂觀樸素的生活愿望。
三、結語
中國民間造物藝術是民族精神的文化根脈,維系的是民情、親情、國情,反映的是普通百姓的家國情懷,是中華傳統文化藝術的生命臍帶。中國民間造物經過幾千年的延續發展,雖然在近現代受到西方工業革命、現代科學技術、當代設計文化的沖擊和影響,但其所遵循的自然發展規律,尋求自然、人、物的有機統一平衡發展的造物精神,依然對當代中國本土文化的設計創新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