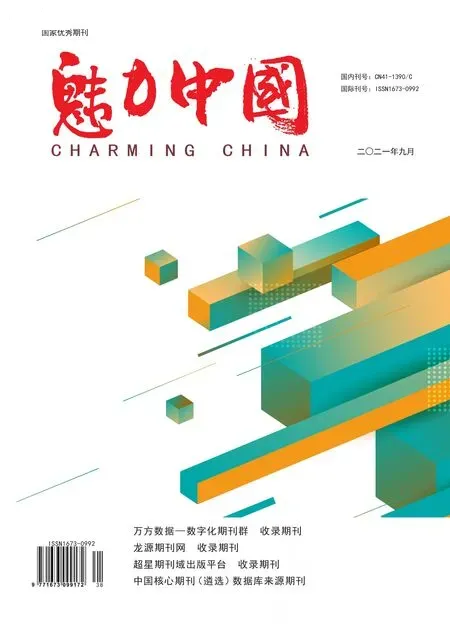后脫貧時代農村電商可持續發展促進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
張曉雯
(四川民族學院,四川 康定 626001)
新中國成立70 年以來,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經歷了集體化、社會化和社區化幾個階段,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大力推進與2020 年“后脫貧時代”的到來,完善農村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尤其是西部農村脫貧攻堅工作成為首要任務之一。農村電商作為農村連接外部的一個重要平臺,成為實現鄉村振興、達到精準扶貧目標的主要手段和有力推手,如在涼山彝區,至2020 年,涼山州所有貧困戶脫貧,所有貧困村退出,11 個貧困縣實現摘帽。涼山奪取了脫貧攻堅全面勝利,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全面消除,農村群眾圓了脫貧奔小康的夢想。十三五”期間,涼山州通過易地扶貧搬遷讓7.44 萬戶35.32 萬人搬離了貧瘠之地。目前四川涼山地區部分農村電商物流體系發展比較遲緩,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經濟的大力發展,影響新農村業態形式接受程度,電商物流配送成為了新興業態的瓶頸和短板,“不便、不通、不快”成為農村電商發展的標簽[1]。李克強總理于2019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發展消費新業態、新模式,促進線上線下消費融合,共同發展,構建健全的農村流通網絡,支持快遞、物流大力發展。”對此,西部農村地區相關部門也要大力響應中央號召,將發展農村電商經濟作為主要任務之一,為加快城鄉融合及農村經濟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一、農村互聯網及電商發展現狀
我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47 次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20 年12 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9.89億,較2020 年3 月增長了8540 萬,互聯網普及率達到70.4%,為我國成為全球唯一后疫情時期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GDP)首度突破百億、完成脫貧攻堅等任務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網絡扶貧行動模式向縱深發展并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帶動了邊遠貧困山區非網民群眾的轉化速度,在網絡覆蓋方面,貧困地區通信“最后一公里”被打通,截至2020 年11 月,貧困地區通光纖比例達到98%。在農村電商方面,電子商務進村工作實現了全面覆蓋832 個貧困縣,并大力支持“互聯網+”新業態模式在貧困地區的大力推進,有效增加了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農村電商的發展為我國農村消費模式實現了便利性、多樣性,改變傳統消費模式的同時促進農村地區商業形態與金融服務模式發生巨大變化[2]。“電商平臺+公司+基地+農戶”的形式有效解決了農產品“難賣”的問題,且貧困地區農產品通過“三品一標”認證體系提升了品質,也有效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
有學者研究表示,農村電商通過整合資源配置、制定合適的產業規劃標準、促進產業融合和集群以及改變產業生命周期等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有效優化。目前,西部農村地區電商發展也有一定起色,以甘孜州為例,甘孜州為了全力脫貧攻堅、推進鄉村振興、加快“1+6+N”鄉村振興規劃體系建設,在甘孜州委十一屆八次全會上提出了產業富民、交通先行、城鄉提升等戰略,全力創建國家生態建設示范區,并結合自身實際發起沖刺,為電商發展、鄉村振興、鞏固提升脫貧攻堅、梯度建設貧困地區奠定良好基礎,同時通過政府自建及引進大型平臺建、培訓本地企業等多種方式,完善了服務、物流及配送體系,實現后脫貧時代農村電商的可持續發展。
二、實現脫貧攻堅后農村電商經濟振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四川省作為全國脫貧攻堅任務最重的省份之一,全省共有45 個深度貧困縣、935 個深度貧困村,共36.4 萬名貧困人口。針對深度貧困地區,要做好產業基礎設施“七大攻堅行動”,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培育、就業增收、培養本地人才等方面多下功夫,結合農村電商經濟振興發展,構建長效脫貧攻堅機制,注重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及“造血機能”。
(一)農村電商新技術有效推進城鄉融合
農村電商新技術充分融合了物聯網、區塊鏈、大數據、云平臺等技術,提高農村農業生產、流通效率優化等目標,充分整合農產品金融、經營、倉儲、物流等多項資源,大大減少了農業產業鏈之間的其他渠道,結合數字經濟技術,改善了西部農村地區的農業生產落后、經營不良等問題,幫助西部農村地區電商構建農村經濟優良發展的系統性框架。同時結合農村網點、農村電商平臺、農產品直播等多樣化形式帶動西部地區農村特色化產業發展,形成農村電商帶,增加貧困地區居民就業率,也有效促進農村地區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此外,通過結合網絡技術對當地農村居民進行素質培訓,提升了西部地區農民的文化素質水平與生活面貌,依托于新網絡、新技術、新媒體促進新興產業鏈發展,大大縮短了農村與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改善農村經濟規模小、局限高的限制,為農村經濟水平的快速、高效發展提供良好保障。
(二)農村電商可持續發展有助于鄉村振興
農村經濟發展來源之一就是各種農產品的銷售,因此需要對銷售渠道進行拓寬。隨著網絡技術及物流運輸技術的逐漸發展,通過各種社交、電商、直播等平臺的出現,農產品銷售平臺也漸漸寬泛,使電子商務的發展前景也變得廣闊起來。據2020 年京東大數據統計,2020 年重慶農產品線上銷售額增長3.8 倍,位居全國第五,線上農產品銷售成為重慶市農村地區的農戶重要收入來源之一,提高了農戶生活水平和消費活力[3]。通過農村電商的可持續長期發展,有效轉變了農村經濟增長形式,通過農村地區電商平臺將城鄉消費者充分鏈接,利用大數據進行調節、指導,促進鄉村振興。
(三)農村電商發展為后脫貧時代鄉村振興提供新動能
鄉村振興為農村地區電商發展提供了新機遇,各地政府加大農村地區政策及資金的扶持力度,社區電商、社交電商已經能夠摸索出適合自身發展的農村電商之路,在農村地區實施信息化發展戰略,有效提高農村地區產業現代化進程。同時結合并運用農村電商平臺整合農村農業資源,實現規模化、集約化訂單生產模式,通過電商平臺拓展農村經濟市場,形成產出、供應、銷售等環節緊密銜接的鏈條,成為后脫貧時代鄉村振興、農村致富的選擇途徑之一,為鄉村振興工作發展提供新動能。
三、實現后脫貧時代農村電商可持續發展促進鄉村振興的路徑
(一)結合電商新技術,培養創業型人才
通過利用先進技術支撐,組織西部農村地區富余勞動力進行電商理論知識培訓和實戰演練,培養具有真知識、真能力的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電商人才,結合政府及相關部門的領導政策,采用企業與政府、企業與農戶合作共贏的模式,積極嘗試“村集體+合作社+電商平臺”的經營模式,也可以采用集團化運行模式,統一種植、收購及銷售,實現三方合作伙伴關系,保持農村電商的可持續發展。如在高原藏區,2019 年來已經實現聚焦“兩不愁、三保障”目標,倒排工期、細化責任、加強統籌,確保年底藏區剩余的16 個貧困縣、305 個貧困村、4.3 萬貧困人口摘帽脫貧,基本消除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此外,培養創業型人才,打造適應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數字化樣板,促進智慧農業與產業鏈的有效銜接,形成農產品“產運銷”一體化發展。
(二)加速農產品升級,打造品牌化建設
品牌效應是所有產品銷售的命脈,同樣農產品品牌建設也是農村電商的主要工作。可以推行“商業+種植地+農民”的模式,實現標準化種植與管理,從生產、銷售、運輸等全流程實現安全管理工作的深化,構建農產品溯源體系,在保證農產品品質的前提下,企業與生產源頭保持積極溝通,一方面能夠實現種植及生產計劃的及時調整,另一方面能夠滿足購買用戶的消費需求,不斷補充、豐富農產品的品類和數量,實現一站式購物,增強電商平臺客戶黏性。此外,通過農產品品牌建設工作的加強,使得農業產品品牌 成為無形資產,增加市場影響力,增大產值,實現農產品利潤最大化,政府及相關部門也要加強平臺監督與質量把關,確保農產品電商平臺銷售 信譽度。
(三)構建電商物流體系,保障服務質量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的閉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地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的進度,道路的通暢不僅能夠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也給農村電商發展提供了良好契機。有關數據統計顯示,2020 年我國淘寶村數量超過5000 個,但在交易規模超過一億元的淘寶村中主要分布在浙江、廣東、江蘇等沿海城市,重慶、陜西、貴州等西部地區則排名靠后,究其原因是西部地區農村寬帶覆蓋率的“數字鴻溝”,此外還有資金緊缺等問題,導致物流成本較高[4]。因此相關部門要予以西部農村地區物流企業金融政策支持,有效彌補當地發展短板,確保農村電商物流體系的構建完整度,提高物流服務質量。
(四)實現供應鏈管理,構建一體化模式
結合供應鏈管理網貨下行的物流一體化模式,將電商企業作為農產品生產者及供應者,實現農戶線上購物較實體購物質量更好、價格更低的目標,確保農村電商與農戶合作共贏。隨著云計算、5G 網絡、人工智能等互聯網新技術的涌現,為發展農村電商構建可控、高效的“智慧物流”奠定良好基礎,實現物流自動化、智能化與可視化,促進農村電商智能化供需匹配,有效、合理安排資源儲備,對農村電商組單及派單智能化、提升運輸時效、確保后脫貧時代電商可持續發展提供契機[5]。
四、結語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時代背景下,實現鄉村振興戰略,提升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目標,而農村電商可持續發展是一項系統化工程,必須構建穩定的營銷環境,并結合政府及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形成電商企業+農戶生產+政府支持的閉環模式,形成各方助力的聚集效應,與此同時,也需要有意愿投身農村電商可持續發展的創新型人才積極參與進來,幫助西部農村地區在后脫貧時代下實現農村電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促進我國經濟水平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