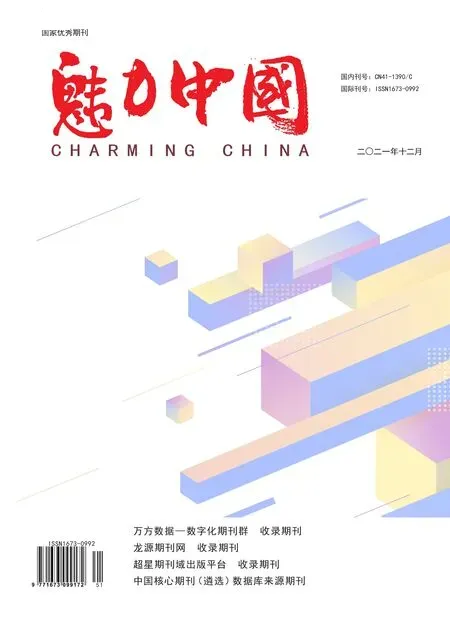農村基層治理的困境和對策研究
王佳穎
(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天津 300387)
農村是國家“三農”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的重要的關鍵一步,農村基層治理的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體現。但是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經濟結構發生巨變,農村治理環境復雜多樣,給農村基層治理帶來不少困難。需要我們找到其原因,為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掃除障礙,助推鄉村振興。
一、目前我國農村基層治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基層治理主體能力薄弱
1.農村基層黨組織
部分基層黨組織領導能力不足,部分黨員干部不能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一方面,有些農村黨員尤其是村集體黨員干部不能發揮黨員應該有的先進性,在農村這個熟人社會,容易被自己的私利沖昏頭腦,不能跳出自己利益的旋渦,沒有作為農村先進分子的大格局,凝聚村民,帶動村民,為集體或村民謀利益為村子求發展的責任意識不夠強烈,領導村里的各方面事物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部分基層黨組織在傳達和落實中央政策時存在不到位的現象,有的在政策實行時只是流于表面,有的也會敷衍了事,面對工作不積極,不主動,責任意識差。
2.村民
部分村民的自律性不高,自治能力不足。相比于城市農村沒有那么多的“規矩”,村民的生產生活不受約束,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有較強的自由性,自我意識較強,不喜歡受到約束和管控,也就不愿意參與到村子的治理當中去,嚴重缺乏集體意識。再者農村是個典型的熟人社會,族際關系和血緣關系強烈,自治能力不足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在選舉時容易受到人情和血緣關系的影響,不能公正地投上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甚至有些候選人為了讓自己成功當選會拉幫結派,動員自己家族中的人為自己的官位“鋪路”。在平時的集體和公共生活中,保護集體利益和集體財務的意識不夠高,個人素質和知識見聞都需加強,政治文化素質較低等等。
3.村干部
當前,有一些村干部不能完全掌握中央對于農村的方針政策,專業性不強,缺乏農村基層治理的有效方法和手段,總憑經驗做事,遇到新問題不懂如何找到新策略,老辦法又解決不了新問題,往往循環往復,問題最終得不到解決,擱置惡化。有些村干部對農村基層治理不重視,不對村子的總體規劃進行全面掌握就盲目進行產業發展,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治理能力不足。
(二)農村基層治理方式存在不足
在農村基層治理中部分基層干部為了完成基層事務或提升自己的“業績”,常常會使用非正式的方式和策略。主要表現為策略主義和形式主義,在某些政策的下達和規則的實行需要村民配合時,村干部會以說好話,講情分,給回報之類的軟方式來懇求群眾配合,這就是歐陽靜所說的策略主義。[1]比如在處理村容村貌時,如果有村民不配合,村干部就會對村民進行言語上的勸說,戴高帽,承諾給予好處等等。其次,在治理方式中還存在著形式主義這樣的弊病,就是利用虛假、名不副實的面子工程來充當工作成果等行為,欺上瞞下,不僅勞神傷財還惹得村民怨聲載道,導致村干部和村民之間出現隔閡。
(三)農村基層治理體系不健全
目前,由于諸多因素,農村基層治理體系還存在著不健全和各個系統之間協調不規范的問題。具體來看,一是中央所要求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體系還主要依靠當地黨組織和基層政府的幫助,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度不高,參與主體單一。參與主體的自治素養和自治能力還需要進一步的提升和規范。二是農村基層治理和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不夠完善。農村治理和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農村經濟發展,農村產業的轉變等一系列的基礎工作之間的協調發展機制不夠健全。三是農村組織體系不能滿足農村基層治理的需求。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處于渙散的現象,村民自治組織有些也徒有虛名,流于形式,不作為的事情時有發生。村里沒有專門的監督組織,村民監督不到位。部分的文化發展組織處于空白狀態,不能為村民提供精神文化需求,引導村民正確的文化價值觀,糾正村內落后文化,腐朽文化。
二、農村基層治理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農村經濟文化發展程度低
大多數農村主要以務農為主,農作物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經濟結構單一,農作物處于市場價值的最低端,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再加上些許天災人禍,農業收益不穩定。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城鎮化的發展,村里年輕人為尋求更高的發展空間,進入城市的洪流,導致農村人口流失嚴重,從事農業生產的大多為婦女,老人。因此,農村經濟發展程度低,農村基層治理也就缺乏一定的物質基礎,失去動力,成為農村基層治理的一大短板。經濟發展不充分也會相應地導致文化發展水平不高。而且農村教育水平相較于城市還是薄弱的,再加上農村年輕人外流,所以老年人成為參與公共生活的主力軍,這就導致農村基層治理的整體文化水平下降,政策接受程度低,農村基層干部完成基層事務的難度加大。農村文化發展不充分,農民精神文化境界不高也會滋生一些諸如重男輕女,封建迷信等腐朽文化侵蝕村民精神世界,腐蝕農村治理的思想基礎。
(二)農村血親化的治理環境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這本書中說:“鄉土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這種社會的人是在熟人里面長大的”。[2]農村是典型的熟人社會,凡事都講究“情”這個字,這是農村較為普遍的形式規則。人際關系都是以血緣、地緣或姻緣關系為紐帶進行交往,同時講究禮治秩序、無訟、無為政治和長老政治。[3]所以,農村社會秩序的維持更多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這個觀念已在村民心中根深蒂固,世世代代遵循著這樣的處事原則。村子里錯綜復雜的關系網絡以及家族之間盤根錯節聯系,農村關系網絡自然由血緣關系構成,在碰到重大事件時遭到“情”字影響很難表達自己的心聲。
(三)農村基層治理機制不健全
農村基層治理機制不健全,村社一體、政經不分等問題是造成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困境的重要根源。農村基層治理結構分為縣、鄉、村三級,但是這三者之間治理權責關系不清,資源分配和布局失衡。[4]一方面,鄉鎮政府過多干預基層民主,有的甚至直接插手基層治理。基層鄉鎮政府和農村基層治理主體之間、村委會和村黨支部委員會權責關系未理順,很多地方鄉鎮政府擁有任免村支部書記、村委會的權力,影響著農村村委會組織成員的選舉。另一方面,村委會有著很強的行政管理職能,在日常管理村集體的過程中,受到上級基層政府的派遣,承擔著過多的行政事務,減弱了為本村村民服務的功能,不利于全心全意為本村村民服務,降低處理本村事務的有效性。
三、提高農村基層治理水平的對策
(一)提高治理主體的治理能力
首先要提高基層黨員干部治理能力。黨員干部才是基層治理的排頭兵,在基層治理的過程中至關重要。要提升黨員干部的學習能力,提高對基層工作的認識,增強學習意識。必須要不定期對村鎮黨員干部進行教育培訓工作,嚴格制定黨員教育、管理和監督的機制,要讓黨員干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要完善黨員干部的考核機制,激發基層黨員干部內生動力。制定科學合理的考評體系,鼓勵基層黨員干部會干事,能干事,干好事。
其次,要加強基層工作人員的培訓,提升主動服務的意識。基層工作人員是實現政策最后落地和促進村民積極參加農村治理的強心劑。基層工作人員是實現政策落地的最后一步,所以需要把好關,做好事。一是要求基層工作人員傳達政策要快,尤其是這個信息發達的時代,市場瞬息萬變,要盡快將信息傳達給村民;二是要把政策給村民講好,講得透徹,講得明白,講到村民心里去,積極了解村民真正的需求,為村民辦實事,增強公信力。
最后,要樹立村民的主人翁意識,積極參與村治理。農民是農村基層治理的主體,提高村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提高村民參與村務治理積極性,加強村民參與村民自治意識,對加強基層治理有著積極意義。自治的核心是參與,要拓寬村民參與渠道,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及時公開村務,做到透明化,讓村民及時了解到村務的進展程度,保證村民的知情權,讓村民主動參與到村務中,而不是被動參與。與此同時應主動建立教育培訓機制,為村民普及科學法律知識,提高村民治理能力。
(二)加強基層“三治”融合的治理體系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建立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德鄉村治理體系”,自治固本、法安天下、德潤人心,面對農村基層治理的紛繁復雜的治理環境,用好這“三治”極為重要。要把“三治”有機融合并貫穿于基層治理的整個過程中,發揮基層法治的強制性、規范性功能,彌補基層德治、基層自治原則性、規則性不足的問題,例如,農村社會固有的“熟人社會”現象,可以運用法治的手段進行治理,積極培育村民的法律意識;發揮基層德治的極致溫和的低成本功能,彌補基層法治、基層自治成本高、內生性德不足的弊病,中國自古以來講究德治,“德潤人心”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以此加強村民對本村治理的積極性,對基層干部的認同感;發揮基層自治協商民主、符合實際的功能,彌補基層法治剛性不足的弊病,協商民主是治理的一種基本手段,民主協商更能集中民智,聚集民心,合乎民意,形成有效治理。
(三)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農村基層治理的“主心骨”,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部署落地落實起著重要作用,要充分發揮起“主心骨”的身份作用。想要加強農村基層治理,必須充分發揮農村黨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引導作用,圍繞班子建設、干部隊伍建設增強黨的組織凝聚力。讓基層黨組織、黨員干部站在群眾中去,真正為百姓做好事、做實事,才能贏得群眾尊重,不斷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
總之,農村基層治理工作任重道遠,要想根本解決農村發展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農村基層治理主體更要立足當下,根據當地具體情況因地制宜,積極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尋找有效的治理措施,才能更好促進經濟發展,助推鄉村振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