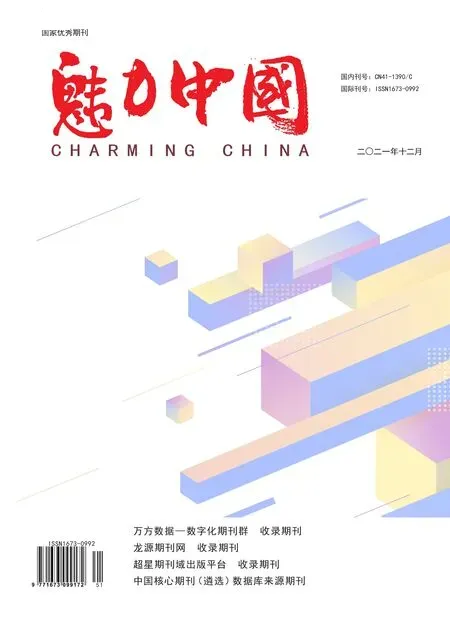關于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路徑探索
楊敏 盧波 張波
(中國石油東方地球物理公司西南物探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213)
引言
2021 年3 月12 日,國家公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tǒng)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近年來敲打著無數人神經的“延遲退休”,終于迎來了黎明破曉、呼之欲出的時刻。一時間,舉國上下,議論紛紛,大有一幅“狼來了”的畫面,其形勢不亞于中國加入WTO 的前夜。
根據現行政策規(guī)定,我國職工現行退休年齡是:男性60 周歲,女性干部55 周歲、女性工人50 周歲。該政策于1978 年頒布實施,當時中國人均壽命不到70 歲,此后四十余年間,盡管我國社會高速發(fā)展、改革開放取得矚目成就、醫(yī)療保障條件逐步完善、人均壽命不斷增長,但至今基本未對該政策作出大的調整或實質性改革。2021 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 歲及以上人口占18.7%,65 歲及以上人口占13.5%,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較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的13.26%增長了5.44 個百分點。按照聯合國傳統(tǒng)標準,一個地區(qū)60 歲以上老人達到總人口的10%(新標準是65 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的7%),即該地區(qū)視為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顯然早已步入老齡化社會。基于我國人口結構變動的事實,早從上個世紀90 年代開始,決策層和學術界就開始反思現行退休年齡政策的合理性、適用性,反復研究論證適應社會發(fā)展新形勢、新特點的退休配套政策。學術界率先提出了“延遲退休”的政策建議,認為基于預期壽命、人口結構以及退休制度等因素的現實狀況應適時對退休政策進行調整,官方部門在對延遲退休問題保持審慎態(tài)度的同時也在穩(wěn)健推進[1],此后不斷發(fā)展發(fā)酵。
延長退休年齡通常被認為一方面可以增加繳費,另一方面可以縮短領取養(yǎng)老金的年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養(yǎng)老金危機。然而,在嚴峻的就業(yè)形勢下,部分學者旗幟鮮明地反對延長退休年齡[2],認為延遲退休會減少年輕人的就業(yè)機會,給就業(yè)市場造成更大壓力,同時還會滋生代際收入轉移、出生率影響等問題。由于時代背景局限、出臺阻力太大、推進程序復雜、后續(xù)影響深遠等因素,直到“十三五”收官,我國的延遲退休政策仍處于“紙上談兵”、書面求證的階段。當前,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和社會保障問題愈加突出,加之養(yǎng)老金儲備缺口越來越大,調整完善現行退休政策、探索延遲退休年齡的可行性,是我們應當高度關注、堅定推進的當務之急。
一、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重要意義
國際經驗表明,人口老齡化將給國家的社會經濟帶來深刻影響,尤其是對養(yǎng)老保障體系、勞動就業(yè)等方面影響巨大。上世紀90 年代起,我國城鎮(zhèn)職工基本養(yǎng)老保險制度向社會統(tǒng)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統(tǒng)賬結合”模式轉軌[3]。由于未解決好制度的轉軌成本問題,加上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導致養(yǎng)老金儲備缺口越來越大,我國養(yǎng)老保險基金面臨巨大支付壓力。
(一)這是人口結構老齡化的必然要求
國家近期公布數據顯示,我國人均壽命已達77.4 歲,但自2013 年以來生育率逐年降低,老年人增多、青壯年減少,社會正步入“老齡化”的趨勢不可逆轉,“未來一段時期將持續(xù)面臨人口長期均衡發(fā)展的壓力”。改革開放以來因國民讓渡部分自身利益的“人口紅利”正逐步透支,而要實現“老有所依、老有所養(yǎng)”的社會保障目標,現有的社會保障資金規(guī)模勢必難以支撐。在這種情況下,延長退休年齡、拉長工作年限、調整“繳”“領”基數,開源節(jié)流、共克時艱,將極大緩解國家負擔和保障壓力,更有利于應對人口結構老齡化的沖擊。
(二)這是避免人力資源浪費的實際舉措
從我國國情來看,國家、社會對國民教育的重視程度高,但整體教育周期過長,學用脫節(jié)、訓用不一致的現象還比較普遍,社會對教育支出的回報率不高。以培養(yǎng)一名大學生為例,從7 歲入學到23 歲大學畢業(yè),國家將承擔16 年的教育支出;且從當前的形勢來看,今后攻讀全日制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學生將越來越多,教育時間將進一步拉長。同時,參加工作后,社會各機構在人才的選拔培養(yǎng)、作用發(fā)揮、穩(wěn)定保留等方面而采取的培訓、考核、激勵等措施和機制,將進一步增大人力資源成本。因此,適當延遲退休,延長職業(yè)生涯的“黃金期”,可進一步挖掘社會人力資源的潛力和效益,實現“人盡其材”“人盡其用”。
(三)這是尊重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具體體現
現行的退休政策中規(guī)定的退休年齡,是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參照國際標準,按人均壽命70 歲測算設置的。但隨著人均壽命延長,國民精神層次提高、物質需求增加、綜合素質增強,如果過早脫離工作狀態(tài),可能引發(fā)“退休綜合癥”等社會心理問題,催生老齡人非正規(guī)“再就業(yè)”浪潮,增大流動無業(yè)人口管理難度,甚至消極社會風氣、加劇社會矛盾、引發(fā)犯罪問題等;另一方面,中青年占比變小,工作生活壓力陡增,社會內生動力不足,于國家極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近年來生育率逐年降低即為一個警示信號。對比發(fā)達國家,美國標準退休年齡為67 歲,日本標準退休年齡為65 歲(擬延長至70 歲),我國擬延遲退休也在情理之中。
二、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
改革,改制革新、破而后立。延遲退休,涉及全員、利益攸關,其核心問題是:在延長社保繳納年限的同時,縮短了領取養(yǎng)老金的時間,讓人產生了“利益受損”的心理落差。不能兼顧所有人的利益,社會上便有了不同的聲音。反對聲音最大的,應該來自于體力勞動者、自由職業(yè)者等高強度、高體力的群體,以及無固定收入人員和失業(yè)者等,延遲退休便延長了他們高強度工作、無保障時間。由此可能導致社會公平失序、引發(fā)社會矛盾。
(一)人才更替變慢
各行各業(yè)的骨干人才在崗時間增長,雖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穩(wěn)定保留的問題,可以支撐行業(yè)高質量穩(wěn)定發(fā)展,但這類群體可能出現思維觀念過時、知識儲備陳舊、決策布局保守、工作狀態(tài)下滑等問題。同時,在不增加就業(yè)崗位的前提下,現有人員在崗時間越長,就越缺少新鮮血液注入,人才的更新迭代速率變低,行業(yè)的創(chuàng)新性、執(zhí)行力、高效率必然大打折扣,從長遠來看似乎得不償失。尤其是對頂層管理人員來講,他們可能受“平穩(wěn)著陸”“補償心理”等影響,增大退休前違紀違規(guī)風險,反而制約行業(yè)發(fā)展,進而影響社會發(fā)展大局。
(二)失業(yè)人口增多
短期內,在新的經濟增長點被發(fā)掘、國際勞務輸出路子被鋪開、行業(yè)領域分工再細劃之前,社會就業(yè)機會將不會明顯增加,人力資源與工作崗位供大于求的現象將更加突出,一方面就業(yè)門檻將明顯提高、“畢業(yè)即失業(yè)”成為新常態(tài),另一方面行業(yè)內卷現象加劇、“中年裁員”增多、失業(yè)率將大幅增加,人人都將普遍缺乏工作安全感。同時,隨著信息化、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高新技術及概念的日漸成熟、推廣運用,現代社會各行業(yè)對從事機械重復低智工作的“流水線上的人才”的依賴程度將進一步降低,對人的全面綜合素質要求將越來越高,“人滿為患”與“人才難求”的現象將長期存在,這種人力需求的“精英化”趨勢將進一步加劇失業(yè)矛盾。
(三)社會穩(wěn)定難控
隨著社會發(fā)展進步、經濟高速發(fā)展,人民需求旺盛、生活成本增加、失業(yè)率不斷攀升,社會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實現“推動區(qū)域協調發(fā)展”“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目標任重而道遠。對無固定工作、低收入或無收入人群,如果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們將成為社會最大的不穩(wěn)定因素。這部分人基數大、困難多、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長期缺乏穩(wěn)定收入來源,他們“老有所養(yǎng)”的訴求最為強烈,延遲退休對他們來說意味著推遲領取養(yǎng)老金、自力更生與社會保障之間的“空檔期”也將進一步拉長,因其心理落差導致的不可控事件也最多,由此可能引發(fā)大量社會問題甚至違法犯罪。
三、對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的幾點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政策好不好,要看鄉(xiāng)親們是哭還是笑。”治大國如烹小鮮,延遲退休于國大利,但動的是群眾的奶酪、涉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理當謹慎對待、徐徐圖之。《綱要》明確“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tǒng)籌兼顧”的實施原則,表明延遲退休將強力推進,但不刮“暴風雨”、不搞“一刀切”,將充分考慮多方因素、平衡全局利益而穩(wěn)妥推進。
(一)小步快走、預留緩沖區(qū)間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提升、世界重心東移,中美之間的對抗將日益“白熱化”,妥善穩(wěn)慎解決民生問題、實現在彎道超車中輕裝上陣,是我們面臨的時代大考。延遲退休已經成為國際共識、大勢所趨,但這種覆蓋全員、震動“國基”的政策,不可能就地劃線、一蹴而就,極大可能采取“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策略,可設置3-5年的過渡期,期間依據工作年限逐步推遲退休年齡,最終實現新老并軌;其次,堅持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多勞多得、少干少得,把工作年限、工作性質、工作強度等因素納入社會保障計算范疇,倡導愛崗敬業(yè)、“先苦后甜”、酬勞對等的價值導向,增強個人自主選擇權;第三,以點代面、先易后難、穩(wěn)步推進,兼顧操作性、可控性、靈活性,應從政府機關、企事業(yè)單位、社會團體等機構試點鋪開,再向自由職業(yè)者、農民工、無固定工作流動人員等延伸,同時高度關注特殊行業(yè)領域、特殊人群的現實訴求,疏通“堵點”、降溫“燃點”,最大限度化解矛盾和阻力。
(二)靶向精準、突出重點群體
為確保新政策高效、精準、平穩(wěn)落地,必然要區(qū)分不同行業(yè)類型、工種崗位、尤其是突出高風險行業(yè)、低收入或無收入群體這個重點。充分結合實際情況、分類制定適用標準,差異化延遲年齡,在保證公平公正的大前提下杜絕“絕對平均主義”。同時,在突出對下行收入群體基本保障的基礎上,堅持“多交多領、少交少領”總構想,細化保障“級差”,進一步激發(fā)群眾參工熱情、緩解社保資金壓力,實現社會保障“按需分配”與“按勞分配”相結合,增強新政的針對性、合理性。
(三)投石問路、及時完善機制
對于一個有著14 億人口的大國強國,延遲退休政策完全沒有可照搬照抄的“標準答案”,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在前進中探索符合國情的解決方案。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密切關注、實時掌控,及時調整完善政策規(guī)定,把人民群眾的憂思關切擺在首位。在總體框架下,各級地方政府應當主動作為,細化制定適合當地實際的配套措施,確保延遲退休政策減阻力、增活力。
結語
從國家長治久安的層面出發(fā),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我國當前必然要跨過的“獨木橋”,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選擇。但每一項公共政策的出臺,都會觸碰到公眾權益,且不能兼顧所有人的利益,必然會遭遇質疑和反對。因此,在具體方案的推行實施上,應當謹慎對待、徐徐圖之,以“漸進式”理念為導向,采取小步快走、預留緩沖區(qū)間,精準施策、突出重點群體,投石問路、及時完善機制等措施方法,按類別、分步驟有序推進該項工作,確保政策穩(wěn)步實施、順利推進、落地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