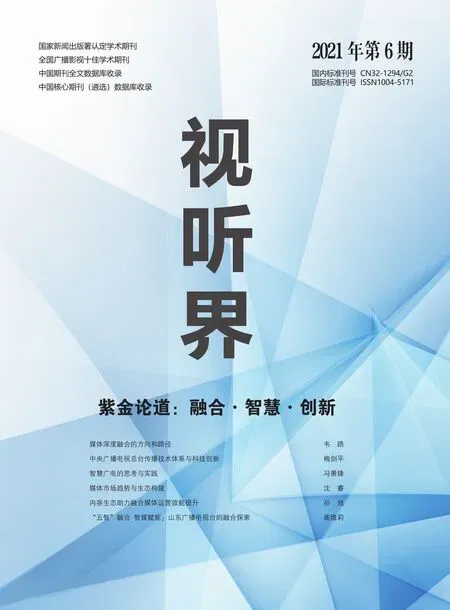公共傳播時代的媒介倫理
顧理平
我們曾經用“激動人心的傳媒變革”來形容智媒時代的到來對整個社會的深刻影響。事實上,這樣的比喻毫不夸張。智媒時代到來,不僅深刻影響著新聞信息生產和傳播的整體格局,更給所有的社會成員提供了自由參與公共事務的諸種可能性。而智能手機的普及,則讓這種可能變成了現實。于是,輕觸屏幕之機,小到家長里短社區民情,大到國計民生世界局勢,幾乎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參與評論和表達建議,這當然是令人欣喜的傳媒生態變化。但是,我們也遺憾地看到,并不是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對這種猝然而至的機會做好了準備,也不是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具有相應的新媒體素養。于是,我們就會在新媒體平臺上看到流言傳播、涉黃信息、粗俗話語、不堪畫面……一句話,智能媒體海量信息傳播中,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媒介倫理失范行為令人憂心。
傳統媒體時代,新聞信息傳播過程中也存在虛假新聞、低俗信息等媒介失范行為,但就總體而言,由于當時的傳媒業作為專業性較強的行業,新聞從業者大多具有較高的專業能力和媒介素養,加上媒體把關人的存在和行業規范的嚴格約束,新聞傳播過程中的失范程度較輕,發生情況也比較少見。進入智媒傳播時代,由于智能傳播技術提供的諸多便捷功能,即使是一個目不識丁者,也可以通過視頻、語言等參與傳播過程,“人人都是傳播者”似乎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日常。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社會成員實際上并不真正了解微信等新媒體平臺實際上是作為大眾傳播媒體存在的,也并不清楚自己有意無意傳播的各種信息會帶來何種影響。換句話說,他們并沒有很好地具備相應的媒介素養和媒介倫理認知,導致媒介倫理失范行為頻繁發生。
科學的媒介倫理是規范傳播秩序、弘揚社會主流倫理道德理想的重要保證。在傳統媒體時代,以《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為基礎的媒介倫理,是規范新聞傳播活動的重要規則。在此基礎上,相應的新聞媒介還根據自身特點,制定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區域、行業規范和內部規則來確保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和倫理原則。與此相對應,在正面倡導的同時,對新聞失范行為的懲處也會適時施行,諸如此類的措施,確保了傳統媒體正向、積極作用的有效發揮。智媒時代,上述《準則》依然發揮著對新聞從業者的規范作用,并且經過幾次修訂,也更好地體現著時代精神。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智媒時代的新聞信息傳播已經進入到一個復雜的傳播生態中,傳授者的分野已經消失,把關人的缺位(實際上是前置轉為后置)令信息傳播不再存在前置嚴格的審查核實過程。海量的信息主要不再由專業人士生產,而變成所有社會成員共同生產……曾經對專業傳播者行之有效的傳播媒介倫理準則,并沒有也無法適時地發揮規范所有傳播者的作用。面對這樣的傳播生態,我們除了需要培養全體社會成員的媒介素養,尤其是新媒體素養外,特別需要有更好的規范全體社會成員的媒介倫理的手段出現。具體而言,我們需要將國家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優秀的倫理道德原則和文化精華,通過適當的方法和途徑,促使其像規范新聞專業從業者的《準則》一樣,成為全體參與新聞信息生產、傳播過程中不同環節的公民共同遵守的準則。在強調正面倡導的同時,也注意發揮對嚴重失范行為的懲治作用。在新聞傳播實踐中,國家相關部門已經對存在包括倫理失范行為在內的有問題的APP、微信公眾號等進行下架、禁言等處罰,發揮了較好的威懾作用。事實證明,倡導和懲處的共同作用,是確保傳播規范的重要手段。
清朗的網絡環境中傳播的優質內容是每個有現代意識的社會成員共同期待的精美精神養料。這樣的精神養料不會自然產生,它需要全體社會成員持續不懈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