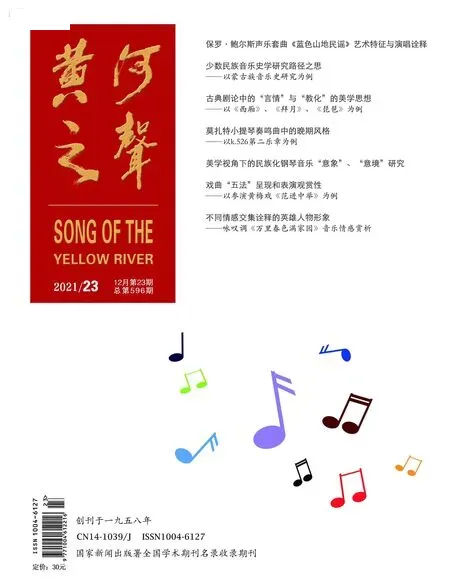論歌曲寫作中藝術性特點的體現
——以三首歌曲為例
張政睿
一、西方浪漫派晚期的多調交織——《青春頌》
《青春頌》是奧地利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于1908年創作的交響組曲《大地之歌》的第三樂章(Das Lied Von Der Erde - 3. Von Der Jugend),原作是一首配以交響樂隊伴奏的男高音獨唱聲樂作品,本文分析的是縮減后的鋼琴伴奏版本。這首作品靈感來源于中國唐代詩人李白的作品,因此帶有翻譯成中文的歌詞(原作:李白《宴陶家亭子》)。這是一首帶引子的再現單三部曲式結構的作品。
(一)調性特點分析
由于馬勒身處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正是浪漫主義晚期與民族主義崛起的時期,因此這個時期作曲家的寫作已經打破一些古典音樂中的寫作規范,在調性方面會非常自然的使用調性游離手法。在這部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其頻繁的平行大小調,同主音大小調的交替等。
首先,作品的開頭使用了降B大調作為主調性展開,直到第一部分結束時(第35小節)才發生了第一次轉調,轉向了其平行小調(g小調)的同主音大調G大調。向下小三度的色彩性轉調使我們可以清楚的感受到調性的升華,而此處也剛好是作品第二部分的開始。
作為對比中段,當作品進行到第55小節時,作曲家運用相同的轉調手法,將調性轉到了同樣是其平行小調(e小調)的同主音大調E大調,再次將色彩提升,此處是與旋律聲部的呼應和與首部主題的鮮明色彩對比。當作品進行至64小節時和聲與調性已經十分復雜,作品先是轉到E大調的同主音小調e小調,在4個小節的鞏固調性后再次轉到了它的平行大調G大調,而最后在69小節屬七和弦的幫助下轉到了g小調,從而開啟了中部的第二主題。
剛好由于g小調是降B大調的平行小調,所以在中部第二主題中作品的調性不斷在降B大調與g小調中游離,使調性不穩定。而在中部主題結束后第90小節,作者使用了g小調三級的重屬導七和弦解決到了降B大調的主和弦,從而確定了再現部分降B大調的調性。
(二)和聲特點分析
作品除了調性轉換十分精妙,在此對幾個特殊和弦舉例說明。
首先是作品第60-63小節處作者大量帶有變音的離調和弦的使用,體現了浪漫主義晚期作曲家寫作的和聲技巧,如#5SII7/D等諸如此類的和弦,和弦中三音和音的升降是為了傾向解決至下一個和弦音,其中還包含等音的轉換。同樣的和弦邏輯在作品第86-90小節處也有體現。
在作品第68-75小節和聲的進行也十分精彩。首先是G大調的主和弦接了降二級和弦的屬七,緊接著使用屬七和弦轉到其同主音小調,在3個小節調內自然和弦的運用后,在73小節第四拍使用了重屬導和弦接了74小節第一拍的下屬和弦,在第四拍又使用了D7/DTIII也就是后邊要去降B調的屬七和弦。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完成了旋律的色彩變化同時也完成了低音的級進下行線條,十分具有藝術性。
(三)其他音樂創作特點分析
除了作品本身的曲式,調性,和聲等具有較明顯的特點之外,作曲家在其他方面也體現出浪漫主義晚期作品風格的獨特之處。
作品全程的屬音持續的運用。作品在開始就使用了主和弦的五音,也就是屬和弦的主音并一直持續至中部主題出現,這里可以解釋為屬持續。而在浪漫主義之前,這樣長度的屬持續音是并不常見的,且屬持續最終一定會解決。在這里就體現了作曲家對調性的把控,這里同樣可以解釋為是建立在屬調性上的主調,雙調性的重疊以增加其不穩定性。在這里也體現了作曲家強烈的個人風格。
其次是作品的速度,旋律,節奏,表情等因素。作品的開始速度是急板,其節奏雖然簡單但張弛有度,斷句感非常好。作品中部速度雖然沒有變,但是節奏的變化使長音凸顯,小調的感覺也使情緒得到了轉換,伴奏織體的簡化也使作品了寂靜祥和的感覺。
總的來說,整首作品無論是從曲式結構,調性特征,和聲技法,旋律特點來說都與古典主義時期的作品有很大的區別,浪漫派作曲家的多調交織是其藝術性特點的展示方式,這是值得在歌曲寫作中借鑒的。
二、巧妙的旋律發展安排與中國式的感情遞進——《玫瑰三愿》
《玫瑰三愿》是我國近代的一首經典的抒情性藝術歌曲,由近代著名作曲家黃自先生創作于1932年,這是黃自先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品借玫瑰凋零的場景抒發在淞滬之戰停戰后,對祖國蕭條和人民內心憂傷的情緒。歌詞來自同時代的文學家龍七先生,注重結合詩的韻律和情感。由于我國的藝術歌曲是在近代產生并發展起來的,黃自也是創作藝術歌曲的重要的作曲家。這首作品結合中國的民族音樂特征,吸取了西方剛引進來的作曲技術,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和個性化的一首作品。
(一)曲式結構分析
作品的引子部分即是作品的前奏,調性為E大調共4小節。這部分是首部主題樂句的簡短導引,基本采用了與主題相同的節奏與旋律。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節拍變化,雖然以6/8拍為主但在第三小節簡短的變化為9/8拍,是使樂句擴充,達到放緩速度的效果且加強了歌唱前氣口的引入。
作品的第一部分是作品的主歌部分,由兩個樂句組成,調性為E大調,節拍以6/8為主,在結尾處簡短變化為9/8拍又回到6/8拍,作用與引子部分相同。其旋律線條呈波浪形,以級進為主跳進為輔,對節奏長短的把控十分切合斷句習慣,且每每在三小節處設置高潮點,旋律起伏優美婉轉。
作品的第二部分是作品的副歌,由三個樂句組成,但對比主歌部分無論是節奏還是旋律都有較大變化。旋律方面,旋律以弱起開始,大跳進入高音然后級進下行,相比第一部分的逐步級進上行達到高點有著明顯的區別;而在整體上,大跳也有很強的推動感,在最后一句將作品推向高潮,并在最后的尾聲將旋律緩緩落下使作品意猶未盡。
(二)調性和聲分析
作品以古典和聲為主,和聲連接也體現了古典和聲的連接規律。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歌部分“SII-D7-T”的進行,還有在B樂段的“TSVI-SII-D-T”都是在西方古典音樂中常見的和聲進行。從這里可以看到作曲家對西方古典和聲的掌握十分嫻熟,在同時大量的副屬和弦的使用上我們也能發掘其對情緒的推動具有深刻內涵。
其次是作曲家對各種和弦外音的使用體現了一定的和聲編配技巧。和弦外音的使用作為和聲進行的重要部分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作曲家個人風格,而黃自在這部作品中也體現了其強烈的個人風格(在黃自的其他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他非常擅長使用外音為樂曲增色)。外音作為非和弦音,其與和弦碰撞時會使和聲色彩發生變化,黃自在曲中大量的使用了倚音,延留音,經過音,輔助音等和弦外音且都通過二度的合理解決為和聲增加神秘色彩,使作品具有多聲部線條美感的同時加強了旋律的邏輯聯系,這也是作曲家強大的作曲技巧的體現。
(三)其他音樂創作特點分析
作品的伴奏由小提琴與鋼琴組成,二者既是西方音樂的代表樂器,也是這首作品具有濃郁柔和色彩的來源。首先是小提琴的使用十分獨特。樂曲的前奏是小提琴演奏的主旋律,結合柱式和弦的鋼琴伴奏織體給人以穩定,溫柔,和諧的感覺。在樂曲開始演奏后,小提琴以副旋律的形式與歌唱的主旋律進行交織,這里體現了作曲家對復調技巧的掌握。大部分情況下,小提琴都是主旋律的呼應,而小提琴的旋律線條除了作為句間補充加入外還起到了襯托主旋律的作用。由于本作是為女高音而作,因此小提琴的音色與女高音的音色形成天然的襯托,二者娓娓訴說使人感受到協和的美感。
其次是鋼琴伴奏的織體。同一個和弦使用不同的織體會使作品的情緒產生變化,這首作品雖然伴奏織體簡單,但在每次分解和弦出現的地方都對作品起到了推動情緒的作用。第一次分解和弦的出現是在12小節進入副歌之前,與主歌的織體形成對比且預示副歌的情緒,在副歌中也大量使用了左手分解右手柱式的織體形式,配合以和聲的推動,為樂曲情緒做了良好的鋪墊。而在第25小節簡短的重屬導和弦的襯托下,突然轉化為柱式和弦并休止延長,使情緒舒緩,在結尾又回到了最初的柱式和弦,并以緩慢的分解和弦作為結束,令人回味無窮。
作品中一共出現了三次節拍的變化,都是6/8拍與9/8的轉換(第4小節/第11小節/第25小節)。這些地方都是樂句的結尾,也是下一個主題的開始。在這里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對小節內節拍的擴充而將節奏拖長,為下個氣口做準備。而這里的“氣口”也恰好體現了中國作品中速度較為自由的特點。
總的來說,相比西方浪漫主義晚期的藝術歌曲,20世紀初中國的藝術歌曲雖然也借鑒了西方音樂中嚴謹的邏輯思維與和聲編配手法,但在旋律與節拍的處理上更能體現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方式,而這種美感在當下的流行歌曲中也有所體現。
三、融合西方的浪漫與中國的旋律發展特點——《奮不顧身》
《奮不顧身》是2015年由劉歡與吉克雋逸合唱的一首歌曲。這首歌的作曲、作詞皆由劉歡一手包辦。全曲充斥著怪異又不協和的碰撞,具有一定的魔幻性,歌詞內容也非常藝術化而又直白,且其主題旋律對調性色彩的把控也十分到位。劉歡為電影《鐘馗伏魔:雪妖魔靈》創作的主題曲《奮不顧身》,將電影的魔幻特制和人妖虐戀的愛情故事相融合,整個歌曲呈現出了極強的迷幻化視聽感官享受。
這首作品是一首男女對唱的作品,作品曲式結構具有再現三部曲式特點,節拍為6/8拍。由于作品是為男女對唱而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給了作曲家進行調性轉換的空間:在主歌部分作曲家就采用了“一句一換”的調性轉換模式,其主要轉換方式是前一句調的落音作為后句調性的主音,這樣的轉調方式一方面便于后句起始音的進入,另一方面也突出了色彩性較強的二、三度關系調的直接轉調帶來的色彩沖突形成強烈的怪異感。
首先由女聲演唱的主歌第一句調性為g小調,落音在其導音#f上,由男聲在#f小調上唱出二聲部,形成了二度對位的復調效果,落音在其上中音a上,此時又由女聲在a小調上唱出第二句旋律,形成小三度關系的轉調,男聲又在#f小調上做出二聲部答句旋律,直到第三句開始由女聲演唱的旋律調性在a小調與c小調中交替,最終結束在g小調的屬和弦上完成主歌第一遍的終止。第二遍主歌調性轉換方式與第一遍主歌一樣,只是男女聲部交換,因此整體調性下移了純四度。整個主歌部分的特點是:一聲部調性色彩不斷提升(g-a-d-c-g)二聲部進行與之對置的二、三度調性的色彩性襯托,形成不協和的音響效果。在副歌部分雖然沒有如同主歌部分的多調變換,但也采用了同主音大小調交替的方式,由副歌一開始的小調色彩轉為大調色彩并采用了皮卡迪終止來增加結束時的意外感。
雖然調性轉換十分頻繁,但作曲家在和聲方面卻沒有太多設計,其和聲的亮點除了大量使用三度疊置的高疊和弦來增加其調性的不穩定性外,還有就是對三全音關系和弦的連接:如在主歌部分的結尾處作曲家就使用了降II級和弦接屬和弦這樣的進行。雖然這樣的進行在浪漫派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經比較常見了,但在中國當代流行音樂中使用的還不是很頻繁,因此會給人一些意外感。
當然,作為一首為電影創作的主題曲,一方面需要考慮其藝術性特點,同時也要考慮到聽眾的感受,因此在作品中也不可避免的聽到一些現代化的配器方式,如加入電聲樂器、合成器等來豐富作品的聲部從而產生更好的聲場效果;再比如弦樂中大量使用流動的織體以強調其音樂的起伏轉折,襯托調性的交織變換給人以更豐富的聽覺體驗等等。這些雖然不是本文闡述對比的重點,但也是藝術性表達中不可忽視的關鍵一環。
結 語
通過分析和對比三首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風格的聲樂作品可以發現,在歌曲創作中作曲家對音樂要素的把控十分重要,無論是浪漫派晚期的調性轉換方式,還是中國作品中注重旋律發展的特點,還是當下流行歌曲中對復雜調性交織的運用,都是其藝術性特點的體現。作為作曲專業的學習者,在未來的歌曲創作中除了要把控詞曲結合的特點,同時也應注意到突出作品的藝術性特點,在聽眾審美日益提高的今天,不斷創作出更有感染力兼顧藝術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