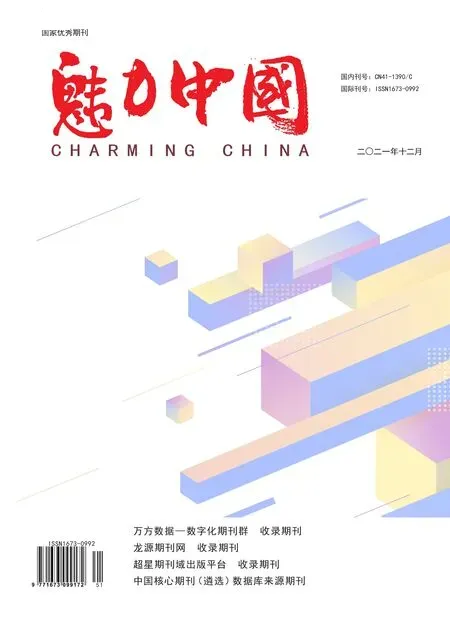以生態倫理視閾試析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
卞藝霏
(哈爾濱商業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8)
習總書記生態文明思想中豐盈的生態倫理觀,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生態倫理觀的繼承發展與時代回應。對馬克思生態倫理觀的深入研究,將毫無疑問地有利于我們更清晰地理順習總書記生態文明建設的思想脈絡。
一、馬克思生態倫理蘊含的三重規定性
(一)自然價值觀
馬克思認為,“人(和動物一樣)靠無機界活,而人比動物越有普遍性,人賴以生活的無機界的范圍就越廣闊……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現出來。”毫無疑問地,馬克思承認自在自然的先在性,更不否認人類和其他所有生物都依托自然而得以維系生存。然而生態倫理視閾研究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實際上指的是“人化自然”。因比之其他生物,人類所特有的主觀能動地實踐活動改造了原初的自然從而實現“人類意志駕馭自然的器官”的轉變。“人化自然”使自然具有了屬人特性,換句話說已經內化為人的部分,才使研究人與自然間倫理關系成為可能。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故在“人化自然”的同時也促生了“自然化人”。在“自然化人”過程產生的自然價值體現在人類社會則是,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自然反塑造價值。
(二)人道主義的主體地位
馬克思沒有因為要突出強調人的主體性地位,而把自然從屬于人,僅將自然劃分到一個社會范疇。反而更加強調的是人與自然不僅相互聯系還相互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他提出,“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人類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的自然性,即人類作為普通的物種依屬于自然,代表一種物的尺度。然而對于人類來講,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應是有機統一的內在的結合。要知道,外在的尺度只在生存論層面有意義,它只規定了人類生存的尺度。人的價值選擇才是決定外在的、囿于生存論的尺度是否能夠成為一種道德規范的關鍵。為了具有倫理的內涵,必須把物的尺度內化成人的尺度,而成為居于主體性地位的人的內在要求。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關系需要站在人的社會性立場。
因此,只有人道主義,而不是自然主義,才能作為生態倫理的基礎。
(三)勞動系聯系人與自然的媒介
馬克思指明,“勞動首先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資,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馬克思主義生態倫理的核心是勞動與自然的關系。“人化自然”與“自然化人”也是通過人類改造自然的實踐勞動從而雙向生成的。人類借以能動地勞動實踐來確認并實現自身的本質。在現實中不可能存在抽象的“類”本質的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是歷史的且具體的。因勞動而使得人類利用自然的道德合理性的實現。勞動于道德意義上的合理性,即其發展了人,使人得以成為區別于其他物種的人。勞動人類得以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必要手段。然而隨著逐步發展到資本主義的社會階段,私有財產、階級分化及勞動分工的出現,迫使勞動逐漸成為了“異化”的勞動。勞動的“異化”導致生態倫理的異化。具體表現在這幾個方面:第一,由勞動者和其生產的勞動產品間的異化而造成的生態倫理異化;第二,勞動者和人化自然過程的異化;第三,異化勞動致使自然和勞動者類本質的異化;第四,因勞動的異化從而人與自然生態權利地異化。資本主義盲目追求物質生產利益的生產方式,導致人與自然的雙重異化。
二、馬克思生態倫理的方法論特征
(一)普遍聯系
馬克思生態倫理摒棄了孤立靜止地處理人和自然間關系問題的視角,與此相對的,把自然、人、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等歸屬于普遍聯系的整體系統的范疇。正是通過普遍聯系地方法論讓馬克思發掘出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才是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的深層根源。從而引申出徹底解決生態危機及最終實現馬克思主義生態倫理愿景,需要無產階級進行根本性地社會變革實踐。
人類擺脫了作為一般類存在物只被動地接受自然的從屬性地位,運用主觀能動地勞動實踐將自然轉變為人化自然。人類通過不斷在理論和實踐層面規定自然、人化自然,而最終形成了社會。
資本主義的社會大生產于生態倫理的發展既有積極促進的推動,更不乏落后腐朽的阻礙。其積極的一面:在于工業化的資本主義,把囿于孤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中,備受封建奴役性勞動苦楚的農民從土地剝離,將他們大部分集中到城市并進入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生產的流程,從而推動形成了徹底解決生態問題的階級力量--無產階級;消極的一面:則是資本主義流水線式勞動分工消解了人能動創新地實踐活動,致使勞動者和技術分離。生態倫理視閾的自然是人化自然,毫無疑問地,畸形發展的人造成了畸形發展的自然。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盡管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確實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超越資本主義生態倫理的解放力量也蘊藏其中,即無產階級終將完成徹底地社會主義變革從而實現人和自然的雙重解放。
(二)辯證唯物主義
馬克思生態倫理中,人和自然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的。人歸屬于自然系統的一部分,借由社會實踐勞動的媒介,和自然產生關系:通過實踐勞動,使自然具有屬人性,從而將自然轉變為人化自然。人和自然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具有鮮明的對立統一的辯證屬性。馬克思生態倫理的辯證法,是超越了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及自然主義的新的生態倫理。
因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雙向互動的,人類通過勞動實踐作中介,既表現為自然向人的生成趨勢,也表現為人向自然生成的趨向。“人同自然的關系直接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關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規定。”需要注意的是,實現人和自然間物質變換的勞動不是自覺盲目的實踐活動,而是以能否創造有用的使用價值為標準的有用勞動。其亦是人類利用改造自然遵循的倫理標準,即判斷該行為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的直接依據。盡管自然的先在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人類利用改造其還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事實上,自然不僅提供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料,更供給了人類以豐富多姿的精神食糧。在人類利用改造自然的進程中,必須肩負以美表現自然的權利責任。馬克思提出,“從理論領域說來,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另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實現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同樣,從實踐領域來說,這些東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一部分。”
(三)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基于社會兩對基本矛盾,指明歸屬于意識形態范籌的生態倫理,也必然是由特定的經濟基礎決定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引發了異化畸形的生態倫理關系。基于馬克歷史唯物主義視角,最終尋求出解決生態倫理問題以期實現人和自然的雙重解放的道路,無法存在于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主義生態倫理的理論爭端中,只能存在于變革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實踐活動中。
馬克思不是僅僅簡單地將包括生態倫理在內的道德劃為意識形態的范疇,更側重其是不同社會歷史階段實踐作用而形成的社會歷史產物。因不同歷史階段存在著不同的生產關系,這就致使由其影響決定著的生態倫理總是具有相對性的特征;而在限定的歷史階段的生態倫理同時又是準確真實的。在不斷發展變化著的歷史進程中,總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完善人的生態本質規定性,從而一步步促進人和自然間關系的雙重解放。因此,于特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對應形成的生態倫理是具有相對程度意義上的合理性的。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內在規定,永遠無法脫離歷史,歸納出永恒真理性的生態倫理準則。
馬克思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看待資本主義,承認其比之傳統封建主義是有一定的進步性的,他切斷了傳統意義上的人和自然的關系,為新的生態倫理關系的生成提供了新的階級基礎;然而其社會制度決定的片面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瘋狂攫取生態環境資源并大肆破壞,導致人和自然間的矛盾日趨尖銳。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工人階級也在資本主義不自覺的創造中,逐漸發展壯大為變革社會的決定性力量。
三、馬克思生態倫理囊括的時代價值
一定的經濟社會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的構建向度,相應地意識形態也會能動的影響現實經濟社會的發展。落實到生態倫理的研究中也是如此,歸納分析馬克思生態倫理觀主要源于其根本上決定了習總書記新時代生態倫理框架的筑基方向,是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道德旨向的抓手。
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生態倫理視閾的普遍聯系、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并以此和諧、正義的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態生產力,最終實現人和自然間的雙重解放。還要時刻警惕防范掉入狹隘片面的“人類中心主義”或“自然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陷阱中去,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不能走入理論破局的誤區,而要倡導積極能動地實踐勞動以紓解人和自然間的生態倫理問題。習總書記繼承發展了這一馬克思生態倫理觀,提出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發展理念,也即表達了對人和自然間關系的倫理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