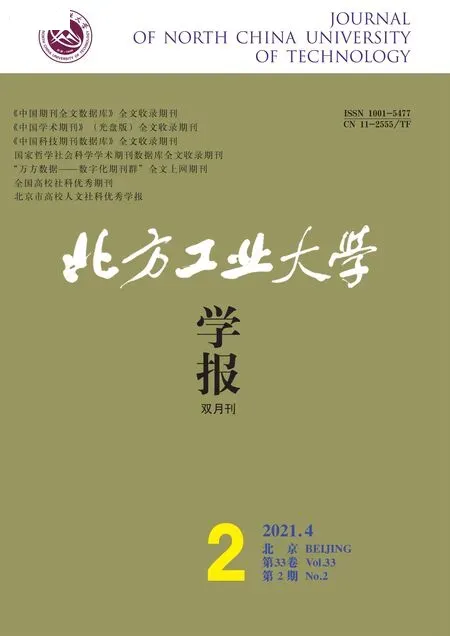當(dāng)代日本歌舞伎界世襲制的歷史文化因素解讀*
張 蓓
(1.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日本學(xué)研究中心,100089,北京;2.天津財經(jīng)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300222,天津)
2017年11月,日本松竹公司為歌舞伎世家松本幸四郎家舉辦了“高麗屋三代襲名慶祝會”,對外公布了二世松本白鸚、十世松本幸四郎和八世市川染五郎祖孫三代將于次年同時襲名的重大消息,這是時隔37年后日本再次出現(xiàn)祖孫三代同時襲名的盛況,也是平成時代歌舞伎界最后一次大型盛會,引發(fā)社會極大關(guān)注和討論。究其原因,除了藝術(shù)世家的社會影響力和演員自身的知名度以外,戰(zhàn)后歌舞伎界一脈相承的血緣關(guān)系、愈演愈烈的世襲現(xiàn)象也成為輿論焦點(diǎn)。在經(jīng)歷了明治維新和戰(zhàn)后民主化改革之后,日本已經(jīng)成功跨入亞洲民主國家行列。然而,在社會民主化的大趨勢下,戰(zhàn)前一直崇尚“實(shí)力主義”,推行養(yǎng)子、婿養(yǎng)子繼承家業(yè)的歌舞伎界為何逆勢而行,重新建立起世襲制?這一問題僅從戰(zhàn)后日本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和西方現(xiàn)代文明對東方傳統(tǒng)藝能的沖擊方面難以得到深刻剖析,它還與古代日本社會的家族制度、身份等級制度和松竹公司的商業(yè)運(yùn)作密切相關(guān)。
1 戰(zhàn)后日本歌舞伎界世襲制的現(xiàn)狀
近代日本經(jīng)歷了明治維新和戰(zhàn)后民主化改革兩次洗禮,政治上逐步由幕藩體制走向了西方的代議制民主,躋身亞洲民主國家行列。然而與全社會的民主化進(jìn)程相悖,歌舞伎界卻一改戰(zhàn)前收養(yǎng)養(yǎng)子、接納婿養(yǎng)子繼承家業(yè)的傳統(tǒng),轉(zhuǎn)而開始推行以血緣和家族為重要標(biāo)志的“縱向”世襲制,并通過聯(lián)姻“橫向”發(fā)展家族關(guān)系網(wǎng),形成了與民主社會格格不入的門閥現(xiàn)象,學(xué)者中川右介形容道:“八成的歌舞伎演員都是親戚”。[1]世襲制雖非歌舞伎界所獨(dú)有,能樂、狂言界也存在子承父業(yè)的現(xiàn)象,但根據(jù)“日本藝能實(shí)演家團(tuán)體協(xié)議會”①調(diào)查顯示,一線歌舞伎演員的數(shù)量、歌舞伎演出的場次及頻率都遠(yuǎn)超其他門類的傳統(tǒng)藝能。[2]顯然,相較而言歌舞伎界的世襲制無論從演員體量還是藝術(shù)門類本身的社會影響力來說更具代表性和研究價值。
2013年4月,擁有130余年歷史的歌舞伎圣地——歌舞伎座經(jīng)過第四次大規(guī)模整修后重新開門迎客。首場演出,松竹公司組織了歌舞伎界最具盛名的市川團(tuán)十郎家、尾上菊五郎家、中村歌右衛(wèi)門家、片岡仁左衛(wèi)門家、松本幸四郎家、中村吉右衛(wèi)門家以及守田勘彌家這七大家族參與其中,這一舉動不僅彰顯了歌舞伎座在日本傳統(tǒng)藝能史上的重要性,也體現(xiàn)出這七大家族在業(yè)界不可動搖的中心地位。通過梳理七大家族的家譜可以明顯看出,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為分水嶺,在選定繼承人方面戰(zhàn)前與戰(zhàn)后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兩種態(tài)勢,即戰(zhàn)前遵循“實(shí)力主義”戰(zhàn)后推行“門閥主義”。李玲認(rèn)為:“名題下出身的藝人晉升至名題非常少見,因此歌舞伎的等級制度并非實(shí)力優(yōu)先,而是以家系與血統(tǒng)為重。”[3]誠然,諸如坂東玉三郎、片岡愛之助等享譽(yù)世界的歌舞伎演員也并非梨園子弟,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他們也僅是眾多歌舞伎演員中的個例,并且探討他們的成功也不能忽視他們是先以養(yǎng)子身份進(jìn)入歌舞伎世家,后又揚(yáng)名立萬的基本事實(shí)。
歌舞伎界何以出現(xiàn)這樣的“返祖”現(xiàn)象?以往的研究多從戰(zhàn)后日本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和西方現(xiàn)代文明對東方傳統(tǒng)藝能的沖擊這一角度進(jìn)行分析,日本戲劇學(xué)家兒玉龍一認(rèn)為:“二戰(zhàn)前,收養(yǎng)才能出眾的孩子作養(yǎng)子,將家業(yè)傳于庶子的現(xiàn)象極為多見。戰(zhàn)后,家業(yè)僅傳給親生兒子的做法才逐漸多了起來。最大的原因是歌舞伎生存發(fā)展的基礎(chǔ)縮小了。日本國內(nèi)曾經(jīng)遍布大小歌舞伎劇場,還出現(xiàn)了扎根本地的歌舞伎演員。甚至到地方巡演時,還可以臨時在當(dāng)?shù)卣业匠鲅輧和巧男⊙輪T,群眾基礎(chǔ)極其廣泛。然而進(jìn)入昭和時代后,地方舉辦演出的方式發(fā)生了深刻變革,演員薪酬逐年遞減,歌舞伎與整個社會之間產(chǎn)生了距離,進(jìn)而喪失了人才的流動性。”[4]毋庸置疑,明治維新后日本拉開了學(xué)習(xí)西方的大幕,全力推動現(xiàn)代化,其影響滲透到了日本社會的每個角落,傳統(tǒng)藝能界也不例外。突出表現(xiàn)在,“四民平等”制度的實(shí)施使日本社會突破了階層的束縛,賦予了普通民眾更多自由選擇的機(jī)會。同時,紛紛涌入的西方現(xiàn)代文明帶來了新鮮的氣息,也讓傳統(tǒng)藝能一時間黯然失色,受眾基礎(chǔ)和從業(yè)人員數(shù)量均受到嚴(yán)重擠壓。然而,歌舞伎畢竟誕生于江戶時代,除了明治社會的深刻變革等客觀原因,分析戰(zhàn)后歌舞伎界世襲制的形成還不能忽視古代日本社會的歷史文化因素及這門戲劇藝術(shù)本身的特質(zhì)。
2 家族制度與歌舞伎
中日兩國對“家”的涵義界定不盡相同。“中國的‘家’是以婚姻和血緣關(guān)系為紐帶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日本的‘家’是以家業(yè)為中心、以家產(chǎn)為基礎(chǔ)、以家名為象征的家族經(jīng)濟(jì)共同體。”[5]換言之,血緣的代代相續(xù)并不是日本家族追求的首要目標(biāo),家業(yè)的后繼有人、綿延不斷才是根本。
日本歌舞伎世家的家業(yè)即指家藝,其傳承正是通過“家”的代代延續(xù)來完成的。又因?yàn)楦栉杓繉儆趹騽∷囆g(shù),“藝”的精湛與否直接關(guān)系到“家”的安危所在。因此,自歌舞伎發(fā)端的江戶時代起,市川團(tuán)十郎、尾上菊五郎以及松本幸四郎等各大名門世家就已經(jīng)開始精心錘煉技藝,以求家業(yè)昌盛、家族永續(xù)。可以說“保家”是歌舞伎世家的首要任務(wù),而“修藝”正是“保家”的不二法門。
“藝”是家業(yè)的核心,“人”是傳承的主體,“人”的素養(yǎng)直接關(guān)乎“藝”的高低,因此歌舞伎世家極為重視繼承人的選定問題。日本人家業(yè)繼承人的選擇可以不必受血統(tǒng)和系譜關(guān)系的限制,被認(rèn)定為具有親子身份關(guān)系的養(yǎng)子可以繼承家業(yè),這就是日本家族中的“模擬血緣關(guān)系”。[6]換言之,日本家族在選定繼承人時首先需要考慮的不是候選人的血統(tǒng),而是能力。在歌舞伎界,為了能使家業(yè)不至凋敝?jǐn)÷洌鞔笫兰以诶^承人選拔方面并不一味追求血統(tǒng)的絕對純正,將外形出挑、潛質(zhì)優(yōu)良的孩子收為養(yǎng)子,或者以招婿上門的方式把堪當(dāng)大任的人才以婿養(yǎng)子的身份吸納到家族內(nèi)部,這在二戰(zhàn)前是業(yè)界的通用做法。以市川團(tuán)十郎家族為例,二世市川團(tuán)十郎就將養(yǎng)子升五郎選定為家業(yè)繼承人,九世也因沒有男性子嗣而把家中事務(wù)托付給女婿市川三升,其后繼承家業(yè)的十一世也是養(yǎng)子出身。如果將血緣作為能否繼承家業(yè)的必要條件,那么市川家族恐怕也會早早止步于二世,就不會出現(xiàn)日后穩(wěn)居歌舞伎界頂端的“市川宗家”了。
“模擬血緣關(guān)系”的成立,給歌舞伎世家的傳承帶來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在選拔繼承人這一問題上不“唯血緣”,而是在更廣泛的范圍內(nèi)擇優(yōu)選用,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家族敗落的悲劇發(fā)生,最大限度保證了家業(yè)的延續(xù)。總而言之,選賢用能、維系家業(yè)是各大歌舞伎世家的終極目標(biāo),因此“能者居之”一直是選定繼承人的重要原則。
有鑒于此,歌舞伎界一直被世人劃歸到“實(shí)力主義”的陣營,但不能否認(rèn)的是,歌舞伎畢竟脫胎于充斥著世襲制和身份等級制度的江戶時代日本社會,從誕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了國家和時代的烙印。日本的世襲制由來已久,從平安時代開始已經(jīng)有公家世襲擔(dān)任某種特定官職的制度,史稱“官司請負(fù)制”,這一制度在鐮倉及室町時代得到進(jìn)一步鞏固和發(fā)展。進(jìn)入武家社會后,雖然公家大權(quán)旁落,但等級細(xì)化程度卻愈來愈高。從攝關(guān)到一般官吏都是按照家族、家格的等級來任命的,由上至下分別是:攝關(guān)家、清華家、大臣家、羽林家、名家和半家,這些家族也成為明治維新后華族的前身。由于家格始終不變,依據(jù)家格高低所能擔(dān)任的職位自然也不會變。在這種情況下,出身低家格的人,無論能力如何突出,也不可能擔(dān)任超出家族等級的官位,世襲制成為日本社會穩(wěn)定的基石。更為關(guān)鍵的是,天皇作為日本社會的最高權(quán)威和“總本家”,“萬世一系”世襲罔替,這深刻影響著日本歷史的任何一個階段,是日本世襲制的基本底色和根源所在。
世襲制滲透到日本社會的各個角落,雖然不唯血緣、接納才能出眾的養(yǎng)子和婿養(yǎng)子來繼承家業(yè)一直被視作是歌舞伎界“實(shí)力主義”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但不應(yīng)忽視的是,其前提是建立在“經(jīng)營共同體”——“家”的延續(xù)這一首要目標(biāo)之上的。換言之,為了“家”的延續(xù),世襲制可以暫時被舍棄,所謂的崇尚“實(shí)力主義”也僅僅是“家”的延續(xù)大框架下的“權(quán)宜之計”而已。一旦首要目標(biāo)發(fā)生變化,世襲制又會卷土重來,重新回到歌舞伎的世界當(dāng)中。
3 身份等級制度與歌舞伎
“家”的延續(xù)這一首要目標(biāo)為何會發(fā)生變化?剖析這一問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歌舞伎世家的延續(xù)與否,受到古代日本社會身份等級制度的深刻影響。
16世紀(jì)末,豐臣秀吉實(shí)行兵農(nóng)分離政策,武士身份得以真正確立。進(jìn)入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建立幕藩體制的同時,將社會劃分為“士農(nóng)工商”四個階層,身份等級制度和世襲制在法律上得以固化,自此階層的身份等級和所從事的職業(yè)被緊密捆綁在一起。當(dāng)然,歌舞伎界也不得不遵從國家法律,子承父業(yè)代代相傳。
在日本歷史上,從事藝術(shù)表演的人一直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在中世,藝人被劃歸“非人”。到鐮倉時代,初代將軍源賴朝發(fā)布政令設(shè)立機(jī)構(gòu)“彈左衛(wèi)門”管理“穢多”和“非人”。1603年,德川幕府成立。同年,日本出云地區(qū)的巫女阿國始創(chuàng)阿國舞蹈,歌舞伎開始萌芽。雖然歌舞伎誕生于江戶時代,但因德川幕府仍然沿用舊制,歌舞伎演員也同其他藝人一道被劃歸“彈左衛(wèi)門”管理。1673年,江戶歌舞伎創(chuàng)始人初代市川團(tuán)十郎襲名市川海老藏,歌舞伎進(jìn)入高速發(fā)展期。為了尋求社會地位的提升,團(tuán)十郎組織歌舞伎演員以源賴朝發(fā)布政令時歌舞伎還未出現(xiàn),理應(yīng)不適用該政令為由起訴到奉行所,最終判定團(tuán)十郎勝訴,歌舞伎演員才從“非人”的泥潭中解脫出來。雖然擺脫了“非人”的身份,但歌舞伎演員的社會地位并未得到實(shí)質(zhì)性的改變,世人仍然使用“河原乞丐”等蔑稱來稱呼歌舞伎演員。
一方面,嚴(yán)苛的身份等級制度帶來了職業(yè)世襲和階層固化,阻斷了歌舞伎與其他行業(yè)間的人員流動,另一方面,低下的社會地位也降低了其他階層人員進(jìn)入歌舞伎界的意愿。在這樣的雙重夾擊下,各大世家時刻面臨著因沒有適宜男丁繼承家業(yè)而導(dǎo)致家族消亡的危機(jī)。收養(yǎng)養(yǎng)子和接納婿養(yǎng)子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危機(jī),但又因?yàn)樯矸莸燃壷贫鹊南拗疲谔暨x養(yǎng)子和婿養(yǎng)子時留給歌舞伎世家的選擇并不多,更多情況下是將其他世家內(nèi)繼承家名無望的家庭成員吸納到自己家族中,因此這種流動也僅能看作是行業(yè)內(nèi)部的流動,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歌舞伎界與其他行業(yè)之間隔絕的基本狀態(tài)。福澤諭吉形容當(dāng)時的日本社會,“就好像日本全國幾千萬人民,被分別關(guān)閉在幾千萬個籠子里,或被幾千萬道墻壁隔絕開一樣,簡直是寸步難移”。[7]
綜上,森嚴(yán)的身份等級制度會隨時引發(fā)行業(yè)內(nèi)的人才短缺,而人才短缺是導(dǎo)致家業(yè)中斷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穩(wěn)居江戶歌舞伎界頂端的“市川宗家”為例,1704年二世市川團(tuán)十郎從父親手中繼承藝名,完成了歌舞伎藝術(shù)有史以來的首次襲名。1727年二世團(tuán)十郎又將家名傳給了養(yǎng)子升五郎,可惜升五郎在襲名之后不幸染病,22歲就撒手人寰。由于當(dāng)時市川宗家內(nèi)部并沒有繼承家業(yè)的合適人選,因此在三世團(tuán)十郎去世后的第12年,市川宗家才將二世松本幸四郎收為養(yǎng)子,并允許其襲名四世團(tuán)十郎繼承家業(yè)。傳承到九世時,家族內(nèi)部又遇到了家業(yè)無人繼承的難題。無奈之下,只得由九世的女婿市川三升暫管家中事務(wù)并積極尋找繼承人,終于在1940年將七世松本幸四郎的長子收為養(yǎng)子承襲家業(yè),家族才得以延續(xù)。由此可見,即便是高高在上的“市川宗家”,歷史上也幾次三番受到后繼無人的困擾,其他世家的境況就可以推想一二了。
明治維新后,政府雖然明文規(guī)定實(shí)行“四民平等”制度,一定程度上打通了階層流通的路徑,然而長期根植于日本社會深層的身份等級觀念并沒有立刻隨之消失。有研究指出:“皇族、華族、士族、平民四種新的身份取代了江戶時代的士農(nóng)工商,并在‘四民平等’的招牌下繼續(xù)演繹著新的身份差別。”[8]從明治時代到二戰(zhàn)結(jié)束,雖有二世市川左團(tuán)次在1928年訪蘇公演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出現(xiàn),但歌舞伎演員的社會地位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經(jīng)濟(jì)窘迫、生活困難。三世中村翫右衛(wèi)門回憶自己在1920年通過名題考試正式襲名時說:“按照事先約定,費(fèi)用都是由大谷社長出的。”[9]大谷竹次郎正是日本松竹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松竹公司是目前日本最大的綜合性民營娛樂集團(tuán),經(jīng)營范圍橫跨電影、戲劇和音樂領(lǐng)域,在歌舞伎商業(yè)演出市場中占據(jù)壟斷地位。松竹公司的商業(yè)運(yùn)作是戰(zhàn)后歌舞伎界世襲現(xiàn)象加劇的另一個推手。
4 松竹公司的商業(yè)運(yùn)作與歌舞伎
日本的近代劇場與近世劇場的最大區(qū)別就在于其經(jīng)營是否是商業(yè)行為。[10]松竹公司較早實(shí)現(xiàn)了劇場運(yùn)營的商業(yè)化,而商業(yè)化運(yùn)營直接推動了松竹公司在經(jīng)營空間、演員吸納方面絕對優(yōu)勢的確立。
1890年代,松竹公司從經(jīng)營京都新京極的歌舞伎座、明治座、夷谷座和大黒座、布袋座這5家劇場起步,通過兼并收購其他劇場的方式迅速擴(kuò)張商業(yè)版圖,僅僅花費(fèi)了不足20年時間就將勢力從京都、大阪發(fā)展到東京。1913年,松竹公司拿下了東京歌舞伎殿堂——歌舞伎座的直營權(quán),標(biāo)志著其在首都圈歌舞伎商業(yè)演出市場中強(qiáng)勢地位的確立。時至1920年代,首都圈的演出市場形成了松竹公司、帝國劇場和市川座三足鼎立的態(tài)勢。1928年和1929年,松竹公司先后實(shí)現(xiàn)了旗下東京、大阪地區(qū)劇場的股份制改革,完成了藝術(shù)經(jīng)營的近代化。
演出空間的持續(xù)擴(kuò)張加速了松竹公司在歌舞伎商業(yè)演出市場一家獨(dú)大局面的形成,嚴(yán)重擠占了其他經(jīng)營者的生存空間,引發(fā)了行業(yè)內(nèi)激烈的資源爭奪戰(zhàn)。1917年,松竹公司與根岸興行部劇團(tuán)圍繞歌舞伎演員市川松蔦是否出演該劇團(tuán)演出的問題發(fā)生紛爭,其結(jié)果是,松竹公司逐步改變以往口頭邀約演員演出的方式,改為與演員簽訂專屬合同,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了歌舞伎演員對松竹公司的依附關(guān)系。其后雖偶有1920年二世市川猿之助脫離松竹另立春秋座舉辦演出,及1936年十一世市川團(tuán)十郎加入東寶劇團(tuán)等事件發(fā)生,但最終都以演員發(fā)展不順不得以重回松竹公司而告終,這些都反映出其堅固的壟斷地位并未發(fā)生動搖。
松竹公司的商業(yè)運(yùn)作推動了其在歌舞伎演出空間和演員吸納方面絕對優(yōu)勢的形成,而演出空間和演員吸納方面的絕對優(yōu)勢又反過來為松竹公司的商業(yè)運(yùn)作加足了馬力,前者與后者形成了閉合的邏輯利益鏈條。這一方面削弱了歌舞伎世家在處理諸如家族繼承等事務(wù)方面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將家族利益緊密捆綁在松竹公司的商業(yè)利益之上。因此,當(dāng)世襲制符合雙方利益時,那么它的確立就順理成章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日本國內(nèi)進(jìn)入經(jīng)濟(jì)大蕭條,戰(zhàn)時劇場內(nèi)觀眾爆滿的盛況一去不復(fù)返,加之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入侵,歌舞伎等傳統(tǒng)藝能演出市場經(jīng)營受困。為應(yīng)對新形勢,松竹公司開展多種經(jīng)營,將上演歌舞伎無法盈利的傳統(tǒng)劇場轉(zhuǎn)型成為演出新派戲、喜劇、家庭劇、小品以及電影的新興劇場。在歌舞伎的低潮期,松竹公司仍舊看好未來市場潛能,以多種形式給予補(bǔ)貼,為歌舞伎界保留了基礎(chǔ)力量。二戰(zhàn)結(jié)束后,松竹公司推動歌舞伎于1960年和1961年分別實(shí)現(xiàn)了訪美、訪蘇公演。1950—1960年代,日本電影界出現(xiàn)了一股“忠臣藏”熱潮,松竹公司順勢推出了由歌舞伎演員主演的《忠臣藏 花之卷·雪之卷》(1954)《大忠臣藏》(1957)兩部電影,把他們推向更廣闊的領(lǐng)域。1985年4月,松竹公司為十二世市川團(tuán)十郎舉辦了襲名公演,掀起了新一輪歌舞伎熱潮。在松竹公司的商業(yè)運(yùn)作下,歌舞伎世家的“家”延續(xù)危機(jī)中的經(jīng)濟(jì)因素影響逐步減弱,演出收益也穩(wěn)步攀升,因此讓有直接血緣關(guān)系的后代繼承家業(yè)成為上佳選項(xiàng)。與此同時,襲名公演已經(jīng)成為帶動歌舞伎演出票房的絕佳賣點(diǎn),“歌舞伎(松竹)以襲名盈利,寶冢以退團(tuán)盈利”[11],而祖孫三代或者父子兩代同時襲名能夠瞬間抓住公眾眼球,保證上座率,為松竹公司博取最大經(jīng)濟(jì)利益。由此,松竹公司和歌舞伎世家在世襲制上達(dá)成了利益共同點(diǎn)。
時至21世紀(jì),日本開始實(shí)施的國家層面的文化振興戰(zhàn)略,推動了歌舞伎藝術(shù)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2001年日本制定了《文化藝術(shù)振興基本法》,就是這部法律將1990年代提出的“文化振興”說法改為“文化藝術(shù)振興”,擴(kuò)大了對文化概念的解釋,顯示了對文化振興認(rèn)識的深刻。[12]國家對藝術(shù)的重視為歌舞伎行業(yè)插上了起飛的翅膀,除了可觀的經(jīng)濟(jì)收入之外,隨之發(fā)生巨變的,還有歌舞伎演員的社會地位。十五世片岡仁左衛(wèi)門、二世中村吉右衛(wèi)門、七世尾上菊五郎等人被認(rèn)定為“人間國寶”,令和元年,五世坂東玉三郎與諾貝爾化學(xué)獎得主吉野彰等人一起獲得日本文部科學(xué)省授予的“文化功勞者”稱號,這些都彰顯了歌舞伎演員今非昔比的社會地位。
掙脫了身份等級制度枷鎖的歌舞伎界,在國家政策的扶持和松竹公司的商業(yè)運(yùn)作下,全行業(yè)風(fēng)生水起,展現(xiàn)出旺盛的生命力。各大世家不僅贏得了極高的社會聲譽(yù),也擁有了與之匹配的經(jīng)濟(jì)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家”的延續(xù)已經(jīng)不再是歌舞伎世家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了,加之戰(zhàn)后各大世家子嗣綿延,家族的首要目標(biāo)悄然發(fā)生變化,世襲制自然也就“死灰復(fù)燃”重新回到歌舞伎的世界當(dāng)中了。
5 結(jié)語
卡爾·科恩說:“平等在民主中處于核心地位。”[13]在亞洲民主國家日本出現(xiàn)諸如歌舞伎界這樣以血緣和家族作為重要標(biāo)準(zhǔn)的世襲制無疑是不平等的,也是違背全社會民主化的大趨勢的。然而,通過縱向梳理日本社會的歷史文化因素不難發(fā)現(xiàn),脫胎于江戶時代的歌舞伎自始至終都無法脫離家族制度和身份等級制度的影響,戰(zhàn)前展現(xiàn)出來的所謂的“實(shí)力主義”不過是“家”的延續(xù)這一首要目標(biāo)下的“權(quán)宜之計”而已。加之在歌舞伎領(lǐng)域深耕多年的松竹公司成功的商業(yè)運(yùn)作,為該行業(yè)貼上了名利雙收的醒目標(biāo)簽,成功將世家子弟留在了行業(yè)內(nèi)部。因此,戰(zhàn)后世襲制的回潮不是偶然,而是古代日本社會歷史文化因素在當(dāng)代的“重現(xiàn)”。令和開啟,新冠疫情下歌舞伎界何去何從,是值得世界關(guān)注的重大課題。
注釋:
① “日本藝能實(shí)演家團(tuán)體協(xié)議會”成立于1965年,由影視演員、歌手、舞蹈演員、傳統(tǒng)藝能演員等組成。目前受日本文化廳委托負(fù)責(zé)版權(quán)的集中管理、從業(yè)人員的扶持和行業(yè)現(xiàn)狀調(diào)查研究及政策建言等工作,相當(dāng)于日本的演出行業(yè)協(xié)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