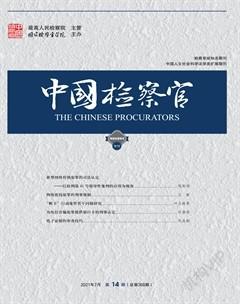新型網(wǎng)絡(luò)傳銷犯罪的司法認定
鄒利偉
摘 要: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來臨后,新型網(wǎng)絡(luò)傳銷成為傳銷活動的主流,且發(fā)展態(tài)勢迅猛。最高人民檢察院第41號指導(dǎo)性案例對于辦理新型網(wǎng)絡(luò)傳銷案件具有很強的指導(dǎo)意義。在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的客觀構(gòu)成要件特征認定上應(yīng)堅持實質(zhì)判斷的原則,在主觀構(gòu)成要件特征的認定上應(yīng)準確區(qū)分主觀故意與違法性認識,同時應(yīng)通過把握騙取財物的本質(zhì)特征區(qū)分金融創(chuàng)新與傳銷犯罪。
關(guān)鍵詞:新型網(wǎng)絡(luò)傳銷 實質(zhì)判斷 騙取財物
傳銷犯罪活動逐步經(jīng)歷了傳銷經(jīng)營,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wù)為名的欺詐式傳銷,傳銷標的虛擬化、金融化的新型網(wǎng)絡(luò)傳銷等不同階段。自2010年以來,各種傳銷組織依托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利用現(xiàn)代信息通訊工具,借助網(wǎng)站、應(yīng)用程序、第四方支付、充值及跑分平臺等網(wǎng)絡(luò)黑灰產(chǎn)業(yè),大肆進行網(wǎng)絡(luò)傳銷。傳銷組織緊跟當前社會熱點,以“區(qū)塊鏈”“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云經(jīng)濟”等概念進行包裝炒作,借助合法成立的公司,尋求專家、社會名流背書,網(wǎng)絡(luò)消費返利、原始股、虛擬幣、微商、廣告返利、慈善互助等各種網(wǎng)絡(luò)傳銷形式、類型層出不窮,呈現(xiàn)井噴式爆發(fā)的態(tài)勢。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fā)的第41號指導(dǎo)性案例葉經(jīng)生等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案,對于準確區(qū)分金融創(chuàng)新與網(wǎng)絡(luò)傳銷,依法認定犯罪具有極強的司法運用指導(dǎo)價值。
一、檢例第41號指導(dǎo)性案例:基本案情與爭議焦點
2011年6月,葉經(jīng)生等人注冊成立了上海寶喬網(wǎng)絡(lu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喬公司”),并開發(fā)了“金喬網(wǎng)”網(wǎng)上商城。同年11月,葉青松加入寶喬公司并擔任浙江省總代理。葉經(jīng)生等人通過招商會或論壇等形式宣傳、推廣“金喬網(wǎng)”的經(jīng)營模式。“金喬網(wǎng)”在全國各地設(shè)立省市縣三級區(qū)域代理,享受本區(qū)域內(nèi)保證金和購物消費業(yè)績累計計酬。經(jīng)銷商會員注冊必須經(jīng)上線經(jīng)銷商會員推薦并上交保證金,發(fā)展下線經(jīng)銷商可獲得推薦獎金。在商城“消費”的消費額可參與商城的雙倍返利。截止案發(fā),“金喬網(wǎng)”共發(fā)展會員3萬多人,涉及資金1.5億余元。
檢察機關(guān)以被告人葉經(jīng)生、葉青松犯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向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葉經(jīng)生、葉青松及其辯護律師則辯稱被告人經(jīng)營的“金喬網(wǎng)”屬于金融創(chuàng)新,來源于某教授的理論,消費款、保證金不屬于傳銷活動的入門費,會員之間也不存在層級關(guān)系,更沒有以人數(shù)計酬,“金喬網(wǎng)”的經(jīng)營模式不屬于傳銷;主觀上也從未意識到從事電子商務(wù)是傳銷行為,不存在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的故意。“金喬網(wǎng)”的經(jīng)營模式是否符合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的客觀構(gòu)成要件特征,兩被告人主觀上有無非法傳銷的故意是本案的爭議焦點。
公訴人提交了寶喬公司工商登記資料、銀行賬戶明細、勘驗檢查筆錄、電子數(shù)據(jù)、寶喬公司工作人員證言、參與傳銷人員證言、鑒定意見等證據(jù),并由鑒定人員出庭作證,證實兩被告人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的事實。在庭審答辯中,公訴人提出應(yīng)以穿透式的司法方法對本案進行實質(zhì)判斷。最終,法院以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對兩被告定罪處罰。
二、展開實質(zhì)審查:客觀構(gòu)成要件特征的具體認定
葉經(jīng)生等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案在“指導(dǎo)意義”中指出,無論其表現(xiàn)形式如何變化、手段如何翻新,都要牢牢把握本罪的本質(zhì)特征。這實際上提煉出了針對新型網(wǎng)絡(luò)傳銷的實質(zhì)判斷的司法方法。而“指控與證明”部分公訴人答辯“本質(zhì)系入門費”“本質(zhì)為設(shè)層級”“本質(zhì)為拉人頭”則為實質(zhì)判斷的具體展開提供了實踐路徑。具體而言:
(一)入門費的判斷:“名”的泛化與循“名”責“實”
傳統(tǒng)的線下傳銷,是以有形的商品或者服務(wù)作為傳銷的標的。進入新型網(wǎng)絡(luò)傳銷時代,傳銷的對外名義進一步泛化,不再僅僅局限于傳統(tǒng)的商品、服務(wù),而表現(xiàn)為一種意定權(quán)利或虛擬標的,比如虛擬幣、原始股、積分等。刑法第224條之一規(guī)定的“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wù)等”中的“等”應(yīng)作等外等的理解。葉經(jīng)生等人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一案,是以繳納保證金開立網(wǎng)上商鋪、繳納10%消費款讓渡經(jīng)營利潤為名義繳納入門費。
不管以什么名義,如果參與人繳納費用在于獲取發(fā)展下線的資格,不關(guān)注標的的實際價值,即使不屬于商品、服務(wù),也可以判斷為入門費。該案中,公訴人指出上交保證金才有資格享受推薦獎金,繳納10%消費款才可能有返利收益,實質(zhì)上就是入門費。是否是入門費的判斷關(guān)鍵不在于對外的名義,而在于表面的名義下是否有實質(zhì)的內(nèi)容,若名實不符,循“名”無法責“實”,則應(yīng)揭開“名”的面紗,進行“實”的判斷。該案中,僅有“保證金”“商家讓利”之名,而無保證金、商家讓利之實,實質(zhì)為入門費。
(二)設(shè)層級的判斷:代數(shù)關(guān)系與層級獲利
實踐中,有些不法分子為了規(guī)避法律,在傳銷活動中,不再對內(nèi)部的人員設(shè)定身份或者區(qū)分等級,上線和下線之間并沒有明顯的身份等級差別,只有加入傳銷組織時間先后的區(qū)別。對層級關(guān)系的理解,要注意對層級的認定不能局限于傳銷組織自身的身份或者等級設(shè)定,而要靈活理解和把握立案標準,只要客觀上存在上下線關(guān)系,且參與人從發(fā)展的下線或者下下線中獲取收益,就要認定層級關(guān)系。這也體現(xiàn)了實質(zhì)判斷的司法方法。
本案中,公訴人舉證證實會員層級呈現(xiàn)塔狀的形態(tài),一共68層,獎金以不限制代數(shù)的方式計算,上線成員可通過下線、下下線成員發(fā)展成員獲取獎金。上線的人員能夠借助下線、下下線成員的加入獲得利益,并按照一定的結(jié)構(gòu),即普通會員、股權(quán)會員以及區(qū)域代理進行層級的設(shè)定,實際為設(shè)層級。
該案上下級經(jīng)銷商會員的層級關(guān)系體現(xiàn)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經(jīng)銷商會員存在上下代的關(guān)系,上代的經(jīng)銷商會員可以拿到下代的經(jīng)銷商會員的業(yè)績獎金,但會員之間沒有級別之分,只有代數(shù)的區(qū)別,即有代數(shù)無級別;第二種情況是既有代數(shù)區(qū)別,又存在級別關(guān)系,如“金喬網(wǎng)”內(nèi)部會員分為一般會員、股權(quán)會員、區(qū)域代理等級別。
(三)拉人頭的判斷:瓜分下線與人數(shù)計酬
獎金或者返利的多寡取決于下線、下下線參加人員的多少,這是傳銷“拉人頭”的特征。網(wǎng)絡(luò)傳銷不會創(chuàng)造任何經(jīng)濟利益,組織者、參與者的收益全部來源于傳銷人員投入的資金,實際上是上線瓜分下線資金的圈錢游戲,先加入人員獲得的利益來源于后加入者向傳銷組織上交的入門費。
拉人頭計酬分為兩種情形:一是直接以發(fā)展人員的數(shù)量作為計酬依據(jù)。二是表面上是以銷售業(yè)績作為計酬依據(jù),實質(zhì)上仍屬于“以發(fā)展人員的數(shù)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jù)”。葉經(jīng)生等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案中公訴人答辯也指出,推薦的人數(shù)作為發(fā)放傭金的依據(jù)系直接以發(fā)展的人員數(shù)量作為計酬的依據(jù);后加入人員的數(shù)量直接決定了某個區(qū)域整體業(yè)績和返利數(shù)額,本質(zhì)上就是以發(fā)展成員數(shù)作為獎金發(fā)放的標準,本質(zhì)上仍為拉人頭。
三、厘清故意與違法性認識:主觀構(gòu)成要件特征的準確判斷
本案兩被告人均辯解沒有認識到“新型電子商務(wù)”屬于傳銷,公司的創(chuàng)意來源于某教授的某種理論,兩人也特意請教了律師,招商會上當?shù)卣藛T也予以支持,沒有犯罪的主觀故意。筆者認為,對上述辯解,應(yīng)當通過準確區(qū)分構(gòu)成要件故意與違法性認識進行審查判斷。
(一)故意認識因素的內(nèi)涵
構(gòu)成要件故意是指行為人認識到了某一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情節(jié),仍意欲或放任其發(fā)生。認識包括感官上的感知和思想上的理解。構(gòu)成要件要素既有描述的要素,也有評價的要素,前者為記述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后者為規(guī)范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1] 記述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側(cè)重于感官上的感知,規(guī)范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則需要思想上的進一步理解。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的構(gòu)成要件情節(jié),如入門費、設(shè)層級、拉人頭等具體特征,屬于規(guī)范的構(gòu)成件要素,要求行為人在思想觀念上能夠理性把握。
(二)思想上理解不等于違法性認識
思想上理解并不要求精準的法律概念分類,后者屬于涵攝錯誤,屬于違法性認識的內(nèi)容。[2] 即不要求行為人精確地判斷該行為是傳銷活動,只要行為人在一般的社會意義上理解到交了錢才能獲得返利或回報的資格,不同的人在整個組織中有著上下線關(guān)系,參與人通過發(fā)展下線能夠獲得利益,且參與的人員越多獲利越多等,不管行為人是不是將其判斷為傳銷行為,都要認定存在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的故意。
在具有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故意的情形下,對具體活動是否為國家法律允許沒有認識或認識有誤,則屬于違法性認識錯誤。本案中,公訴人通過訊問以及舉證證明了兩被告人對于入門費、設(shè)層級、拉人頭等與一般人對傳銷的理解是相符的,從而證實了主觀上系故意。兩被告人辯解沒有認識到“新型電子商務(wù)”屬于傳銷,不知道國家不允許,不妨礙主觀故意的認定。
(三)違法性認識錯誤能否避免的認定
對于違法性認識,原則上遵循的是“不知法律不免責”。克勞斯·羅克辛教授在違法性認識錯誤能否避免的具體判斷上提出了三項基準,即行為人有無對行為的合法性產(chǎn)生懷疑、其所從事行為所在領(lǐng)域的特殊性以及行為對法益的威脅程度。[3] 具體來說,如果當事人在對行為是否合法有懷疑的情形下,仍抱著僥幸的心理,則應(yīng)當認為其存在過錯。對于領(lǐng)域的特殊性而言,不同的領(lǐng)域有著不同的法規(guī)范密度及特殊規(guī)制規(guī)則,密度越大、規(guī)則越特殊,注意義務(wù)越高。而當一個行為可能會對公共利益及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法益造成威脅或侵害時,行為人的審慎義務(wù)也越高。
對于網(wǎng)絡(luò)傳銷犯罪的違法性認識錯誤是否可以避免,可以進行如下判斷:網(wǎng)絡(luò)傳銷犯罪多打著“金融創(chuàng)新”的旗號,說明行為人認識到其行為處于金融的特殊領(lǐng)域,而在該領(lǐng)域內(nèi),國家法規(guī)范的密度大大超過一般的民事、商事領(lǐng)域,且有著不同于一般領(lǐng)域的特殊法規(guī)范。再者,網(wǎng)絡(luò)傳銷行為涉及人員眾多,涉及資金數(shù)額龐大,稍有不慎都會對公眾的資金安全帶來威脅。在葉經(jīng)生等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案中,被告人葉青松在供述中也稱其對公司能否兌付資金及合法與否有著巨大的擔憂。綜合以上幾點,可以認為葉經(jīng)生、葉青松等人的違法性認識錯誤是可以避免的。
四、界定金融創(chuàng)新與網(wǎng)絡(luò)傳銷:騙取財物本質(zhì)特征的區(qū)分把握
新型網(wǎng)絡(luò)傳銷打著“金融創(chuàng)新”的旗號,傳銷組織多以合法成立的公司面目出現(xiàn),以熱點概念進行包裝,迷惑性強,識別難度大。歸案后,犯罪分子多辯解其行為系經(jīng)濟創(chuàng)新活動。辦案人員如何準確界定金融創(chuàng)新還是網(wǎng)絡(luò)傳銷,應(yīng)當通過牢牢把握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的本質(zhì)特征予以認定。
(一)騙取財物的內(nèi)涵
騙取財物是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的本質(zhì)特征。[4] 但如何認定騙取財物,則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騙取財物是對行為性質(zhì)的詮釋,我國刑法中有多處涉及“騙”的罪名,詐騙罪、集資詐騙罪都有類似“騙取財物”的規(guī)定,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中的騙取財物應(yīng)與詐騙犯罪作相同的理解。但筆者認為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中騙取財物的界定,是為了區(qū)分經(jīng)營性傳銷與欺詐性傳銷,不同于詐騙罪中的“騙”,它不是對行為的界定,不要求具有詐騙的特殊構(gòu)造,而是對整個傳銷組織的界定。
實際上,傳銷活動分為兩種,一種是經(jīng)營性傳銷,傳銷只不過是銷售貨物、提供商品的一種營銷手段,發(fā)生了真實的買賣關(guān)系,即《禁止傳銷條例》第7條第3項中規(guī)定的團隊計酬行為。另一種是欺詐性傳銷,沒有實實在在的商品交易內(nèi)容,出售商品、提供服務(wù)只是外在的名義,購買商品的人實際上也不關(guān)心是否物有所值,參加傳銷的目的是從他人繳納的入門費中獲取收益。經(jīng)營性傳銷仍然有貨物或商品的交易,參與經(jīng)營性傳銷人員的獲利仍然來源于銷售行為。欺詐性傳銷歸根結(jié)蒂是龐氏騙局,本身不會創(chuàng)造任何經(jīng)濟價值。因此,我國刑法在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中以“騙取財物”對傳銷活動進行限定,其目的在于縮限打擊范圍,將經(jīng)營性傳銷排除在外。
(二)將騙取財物作為金融創(chuàng)新與網(wǎng)絡(luò)傳銷的根本區(qū)分標準
公司是最基本的市場細胞,在整體的社會分工、市場經(jīng)濟運行中承擔基礎(chǔ)的作用,會創(chuàng)造經(jīng)濟效益、社會效益。而傳銷行為沒有實質(zhì)的經(jīng)營活動,不會創(chuàng)造價值,傳銷活動不具有可持續(xù)性。傳銷組織收取的下線資金并沒有參與到整體的市場經(jīng)營中,而是作為傭金或返利被層層盤剝,且主要為高層級人員所獲取,上線的經(jīng)濟來源系后加入者繳納的入門費。
本案在“指導(dǎo)意義”中明確揭示了傳銷犯罪的本質(zhì),即沒有創(chuàng)造任何經(jīng)濟或社會價值,其組織、運營方式不具有可持續(xù)性,先加入者的收入來源于后加入人員的入門費,通過不斷發(fā)展人員謀取利益從而騙取財物。這一本質(zhì)特征為我們區(qū)分金融創(chuàng)新與網(wǎng)絡(luò)傳銷提供了基本的區(qū)分標準。圍繞這一本質(zhì)特征,審查判斷涉案企業(yè)有無實質(zhì)經(jīng)營活動,有無創(chuàng)造經(jīng)濟價值,抑或只是披著“金融創(chuàng)新”的外衣。本案公訴人在答辯中也指出,寶喬公司沒有實質(zhì)性的經(jīng)營行為,沒有創(chuàng)造經(jīng)濟價值,實際用后參加人員繳納的費用兌付先加入人員的獎金和返利,人員不可能無限增加,資金鏈必然斷裂。寶喬公司的“經(jīng)營行為”就是從后加入人員上交的財物中謀取自己的非法利益,體現(xiàn)了傳銷活動騙取財物的本質(zhì)。
(三)區(qū)分金融創(chuàng)新與網(wǎng)絡(luò)傳銷的具體方法
葉經(jīng)生等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案的辦理,還為司法實踐如何把握本質(zhì)特征區(qū)分合法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與非法傳銷組織提供了具體方法。在案件審查中,要注意針對傳銷網(wǎng)站的經(jīng)營特征與其他合法經(jīng)營網(wǎng)站的區(qū)別,重點收集企業(yè)資金投入、人員組成、資金來源去向、網(wǎng)站功能等方面的證據(jù),揭示傳銷犯罪的本質(zhì)特征。
合法的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會以巨額的資金投入建立其經(jīng)營規(guī)模匹配的電子商務(wù)系統(tǒng);招募配備大量專業(yè)的服務(wù)、技術(shù)、監(jiān)管、推廣人員;資金來源于企業(yè)正常經(jīng)營收入,并用于企業(yè)正常運轉(zhuǎn)及擴大經(jīng)營規(guī)模;網(wǎng)站功能齊全、系統(tǒng)設(shè)置合理,軟硬件均能符合新型電子商務(wù)的技術(shù)需求。而傳銷組織全部人財物的安排及主要活動都是緊緊圍繞引誘群眾繳納入門費,通過夸大宣傳發(fā)展下線、下下線,從中非法謀取不法利益展開。葉經(jīng)生等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一案,公訴人通過舉證證實了“金喬網(wǎng)”投入的資金300余萬元,沒有建立與其宣傳匹配的電子商務(wù)系統(tǒng);公司沒有匹配與之電子商務(wù)系統(tǒng)相應(yīng)的售后服務(wù)人員、系統(tǒng)運營及維修人員、市場推銷人員和監(jiān)督管理人員,公司的員工從事的主要是欺騙公眾,收取入門費和發(fā)放獎金、返利,而公司從中牟利。其網(wǎng)站功能過于簡單,系統(tǒng)配置簡陋,完全不符合新型網(wǎng)絡(luò)商城的標準。進而公訴人在發(fā)表公訴意見中指出,寶喬公司所有人事、財物的設(shè)置都圍繞著如何欺騙公眾繳納入門費,其從中獲取不法利益,本質(zhì)上是通過合法公司的外衣,以電子商務(wù)、金融創(chuàng)新的幌子騙取財物。
*浙江省麗水市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323050]
[1] 參見[德]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刑法總論教科書》,蔡桂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頁。
[2] 參見 [德]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頁。
[3] 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頁。
[4] 參見陳興良:《組織、領(lǐng)導(dǎo)傳銷活動罪:性質(zhì)與界限》,《政法論壇》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