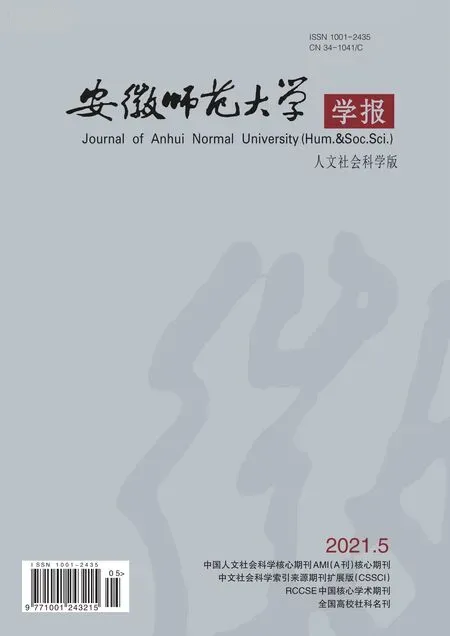“王右丞體”的詩學內涵與佛學淵源*
張 勇
(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安徽蕪湖 241000)
一、引 言
“體”是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范疇,具有豐富的內涵。羅根澤將其分為兩類,一是體派,即風格,如元和體、西昆體、李長吉體、李義山體等;二是體類,即體裁,如詩體、賦體、論體、序體等。[1]150羅宗強也將其分為兩類,一是體裁,二是體貌,后者包括“某一位作者作品之體貌特征”。[2]羅宗強所謂“體貌”與羅根澤所謂“體派”意思相同,都是指文學作品的風格,兩位先生也都把“以人而論”之“體”歸為此類。這一觀點得到學界的普遍贊成。本文也是在“風格”意義上討論“王右丞體”概念。
作為“以人而論”之“體”,“王右丞體”應具備三個基本特征。一是獨特性,其內涵應為王維詩所特有或在王維詩上表現得最為突出或由王維首創而后被發揚光大。二是多樣性,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來看,其內涵具有不同的表現。三是普遍性,在這多樣性表現的背后有一個共同的、普遍的、穩定的風貌特征,此特征為不同題材、不同意境的王維詩所共有,不會因為表現內容的改變而改變。
從目前來看,關于王維詩風的研究多如恒河沙數,而對“王右丞體”的專題探討卻寥若晨星,關于其定義,姑舉兩例:
王右丞體指王維詩體。……其主要作品為田園山水詩,體物精細、描寫傳神,悠閑自適,富有禪趣,成為唐代田園山水詩的代表人物。[3]703
王右丞體,盛唐詩人王維的詩歌體制風格。……王詩題材、詩風多種多樣,尤擅以五言詩形式寫山水田園風光和隱逸情趣,意境優美,韻味醇厚,語言清麗,音調和諧,往往熔詩情、畫意、音樂美于一爐,風格以清腴自然、明麗秀逸為主。[4]689-690體裁多為五言,題材多為山水田園風光,意境閑適優美,風格清腴秀逸,這可謂當前“王右丞體”的“典型性”定義。顯然,此定義是從山水田園詩的角度下的,傳達出了王維部分山水田園詩的風格特征。問題是,王維詩并非僅有山水田園題材,還有大量送別贈答、應制奉和、游俠邊塞等題材,這些題材的詩也有很多膾炙人口的名篇,可與山水田園詩平分秋色,因此僅以山水田園詩為范例來定義“王右丞體”,難免以偏概全。即使只看山水田園題材,王維詩也不都是清淡玄遠一派,也還有相當數量的雄渾壯麗之作。從目前來看,關于“王右丞體”的詩學內涵問題似乎并未解決。
作為一個詩學概念,“王右丞體”提出于南宋,在以后的歷史長河之中被不斷闡釋、不斷豐富,因此要正確揭示其詩學內涵與生成根源,必須將其置于闡釋史中加以考量。
二、從“輞川體”到“王右丞體”
在“王右丞體”概念提出之前,人們早已開始了對王維詩風格的探討,如殷璠的“詞秀調雅”論[5]66,司空圖的“澄澹精致”論[6]196,蘇軾的“詩中有畫”論[7]2209,等等。從現有資料看,最早以“體”論王維詩者為南宋的朱熹。他提出“輞川體”概念。
王維裒集自己在輞川別業與詩友裴迪往來唱和的二十首田園詩,題為《輞川集》。這組詩,體裁全為五言絕句,詩題全為別業中的景物,所描繪的全為別業中的自然風光,所抒發的全為山林閑適之趣,整部《輞川集》具有一種淳古澹泊、清幽絕俗的風格特征。朱熹把這一特征稱為“輞川體”,并效法此體而作《家山堂晚照效輞川體作二首》:“夕陽浮遠空,西峰背殘照。爽氣轉分明,與君共晚眺”;“山外夕嵐明,山前空翠滴。日暮無與期,閑來岸輕幘”。[8]這兩首詩,體裁都為五言古絕,題材都為田園風光,都具有翛然清遠的風格特征,這是對《輞川集》的仿效,由此折射出朱氏對“輞川體”的理解。
朱熹之后,“效輞川體”作品層出不窮。明人胡應麟有《暇日效右丞輞川體為五言絕三十章》[9]622-624,清人樊增祥“仿右丞輞川詩體”而作《東溪詩》二十首[10]1-3,王相作《草堂雜詠擬輞川體》十首①王相《友聲集》“草堂雜詠”,清咸豐八年信芳閣刻本。,這些仿效“輞川體”之作,全為五絕,全是對自然風光的描摹,全以清幽淡遠為風格,在體裁、題材與風格等方面都與朱熹保持著高度一致,由此可見這些作者對“輞川體”內涵的心領神會。
再回頭看一下前文所引現代人對“王右丞體”的定義,它們非常接近朱熹等人所理解的“輞川體”,也就是說,現代人所定義的“王右丞體”其實僅代表了王維輞川詩及其近似者的風格特征,并不能代表王維詩的整體風貌。
繼朱熹提出“輞川體”后,嚴羽又提出“王右丞體”概念。他在《滄浪詩話·詩體》中說:“以人而論”有“王右丞體”。遺憾的是,嚴羽未對此概念作任何解釋。至明代,黃溥效仿嚴羽“因人名體”,又提出“摩詰體”概念[11]1041,同樣也未作解釋。“摩詰體”與“王右丞體”,都是“因人名體”,都著眼于王維詩的整體風格,二者是同等內涵的概念。
與“效輞川體”并行,明清時期也出現大量“效王右丞體”作品。如龔培序《秋居仿王右丞體》:“他鄉聊偃息,去住兩無心。閉戶讀書久,卷簾秋色深。酒逢開口笑,詩作掉頭吟。別有無言趣,臨風張素琴。”①龔培序《竹梧書屋詩稿》卷二,清康熙五十一年竹梧書屋刻本。又如張英《山居幽事戲擬右丞體三十首》[12]564-566,這三十首全是六言絕句,明顯是在仿效王維的《田園樂七首》。再如喻時《西樓歌》:“近帶兮覺山,遙連兮燕麓。日畿兮萬年,龍虎抱兮京轂……”[13]6446詩前小序曰“效摩詰體”,這是在仿效王維《登樓歌》等騷體詩。以上“效王右丞體”作品,或為五律或為六絕或為騷體,體裁多種多樣,這與同時期皆為五絕的“效輞川體”大不相同,題材、風格上也與之有很大差異。由此可見,在世人心目之中“王右丞體”與“輞川體”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就王維詩整體而言的,因此應該能包括后者,也應該比后者更具普遍意義。從目前研究來看,“輞川體”的內涵已經十分明確,而“王右丞體”之內涵仍處待發狀態。
三、“王右丞體”的整體風貌
盡管早在唐代人們就已經開始研究王維詩的風格特征,但對“王右丞體”內涵的集中探尋卻是在明清時期。此期,“辨體”之風盛行,出現了諸多“文體學”著作,如《文章辨體》《文章辨體匯選》等。在這一學術思潮影響之下,“王右丞體”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
率先對“王右丞體”作全面闡述者為明代的王世貞。他說:“凡為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傅合,渾融疏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14]1009他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指出“摩詰體”在意境、表達等方面的特征,突破了山水田園詩的范圍,而把視野拓展到整個王維詩。
明末清初,費經虞把“王右丞體”的闡釋又向前推進一步。其《雅倫》卷二《王右丞體》,匯集歷代闡釋“王右丞體”的資料:
盛唐王維之詩。殷璠云:“王維詩辭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為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徐伯臣云:“右丞詩發秀自天,感言成韻,辭華新朗,意象幽閑。上登清廟則情近珪璋,幽徹林野則理同泉石。言其風骨,固盡掃微波;采其流調,亦高跨來代。于《三百篇》求之,蓋《小雅》之流也。”敖器之云:“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蘇子瞻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陳后山云:“右丞、蘇州皆學陶,王得其自在。”顧華玉云:“王公得詩家之情。”②費經虞《雅論》卷二,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此段匯集從唐代殷璠至宋代蘇軾、陳師道、敖陶孫再到明代顧璘、徐獻忠等人對王維詩風格的經典論述,顯然是想從多角度詮釋“王右丞體”的內涵。費經虞還結合王維詩來論證“王右丞體”在不同層面的風格特征。如以《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為例論“典雅”,以《送李睢陽》為例論“深厚”,以《少年行》為例論“俊逸”,以《鳥鳴澗》《欹湖》《白石灘》《竹里館》《送元二使安西》為例論“清新”,以《藍田石門精舍》《山居秋暝》為例論“自然”,以《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積雨輞川莊作》為例論“淡遠”,以《華子岡》為例論“峻潔”等。
王世貞與費經虞等人對“王右丞體”的探討,已經大大超越了那些“王右丞體”的仿效之作與只言片語式的點評,而進入自覺的、全面的探討階段,表現出從局部到整體、從創作到批評、從感性到理性的變化。在此基礎之上,人們開始探討“王右丞體”更具超越性、普遍性、穩定性的整體風貌與特征。
翁方綱論王維詩說:“平實敘事者,三昧也;空際振奇者,亦三昧也;渾涵汪茫千匯萬狀者,亦三昧也。此乃謂之萬法歸原也。”[15]287王詩風格多種多樣,有“平實敘事”者,有“空際振奇”者,有“寂寥沖淡”者,有“渾涵汪茫千匯萬狀”者,而在這多樣風格的背后有一個“萬法歸原處”,即能夠涵蓋這一切外在表現的更具普遍意義的特征。那么,這個“萬法歸原處”是什么呢?翁方綱的答案是“三昧”。“三昧”是一個佛教術語,本意為禪定,指心定于一處而不散亂的精神狀態。翁氏用“三昧”來表達“王右丞體”的“萬法歸原處”,顯然與這個概念的原意無關。那么,他所謂“三昧”到底是指什么呢?
唐代以后,“三昧”一詞被南宗禪賦予了新內涵。惠能解釋“一相三昧”說:“于一切處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16]220把“三昧”定義為“不住相”,這是一種不執著于外在色相、不即不離、不粘不滯的“不二”境界。翁方綱正是在“不住相”這一意義上理解“三昧”的,在他看來,“不住相”是王維詩的“萬法歸原處”。
在評論王維《夷門歌》時,翁方綱直接點明了這個“萬法歸原處”。他說:“所謂‘羚羊掛角’‘不著一字’者,舉此一篇足矣。此乃萬法歸原處也。”[15]287“羚羊掛角”,禪林用語,比喻泯絕蹤跡、不著色相的境界。①如《景德傳燈錄》卷十六:“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什么處捫摸?”(《大正藏》第51冊,第328頁)“羚羊掛角”“不著一字”即“不住相”,翁方綱明確指出王維詩的“萬法歸原處”就在于此。
翁方綱后,清人張文蓀繼續探討“王右丞體”多樣性表現背后的“萬法歸原處”。與翁氏一樣,張文蓀也認為“王右丞體”的根本特征是“不住相”。他說:“雄快事說得安雅,是右丞詩體。”②張文蓀《唐賢清雅集》卷三,清乾隆三十年抄本。王維詩內容豐富,有的偏于“雄快”,有的偏于“安雅”,“王右丞體”之根本特色不是由這些內容決定的,而是由這些內容的表達方式決定的。張文蓀認為,只有把“雄快事說得安雅”——說“雄快”而不著“雄快”之相,才是“王右丞體”。這其實是說,“王右丞體”的根本特征是“不住相”。在評價王維《隴頭吟》時,張文蓀又說:“極凄涼情景,說得極平淡,是右丞家數。”③張文蓀《唐賢清雅集》卷一,清乾隆三十年抄本。本為“極凄涼情景”卻表現得“極平淡”,換言之,說“凄涼”而不著“凄涼”相,這才是“右丞家數”,即“王右丞體”的本質特征。錢鍾書論“文如其人”說:作家的創作個性不取決于“所言之物”,而取決于“言之格調”,因為“其言之格調,則往往流露本相”。[17]163張文蓀對“王右丞體”的解釋正合此意。總之,在張文蓀看來,不論“雄快”還是“安雅”,“凄涼”還是“平淡”,這些都是王維詩外在的、局部的特征,只有“不住相”才是王維詩的共性,才是“王右丞體”的“萬法歸原處”。
作為“王右丞體”的“萬法歸原處”,“不住相”是就審美構成而言的,若就審美感受而言,則表現為“渾厚”之風貌。胡仔說:“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18]257“渾厚”為“不住相”之果,“不住相”為“渾厚”之因,二者相依相存,融合共生。“王右丞體”之“渾厚”,也被闡釋者稱為“深厚”“溫厚”等。費經虞以《送李睢陽》為例解釋“深厚”說:“魯國規模,先秦冠服,不露鋒芒,夷然安簡,于此而思深厚焉。”④費經虞《雅倫》卷十六《品衡上》,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指出“王右丞體”之“深厚”根源于“不露鋒芒”。費氏又論王維詩之“溫厚”曰:“圓不加規,方不加矩。”⑤費經虞《雅倫》卷九《格式八》,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說“圓”而不著“圓”相,說“方”而不露“方”痕,故能給人“溫厚”之感。費氏深刻揭示了“王右丞體”之“厚”味與“不住相”之間的關系。
綜上所述,“王右丞體”的根本特征,表現于審美構成為“不住相”,表現于審美感受為“渾厚”,綜合這兩個方面,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渾厚無跡”。“無跡”,即“不住相”,也就是宋人張戒所說的“不露筋骨”⑥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蓋摩詰古詩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上冊,第460頁。。“渾厚無跡”是“王右丞體”的本質特征,是王維詩最具普遍性、穩定性的特征,它不因題材、體裁、意境的改變而改變。
四、“王右丞體”的多維表現
“渾厚無跡”是“王右丞體”的總體風貌,這一總體風貌在王維詩的感興、意境、情趣、結構、語言等方面均有鮮明體現。
(一)感興上,興會神到、不可湊泊
感興,是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范疇,指創作過程中情感的興起及創作沖動的產生。前引王世貞對“王右丞體”的解釋——“凡為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傅合,渾融疏秀,不見穿鑿之跡”,即是從感興角度而言的。“意興”,即感興。王世貞指出,王維的詩歌創作完全出于自然的靈感觸發,興會神到,情景渾融,毫無穿鑿痕跡。對此,王夫之也有精到見解:“意至則事自恰合,與求事切題者雅俗冰炭。右丞工于用意,尤工于達意。景亦意,事亦意,前無古人,后無嗣者,文外獨絕,不許有兩。”[19]101強調“王右丞體”在感興上的“渾厚無跡”特點以及此特點的獨一無二性。類似的闡釋還有,王士禛《帶經堂詩話》:“興來神來,天然入妙,不可湊泊”[20]518;徐獻忠《唐詩品》:“右丞詩發秀自天,感言成韻”[21]372;唐汝詢《唐詩解》:“偶然托興,初不著題模擬。”[22]702“興來神來”“發秀自天”“偶然托興”,都是強調“王右丞體”的興會神到、不可湊泊特點,與此相反者,則為王夫之所謂的“求事切題”、唐汝詢所謂的“著題模擬”。
(二)意境上,興象淡遠、不落聲色
方東樹論王維詩說:“尋其所至,只是以興象超遠,渾然元氣,為后人所莫及;高華精警,極聲色之宗,而不落人間聲色,所以可貴。”[23]387“興象超遠”“不落聲色”為“王右丞體”在意境上的特征。李東陽也有近似闡釋:“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24]1369“淡而遠”,近于佛家所謂的“不即不離”“是相非相”,如九方皋相馬,略其玄黃而獨取俊逸。王維詩,有的以“清遠”勝,有的以“雄渾”勝,意境雖然不同,但都具有興象淡遠、不落聲色的特征,因此被陸時雍贊為“雄渾而不肥,清瘦而不削”[25]384。“雄”而不臃腫,“清”而不瘦削,不著“雄”跡,不露“清”痕,因此給人“渾厚無跡”之感。
王維山水田園詩大都具有“幽靜”的意境,但從語句上絕看不出“幽靜”的痕跡。賀貽孫說:“王右丞詩境雖極幽靜,而氣象每自雄偉。”[26]172寫“幽靜”之境卻以“雄偉”氣象出之,從而避免粘著于“幽靜”之相,這才是“右丞家數”。王維很多詩句,如“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云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①《送邢桂州》《奉和圣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王維著,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本文所引王維詩均出自該書。,都是將幽靜之意寓于雄偉氣象之中,從而形成“王右丞體”鏡花水月般的幽遠詩境。
興象淡遠、不落聲色,并非山水田園詩所專有,王維其他題材的詩也是如此。如《敕賜百官櫻桃》: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才是寢園春薦后,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該詩描寫敕賜櫻桃場景,借以歌頌君恩隆厚。這本來是個“濃”而“近”的主題,作者卻寫得極為淡遠,似乎不帶任何感情色彩,雖處處頌贊,卻沒有半點頌贊的痕跡。五六兩句“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寫櫻桃毫不著相。對比一下韓愈的《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該詩也描寫敕賜櫻桃,其中兩句說“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直接描寫櫻桃的香與色,略顯直露、粘滯。因此苕溪漁隱說:“二詩語意相似。摩詰詩渾成,勝退之詩。”[18]60兩詩雖然意旨相同,但右丞詩在意境上更加淡遠渾成。
(三)情趣上,富有禪悅、不著禪跡
審美趣味上,“王右丞體”帶有濃厚的禪悅特征。施閏章說:“詩不可無道氣,稍著跡,輒敗人興。右丞體具禪悅……鳶飛魚躍,不知與道何與?”[27]2明確提出“右丞體具禪悅”命題,并指出“右丞體”之禪悅具有“渾厚無跡”的特點。
“右丞體具禪悅”,在明清時期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因此“禪悅”成為當時“效右丞體”竭力追求的目標。遺憾的是,絕大多數的“效右丞體”之作,禪機外露,有禪語無禪趣,缺少右丞詩的渾厚之味。例如,沈壽榕評價王文治(字夢樓)的“效右丞體”詩:“夢樓詩法右丞體,比較書名欲細論。理障未除翻是累,空言禪悅近旁門。”①沈壽榕《玉笙樓詩錄·續錄》卷一,清光緒九年刻增修本。批評其空言禪悅,徒增理障。此例從反面說明“右丞體具禪悅”命題的深入人心。
(四)結構上,渾淪無跡、高厚沉雄
關于“王右丞體”結構布局上的特點,方東樹說:“渾顥流轉,一氣噴薄,而自然有首尾起結章法。”[23]389朱庭珍說:“自起至結,首尾元氣貫注,相生相顧,镕成一片,精力彌滿,渾淪無跡,自然高厚沈雄。”[28]2398黃生說:“章法、句法、字法皆極渾渾。”[29]971“王右丞體”的章法、句法結構,隨作者一氣之流轉而曲折圓轉、渾淪無跡,因此給人以高厚沉雄之感。如《藍田山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遙愛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舍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遙蔭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瑤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覿。前八句寫藍田水路見聞,首二句突出“無心”,以此統領全篇。二解,前四句寫舍舟登岸及所見松柏之下的僧人,后四句寫精舍中僧人朝梵夜禪、不關世事的生活場景。三解,前四句寫自己憩息精舍的感受,后四句寫告別精舍,暗用《桃花源記》典故以示石門之精妙。全詩以“無心”起而以“有得”終,中間千回百轉,圓轉無跡,無心順有、得無所得的微妙禪機寓于渾圓活潑的字句之中,不著半點跡相。
(五)語句上,出語圓活、靈脫渾化
對于王維詩的語言特色,唐宋人已有經典概括,代表性的說法有殷璠的“詞秀調雅”說,張戒的“詞不迫切”說[30]459。明清時期,“王右丞體”的語言特色更是討論的重點。前引王世貞所謂的“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即是強調“王右丞體”在語句上的“渾厚無跡”特色。費經虞將“王右丞體”的語言特色概括為兩點,一是“圓活”,二是“典雅”。關于前者,他說:“出語圓活,下字平貼,對法流動,若不曾用一毫意。”②費經虞《雅倫》卷十七《品衡中》,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指出“王右丞體”在字句、對仗上的自然、靈動特色。關于后者,他說:“典者,用古無痕;雅者,出辭有度。博贍而卻橫筋露骨,只謂之編事,而不謂之典;樸茂而無靈脫渾化,只謂之癡重,而不謂之雅。”③費經虞《雅倫》卷十六《品衡上》,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費氏所謂“典雅”有其特定的內涵:“典”者,雖“用古”而“不橫筋露骨”;“雅”者,雖“有度”而“靈脫渾化”。此“典雅”觀,可謂“辭秀調雅”論與“詞不迫切”論的綜合,恰切地指出了“王右丞體”靈脫渾化而不橫筋露骨的語言特色。
五、“王右丞體”的佛學淵源
“王右丞體”之“渾厚無跡”風貌及其諸方表現,其背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而佛教的影響無疑是最重要者。對此,趙殿成(1683—1743)在《王右丞集序》中有深刻論述:“(右丞)天機清妙,與物無競,舉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膠滯其中,故其為詩,真趣洋溢,脫棄凡近。”[31]卷首佛教“不膠滯于萬物”的人生態度融化于王維詩中,便呈現為“真趣洋溢,脫棄凡近”的藝術風貌。“不膠滯于萬物”,是一種不粘不滯的“不二”境界,也就是“不住相”。趙殿成指出“不住相”是形成“王右丞體”之“渾厚無跡”藝術風貌的總根源。
為達“不住相”之境,佛教創設諸多“法門”,如“語無背觸”“正言似反”“以用顯體”“反常合道”等,這些“法門”都是用來破除“邊見”引人證悟“不二”之真性的手段。當深諳佛學的王維把這些方法手段巧妙運用于詩歌創作之中時,便形成了“王右丞體”渾厚無跡的審美特征。
(一)語無背觸
關于“王右丞體”的形成,趙殿最(1668—1744)在為其弟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所作序言中說:“右丞通于禪理,故語無背觸,甜徹中邊,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32]565他認為“王右丞體”的密碼在于“語無背觸”。“背觸”為禪林術語,“觸”表示肯定,“背”表示否定,不論是“觸”還是“背”都屬于一端之“邊見”,只有“背觸俱非”方為不執兩端的“中道”。“王右丞體”鏡花水月般的渾厚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這“語無背觸”的表達方式。
如《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首聯說自己中歲好道,晚年悟入“空”境,頷頸兩聯描寫獨來獨往的“空”境。如果語意就此結束的話,詩意上也就住了“空”相,住“空”相即為“觸”。為了防止這一現象的發生,尾聯反其意而為之,不再寫“空”而寫與林叟的忘我談笑,這樣就把那種坐看云起的孤獨拉回充滿溫情的人世間,從而掃除“空”相,進入非有非無的“中道”。整首詩,在表達上“語無背觸”、不著有無,因此在詩境上不粘不滯,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
(二)正言似反
“正言似反”,語出《普曜經》卷七,其意為正話反說,這樣能避免粘著于相,從而破除“邊見”,導人體悟本來“不二”之“真性”。受佛教影響,王維詩經常采用這種方法來增強詩的“渾厚無跡”效果。
欲言“寂”反言“喧”。如《秋夜獨坐》:“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本欲寫山夜的寂靜,卻寫山果落地的聲音與燈下草蟲的鳴叫,從而避免住于“寂”相。對比一下柳宗元《江雪》的前兩句“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直接描寫死一般的寂靜,住了“寂”相而落于“枯寂”之中,因此缺少王維詩的渾厚之氣。
欲言“頌”反言“諷”。如《贈劉藍田》:“籬中犬迎吠,出屋候柴扉。歲晏輸井稅,山村人夜歸。晚田始家食,余布成我衣。詎肯無公事,煩君問是非。”前四句寫村人交稅夜歸情景,這種情景出現于歷代詩歌之中多為批評雜稅繁重之意①顧可久注本詩曰:“急征繁苦之意。”(《唐王右丞詩集》,明萬歷十八年吳氏漱玉齋刊本),如果這樣理解的話,整詩便為諷諭主題。再仔細品味一下五六兩句,發現事實并非如此。這兩句寫的并不是村民交完稅以后的貧困生活,相反,卻是一種衣食無憂的滿足感。由此,重新審視全詩,前六句描繪的其實是一幅淳樸安樂的鄉村生活畫卷,最后兩句不但不是諷刺劉藍田為官不作為,反而是對其“無為而治”政績的贊美。這是一首美政詩而不是諷諭詩。美政主題卻以諷諭面目出現,贊美之意表達得渾然無跡,整詩立言超妙、詩意渾厚。
王維詩中這種“正言似反”的例子還有很多。如《積雨輞川莊作》:“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欲言“和”反言“爭”,言“爭”更見其“和”。又如《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欲言“空”反言“有”,言“有”愈見其“空”。再如《送劉司直赴安西》:“苜蓿隨天馬,蒲桃逐漢臣。”欲寫戍邊將士功勞之大,卻寫苜蓿、蒲桃這些細小之物,欲言“大”反言“小”,言“小”愈見其“大”。“正言似反”手法的運用,使“王右丞體”具有一種渾淪無跡、玲瓏剔透的美感。
(三)以用顯體
體用思維是佛教尤其是禪宗重要的思維方式。體,即體性,指不變的、無分別的本性;用,即相用,指變化的、有差別的現象。體是不可言說的,只能借言用以明體,這就是“以用顯體”。這種手法運用到藝術創作上便會產生“渾厚無跡”的藝術效果,正如明人王驥德所說:“不貴說體,只貴說用。……令人仿佛中如燈鏡傳影,了然目中,卻摸捉不得,方是妙手。”[33]144
關于王維“以用顯體”的表達方式,王夫之舉例論證說:
右丞之妙,在廣攝四旁,圜中自顯。如終南之闊大,則以“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顯之;獵騎之輕速,則以“忽過”“還歸”“回看”“暮云”顯之。……右丞妙手能使在遠者近,摶虛作實,則心自旁靈,形自當位。[19]98
王夫之以《終南山》《觀獵》為例說明王維詩“廣攝四旁,圜中自顯”之妙。“圜中”為虛、為體,“四旁”為實、為用,王維詩能摶虛作實、以用顯體,故而不露痕跡,渾然天成。
又如《漢江臨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這兩句,因表達方式及語意上近于佛家“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之“中道”,而被世人視為禪意詩句的典范。對此,明人陸時雍不以為然:“此語亦落小乘。”[25]381理由是,王維把“山色有無”這一“體”直接說了出來,這就住了相,因此只能達到“小乘”水平。其實,陸氏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并沒有真正理解這句詩的深層含義。此處之“山”,并非地上之山而是水中之山。詩人欲寫水的波濤,卻寫水中時有時無的山色,以此來顯現波濤的洶涌。“山色有無”為“用”,而水波洶涌才是未言之“體”。這就是言用不言體、于相而離相,不但未落“小乘”,反而可稱無上之妙品。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送邢桂州》:“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欲寫天色昏卻寫“江湖白”,欲寫潮水白卻寫“天地青”,言用不言體,以用而顯體。《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表面寫竹聲,其實是寫雪聲,絲毫不著跡象,被潘德輿贊為“不言雪而全是雪聲之神”[34]23。《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隔窗云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隔窗的云霧、鏡中的山泉,讓人感覺透心的涼爽,不言避暑卻不離避暑,這也是“以用顯體”的范例。
(四)反常合道
禪宗經常用一些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相違背的意象來表達凡圣共泯、生佛俱空的“不二”世界,這些意象雖違背世俗邏輯卻合乎禪理,故曰“反常合道”。王維“雪中芭蕉”圖即是這種表達方式的產物,“王右丞體”的“渾厚無跡”特征也與其有重要聯系。
王世貞論“摩詰體”曰“不拘常調”“自出宮商之表”,費經虞引殷璠語解釋“王右丞體”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所謂“出常境”“不拘常調”“自出宮商之表”,都是指王維詩在遣辭、用韻、對仗等方面不拘泥于固定格式,雖然打破了常規,語意卻更加渾圓活潑、自由自在。
對于律詩而言,用字重復是一大忌諱,但王維詩卻不時出現這種情況。如《送梓州李使君》前四句:“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半雨,樹杪百重泉。”重復使用“樹”“山”二字,但由于語意一氣貫通,讀起來令人感覺渾然輕妙,絲毫感覺不到重復。這種“犯重”現象,雖違背律詩規則,卻令語意更加渾厚,毫無人為痕跡。唐人近體詩特別講究粘對,失粘被視為一大缺陷,而王維詩卻時常出現失粘現象,這不但未傷其真美,反令語意更加渾成。如《送元二使安西》,黃生評曰:“失粘,須將一、二倒過,但畢竟移動不得,由作者一時天機湊泊,寧可失粘,而語勢不可倒轉,此古人神境,未易到也。”[35]979
綜上所述,“語無背觸”“正言似反”“以用顯體”“反常合道”,四者都是佛教用來破除“邊見”引人證悟“不二”之真性的方便法門,當它們被王維巧妙運用于詩歌創作之中時便形成了“王右丞體”渾厚無跡的審美特征。陸時雍評王維詩說:“以自然合道為宗,聲色不動為美。”[35]384道,在禪家表現為不即不離的“真性”,在王維詩中則表現為不動聲色、不露痕跡的玲瓏剔透之美,這一“真”一“美”是內外相通的。要說明的是,長期浸潤于佛學中的王維,在運用這些佛教“法門”進行詩歌創作時,完全是“興來神來,天然入妙,不可湊泊”的,因為這些“法門”已經完全融入了他的“根性”之中,創作對他來說只是其“根性”的自我敞開。
六、結 語
至此,我們可以給“王右丞體”下一個較為完整的定義了。“王右丞體”是一個內蘊豐富的詩學結構。“渾厚無跡”為其總體風貌,具體表現為:感興上,興會神到、不可湊泊;意境上,興象淡遠、不落聲色;情趣上,富有禪悅、不著禪跡;結構上,渾淪無跡、高厚沉雄;語句上,出語圓活、靈脫渾化。“王右丞體”的形成深受佛教的影響,“不住相”是其生成的總根源,“語無背觸”“正言似反”“以用顯體”“反常合道”等佛教“法門”則是其具體成因。
“渾厚無跡”及其諸方表現,作為“王右丞體”的審美特征,是否具有獨特性呢?這些特征當然不為“王右丞體”所獨有,盛唐詩歌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但這些特性在王維詩中表現得最為突出。比較一下王維詩與其他風格相近的詩,就會明白這一點。
王維與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由于同為唐代山水田園詩的代表而被后人合稱為“王孟韋柳”。關于王維與其他三人詩風的區別,趙殿最說:“唐之詩家稱正宗者,必推王右丞。同時比肩接武如孟襄陽、韋蘇州、柳連州,未能與之先也。孟格清而薄,韋體淡而平,柳致幽而激。”[32]565孟浩然詩露“清”痕,故“清而薄”;韋應物詩著“淡”跡,故“淡而平”;柳宗元詩住“幽”相,故“幽而激”。總之,孟韋柳三人之詩,都因“住相”而缺少王詩的“渾厚”之味。由此可見“渾厚無跡”之于“王右丞體”的獨特意義。
“王孟韋柳”四人中,詩風最接近的是王與孟,因此明人朱權提出“王孟體”概念。[36]561“王孟體”內涵應為二人詩風的交集處,這一交集處是什么?胡應麟說:“王、孟閑澹自得,其格調一也。”[37]37“閑澹自得”即清淡自然,是王孟詩風格最接近的特征,也是“王孟體”的核心內涵。王孟詩體雖都具有“清淡”特征,但兩人之“清淡”是有區別的。朱庭珍引紀昀語論王孟詩之“清”上的區別說:“王清而遠,體格高渾。孟清而切,體格俊逸。王能厚,而孟則未免淺俗,所以不及王也。”[38]2348王“清而遠”,孟“清而切”,因此孟詩缺王詩的渾厚之氣。同樣,胡應麟論王孟詩之“淡”上的區別也說:“孟詩淡而不幽,時雜流麗;閑而匪遠,頗覺輕揚。”[37]68-69“淡而不幽”“閑而匪遠”,是說孟詩住“淡”相,露“閑”跡,缺少王詩的“幽遠”之味。胡應麟與紀昀在評價王維詩時都用了一個“遠”字,“遠”即“不住相”,故而“渾厚無跡”,這是王詩與孟詩最重要的區別。
上文說過,“王右丞體”在感興上具有興會神到、不可湊泊之特征,相比之下,孟浩然詩在感興上則缺少這種渾然之機。王世貞說:“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為佳。……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14]1006雖然孟詩在寫成之后也不乏“超然之致”,但在感興上仍難掩“造思極苦”,因此孟詩在“渾厚無跡”上較王詩要略遜一籌。
自從蘇軾指出王維詩“詩中有畫”特點后,世人多視此為“王右丞體”的本質特征,并試圖以此把王維詩與孟浩然詩區別開來。賀貽孫認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他說:“詩中有畫,不獨摩詰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寫生,其便娟之姿,逸宕之氣,似超王而上,然終不能出王范圍內者,王厚于孟故也。”[26]171王孟之詩都具有“詩中有畫”特點,且在畫面的營造方面,孟并不在王之下,因此“詩中有畫”不是王孟二人詩體的本質區別,其本質區別在于是否能做到“渾厚無跡”。誠哉是言!
總之,“渾厚無跡”及其在感興、意境、情趣、結構、語言等方面的表現,是“王右丞體”的根本特征,它不僅具有普遍性,能概括王維詩的整體特征,而且具有獨特性,是“王右丞體”區別于其他詩人之體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