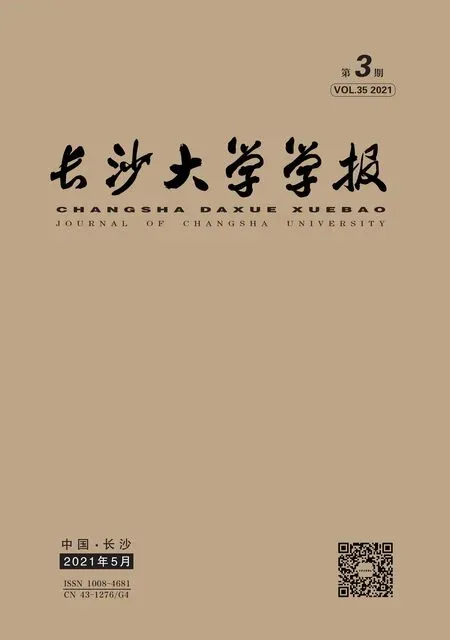中國傳統(tǒng)美學視域下徽州意象水彩藝術研究
甘興義,甘奧深
(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澳門 999078;中國美術學院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4)
我國傳統(tǒng)美學以審美意象為核心,集理念、思想、流派、體系與哲學、藝術學、美學等諸多方面的內(nèi)容為一體,其研究對象通常為各個歷史階段、各個流派及其藝術作品所表現(xiàn)出來的美學意涵和特征,如“氣韻生動”“傳神寫照”“觀物取象”“立象以盡意”等命題以及這些命題之間的異同、關聯(lián)及轉化。徽州意象水彩藝術正是在我國傳統(tǒng)美學的滋養(yǎng)中而生,以其獨特的美學表現(xiàn)和格調(diào)在中國水彩藝術領域獨樹一幟。它通過吸收傳統(tǒng)美學中的意象觀念,采用老莊美學思想,借助當?shù)貍鹘y(tǒng)民居建筑中鮮明的美學特色和厚重的文化內(nèi)涵,以意為美、以道為美、同構為美,輔之氣韻、意蘊,融入各家所長,在畫風上逐漸具備自身獨特的、無可替代的元素,形成極具中國特色的意象水彩,成為中國水彩藝術中別具一格的存在。
一 傳統(tǒng)美學意象與徽州意象水彩藝術
宇宙之中有兩種力量,相異相依,相輔相成,相對相持,比如天地、男女、動靜、生死等。昔者圣人用一長橫(陽爻)和兩短橫(陰爻)象征兩只水鳥在和鳴,這可謂人世間最簡潔的意象,寄寓尋找佳偶的情思,蘊含了豐富的意蘊。抽象言之,我國的傳統(tǒng)美學常常把情與景的統(tǒng)一作為審美意象的基本構架,而藝術家在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的時候,情景融合是其情感表達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審美意象的真實體現(xiàn)和情與景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lián)。意象同樣也是西方哲學美學中的重要概念,而在20世紀初期西方現(xiàn)代文學領域中所產(chǎn)生的意象派的觀點就與我國古老的意象觀不謀而合。
一切藝術創(chuàng)造都包含意象,藝術家們通過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性開啟對意象美的自覺追求。徽州意象水彩藝術繼承了我國傳統(tǒng)的意象觀,取象于自然,其意象蘊含著豐富的美學內(nèi)涵,實現(xiàn)了情與景的完美融合,詮釋了中國水彩藝術的形式之美、內(nèi)容之美及意境之美,其地域特色鮮明。2006年1月8日下午,北京大學博雅會議中心舉辦了“意象之間學術研討會”,邵大箴、林陽、劉建、李一、尚輝、王維新、丁寧等眾多知名美術評論家與會研討,多家雜志如《美術觀察》《中國水彩》等對此次會議進行了報道。名家們尤其對丁寺鐘在徽州意象水彩藝術上的創(chuàng)新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與認可。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徽州意象水彩藝術已進入一個嶄新的高度,意味著徽州意象水彩藝術的成就得到了中國當代藝術界權威學者、專家的認可。
從傳統(tǒng)美學來看,徽州意象水彩藝術再造了一種新的圖示語言,介于抽象與具象之間,是一種具有民族性的藝術語言,其作品往往給人一種無限的聯(lián)想。著名的美術評論家、史論家邵大箴在《視野、修養(yǎng)與境界》一文中評價了丁寺鐘的徽州意象水彩藝術的成就,指出意象水彩是中國水彩發(fā)出耀眼光輝的一個方向,意象水彩的審美特征反映了創(chuàng)作主體與自然客體的辯證關系,并充分發(fā)揮了主體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使想象力達到一種自覺的追求;徽州意象水彩藝術的意象美則是狂放又嚴謹、激越又沉穩(wěn)的,體現(xiàn)了創(chuàng)作主體心靈與自然的相互交融。這種意象,不是孤立的物象,而是一幅造化自然、氣韻生動的圖景,表現(xiàn)為宇宙本體和生命“氣”的融合,也是景與情的融合。
徽州意象水彩藝術除了具有藝術上的美感,更具有深刻的哲理性,這離不開藝術家對徽州意象水彩藝術哲理性的思考。在創(chuàng)作與鑒賞的過程中,意象的形式美感與哲理性思考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傳統(tǒng)美學的重要命題,能將二者進行融合的人并不多,但丁寺鐘做到了。在對“意象”的詮釋上,丁寺鐘將“意”理解為創(chuàng)作者內(nèi)心情感的流露與釋放,是一種高尚情懷的思維傳遞。在藝術里,感性的東西是經(jīng)過心靈化了,而心靈的東西也借助感性化而顯露出來了[1]63。而“象”除了指物象的形象外,他還認為具有抽象的含義。因此,在他看來,“意象”所呈現(xiàn)出來的思想內(nèi)涵既具有哲理性,又具有審美觀照。可以說,丁寺鐘把徽州意象水彩藝術的神韻與情致推向一個高度,一個意象美的高度,這種意象美擺脫了客觀物象的束縛,吸納了抽象元素,最終形成具有中國傳統(tǒng)情韻之美的意象水彩意境。
二 老莊美學思想與徽州意象水彩藝術
在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老子和莊子的思想中也有對美學的見解。老子的“道”指的是在天地產(chǎn)生之前就存在的原始混沌,不依靠外力而存在,“道”生萬物,是“無”和“有”的高度統(tǒng)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2]2“獨照之象,窺意象而運斤。”[3]35從審美的角度來理解,即審美客體不是孤立存在的,審美觀照也不是孤立的,審美觀照的實質(zhì)是把握客觀對象的本體和生命。莊子的“道”是客觀存在的,具有最高之美,他認為對于“道”的觀照是人生最大的快樂。而徽州意象水彩藝術的至美境界正是對“道”的觀照的體現(xiàn),“虛靜”“自然”“象”“氣”“妙”“味”等諸多美學內(nèi)蘊,在徽州意象水彩藝術作品中都得到了集中體現(xiàn)。這些都是自然美的體現(xiàn)。
崇尚自然也是老莊的美學思想。徽州意象水彩藝術傾向于將抽象元素與主觀色彩相融合,重點在于表達主觀情感,彰顯出對天地自然之美的追尋和體驗。著名水彩畫家傅強教授所創(chuàng)作的《印象徽州》《徽風皖韻》和《徽州元素》等一系列優(yōu)秀的意象水彩畫作品就彰顯出強烈的自然美。這些作品是不同材料與技法語言的融合,加上主觀色彩的巧妙運用,呈現(xiàn)出一種和諧意象,透射出自然界萬物本體和生命之存在,也體現(xiàn)出老子“道”“氣”思想的審美內(nèi)涵。正如嚴羽所說:“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4]48徐公才教授的創(chuàng)作則更傾向于表現(xiàn)“虛靜”和“自然”。他創(chuàng)作的《春》《蕓》和《徽州情——黑白交響曲》等作品均以“意象”為表現(xiàn)手法,使人們直觀地感受到徽文化的博大精深與獨特魅力,其別具一格的圖示化語言構建和再現(xiàn)了“虛靜”與“自然”。
莊子美學思想的核心是“大美”思想,主張質(zhì)樸混沌的大自然本身是最為完善的,具有一種至高無上的美,而徽州意象水彩藝術領軍人物柳新生和丁寺鐘的創(chuàng)作就體現(xiàn)了這一點,不過他們在對自然意象的表達方面各有不同。柳新生善于進行抽象概括,丁寺鐘則善于將生活融入作品。柳新生將中國傳統(tǒng)水墨畫和大寫意的技法語言融入意象水彩的創(chuàng)作,對人性理念和生命起源也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從事水彩畫學習與創(chuàng)作長達六十余年,其代表作《山魂》《白樺之夢》《白馬》等,飽含對自然界的無限熱愛,流露對生命的思考與探索,體現(xiàn)了中國水彩藝術對自然美的追求和審美價值取向。可以看出,柳新生的意象水彩作品強調(diào)審美觀照,彰顯了藝術家審美心胸之臻境。丁寺鐘筆下的意象水彩風格則宛如其人格的寫照,他把對世界的認識與對生活的真實感受融入作品,使其呈現(xiàn)出濃厚的現(xiàn)實感官色彩,拉近了畫作與生活的距離,體現(xiàn)出自然美、生活美。丁寺鐘的水彩世界是自由感受與審美胸懷的高度融合,讓人感受到恢宏的創(chuàng)作空間與豐富的文化視野。為了體驗不同的民族文化與風土人情,丁寺鐘踏遍世界各地,他獨特的精神內(nèi)涵和精神氣質(zhì)可以從其作品《青青坡上草》《春初》和《春天的意象》中體味到。
徽州意象水彩藝術營造了獨特的審美意境,賦予水彩藝術以特有的精神品質(zhì),充分展現(xiàn)了自然之美。意象水彩中的水與彩,和中國水墨中的水與墨一樣,都是取象于天地自然。藝術家們通過對自然物象的梳理,將內(nèi)心情感融入作品,以表現(xiàn)萬物與天地陰陽交錯的飽和張力,丁寺鐘則通過水與色、黑與白的鋪陳組合將這種張力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丁寺鐘在對“意”與“象”的表達中,著重表現(xiàn)了對“象”的審美情趣,他通過從混沌中躍出的紋理和線條,突出畫面所產(chǎn)生的視覺空間和整體氣韻。更重要的是,丁寺鐘作品里體現(xiàn)的自由奔放與莊子美學的內(nèi)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丁寺鐘意象水彩中的“自由奔放”在哲學上體現(xiàn)的是實踐對客觀世界的改造,以使外在世界符合自己的目的,使自在之物變?yōu)樽晕抑铩6@正好契合了莊子“心中無物,自有乾坤”[5]51的思想。徽州意象水彩藝術的內(nèi)涵與博大精深的傳統(tǒng)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滲透,抽象化的符號(主要指點線面)重構了物象在作品中的視覺感染力,使得人們對意象水彩產(chǎn)生無限的想象,凸顯了水彩中水與色的自然融合之美,達到“氣韻生動”“觀物取象”的藝術之臻境。其中關于“象”的審美內(nèi)涵至關重要,與莊子美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是審美與自由辯證關系的體現(xiàn),水與彩的碰撞與融合、滲透與布局、分離與歸納也將這一點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三 徽州建筑美學與徽州意象水彩藝術
天下建筑看中國,中國建筑看徽州,徽州建筑博大精深,有著一種獨具特色的美學意蘊和文化內(nèi)涵,不僅以儒家倫理道德秩序為主要精神,還體現(xiàn)了老莊思想和道家思想。徽州歷史悠久,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母系氏族社會后期,就已經(jīng)有人類在這片土地上生產(chǎn)勞作、繁衍生息。更重要的是,徽州是程朱理學的發(fā)源地,道家思想也體現(xiàn)于徽州建筑文化之中,這些都使得徽州建筑體現(xiàn)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天人合一”思想。
別具一格的徽州建筑包含了園林的基本要素,其古村落極具美學價值,遠遠望去層層疊疊、黑白相間,給人一種美的享受。正如曹文埴所稱:“青山云外深,白屋煙中出。雙溪左右環(huán),群木高下密。曲徑如彎弓,連墻若比櫛。”[6]127不僅道出了古徽州村落的美景,還道出其具有一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閑適,并呈現(xiàn)出古徽州村落獨有的文化氣息和審美意蘊。徽州建筑的美學理念與文化內(nèi)涵體現(xiàn)是多方面的,也是多視角的,既包含了區(qū)域文化符號語言,也展現(xiàn)了傳統(tǒng)文化的審美取向。也可以說,徽州建筑除了具有地域性特點之外,還體現(xiàn)了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和內(nèi)涵,如徽州建筑所體現(xiàn)的“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這一思想與現(xiàn)如今我們提倡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觀的核心內(nèi)容是一致的,不僅表達了徽州理學中的“禮”思想,也包含了“仁”“和”的社會觀。地域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與內(nèi)涵滲透在徽州建筑的造型與空間布局方面,黑與白的對比、和諧的比例、優(yōu)美流暢的線條、清新淡雅的灰色調(diào)等,構成了徽州建筑那獨有的層層疊疊、黑白相間、參差輝映的和諧人文景觀。優(yōu)美的造型與自然融為一體,其藝術特征與美學內(nèi)蘊讓人們充分感受到人與自然、建筑與自然的和諧之美。
正是徽州建筑所具有的文化內(nèi)涵與由建筑本身所呈現(xiàn)出來的點線面結構,以及與大自然渾然一體的美學特征等,給徽州的意象水彩藝術家們提供了豐厚的創(chuàng)作題材,激發(fā)了他們豐富的想象力和靈感,使得他們的藝術作品體現(xiàn)出徽州村落的精神內(nèi)涵與特色鮮明的美學特征。徽州意象水彩藝術作品中的黑白對比所表現(xiàn)出的強烈空間及水色意蘊正是徽州建筑白墻黑瓦、節(jié)奏韻律的體現(xiàn)。可以說,徽州意象水彩藝術家們所創(chuàng)作出的作品呈現(xiàn)出強烈的帶有徽州建筑藝術特色的特征。徽州建筑也充分展示了時間和空間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即時間和空間組成了人們的生活,這主要體現(xiàn)在徽州建筑的虛實交替以及變化多樣的空間組合:以時間為軸線,將每個單獨的空間進行有序的組合,最終成為統(tǒng)一的整體。這一點,與徽州意象水彩藝術創(chuàng)作中所采取的“追求水色交融的意象之維”[5]34的表現(xiàn)手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也與徽州意象水彩藝術作品呈現(xiàn)出的“以意生色”的創(chuàng)作理念形成巧妙的呼應,即在統(tǒng)一中求變化、變化中求和諧,給人以時空交錯之感。徽州意象水彩藝術創(chuàng)作與道家對時空的起源探究也有著相同之處,其通過藝術作品形式的表達證實了時間是不可逆轉的,但又是循環(huán)往復的。借助徽州建筑鮮明的美學內(nèi)蘊和厚重的文化內(nèi)涵,徽州意象水彩藝術終以其極為獨特的繪畫風貌成為中國水彩畫壇上一種獨樹一幟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豐富了中國傳統(tǒng)水彩藝術的語言面貌。
徽州建筑屬于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建筑中的寶貴財富,無論是其文化內(nèi)涵還是其藝術特征,均體現(xiàn)出其獨有的氣質(zhì),而徽州意象水彩藝術創(chuàng)作汲取了徽州建筑的文化內(nèi)涵和美學特征,成為特色鮮明的徽州文化的一部分[6]105。在徽州意象水彩藝術作品中,黑瓦白墻層次分明,幢幢民居錯落有致,色彩對比鮮明而又富有空間感,與畫面的基本構成元素——點線面巧妙相融,具有極強的文化內(nèi)蘊和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