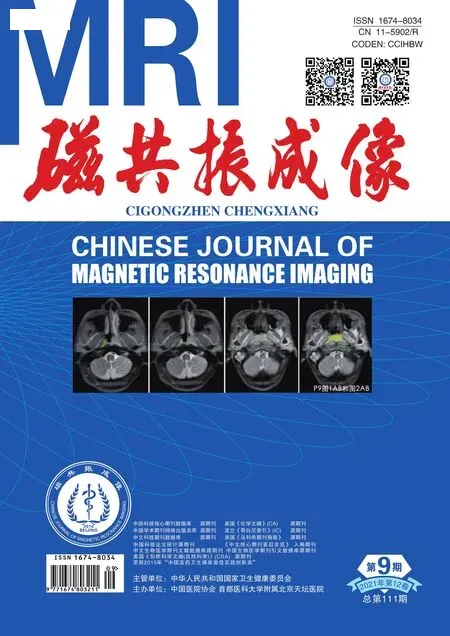斜外側腰椎椎間融合術的術前影像學評估研究進展
韓孟龍,方向軍*,賀中云,顏學亮
作者單位:1.南華大學衡陽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放射影像科,衡陽 421001;2.湖南省株洲市三三一醫院放射科,株洲 412002;3.南華大學衡陽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脊柱外科,衡陽 421001
腰椎退行性疾病是臨床上的常見病與多發病,腰椎椎間融合術作為一種經典、有效的外科治療手段,能夠有效地恢復脊柱的正常序列、重建脊柱穩定性,受壓的神經根獲得直接或間接地減壓,患者的臨床癥狀得以緩解,得到了患者的滿意和醫生的青睞,在臨床上廣泛開展[1]。1932年,Capener[2]報道了前路腰椎椎間融合術(an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ALIF)治療腰椎滑脫的案例,但ALIF具有手術創傷大的缺點,患者可能會出現腹部大血管損傷和男性逆行射精等并發癥[3]。1997年,Mayer[4]首次報道了切口更小、出血更少的微創前路腰椎椎間融合術,大大減少了傳統ALIF的并發癥發生率。隨著影像學的發展、手術器械的改進和微創理念的不斷深入,2006年,Ozgur等[5]率先報道了利用側方切口,由腹膜后間隙經腰大肌纖維進入椎間隙,處理椎間盤組織,進行椎體間融合的手術方式,并將其命名為(extreme lateral interbody fusion,XLIF),但XLIF會損傷腰大肌,盡管術中使用了神經電生理進行監測,但腰骶神經的損傷率依然較高,患者術后出現下肢感覺異常和運動障礙[6]。2012年,Silvestre等[7]首次報道了經腹膜后大血管與腰大肌之間的天然解剖間隙進行腰椎椎間融合的微創手術方式,并將其命名為斜外側腰椎椎間融合術(oblique lumbar interbody fusion,OLIF)。OLIF適用于L1~S1節段的椎間融合,但最適合用于L2~L5節段[8],經腹外斜肌、腹內斜肌及腹橫肌進入腹膜后,進行椎間盤切除和椎間融合器置入,既避免了對脊柱后方組織的損傷,又降低了大血管和腰骶神經損傷的發生率,具有出血少、手術時間和平均住院時間短、術后恢復快等諸多優勢。但經過近十年的臨床廣泛應用,與手術相關的并發癥也愈來愈多地得到報道[9-10],主要包括術中和術后并發癥。如術中操作不當導致主動脈、髂血管或節段動脈的損傷引起出血或血腫,長時間的牽拉和分離組織導致交感神經、神經根或馬尾神經的損害[11-12]。術后并發癥主要有腰骶神經叢過度牽拉導致的一過性屈髖無力和感覺障礙;使用的融合器面積較其他融合術式大,融合器位置放置不當,可出現術后融合器下沉、神經根的壓迫;患者存在骨質疏松,術前評估不充分,術后可能出現椎間隙的塌陷等[13-15]。目前影像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已深入應用于腰椎疾病的診斷、療效的評估[16-17],在腰椎手術前的規劃也有廣泛的應用,筆者將對近年來斜外側腰椎椎間融合術術前影像學評估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期為更好的手術開展提供支持。
1 手術窗大小的評估
OLIF手術窗的大小直接決定了患者能否利用OLIF手術治療疾病的關鍵所在,影像學檢查是術前必不可少的檢查手段,所以許多的學者利用影像學檢查在術前進行手術窗大小的評估研究。Boghani等[18]回顧性分析了300例患者的腰椎磁共振圖像,測量了L2~S1的OLIF手術窗(主動脈內側至左側腰大肌外側的距離)大小,L2~3、L3~4、L4~5分別為(17.3±6.4)mm、(16.2±6.3)mm、(14.8±7.8)mm;L5~S1手術窗(椎間盤中點至左側最近血管的距離)大小為(13.8±8.3)mm;其中手術窗小于1.0 cm的概率,L2~3、L3~4、L4~5、L5~S1分別為10.30%、16.00%、30.00%、39.30%,也就是隨著椎間隙下移,手術窗縮小;同時分析了腹主動脈分叉的位置,52.67%的患者位于L4椎體,24.67%的患者位于L4~5椎間盤水平,13.33%的患者位于L5椎體。Boghani等[18]認為術前應該利用磁共振檢查來確定患者的手術窗大小,并多方面評估OLIF手術能否安全有效地進行。
Tao等[19]對70例患者進行腰椎磁共振掃描,測量了主動脈或左髂總動脈與腰大肌之間的手術窗寬度。發現L1~2的手術窗平均寬度為13.36 mm,L2~3為13.36 mm,L3~4為12.37 mm,L4~5為10.36 mm,男女性別之間手術窗大小無差異;同時還測量了左側腰神經叢至主動脈的距離,L1~2的平均寬度為27.44 mm,L2~3為30.86 mm,L3~4為30.73 mm,L4~5為24.36 mm,且左側神經叢至主動脈的距離與椎間盤的橫向寬度、縱向寬度及腰大肌的厚度呈正相關,與腹膜后血管的位置呈負相關。Tao等[19]認為,通過適度的牽拉腰大肌可擴大手術窗,獲得更大空間來進行椎間盤切除和置入融合器,以獲得更好的操作視野和手術效果,中國人的OLIF手術窗寬度小于白色人種;腹膜后血管所處的位置是影響手術窗大小的主要因素,術前評估血管的位置和脊柱的相關參數,對OLIF手術順利進行至關重要。
Chen等[20]回顧性分析了400例中國腰痛患者的磁共振圖像,將L2~L5的OLIF手術窗分為了血管窗(腹主動脈或左側髂血管左側緣至正中矢狀面的距離)、裸露窗(未被主動脈和腰大肌占據的椎體左前方的區域)、腰大肌窗(被腰大肌占據的椎體左前方區域),由于主動脈分叉和髂血管匯合位于L5~S1,所以將L5~S1分為裸露窗(左髂血管右側至正中矢狀面的距離)、垂直裸露窗(在正中矢狀面圖像上垂直測量從穿過主動脈分叉下方中線的第一條血管到L5下終板的距離)。血管窗是手術的禁區,裸露窗是可以直接進入椎間盤操作的區域。研究發現,在400例患者中L2~3、L3~4水平分別只有1例無裸露窗,在L4~5只有7.25%的受試者無裸露窗,即使沒有裸露窗,但由于腰大肌窗的存在,仍可以進行OLIF手術。左側腰大肌厚度影響手術的難度,同時發現年齡越大,腰大肌的厚度越小,老年女性的腰大肌萎縮,手術中牽拉的難度減小。
Song等[21]回顧性分析了274例腰椎疾病患者的L5~S1椎間隙磁共振圖像。識別L5~S1左右兩側的血管(髂內靜脈或髂內動脈),測量了左右側血管內側面分別至椎間盤中心之間的距離。統計結果顯示,左側血管至L5~S1椎間隙中心的距離平均為12.47 mm,右側平均為16.93 mm,兩者有統計學意義,表明L5~S1右側更適合進行OLIF手術,從右側進入可減少操作對血管的損傷和融合器的安全置入。
Ng等[22]分析了500例患者L4~5椎間隙的磁共振圖像,將OLIF手術窗大小分為4個等級:0級,無手術窗;1級,小手術窗(≤1 cm);2級,中等手術窗(1~2 cm);3級,大手術窗(>2 cm);手術窗的位置標記為前斜形、斜形或斜側形。結果得出:10.50%的患者在L4~L5椎間隙水平沒有可測量的手術窗(0級),35.00%和25.20%的患者分別為1級和2級手術窗,手術窗位置的前斜位、斜位和斜側位分別占3.70%、89.60%和6.70%。術前對手術窗大小的評估,可以及時判斷能否順利進行OLIF手術,影像學檢查是不可或缺的評估手段之一。
2 節段動脈、髂血管及主動脈損傷的風險評估
Wu等[23]收集了50例因泌尿系統或胃腸道疾病行256層螺旋CT腹部血管造影的患者影像資料,記錄了腰椎節段動脈的起源、數量、缺失、走行方向和分支情況,統計發現L2、L3節段動脈每位患者均存在,但96.00%(48/50)的患者存在L1節段動脈,90.00%(45/50)的患者存在L4節段動脈,L5節段動脈只有6例(12.00%)患者存在,L1~L4椎體的血液供應均來自腹主動脈,L5椎體的血液供應來源于髂腰動脈、髂總動脈、髂內動脈和L4節段動脈的吻合支。同時測量了節段動脈的角度,定義為在三維矢狀位圖像上,節段動脈進入椎體方向與椎體前緣縱線的角度,L1~L3的節段動脈與椎體呈銳角(<90°)向上走行,L4、L5的節段動脈呈鈍角(>90°)向下走行,因此OLIF通道的固定針置于L1~2、L2~3椎體的下緣,L3~4、L4~5椎體的上緣。將椎體由前往后分為Ⅰ、Ⅱ、Ⅲ、Ⅳ區,在進行OLIF手術時,應將OLIF的撐開器放置在Ⅰ區和Ⅱ區,而融合器的放置應位于Ⅱ區、Ⅲ區。將每根節段動脈與椎體的關系從上至下分為四種類型,Ⅰ型穿過椎間盤層面,Ⅱ型穿過椎體上緣至椎弓根中間,Ⅲ型穿過椎弓根中間至椎弓根下緣,Ⅳ型穿過椎弓根下緣至椎體下緣,在OLIF手術時最易損傷的為Ⅰ型節段動脈,其次為Ⅳ型節段動脈。
Chung等[24]利用磁共振結合ALIF和OLIF手術對65例患者分析了L5~S1處的左髂總靜脈。根據左髂總靜脈的位置和移動難度,分為三型;Ⅰ型,左髂總靜脈不需要移動,橫向延伸到L5~S1椎間盤左側長度的三分之二或不與椎間盤緊貼;Ⅱ型,容易移動,左髂總靜脈位于L5~S1椎間盤左側長度的三分之二的內側,但與椎間盤之間有血管周圍脂肪組織;Ⅲ型,可能移動困難,左髂總靜脈與L5~S1椎間盤之間無血管周圍脂肪組織。結果Ⅰ型左髂總靜脈有32例(39.20%),32例患者中,有30例左髂總靜脈超過了L5~S1椎間盤左側的三分之二,2例左髂總靜脈不與椎間盤緊貼;Ⅱ型有18例(27.70%);Ⅲ型有15例(23.10%)。手術中有7例患者出現了血管損傷,嚴重不一,其中5例有嚴重的血管損傷,其余2例為輕微血管損傷,7例患者均為左髂總靜脈損傷。在三種類型的左髂總靜脈中,存在血管周圍脂肪組織的Ⅱ型左髂總靜脈更容易在術中牽拉,因為血管周圍脂肪組織提供了左髂總靜脈可移動的空間[25],在沒有血管周圍脂肪組織的類型中,發生血管損傷的風險較高。
Wang等[26]回顧性對300例患者磁共振圖像進行了分析,根據Moro分區(軸位椎間盤從前往后分為6個區:A、Ⅰ、Ⅱ、Ⅲ、Ⅳ、P區)和Zone方法(椎間盤從左往右分為:R、a、b、c、L區)形成網格系統評估了主動脈在L2~3、L3~4、L4~5水平的位置。在L2~3椎間隙水平,28.00%的受試者的主動脈位于Ⅰb區,20.30%位于Ⅱb區,20.00%位于Ⅰc區;L3~4椎間隙水平,20.70%的受試者主動脈位于Ab區,26.00%的受試者位于Ac區,11.00%的受試者位于Ⅰc區;在L4~5椎間隙水平,31.00%的受試者位于Ab區,26.00%的受試者位于Ac區,11.70%的受試者位于Ⅰb區。并且統計得出主動脈的分叉水平主要位于L4椎體水平,男女性別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主動脈位于ⅡR區和Ⅱa區的患者提供了更寬的手術操作通道,理論上降低了與手術入路相關的術中血管損傷發生率。Baker等[27]對165例患者的CT圖像發現有120例患者(72.70%)位于L4椎體。
腰骶移行椎是脊椎常見的先天發育變異,增加手術錯誤定位的可能性,并且L5~S1椎間隙水平的手術窗常被左髂總靜脈阻擋,影響手術的順利操作[28]。Chung等[29]利用CT和磁共振對31例存在腰骶移行椎患者和37例腰骶椎無變異患者比較了髂腔靜脈連接處的位置和左髂總靜脈的形態,近70.00%的腰骶移行椎患者的髂腔靜脈連接處位于低位或極低位,近74.00%的患者在OLIF手術時可能難以牽拉左髂總靜脈;而無變異患者在OLIF手術時,近80.00%的患者可能不需要或容易牽拉左髂總靜脈。Berry[30]報道了1例下腔靜脈位置變異位于左側的患者,由于進行了術前影像學檢查,發現了此類情況,患者改用右側入路進行OLIF手術,避免了下腔靜脈損傷的可能性。上述研究表明術前應借助影像學,評估血管的走行和變異情況,以避免術中損傷血管。
3 神經損傷的風險評估
Wang等[31]前瞻性選取了44名健康志愿者進行3.0 T磁共振掃描,評估了交感神經在OLIF術中的損傷風險。在T2WI橫軸位上確定了左側交感鏈的位置,測量左側交感鏈至主動脈的距離,得出L2~3、L3~4、L4~5椎間隙水平兩者之間的平均距離分別為(11.14±2.89)mm、(9.36±2.79)mm、(6.63±2.94)mm,從主動脈左側邊界至左側交感鏈的距離依次顯著減小。然而L2~3、L3~4、L4~5左側交感鏈至左側腰大肌之間的平均距離分別為(2.96±0.62)mm、(2.83±0.62)mm、(3.07±0.86)mm,各相鄰節段的距離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同時發現,左側交感鏈的位置在L2~3層面更靠后和更靠外側,而在L3~4和L4~5層面更靠內側。不同節段水平的交感鏈損傷的實際風險因其特定的解剖條件而異。L2~3椎間隙水平可為OLIF提供更安全的手術空間,在L4~5節段操作OLIF時,左側交感鏈損傷的風險可能更高。術中長時間對腰大肌的牽拉,導致神經損傷的患者多數出現一過性的癥狀,術前影像學檢查可以提供腰骶神經的走行和分支情況,為避免更為嚴重的神經損傷可以提供一定參考價值。
4 輸尿管損傷的風險評估
Fujibayashi等[32]對27例患者術前進行了泌尿系CT雙期增強掃描,評估了輸尿管的損傷風險。采用腰大肌和椎體分別作為OLIF和XLIF手術的參照解剖標志,對輸尿管的位置進行分類。在OLIF手術過程中,所有病例的輸尿管位置通過直視和手動觸診兩種方式進行評估。同時,將可能的血管異常用三維后處理的圖像進行評估。對于OLIF手術,使用分類1系統,將輸尿管的位置分為:當輸尿管位于腰大肌腹側時,定義為Ⅰ-p;當輸尿管位于腰大肌前半部分時,定義為Ⅱ-p;當輸尿管位于腰大肌后半部分時,定義為Ⅲ-p。對于XLIF手術,使用分類2系統:當輸尿管位于椎體前三分之一的腹側時,定義為Ⅰ-v;當位于椎體的中間三分之一時,定義為Ⅱ-v;當位于椎體的后三分之一時,定義為Ⅲ-v。術前評估了162條輸尿管中的125條,其中113條輸尿管(90.40%)在解剖學上被歸類為Ⅰ-p,即靠近OLIF的手術通道,術中腹膜牽拉不充分時,損傷輸尿管的概率將增加;20條輸尿管(16.00%)被歸類Ⅱ-v和Ⅲ-v,即XLIF手術期間具有潛在的損傷風險。有1例患者,由于血管異常,OLIF被改為傳統的后路手術。術中直視下手動觸診發現所有病例的輸尿管都隨著腹膜向前移動。Fujibayashi等[32]認為CT雙期增強掃描有助于術前評估輸尿管、腎臟和血管結構的位置。術前評估輸尿管的走行可以降低術中潛在泌尿系統損傷的風險。
5 體位改變對手術通道的影響
Farah等[33]對10名健康志愿者分別進行仰臥位、右側臥位左髖關節伸展、右側臥位左髖關節屈曲30°~40°三種體位的磁共振掃描,在L2~3至L5~S1椎間隙水平分別統計三種體位時的左側腰大肌表面積、手術通道大小和血管位置的改變。研究發現左側腰大肌在三個位置的平均表面積為7.83~17.19 cm2;在右側臥位時,從L2~3到L4~5,當左髖從伸展轉向屈曲時,手術通道、腹主動脈和下腔靜脈位置未見明顯改變。當志愿者從仰臥位移動到右側臥位,臀關節伸展時,腹主動脈向右移動了3.66~5.61 mm,而下腔靜脈向右移動了0.92~4.96 mm。當體位從仰臥位移至右側臥位,髖關節處于屈曲狀態時,腹主動脈向右移動了0.47~4.88 mm,而下腔靜脈靜脈向右移動了0.94~4.13 mm。理論上,髖關節屈曲的側臥位有助于避免椎間融合手術中神經損傷的風險。Farah等[33]發現左髖關節伸展或屈曲的右側臥位的手術通道大小沒有明顯的差異,但隨著髖部的伸展,腰大肌的表面積變小,主動脈和下腔靜脈明顯遠離手術通道。Farah等[33]認為,為了避免和減少術中血管、神經損傷,OLIF手術時的體位應采用左髖關節伸展的右側臥位。Kotheeranurak等[34]對40例患者進行了三種體位的磁共振掃描,得出了相似的結論:當髖關節處于中立位時,L2~L5的腹膜后斜通道顯著增加,而在此位置,腰大肌橫截面積和厚度最小。外科醫生可能會受益于在OLIF過程中左髖的中立位置。
張帆等[35]對40例健康志愿者,分別在仰臥位及右側臥位時進行磁共振掃描,測量了L1~L5的OLIF手術通道大小和左側腰大肌的橫截面積。研究發現右側臥位時L1~2、L2~3、L3~4椎間隙水平通道大小顯著小于仰臥位,而L4~5椎間隙水平兩者無統計學意義;不同椎間隙之間右側臥位時的通道大小存在統計學意義,通道大小趨勢為L1~2>L3~4>L2~3>L4~5>主動脈高分叉者L4~5,其中L1~2顯著大于主動脈高分叉者L4~5;在L3~4椎間隙水平,體質量指數、腰大肌截面積與右側臥位呈負線性相關;在L1~2椎間隙水平,腰大肌橫截面積與右側臥位也呈負線性相關。因此,張帆等[35]認為術前若采用仰臥位MRI進行評估可能會存在偏差;OLIF通道受不同節段、體質量指數及腰大肌面積影響,因此節段、體質量指數及腰大肌面積也是術前評估的重要參考指標。
為了明確由仰臥位到側臥位的體位改變對L5~S1椎間隙水平手術窗(左、右髂總靜脈之間的距離)大小的影響,Choi等[36]前瞻性對20例患者進行仰臥位和側臥位的磁共振掃描,結果得出該研究人群L5~S1均存在手術窗,仰臥位的平均寬度為27 mm,側臥位的平均寬度為22 mm,仰臥位到側臥位的位置改變平均減少了5.2 mm。術前影像學檢查通常采用仰臥位,而改變體位時,大血管的位置移動對手術窗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影響,因此,術前有必要采用手術時的體位進行影像學檢查才能更精準地評估手術窗大小及順利進行手術操作。
6 小結與展望
OLIF手術是臨床上治療腰椎退變性疾病的外科手段之一,自2014年引入國內以來,鑒于它的諸多優點,短短十年內迅速在各級別醫院廣泛開展,但術中和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也相應增加,利用影像學檢查的優點進行術前評估就顯得十分地必要。影像學可以采取不同方位、不同掃描形式充分地了解肌肉、血管、神經、臟器等結構的解剖及其毗鄰關系,能有效地提示術者在進行手術時避免損傷相關解剖結構,避免對患者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雖然影像學可以有效地對OLIF進行術前評估,但是目前完成的相關研究結果有限,在未來需加大力度開展關于OLIF尸體研究以及更大樣本、多中心、結合更前沿影像技術檢查方式的影像解剖學研究,如雙能量CT、磁共振神經成像掃描等,以進一步減少OLIF手術并發癥的發生,并使其更好地應用于臨床,讓患者受益最大化。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體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