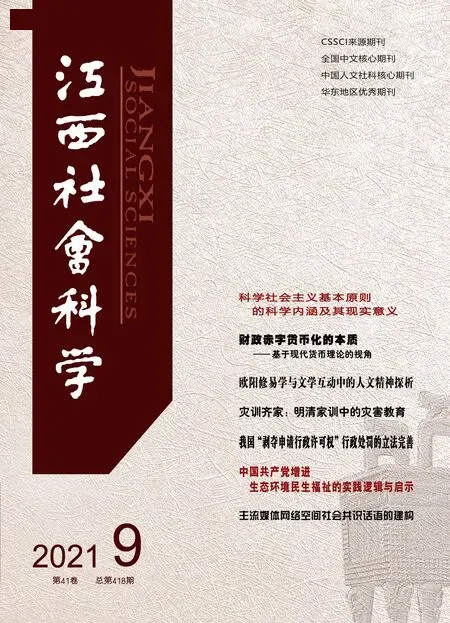青年網紅打卡文化的符號消費及反思
■柳 瑩
近幾年,網紅打卡文化在青年群體中十分流行。通過研究發現,身份建構、社交維系、營銷刺激、審美實踐和數字記憶五個維度的動因共同建構了青年群體進行網紅打卡式消費的行動邏輯。然而,過度沉迷網紅打卡文化會令青年群體迷失于網紅景觀之中,自我主體性面臨解構風險,并且滋長超前消費、跟風消費等不良之風,還會引發市場標準的畸形化等諸多問題。這需要青年個體、政府職能部門和市場合作發力,共同建設繁榮且有序的正規市場,為青年群體塑造正確消費觀念,引導青年消費文化健康發展。
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2020年我國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高達54.3%,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助推力。在整個居民消費群體中,青年群體由于接受能力強,善于制造新消費觀,對其他成員的消費行為具有示范性效應,因此在居民消費群體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幾年來,青年網紅打卡式消費現象蔓延于微博、微信、小紅書等社交平臺,其作為一種由媒介技術、社會文化和青年自我意識互相勾連而形成的消費實踐,不斷嵌入青年群體的日常生活,并且演變為一種備受追捧的時尚文化。
打卡,原意是指公司職員將磁卡放置于讀卡機內,從而記錄上下班時間的考勤行為,在網絡傳播語境中,引申為利用自媒體發布、分享自己消費體驗的一種標記行為,其中蘊含著“這個地方我來過”“這個產品我用過”的表達意圖。青年群體打卡消費的對象種類繁多,例如旅游景點、藝術展覽、時尚店鋪、美食飲品等,打卡者一般會在鏡頭中對它們進行精致構圖并按下快門,接著選取適配濾鏡對圖片美化一番,之后配上精心撰寫的文案,上傳至新浪微博、微信朋友圈、小紅書等社交平臺,由此完成整個打卡流程。與“打卡”緊密相關并經常一同出現的詞匯是“網紅”,這是由于青年打卡的對象一般是同輩群體中的流行事物,網紅城市、網紅景點、網紅奶茶、網紅護膚品等,一切在網絡空間中廣受歡迎的事物皆可加上“網紅”作為前綴,并且因此具備了值得打卡的價值,“最值得打卡的十大網紅勝地”“還不打卡這家網紅餐廳,你就out了”等成為眾多商家營銷宣傳的慣常話術。
那么,為何青年群體如此熱衷于網紅打卡式消費呢?這種消費模式盛行的背后折射出怎樣的消費觀念與心理呢?本文將聚焦于這一現象,從身份認同、符號消費、自我呈現等理論視角出發,分析青年群體打卡式消費的行動邏輯和實踐策略,了解驅動青年采取這一行為的動機和意圖,以此管窺新時代青年的消費心理和生活方式,進而探討當前青年消費文化的嬗變特征和存在的問題,提出正確引導青年群體消費的對策建議。
一、青年網紅打卡文化興起的社會背景
(一)身份認同:社會轉型期青年群體的普遍焦慮
身份認同即個人對自我身份的確認,由自我認同與群體認同構成,前者強調個體通過自我反思從而形成的主體身份感和獨特意識,后者則指個體將自身歸屬于某一特定群體,并從群體中體驗到價值與情感。[1](P7-24)身份的確認關系到個體在社會存在的合理性,是個體獲取生存意義、發展目標的必要條件,然而青年群體由于所處時代背景與個體成長階段的特殊性,他們的身份認同不得不面臨來自內外雙重轉型的壓力:一是經濟社會正處于轉型期,新舊秩序交替更迭,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人才競爭愈發激烈,社會壓力指數不斷攀升;二是青年個體自身的身份轉型,畢業后便告別象牙塔般的校園,踏足社會,搖身變為“打工人”。當微觀個體的角色轉變遇上社會體制、結構、形態的過渡和變遷,一系列挑戰向青年群體襲來,職場奮斗中的困境與壓力、人際交往中的孤獨與困窘、戀愛婚姻中的坎坷與挫折等令許多青年無所適從,他們在迷茫與焦慮中產生對自我的懷疑,同時在原子化社會中難以尋求穩定的群體聯結,認同危機演變為這一群體普遍存在的癥候,青年群體由此萌發出對自我認同和群體認同的強烈渴求。
(二)消費轉向:崇尚顏值與社交屬性的符號消費
凡勃侖在《有閑階級論》中提出“炫耀性消費”這一概念,指出人們利用以“浪費”“奢侈”為特征的消費行為彰顯自身的財富地位。[2](P65-66)法國社會學家讓·鮑德里亞在其著作《物體系》《消費社會》中,強調了商品的符號價值正凌駕于物質價值之上,使得人們對物品的實質需求日漸弱化,并認為:“消費系統并非建立在對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上,而是建立在某種符號和區分的編碼之上。”[3](P70-71)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物質豐富充裕,符號消費備受青年群體推崇,相比商品的功用、性能等實質性價值,他們愈發追求商品所象征的某種社會文化意義,借助消費表達自身的身份地位、情趣品位、個性稟賦等特征[4]。在碎片化、快節奏、媒介化的社會里,除了商品的品牌、價格以外,顏值也成為青年群體價值判斷的關鍵要素,產品是否具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包裝設計,是否可以成為朋友圈或微博內容的素材,有時比它的成分、材質、性能、耐用性更為重要,網紅景點、網紅家電、網紅食品等由于具備高顏值、高流行度、高辨識度的特征,得到廣大青年消費者的喜愛。
(三)技術更迭:社交媒體建構青年表達的“曬”空間
去中心化是網絡技術的突出特征,它使得社會權力關系被重新構建,大眾傳播媒體的渠道優勢日益消解,傳播權、表達權逐漸向曾經處于被動地位的“受眾”下移,每個普通人都可以利用媒介記錄生活,并且在公共化的平臺中進行分享。QuestMobile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Z世代”(95后、00后)移動互聯網活躍用戶規模已經達到3.2億,占全體移動網民數的28.1%,月人均使用時長接近175個小時,高出全網用戶35個小時,“Z世代”用戶中在社交應用方面的月活躍用戶占比高達83.6%。[5]由此可見,媒介化行為已經成為青年群體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媒介行為與日常生活加速融合,青年逐漸成為新浪微博、微信、QQ、小紅書等社交媒體的“重度使用者”。社交媒體構建了一個全球化平臺,方便人們傳播交流各類話題,并且賦予人們構建自我、管理社會關系、進行社會監控和獲取社會資本的權利。[6]青年充分利用具有開放性、交互性、即時性的各種社交媒體,在這類平臺上主動分享關于自我的信息和動態,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細微瑣事、情感體驗、消遣娛樂,也涵蓋對時事熱點的認知看法和對學習工作的思考感悟,流行語“遇到事情不要慌,先發個朋友圈”雖隱含些許調侃意味,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下青年人“諸事皆可曬”“我曬故我在”的心理與狀態。
二、青年網紅打卡消費實踐的具體動因
(一)身份建構:符號堆砌的理想自我
自我呈現是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提出的概念,是指個體在特定觀察者面前通過“表演”來影響他人正在形成的情景定義,以此控制他人對自己形成的印象和對待自己的方式。[7](P1-40)他提出的擬劇論將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交往比喻為舞臺表演,然而,在媒介技術的更迭演進與移動終端的日益普及之下,自我呈現的場域由現實生活延伸至網絡虛擬空間,人們在形形色色的社交媒體平臺樂此不疲地進行著自我“展覽”(exhibition)。[8]
相比于生活中的“前臺”,社交媒體劇場更具優勢。一是表演內容可依自己需求進行個人定制,例如圖片修飾、文案撰寫、視頻剪輯等,最大限度地將與自我相關的文本美觀化、場景化處理,使其更符合自身設定的“劇本角色”。二是觀眾數量更多、類型更廣,除了現實生活中的親朋好友,還包括相識于網絡的陌生人,甚至可以實現“分組可見”的指定傳播。心理學研究顯示,當個體自我概念(如地位、自尊)受到威脅時,通過消費能夠應對威脅的產品可以得到相應補償[9],由此可見,網絡曬圖、曬視頻的打卡行為實質上是青年群體對炫耀性商品的二次消費,是青年群體建構自我認同和紓解焦慮情緒的選擇之一,借助網絡打卡,網紅產品所具有的文化價值和符號意義在社交媒體上被廣而告之,一杯dirty咖啡(網紅冰牛奶咖啡)、一幅藝術畫作、一份擺盤考究的餐食等,這些象征小資生活品位的物品,都是描摹網絡個人畫像的像素點,而手機鏡頭、P圖軟件和美化濾鏡等則成為智能畫筆,青年群體借此對“理想自我”進行充分自由地界定與展示。正如雪莉·特克爾所言:“互聯網中,人們真實、復雜的一面被縮小了,完美、精致的一面則被放大了。在分享的過程中,人們滿足了自己被重視、被認可、被崇拜的需要,甚至還會漸漸對自己產生一種自帶光環的幻覺。”[10]
(二)社交維系:圈層互動中的社交貨幣
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增強了社會的異質性,在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是因社會契約、經濟利益關系等“理性意愿”而相互聯結,缺乏親密、友誼、共同的信仰等情感要素。[11]然而,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遷對應著社會交往方式的變化,媒介生成的交往場景及其信息系統的建構,影響了人們交往行為的運行機制[12],互聯網技術拓寬了個體建構身份與群體交流實踐的可能性,基于興趣、愛好、價值觀等層面認同形成的網絡圈層正全方位地滲透至現代青年群體的生活之中。由于與生俱來的社會性,青年依附群體的心理需求被不斷激發,因此他們將商品的符號意義作為自我概念的外在表達和與社會聯系的載體[13](P111-125),通過消費不同的物品來界定自己與物品相符的身份,將自己與某種類型等同而與其他人相區別[14],利用消費群體共同認可的文化符號以及追求與群體成員一致的審美品位等方式,建立起獨特的身份識別系統,并且以此融入圈層,擺脫被孤立與排斥的窘境。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提出“社交貨幣”概念,將其定義為“存在于虛擬的網絡及離線的現實中所有真實而又潛在的資源”,而“人們通過社交活動所產生的連鎖反應則是社交貨幣購買到的‘商品’”。[15](P30)打卡式消費以數字化照片或流動式影像作為載體,在青年的社交圈層之中傳播擴散,作為一種表征群體身份的文化符號消費行為,一旦得到群體成員的接納、認可與欣賞,青年個體便可獲取群體歸屬感和認同感,如去了一個網紅打卡景點、喝了一杯近期流行的網紅奶茶等,這些行為或能進一步鞏固關系,提供與同事好友討論的共同話題,增進彼此的情感交流;或能實現弱關系的連接,在網絡結識現實生活中未曾謀面但志趣相投的好友。從某種意義上說,打卡式消費行為已經成為青年群體賺取情感補償和人脈資本的一種社交貨幣。
(三)營銷刺激:商家與媒體共謀下的盲目消費
媒介技術的顛覆性變革不僅重構了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也深刻改變了商家營銷推廣的渠道與方式。在社會化營銷的大勢所趨下,商家們紛紛在微博、朋友圈、抖音等陣地“安營扎寨”,精心炮制各種吸睛的營銷策略,通過各式各樣炫目迷人的推銷手法,誘惑人們產生難以壓抑的消費欲望。比如朋友圈打卡集贊享優惠、微博打卡曬單可免單、大眾點評推出的“霸王餐”等推廣活動,吸引眾多青年踴躍參與社交媒體的打卡式消費。
社交媒體的普及也深刻改變了青年群體的信息獲取、思維方式、交往行為、消費習慣。尤其是在短視頻、直播平臺等網絡應用的興起之下,一批娛樂型、消費引導型“網紅”開始崛起[16],他們借助社交媒體在青年消費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打卡式消費的流行推波助瀾。早期的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多指專家學者、名人明星等具有公共屬性的特定人群,但隨著媒介形態的迭代演化,草根階層借助網絡技術的低門檻、開放性等優勢躍升為意見領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由于網絡技術引發的去中心化以及再中心化這一新傳播革命,大眾網紅逐漸迭代為圈層網紅。他們往往顏值高、才藝豐富、活潑善談,并且在自己擅長的細分領域中深耕細作,不斷吸引圈層粉絲的關注,實現注意力資源向經濟收益的轉化,比如擅長口紅推薦的直播博主李佳琦、熱愛美食探店的B站up主盜月社、分享穿衣搭配的小紅書達人三木三木呢……許多平平無奇的產品和無人問津的店鋪、景點,經過網紅的“種草安利”,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競相追捧的搶手貨和趨之若鶩的打卡地。網紅一詞也由對網絡紅人的指代,延伸泛化至對一切在網絡中具有知名度和流行度的事物的形容和稱謂。
(四)審美實踐:彰顯審美趣味與創造力
英國社會學與傳播學教授邁克·費瑟斯通提出“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命題,學者陶東風認為這指的是在藝術和文化領域發生的普遍審美活動開始滲透進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文化現象。[17]相比于文字敘事對文學素養、知識底蘊和思想閱歷的高要求,圖片拍攝和短視頻制作的技能門檻大幅降低,并且在各種拍照軟件和短視頻應用功能的不斷優化之下,美顏、濾鏡、修圖、拼接等編輯功能的操作愈發簡單,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手機、一個鏡頭,就能夠生產符合自己想象的視像作品,審美浪潮由此席卷了現代人的日常生活。
通過對社交平臺與打卡消費相關的內容進行觀察,可以發現這些內容大多呈現出高度的視覺導向和視覺指引,物品時尚精美的包裝設計、餐廳高端大氣或溫馨雅致的環境氛圍、餐品賞心悅目的擺盤、展覽濃厚的藝術氣息、主人公的精致妝容和光鮮衣著,以及經過精巧設計的擺拍動作、場景構圖、濾鏡修飾、文字渲染等,都凸顯出傳播主體對視覺風格和審美藝術的悉心建構。對于青年而言,通過曬圖實現的打卡消費行為,也是一種審美實踐,在對消費符號、消費對象和消費風格等的篩選和加工中,他們努力捕捉和發掘生活的美感,詮釋生活細節中的審美趣味和審美意義。
(五)數字記憶:記錄日常生活中的儀式感
時空性是規約人類存在方式的基礎性要素,當前的新媒介技術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時空維度,具體而言,新媒體使得時間的逆轉與交織成為可能,并且實現了虛擬空間和真實空間的轉換與交融。[18]經由人們網絡分享的打卡消費經歷,使得當下因消費產生的情緒體驗、象征意義被長久保存,積累沉淀為鮮活生動的“數字日志”,人們借助網絡技術可以隨時調取,從而喚起彼時彼刻的回憶與感受。儀式感是一種將日常行為儀式化以賦予其意義的行為,被視作一種熱愛生活的積極態度,去高級餐廳享用美食,去網紅景點拍美照,去看期待已久的電影……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儀式感,鐫刻在每一張精心拍攝的打卡照片里,儲存在每一段美化編輯的打卡視頻里,在青年看來,這些場景或片段可以表達他們對生活情趣的追求,傳遞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三、青年網紅打卡消費現象的反思
(一)景觀泛濫下的主體迷失
居伊·德波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景觀社會”的概念,即“在現代生產條件蔓延的社會中,其整個的生活都表現為一種巨大的景觀積聚,曾經直接地存在著的所有一切,現在都變成了純粹的表征”[19](P58),以此批判當時電視媒介滲透各處的視覺霸權。隨著媒介技術和視覺技術的不斷發展,視覺轉向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描繪勾勒世界的方式開始由語言主導的敘事范式向圖像范式轉變。視覺元素隨處可見,從商場貨架上形形色色的產品包裝設計,到街頭琳瑯滿目的廣告牌位,再到手機屏幕上隨手指滑動而無限更新的各種短視頻,視覺邏輯逐漸主導了人們的文化生產和消費。在這樣的消費語境下,精神性消費超越物質性消費,大眾日趨追求感官愉悅和視覺快感,“商品拜物教”轉向了“形象拜物教”。[20]
商家深諳“視覺消費”之道,制造著符合青年群體喜好的各種網紅打卡地和網紅打卡產品,譬如:餐廳裝修一定要走Ins風(instagram上的圖片風格)或北歐風,天堂鳥綠植、龜背葉裝飾、黃銅色餐具、原木色桌椅等元素是標配;飲料瓶設計一定要特別,充滿少女心的櫻花色、曼妙別致的曲線瓶、搞怪逗趣的文案都可以與瓶身結合;奶茶包裝一定要有風格,古典中式風、輕奢簡約風、英倫復古風、萌萌可愛風應有盡有……總之,萬變不離其宗,必須遵循“顏值即正義”的終極要求。與之相對應的是青年對這些“網紅景觀”的單向度認同。他們興致勃勃地來到網紅打卡地拍照,然后在朋友圈或微博曬出這些精美的照片,當各類社交平臺充斥著這些“網紅打卡”的內容時,為了避免因落伍而遭受圈層排斥,更多的人加入“網紅景觀”的復制生產和流通擴散中,于是小紅書上出現諸如“怎樣拍出高級的打卡照”“探店拍照教程”等帖子,專門提供服飾穿搭、拍照姿勢、濾鏡調色等多方面的建議,而“排隊半小時,拍照一小時,吃完五分鐘”正在成為眾多青年人的消費方式。需要警惕的是,當他們迷戀于那些千篇一律的打卡照收獲的點贊時,消費行為和社會交往的本質意義被遺忘,自身的主體性面臨被解構的危險。正如鮑德里亞所言:“在技術和符號的雙重控制和操作下,客體大量的繁衍增長,客體對于主體不斷增長體現了無比的技術優勢,并使得客體最終取得了勝利,達到了狂熱的程度,由此帶來傳播或者可以被稱為交往的迷狂。”[21](P282)
(二)助長攀比、跟風等不良消費觀念
對青年群體而言,網紅打卡消費行為是一種精致生活的體現,在社交平臺曬打卡照可以獲得他人稱贊,幫助自己融入圈層,打造懂生活、講情調、有品位的個人形象。然而,精致生活的維持離不開一定的經濟基礎,尚處于學校或剛步入職場的大部分青年生活并不寬裕,在房租水電、車貸房貸等開銷支出的壓力下,對精致生活的過分追求可能演變為一種心理枷鎖,產生超前消費、攀比消費、面子消費等不良消費心態,使得“精致窮”“月光族”“負債族”等現象層出不窮。根據支付寶2020年發布的《年輕人消費生活報告》數據顯示,中國1.7億90后中,使用花唄服務的用戶高達6500萬,意味著每10個90后中就有近4人靠貸款消費[22];2019年尼爾森市場研究公司發布的《中國消費年輕人負債狀況報告》則顯示,在中國18-29歲的年輕人中,總體信貸產品的滲透率已經高達86.6%,即使扣除作為支付工具的部分后,實質負債的年輕人比例也高達44.5%[23]。由此可見,許多青年正在通過“花明天的錢”使自己“過今天的癮”,稍有不慎,還可能落入“校園貸”“套路貸”“高利貸”“裸貸”等圈套中。曾經在網絡上風靡一時的,那些為了去上海寶格麗酒店拍打卡照組團的“拼多多名媛們”,也將虛榮心作祟下刻意包裝的“偽精致”暴露無遺。
此外,在商家的持續營銷和網紅博主的“種草安利”下,眾多網紅打卡地成為各大社交平臺上頻繁出現的場景符號。青年群體在從眾心理驅使下,蜂擁一般前往這些餐廳、景點、書店、展覽打卡,使得這些地點交通堵塞、人滿為患。部分網紅為了使自己的打卡照更加具有視覺沖擊力和吸引力,不惜在冰天雪地里穿著比基尼拍照。更有甚者,全然不顧來往的重型貨車,在青海315國道U型路段肆意拍照,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這種盲目跟風的套路式消費習慣是消費需求被異化的表征,夸示性的消費欲望僭越了其他需求,人們在“來了買票,進門拍照”的模式下沉浸于影像謊言之中,成了欲望訴求的鏡像,淪為了巴赫金所預言的“廣場式狂歡”的文化標本。[24]
(三)表里不一、管理滯后的畸形市場
在資本、商家、媒介技術和網民的共同建構之下,網紅打卡文化迅速流行。為了招攬更多顧客,成功打造一家網紅店成為許多商家的理想目標,但是由于部分商家操之過急,致使各種消費亂象屢見不鮮。例如:曾被媒體曝光的上海鮑師傅、喜茶等網紅店,通過雇傭排隊充場人員的方式來制造門庭若市的假象;一些店鋪則花費重金邀請網紅博主寫軟文進行營銷推廣,唯流量馬首是瞻,卻不注重產品質量;或是炒作一些花里胡哨的概念,跟風同質化的裝修模板,吸引年輕人去圍觀,將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拋諸腦后。這些舍本逐末的行為注定不能為店鋪帶來長期效益,因此許多所謂的網紅店鋪如曇花一般,只是短暫地出現了一段時間,便黯然退出市場,如曾以新奇的“占卜”創意火爆抖音的答案奶茶、主打用泡面治愈憂傷卻毫無技術含量的泡面小食堂等。
除此之外,一些網紅景區借助短視頻營銷在諸多旅游勝地競爭中異軍突起,人們紛紛在節假日慕名前來,但與日益洶涌的客流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景區未能及時提升的管理能力和服務水平,導致問題頻出。如:由于與動漫建筑高度相似而走紅網絡的重慶洪崖洞,因游客數量過多導致周邊馬路水泄不通,人們寸步難行;多地景區懸空式棧道人滿為患,限流不力,甚至個別景區因出現安全事故被關停;湖南臨武滴水源景區“天空之境”景點因與宣傳照反差太大被網友吐槽名不副實,等等。這些例子都反映出網紅景區在兼顧“流量”與“質量”時的力不從心,使得眾多游客乘興而來卻敗興而歸。
四、結語
在認同焦慮、消費轉向和技術更迭的社會背景之下,網紅打卡消費行為是青年群體在社交平臺的一種自我呈現策略。他們通過曬圖分享的方式,利用各種符號建構富有品位、精致的個人形象,并以此作為“社交貨幣”,避免圈層排斥,獲取同輩贊許。與此同時,這一行為也承載著他們的日常生活記憶,是留存情緒與感受的鮮活記錄,并且彰顯著他們獨特的審美品位與審美理念。商家與網紅的營銷刺激則促使該現象愈發流行,過于沉迷網紅打卡式的消費文化會令青年群體迷失于網紅景觀之中,逐漸喪失自我主體性,并且滋生攀比消費、超前消費等不良之風,還會引發市場標準的畸形化等諸多問題。筆者認為,這需要青年個體、政府職能部門和市場合作發力,共同建設繁榮且有序的正規市場,為青年群體塑造正確消費觀念,引導青年消費文化健康發展。
青年要樹立對網紅打卡消費的正確認知。一方面,它可以帶給年輕人情感上的滿足,樹立求新求異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在虛榮心和攀比心的作祟之下,網紅打卡消費會成為資本與商家營銷的手段,甚至成為禁錮青年思想的精神枷鎖。年輕人通過網紅打卡消費追求精致生活并沒有錯,但“精致”的標準需要結合自身條件去衡量,若是跳出自己原有階層或接近階層的區間去確認自己的身份認同,則容易因為“跳躍式身份認同”陷入“假精致”的消費陷阱中[25],導致入不敷出、提前透支、負債累累等惡性后果。因此消費的尺度應當受到自身消費能力的制約,要時刻保持對消費主義的警惕和清醒,盡量減少沖動消費、從眾消費、面子消費等情緒化消費。另外,糾正消費能力標榜社會地位的狹隘思想,青年群體對網紅產品的追隨本質上是對物質主義的遵從,忽略了對精神生活的關注,個人的品質、修養、內涵同樣可以構建良好個人形象,而這來源于一種積極充實、努力向上的精神狀態,堅持讀書,保持鍛煉,認真對待學習與工作,積極面對生活中的大小事,也可以成為生活的藝術家。
就政府層面而言,相關職能部門要加強監管。由于網紅產品或店鋪都是利用網絡營銷擴大知名度,因此相關職能部門可利用大數據技術,從搜索引擎、外賣平臺、點評網站等信息渠道抓取相關數據,了解當地網紅市場業態的整體情況,將銷量排名前列的店鋪列入重點監管名單,采取明察暗訪雙管齊下的方式,定期檢查其營業許可證信息、門店擴張規模、產品質量安全等,結合消費者投訴舉報數量、頻率等及時監督這些店鋪的日常經營狀況,形成常態化監管機制。加大處罰力度,對于產品和服務質量不達標的網紅景區、酒店、民宿等,可以采取新聞曝光、責令停業、降星摘牌等措施倒逼整改,對于部分網紅餐廳無視食品安全、雇傭“黃牛”排隊的行為,監管部門應當按照法律法規嚴懲不貸,使其付出高昂的違法成本。
除此之外,網紅景點、店鋪、酒店、展覽等也應加強自律,嚴格遵守行業規范和運營守則,嚴格把控產品和服務質量,并且充分挖掘產品的文化情感魅力,從簡單的規模擴張轉向內涵式、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從而擺脫短壽的命運,使“網紅”可“長紅”,豐富青年群體的精神與物質生活,促進國家經濟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