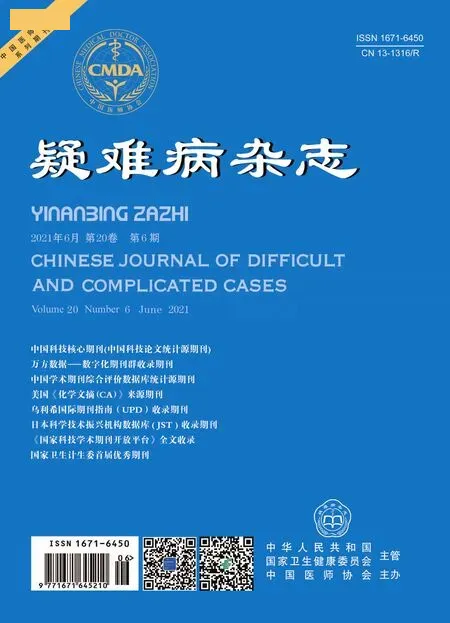以不明原因發熱為主要表現的淋巴瘤患者44例臨床特征分析
湯影子,劉慧敏,郭建瓊,夏杰
2017年全國發熱待查診治專家共識將不明原因發熱(fever of unknown origin,FUO)定義為:發熱時間持續3周以上,體溫≥38.3℃,經住院詳細檢查1周后仍不能明確診斷者[1]。已知可引起FUO的病因達200多種,涉及多學科、多系統,因缺乏特異性臨床表現及實驗室檢查陽性結果,是臨床上常見的疑難病癥。常見引起FUO的病因包括感染性疾病、非感染性炎性疾病、惡性腫瘤性疾病等。在腫瘤性疾病中,淋巴瘤是引起FUO的最主要原因,且往往病程長、確診比較困難。現總結以FUO為主要表現的淋巴瘤患者臨床特征,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14年1月—2020年11月陸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確診為淋巴瘤的成人FUO患者44例,均符合FUO診斷標準[1];病理診斷參照2016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淋巴瘤分類標準[2]。其中男33例,女11例,年齡18~75(45.3±16.1)歲,體質量46.1~82.2(61.3±13.7)kg,所有患者均無家族淋巴瘤病史。
1.2 臨床表現 除發熱以外,其他常見癥狀包括乏力35例(79.5%),體質量減輕24例(54.6%),肌肉關節痛11例(25.0%),畏寒寒戰9例(20.5%),咳嗽咯痰7例(15.9%),咽痛6例(13.6%)等;最常見的體征為淋巴結腫大15例(34.1%),分別位于頸部、鎖骨上、腋窩、腹股溝區,合并皮疹9例(20.5%),合并肝脾大7例(15.9%)。
本組患者熱程中位數為6周(3~90周),熱程3~4周者13例(29.5%),5~13周者24例(54.6%),≥14周者7例(15.9%);表現為低熱及中等程度發熱23例(52.3%),高熱患者21例(47.7%);熱型分布:稽留熱1例(2.3%),弛張熱1例(2.3%),間歇熱3例(6.8%),不規則熱39例(88.6%)。
1.3 實驗室檢查 血常規檢查:白細胞計數降低16例(36.4%),血紅蛋白降低14例(31.8%),血小板降低14例(31.8%),兩系以上降低15例(34.1%);腫瘤標志物異常15例(34.1%),主要為CA125及CA199升高;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升高28例(63.6%);總膽紅素升高9例(20.5%);肌酐水平升高3例(6.8%);乳酸脫氫酶(LDH)升高26例(59.1%);鐵蛋白升高18例(40.9%);降鈣素原(PCT)升高17例(38.6%);C-反應蛋白(CRP)升高29例(65.9%);紅細胞沉降率升高29例(65.9%);血清球蛋白升高20例(45.5%);EB病毒PCR熒光檢測陽性7例(15.9%);骨髓涂片見不明分類細胞/淋巴瘤細胞16例(36.4%)。
1.4 影像學檢查 所有患者均行18F-脫氧葡萄糖正電子發射斷層顯像/計算機體層掃描(PET/CT),其他常用影像學檢查包括腹部彩色超聲、心臟彩色超聲、胸腹部CT、磁共振成像、全身骨掃描等。常見的影像學異常包括脾大25例(56.8%),肝大20例(45.6%),縱隔淋巴結腫大15例(34.1%),腹腔淋巴結腫大20例(45.6%),腹膜后淋巴結腫大11例(25.0%),腹腔積液4例(9.1%),胸腔積液3例(6.8%)等。本組病例PET/CT SUVmax平均值為8.62±4.95,其中2~4者6例(13.6%),>4~8者21例(47.7%),>8者17例(38.6%);攝取值最高的部位分別為淋巴結25例(56.8%),脾臟5例(11.4%),骨骼10例(22.7%),肝臟2例(4.5%)等。
1.5 病理類型 霍奇金淋巴瘤4例(9.1%),非霍奇金淋巴瘤40例(90.9%);B細胞淋巴瘤7例(15.9%):包括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3例(6.8%),濾泡性B細胞淋巴瘤2例(4.5%),伯基特淋巴瘤1例(2.3%),未分型1例(2.3%);T/NK細胞淋巴瘤33例(75.0%):包括外周T細胞淋巴瘤10例(22.7%),血管免疫母細胞性T細胞淋巴瘤6例(13.6%),ALK陰性的間變性大細胞淋巴瘤2例(4.5%),ALK陽性的間變性大細胞淋巴瘤3例(6.8%),皮下脂膜炎樣T細胞淋巴瘤2例(4.5%),脾臟T細胞淋巴瘤1例(2.3%),侵襲性NK細胞白血病2例(4.5%),NK細胞淋巴瘤5例(11.4%),未分型2例(4.5%)。
1.6 誤診情況 本組病例最終確診與初步診斷不符合者23例(52.3%),其中初診為結核病并行診斷性抗結核治療7例,初診為細菌感染性發熱(包括肺部感染、膿毒癥等)并予以廣譜抗生素治療12例,初診為病毒性感染2例,初診為結締組織病并予以激素治療2例。
1.7 診斷及鑒別診斷 本組患者均經過組織活檢病理診斷確診,13例患者經過骨髓穿刺病理活檢及骨髓免疫組化、染色體檢查等確診,9例通過淋巴結穿刺活檢診斷,18例通過淋巴結活檢診斷,2例通過皮膚活檢診斷,1例通過骨骼活檢診斷,1例通過肝活檢診斷。主要的鑒別診斷包括膿毒癥、肺部感染、結締組織病及結核病。
1.8 治療及預后 44例患者按照Ann/Arbor分期(Cotswolds修訂)標準,Ⅰ期1例(2.3%),Ⅱ期2例(4.5%),Ⅲ期24例(54.6%),Ⅳ期17例(38.6%)。按照國際預后指數(IPI)分組,中/高危及高危組39例(88.6%),低危及低/中危組5例(11.4%)。39例患者在住院期間接受聯合化療,其中15例患者在后續治療期間死亡;5例患者因病情危重、進展迅速,確診后未接受聯合化療即死亡。
2 討 論
發熱在臨床上十分常見,且常是首發甚至是唯一癥狀。在可能引起FUO的腫瘤性疾病中,淋巴瘤是最主要原因[3]。淋巴瘤引起發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1)腫瘤細胞和單核巨噬細胞產生的細胞因子(如白介素-1、白介素-6、腫瘤壞死因子、干擾素等)作為內生致熱源作用于體溫調節中樞而引起體溫升高[4];(2)腫瘤細胞侵犯骨髓或脾臟,引起全血細胞減少及免疫缺陷,使各種機會性感染增加而發熱;(3)淋巴瘤細胞侵犯中樞神經系統導致中樞性發熱。以FUO為主要表現的淋巴瘤臨床癥狀缺乏特異性,熱型無規律,本組44例淋巴瘤患者中39例表現為不規則熱,從熱型上也難以總結規律,可能與使用抗生素、非甾體類解熱鎮痛藥及激素等綜合因素有關。最常見伴隨癥狀為乏力、體質量減輕及肌肉關節痛,抗感染治療往往不能緩解發熱及其他伴隨癥狀,但激素及非甾體類解熱鎮痛藥有效,這也是淋巴瘤患者被誤診為結締組織病的重要原因。本組患者最常見體征為淺表淋巴結腫大、皮疹及肝脾大,合并淺表淋巴結腫大患者需與淋巴結結核、組織壞死性淋巴結炎等疾病相鑒別。在本組誤診為結核病的7例患者中,5例合并有淺表淋巴結腫大,但淋巴結穿刺活檢未能確診,最后經淋巴結活檢證實;合并皮疹及肝脾大患者需與結締組織病、特殊病原體感染(如黑熱病、組織胞漿菌病)相鑒別,通過骨髓涂片檢查可以初步排除特殊病原體感染。
本組病例常見的實驗室指標異常包括血象降低、炎性指標升高,淋巴瘤患者血象降低較為常見,如合并噬血細胞綜合征更提示預后較差[5-6]。文獻報道LDH在淋巴瘤早期診斷和預后判斷中有價值,而CRP、鐵蛋白及PCT檢測有助于鑒別感染性與非感染性發熱[7-11],但本研究納入病例資料有限,需擴大研究以進一步探討炎性指標在區分腫瘤性及非腫瘤性FUO患者中的診斷價值。
FUO患者應常規行骨髓穿刺和活檢,文獻報道[12],骨髓檢查可見不明分類細胞患者中伴隨脾大、合并EB病毒感染、診斷為惡性腫瘤者較骨髓未見不明分類細胞患者所占比例更大,而未見不明分類細胞患者多為良性疾病。本組淋巴瘤病例中36.4%患者骨髓涂片可見不明分類細胞/淋巴瘤細胞,提示骨髓檢查未見不明細胞患者不能因此排除淋巴瘤,可能存在疾病早期淋巴瘤細胞尚未入髓等情況,必要時需加做免疫組化、染色體等檢查協助診斷。
18F-FDG PET/CT顯像是18F-FDG功能代謝圖像與CT解剖結構圖像的結合,不僅可以顯示葡萄糖高代謝灶的功能狀態,而且能精確地顯示微小病變,相比單獨PET檢查或CT檢查,PET/CT能一次性完成全身掃描,早期發現病灶,且可對常規影像學檢出的病灶加以定性,具有良好的敏感度、特異度和準確率[13-15]。此外有文獻報道PET/CT對于淋巴瘤的分期、療效評價和預后評估有意義[16]。本組淋巴瘤患者PET/CT SUVmax平均值顯著升高(>8),提示PET/CT SUVmax明顯升高的FUO患者應高度懷疑淋巴瘤診斷,如影像學檢查無法區分腫瘤、結核或炎性病灶,宜盡早行組織活檢[17]。
本組所有淋巴瘤患者均經過組織活檢病理確診,但部分患者可能通過一次活檢尚不能明確診斷,或存在病理組織樣本獲取困難等問題。有報道指出,對于長期發熱高度懷疑淋巴瘤患者,即便其沒有明顯皮損表現,通過隨機皮膚組織活檢仍然有助于提高血管內B細胞淋巴瘤的診斷率,活檢取材需包括至少3個部位,分別為雙側大腿上部及腹部[18]。
淋巴瘤是能夠引起FUO的一大類疾病,確診較為困難,臨床上應予以重視。以FUO為主要表現的淋巴瘤患者臨床癥狀及體征缺乏特異性,需與感染性發熱、結核病、結締組織病等相鑒別。如經足療程抗感染治療效果欠佳患者應懷疑該診斷,并盡早行骨髓穿刺活檢、PET/CT及組織活檢以確診。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無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
湯影子:實施研究過程,資料搜集整理,論文撰寫;劉慧敏、郭建瓊:資料搜集整理,分析數據,論文修改;夏杰:課題設計,論文審核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