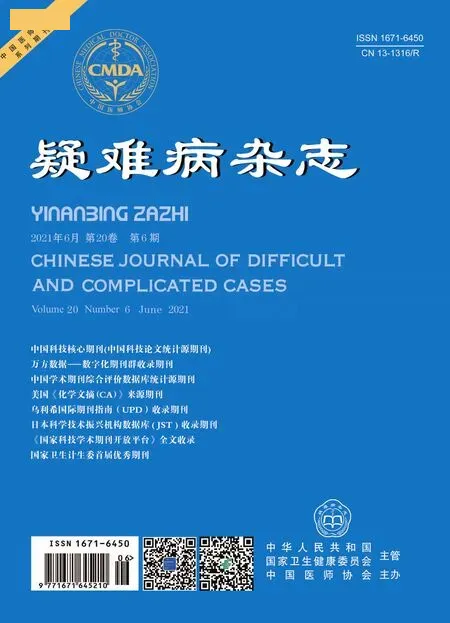冠狀動脈血管生成的機制及治療分子靶點研究進展
顧寧越,張艷達綜述 梁春審校
冠心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是發達國家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國患病率急劇上升、醫療費用支出日益增加的一種心血管疾病[1]。其主要病因在于動脈粥樣硬化(atherosclerosis,AS)斑塊發生發展,造成管腔狹窄或閉塞,引起心肌灌注減少,誘發心肌梗死等臨床事件發生[2]。藥物治療和血運重建術極大地改善了冠心病患者的預后,然而,不能耐受手術或手術獲益有限的患者,需考慮血管新生治療。治療性血管新生(therapeutic angiogenesis)是冠心病藥物治療的新靶點,通過給予生長因子、基因、細胞以促進血管新生,從而達到改善心肌血供的目的[3]。
血管生成過程包括血管新生(angiogenesis)和動脈生成(arteriogenesis)2個階段。血管新生和側支動脈生成可以有效代償心肌缺血,挽救心肌活力。近30年來,治療性血管新生領域持續探索性研究,然而,在粥樣硬化斑塊進展階段,病理性血管新生也曾作為治療靶點,抗血管生成治療在動脈模型中取得進展,但進入臨床研究后未獲得成功。抑制或促進血管新生需要考慮冠心病發展的不同階段,選擇合適的時間窗,才能避免不良事件的發生[4]。
1 冠心病血管新生的機制研究
1.1 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內的血管新生 低氧是引起AS斑塊內血管新生的基本原因。正常情況下,血液中的氧氣可以通過擴散作用從管腔進入血管壁,隨著AS斑塊的進展,AS核心區域血管壁增厚,炎性反應增強,斑塊內的氧耗不斷增加,顯著減少了氧向內膜的擴散,因此產生不平衡的供氧和需氧狀態,導致低氧誘導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HIF)被激活表達且不斷累積[5]。
炎性反應是AS斑塊內血管新生的刺激因素。大量炎性細胞可以通過高滲透性新生血管進入斑塊內,分泌大量的促血管新生因子,造成局部 “血管新生微環境”,促進該部位的血管新生,炎性反應和斑塊內血管新生兩者作用相互疊加,會使 AS 斑塊更有破裂傾向[6]。
生長因子是AS斑塊血管新生的調節因素。最受關注的是VEGF和VEGFR上調,強烈地引起增殖、出芽,內皮細胞管道形成,VEGF激活下游信號通路,轉錄表達促血管新生的相關基因,如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TGF-β)等。FGF是一個重要的促血管生長因子,它促進了內皮細胞和平滑肌細胞增殖,促進毛細血管被周細胞覆蓋,以確保血管的穩定和成熟[7]。
從理論上講,抑制斑塊內病理性血管新生可防治斑塊破裂,但是,目前抗血管生成藥物治療未在臨床試驗中獲得成功,而抗血管生成藥物(主要是抗VEGF/VEGFR)在抗癌治療中的臨床試驗顯示出心血管不良反應,如引起高血壓、心肌缺血和心肌病[8],提示抗血管生成治療或許存在一個治療的時間窗,對嚴重心肌缺血或高血壓的患者是不利的。
1.2 心肌缺血部位的動脈血管新生 缺血缺氧是心肌血管新生的重要刺激因素。AS進展到管腔嚴重狹窄或阻塞時,冠狀動脈血流減少,導致心肌缺氧,缺氧誘導因子-1(HIF-1α)水平隨缺氧時間延長而升高,誘導血管新生相關因子如VEGF、紅細胞生成素(EPO)等表達增加,啟動血管新生級聯反應,在大量的血管新生誘導因子中,VEGF是新生血管形成的關鍵因素[9-10],它特異地作用于血管內皮細胞,刺激其分裂和增殖,誘導血管新生。
在冠心病患者體內,管徑較大的側支循環比缺血心肌周圍小的血管更能起到挽救存活心肌的作用。從血管新生到側支動脈生成,還需要循環中細胞因子的調控和干細胞的動員。 缺氧誘導HIF-1α和VEGF過表達,啟動了血管新生,此后,基質金屬蛋白酶(MMP)產生增加,循環中多種促血管新生的基因(如PDGF、ANGPT1、ANGPT2)及促血管新生的趨化因子和受體(如基質細胞衍生因子-1及受體CXCR4,鞘氨醇-1-磷酸及受體)表達上調,促進了內皮祖細胞(EPC)向缺氧部位的募集,促進內皮細胞(EC)的增殖和分裂(調控細胞周期和DNA的基因復制),募集支持周細胞、平滑肌細胞和基底膜細胞,通過纖維聯結蛋白輔助血管穩定性,以完成動脈血管新生。
決定冠狀動脈側支血管開放、擴張的因素還有壓力階差和切應力,冠狀動脈狹窄兩端的壓力梯度是驅動力,導致流體剪應力增大,細胞黏附分子1(ICAM1)和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VCAM1)上調,促進了單核細胞的募集,與鄰近平滑肌細胞交互作用,產生一氧化氮(NO)及其他促動脈生成分子,激活側支小動脈內皮細胞和側支形成[11]。
然而,人們經常觀察到血管新生能力被抑制而不是增強,缺血毒性(ischemic toxicity)是血管新生能力受損的重要原因,目前尚未得到充分認識。心肌缺血造成的毒性作用之一是心臟中銅含量的損失(copper loss)。雖然這種缺失的原因尚未闡明,但銅在HIF-1轉錄活性調控中的重要作用已經明確,即銅不影響HIF-1α在細胞內的表達,但影響對HIF-1轉錄復合物的形成及其與靶基因中缺氧反應元件的相互作用。補充銅可以刺激HIF-1的轉錄活性,恢復血管新生能力。認識到缺血毒性并努力克服毒性效應將有助于開發治療缺血性心臟病的新療法[12]。
2 冠心病血管生成的分子靶點
自20世紀70年代Folkman提出血管新生的概念,治療性血管新生經歷了VEGF、bFGF單基因導入到內皮前體細胞、心臟干細胞移植不同階段,對血管新生的認識亦發生了明顯變化[13]。近年來,一些小分子化合物靶點、細胞因子調節、內源性祖細胞動員等研究在冠狀動脈促血管新生方面有所突破,是極有希望的臨床候選療法,值得深入探討。
2.1 小分子化合物靶向干預 研究發現許多小分子顯示出能夠調節缺血環境下的功能性新生血管,如鈣蛋白酶、神經肽Y。鈣蛋白酶(calpain)是鈣依賴性硫醇蛋白酶,其過度表達導致了VEGF介導的新生血管結構和整合異常,DN-calpain-1或calpain抑制劑-1可改善VEGF驅動的血管新生[14]。在飲食誘導代謝綜合征豬的慢性心肌缺血模型里,鈣蛋白酶抑制劑顯示可以改善心肌灌注,增加內皮依賴性血管松弛,減少心肌凋亡,改善氧化應激;鈣蛋白酶的下游分子靶點,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SK-3β)的抑制也有同樣的有益作用[15]。
神經肽Y(neuropeptide Y,NPY)是一種與壓力、飲食和脂肪有關的神經遞質,它廣泛存在于中樞和外周神經系統,也存在于心血管系統供應血管、心肌細胞和心內膜的神經元中,參與包括血管收縮、心臟重塑和血管新生在內的生理過程[16]。飼料誘導代謝綜合征和慢性冠狀動脈病變的豬模型顯示,缺血區注射神經肽Y可改善側支循環血管生長,增加血管新生,改善心肌灌注和功能[17]。
鈣調蛋白依賴性激酶Ⅱ(Calmkii,CaMKⅡ)在缺血性心肌病中被過度激活,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CaMKⅡ的激活可能與VEGF的表達增加有關,在原發性心臟微血管分離的內皮細胞(CMECs),觀察到CaMKⅡ的抑制劑KN93抑制了細胞增殖和內皮細胞遷移,CaMKⅡ對于缺血誘導的冠狀動脈血管新生是一個重要的調節因子,它觸發了缺血條件下VEGF的表達[18]。
2.2 細胞因子調節 單核細胞活化在FGF和VEGF介導的血管新生和側支動脈生長中起主要作用。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通過增加巨噬細胞數量,誘導氧化脂質積聚,加重動脈粥樣硬化進展。人類和動物的許多研究都表明,MCP-1及其受體CCR2在動脈粥樣硬化和心肌梗死等疾病中的重要性,阻斷或沉默MCP-1/CCR2在血管治療中可能是有用的,然而,這種治療策略應該謹慎,因為有一些局限性和不良后果[19]。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注射治療慢性穩定性冠心病,有效地促進冠狀動脈側支血管生長及改善心肌功能, 但是,G-CSF也能誘導發生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臨床觀察顯示其內源性血漿水平升高是心血管事件增加的獨立預測因素,使其安全性受到質疑[20]。
2.3 內皮祖細胞動員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內皮祖細胞(EPCs)可以促進再內皮化,通過替換功能失調的內皮細胞,抑制新生內膜的形成,EPCs目前被認為是內源性血管修復的重要貢獻者[21]。有研究觀察心絞痛患者行PCI術后EPCs的募集情況,發現PCI可啟動EPCs時間依賴性動員, CD34+/KDR+細胞的數量與PCI術后內皮損傷程度密切相關[22]。有3個隨機雙盲試驗比較了自體CD34+細胞移植治療頑固性心絞痛的臨床療效和安全性,結果顯示總運動耐力提高,3、6、12個月心絞痛發作頻次下降,24個月病死率明顯降低[23]。
研究發現成人深靜脈含有血管周圍祖細胞,具有克隆形成和促血管新生的潛能,從冠狀動脈搭橋手術患者獲取隱靜脈祖細胞,將大隱靜脈的祖細胞與毛細血管內皮細胞建立了N-鈣粘蛋白介導的物理接觸,移植到免疫缺陷大鼠的下肢缺血模型中,結果顯示可促進缺血肢體的新生血管形成和血流恢復[24]。
此外,在急性或持續性損傷部位旁分泌信號可能是體現治療效果的重要介質。骨髓源性基質細胞(BMSCs)顯示組織特異性應答,動態分泌一組保護心臟的生化混合物, 支持了動態多因子旁分泌信號在介導基質干細胞治療效果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CD133陽性BMSCs有的分泌信號是由不同生物學背景所決定的,包括來自心肌梗死特征的氧化應激損傷心肌細胞的信號,BMSC旁產生的混合因子顯示出對氧化應激損傷細胞的高效修復和心輸出量的改善[25]。
2.4 基因治療 心臟基因治療是一種很有前途的技術。生物工程重組病毒的研發、針對心肌靶向性設計的進展,為治療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豬心肌缺血模型中,用導管將編碼熒光素酶基因的5型腺病毒載體(Ad5Luc,1011病毒顆粒)導入冠狀動脈,心肌無局部炎性反應和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缺血再灌注心肌攝取IC-Ad5,證實了IC-Ad5給藥方案可用于未來人類基因治療試驗[26]。 在小樣本的Ⅰ/Ⅱa期臨床研究中,30例頑固性心絞痛患者接受了AdVEGF-D基因治療,術后3~12 d用放射性PET評價心肌灌注儲備(MPR),隨訪顯示治療組心肌灌注儲備顯著增加,AdVEGF-D基因治療安全可行,耐受性好[27]。在Ⅰ期試驗的長期隨訪研究,31例嚴重患者缺血區心肌直接注射AdVEGF121作為常規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A組)或微創治療(B組)的輔助治療,10年生存率分別為40%和31%,認為腺病毒介導的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治療嚴重冠心病患者是安全的,未來需要進行更大規模的試驗來評估療效[28]。
2.5 中醫藥治療 中醫藥一直是心血管藥理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冠心病在傳統中醫中屬于“心痛”“胸痹”范疇,發病病機在于“淤血阻絡”,治療則需“祛瘀生新”。在促血管新生方面中醫藥有著顯著的療效[29]。麝香保心丸是臨床最廣泛使用的中成藥之一,含有人參皂苷Rb1等活性成分,大鼠心肌梗死模型研究發現,麝香保心丸成藥可增加循環EPCs數量和VEGF的表達[30]。中藥單體藥物如阿魏酸、丹酚酸B可促進VEGF、HIF-α、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表達以達到促血管新生作用。丹參酮ⅡA可減少基質金屬蛋白酶-2分泌,起到血管保護作用,黃芪多糖可促進血管內皮細胞增殖和遷移。進一步體外誘導間質干細胞分化為內皮樣細胞,單藥及聯合用藥對比發現,丹參酮ⅡA和黃芪甲苷可能通過上調連接蛋白Cx37、Cx40、Cx43表達和增強細胞間隙交互,促進了內皮樣細胞的血管生成功能[31]。
3 小結與展望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心血管疾病在介入治療和藥物治療領域有了巨大的突破。但是,由于心血管疾病人數眾多,發病率和病死率較高,缺血性疾病藥物治療新方法將繼續改變治療方式。治療性血管新生是一個活躍的研究領域,小分子物質的調控、細胞因子和干細胞的應用,對于促進血管新生、側支血管生長發揮重要的作用,相信今后在臨床能夠推廣。與此同時,運用抗血管生成藥物治療動脈粥樣硬化斑塊進展的方法雖然符合邏輯,臨床前研究也顯示了一定的應用價值,但是,臨床研究未能獲得突破。抗血管生成治療也存在治療時間窗的選擇,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抗血管生成可能會加重心肌缺血。對動脈粥樣硬化斑塊損傷部位血管新生機制的進一步研究,將有助于設計出基于功能結構的藥物分子以更好的發揮治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