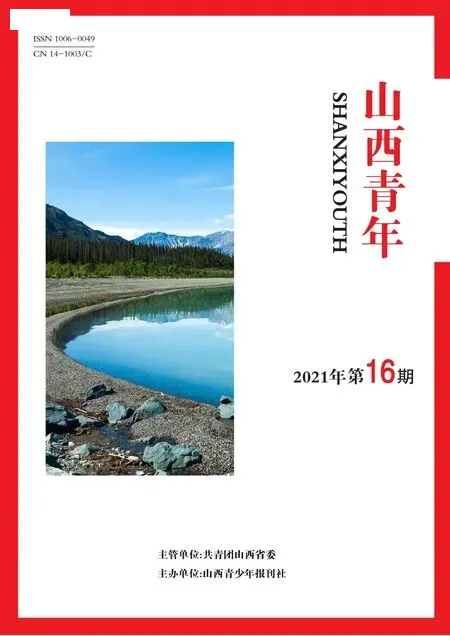社會環境變化視域下家庭教育地位逐漸弱化及改進路徑
梁 歡
(寶雞文理學院,陜西 寶雞 721000)
1966年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教授科爾曼收集4000所學校60萬兒童的數據,撰寫的《關于教育機會平等性的報告》,在國際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報告用大量數據顯示,影響孩子學習成績的主要因素是家庭[1]。家庭教育是對孩子的價值觀、道德觀、倫理觀及生活常識和基本技能的影響和引導,對孩子德智體美勞五育及性格人品等全面發展的全方位教育。家庭教育的主體是家長和孩子,孩子處于正在形成和塑造人格和習慣的階段,隨著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的變化,家長固有的理念和方式無法順利開展家庭教育,因此要改變家庭教育地位弱化的困境,應該借助其他輔助力量來促進家庭教育的進步。
一、家庭教育功能弱化的原因
(一)家庭內部的認同感弱
在我國古代社會,由婚姻產生的血緣關系結合而成的家庭,是集物質生產、人口生產及生活、教育、娛樂、防衛于一體的社會基本單位,在社會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封建社會所提倡的“三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中有兩綱是通過家庭實現的[2]。因此,傳統家庭教育中父母和孩子雙方主體的地位是不對等的,這種不對等對當代社會還存有影響,不對等的主體進行教育互動容易出現偏差。父母容易帶入自己的情緒,孩子在父母面前感受不到充分的尊重和自由,父母與孩子不能進行有效溝通,導致孩子出現抑郁、個性缺失、厭學等問題。父母潛意識認為孩子是自己的“衍生物”,自己賦予了孩子生命,孩子的一切都和父母息息相關,用自己認為的好壞來要求孩子的行為。在此基礎上,孩子和父母缺少溝通和交流,雙方開始抗拒或者不認同對方的行為、看法。同時孩子可以受到不同的文化和認知情感的影響,可以多元選擇,這種無篩選的混亂渠道中,很多是兒童不能自我辨認、自我選擇健康的渠道,這種最基礎的家庭教育方式隨著家庭內部雙方對角色的認同感減弱逐漸走向弱化。
(二)學校教育對家庭教育的功能化
東北師范大學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長趙剛說,我國目前的家庭教育水平與我們這個擁有四個多億家庭數量的國家、與廣大家庭對優質教育的需求還不成比例。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階層固化,中低層的家庭由于生活壓力,對孩子的家庭教育沒有精力來經營,同時教育支出無法充分保障,因此家長把一切教育的側重點放到了學校教育上,一切以學校教育為主,把學校和老師布置的任務作為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一致認為老師和學校的教育是科學的。學校主要是以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為目標,可是就實踐而言,學校的師資設備以及教育體制不同,各種資源有限;同時對于老師的定位是教書育人,即老師主要是以傳授知識為首要任務,同時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內對學生進行其他教育,并且對其他方面的教育實效缺少后續反饋。現在學校會規定父母與孩子的互動交流任務,這些看起來是學校在督促家長自身對孩子的教育,但是這些都是具有表面性、被動性,并不能從深處對家長進行深刻啟發,例如現在很多學校把給父母洗腳、做家務、勞動當作一種家庭作業來布置,強行讓學生打卡。這些本是家庭教育內容的一部分,這種行為會讓家長慢慢喪失家庭教育主體的責任感,家長正好順勢而為,把兒童完全交給學校。在學校的角度看,只是為了能補充家庭教育的缺失,調動家庭教育的積極性,可是過分干涉或者強調任務式,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只是弱化家庭教育的功能,減少家長在家庭教育中應有的壓力和責任感。從而導致學校教育的功能范圍擴大,與家庭教育處于失衡狀態,致使家庭教育的功能化,成為服務學校教育的工具。
(三)課外輔導對家庭教育責任感的削弱
2016年12月中國教育學會調查報告顯示,我國課外輔導的市場規模現已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次[3],由此可見課外輔導已然成為學生生活的重要方面。課外輔導的產生是由于家長們的整體恐慌,家長將自己的不足轉化為對孩子的高期望值。參加課外輔導首先是家長面對現實困境的選擇。一是時間困境,大多數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家長正處在事業的起步或奮斗階段,相當部分家長主要精力用于工作,輔導子女學習的時間有限;二是知識困境,當前中小學課程內容和父母學生時代的課程內容相比已有較大變化,在某些新內容上,部分父母感覺力不從心,也缺乏如何輔導的知識。課外輔導可謂是解決家長的高教育期望和現實困境的一劑“良方”[4]。部分家長為了逃避家庭教育的壓力,或者彌補對學生家庭教育的缺失,同時也是本著為了子女更優秀的成長,會給子女報大量的課外輔導。大量的課外輔導生活會擠壓家庭教育的時間,減少家庭教育的互動,家庭教育無法正常進行,會逐漸降低家庭教育的地位和功能。
(四)家庭教育相關立法的不完善
我國關于家庭教育的法條主要在《未成年人保護法》和《反暴力家庭法》僅有數十條,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立法的地位很低,對于家庭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高,且條文都是比較概括性的,對于實踐操作意義不大。家長和孩子的權利和義務意識不明確,普遍認為家庭是一種隱私且有人情味的環境,家庭教育不能用法律來強制性規定。大眾普遍認為“我”的孩子怎么教育和其他人沒關系,在家庭教育私有環境中父母的權利是最大的,因此部分父母不負責任,對孩子實施家庭暴力、體罰以及人格打壓等,侵害孩子的合法權益,甚至利用孩子的權益進行謀利;同時孩子的權利意識不強,維護自身權益的法律意識淡薄。因此家庭教育立法是保障孩子基本的家庭教育權利,是規范父母的基本家庭教育行為,是家庭教育行為的“底線”。
二、提高家庭教育地位的改進路徑
家庭教育已經由于各種因素形成不同的水平,所以家庭教育應該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來調整發展路徑,適當地借用外力來進行矯正,通過家長、學校、社會和司法四方聯合起來,提升家庭教育的地位和功能。
(一)提升家長的教育素養
家長的教育素養是指家長在子女教育中體現出知識、能力、心態、情感、觀念與價值觀,家長教育素養的提升是家長的理念、知識、能力以及教養方式的全方位提升[5]。在家長不會教的時候,應該設置專門的機構和專業的指導人員來引導和輔助家長,借此來提升家長的教育素養,疏導家庭教育中遇到的問題。在沒有條件把更好的物質財富給孩子時,其實足夠的愛與理解就是對孩子最好的教育,當父母學會用理解和愛來教育孩子,孩子相反的也會學會這樣對待別人。這樣的家庭教育出的孩子性格和人格更加健全,這才是成功的家庭教育。家庭經濟條件很重要,可是愛與理解才是最基礎的教育,學習加強家庭教育內部的認同感,首先應該加強家長教育素養的提升,這樣才能給孩子足夠的自由和尊嚴,只有在孩子享受到平等被尊重的同時,家庭教育環境才會更和諧,更加順暢無阻力,孩子會虛心接受父母的教誨,父母在教育中不斷學習和反思,在此基礎上的溝通和交流才是有效的,家庭教育的實施才會有更好的效果。
(二)明確學校教育的責任
學校教育可以輔助家庭教育功能的實現,但不能駕馭家庭教育。學校應該對學生和家長開設家庭教育課程,讓家長和學生共同上課交流,讓家長學會傾聽了解孩子,同時讓孩子學會理解家長,把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務要交給家長。同時學校可以鼓勵家長把握家庭教育的主動權,以家庭老師的視角來對學生進行管理和教育,學校只能通過輔助,這樣比打卡這種被動形式的任務更有效。從教育扶貧的角度看,政府和社會必須關注弱勢群體家庭教育能力建設,需要出臺更有效力的政策提升家長教育素養。
(三)把握課外輔導的適度原則
父母應該減少課外輔導的學習,根據孩子的學習興趣和天賦,適當地參加少量的課外輔導。國家應該規定課外輔導的次數和科目,專業科目最多兩門,技能特長最多2門,同時參加不能超過三門,應該給家庭教育留足夠的時間。同時應該加強課外輔導的監管,保留高質量有水平負責任的課外輔導機構,給孩子高質量少壓力的快樂學習時間。同時父母也應該學會辨別課外輔導機構的良莠,不要一味地為了把孩子的教育壓力推給別人而無目的無原則地選擇,學會對孩子和家庭負責。
(四)加強家庭教育立法,保障父母孩子的最基本的家庭教育權利
家庭教育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兒童生存與發展權利,提升家庭教育地位,規范家庭教育行為,促進家庭教育行業的規范化、專業化發展。高度重視家庭教育能力建設。家長教不好的時候,家庭教育出現偏頗,子女成長過程中發生問題,那我們要通過教育家庭的立法,來規范家長最基本的教育行為以及該承擔的責任,給子女最基本的健康教育和保障。家庭立法是對家庭教育行為最底線的規定,因此應該完善家庭教育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把立法和實踐問題相結合,同時制訂家校社協同育人有關文件。發揮家長學校、家長委員會、家長會等作用。有序推進《家庭教育指導手冊》的宣傳推廣和應用工作,落實《家長家庭教育基本行為規范》。強化綜合實踐育人,積極開展研學實踐、志愿服務等綜合實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