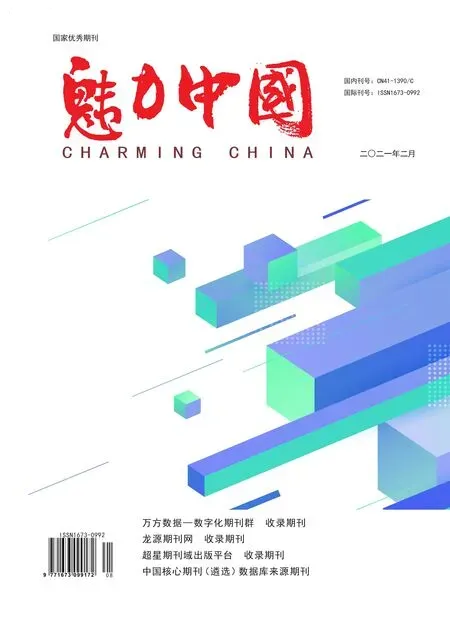導演與觀眾
楊小紅
(濮陽市戲劇藝術傳承保護中心,河南 濮陽 457000)
演出的目的完全是為了觀眾,為觀眾所理解、所接受。舞臺藝術存在著兩對矛盾:一是生活的無限和藝術表現能力的有限之間的矛盾這是各種藝術形式所共有的矛盾(共性):二是戲劇與觀眾之間的矛盾,這是舞臺藝術的特殊矛盾(個性)。這個矛盾的解決,主要靠導演。因為,劇本是文學創作的完成又是舞臺藝術的開始;要把劇本樹立起來變成觀眾一看就懂的動作化的藝術這是導演的職能。一個成功的導演,不僅要有一定的舞臺經驗而且還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這樣才能想在觀眾的心靈處,導在觀眾的理解上,使演出達到預期的效果。
一、正確看待觀眾
觀眾是導演再創造工作的立足點。從進行藝術構思的時候起導演心中就要裝著觀眾,一切意圖都是為觀眾著想,運用各種辦法、調動一切藝術手段使觀眾能接受并承認演出的真實性。只有當觀眾認為臺上的故事是真實可信的,他才能為劇情所吸引,為人物的喜怒哀樂而動情,并由此產生對自己生活經驗的回顧和聯想,從而接受劇本的哲理,受到啟發與教育。
觀眾不僅是演出的接受者,而且也是再創造的參有者。舞臺上的虛擬表演,要借助觀眾的想象和聯想才能完成藝術表演,借助觀眾的想象這不僅是因為舞臺時間、空間有限的緣故,還因為它是尊重觀眾認識的能動性,不把觀眾當傻瓜的一種創作態度“景愈藏,境界愈大”。戲曲藝術以代全以側寓正、以小見大等特有手段,如同山水畫的遠山、斷崖、行云、流水,往往力爭空靈一樣;它無一不是借助觀眾的想象而完成的。因此當導演根據這一特點巧妙地運用各種藝術手段,含蓄地、簡潔地、點到即止地處理些舞臺調度、身段動作以及場面的時候,都是同觀眾進行“意會性商量”的結果。在這里,如果不借助觀眾的想象,沒有觀眾的參與和合作,那是說不清楚的。
觀眾不僅是演出的接受者和再創造的參與者,而且還是演出實踐的檢驗者和評論演出的權威。一個戲排成之后,總要演出一、二場聽聽效果和反映,導演和演員心里才比較踏實。千百人在同一時刻發出贊嘆、驚訝、笑聲等效果,就是權威性的發言。這些效果里有贊許,有同情,有共鳴,有批評。如果得到了你預期的效果,那就證明排練是成功的;如果發生不正常、不必要的反效果,就是對表、導演的批評。導演要根據觀眾意見予以糾正。不過,廣泛、虛心聽取觀眾的意見,并不意味著不分好歹、兼容并蓄。導演不應該有成見,但必須有自己的主見,對于來自觀眾的意見,必須經過仔細分析、研究,然后作出決斷。聰明的導演總會認真地聽取觀眾意見,細心地品味各種效果,然后,根據這些意見和效果作更上一層樓的修改和排練,使演出質量不斷提高。那些認為演出就意味著導演工作的結束,從而放棄在演出中不斷提高的觀點和作法,顯然是不對的。
對觀眾不尊重對藝術不嚴肅的現象,表現在某些表、導演人員利用演出來愚弄觀眾或“討好”觀眾。如有的演員故意制造一些庸俗的笑料和噱頭,引得觀眾發出陣陣哄笑。須知劇中健康的、有意義的笑,只有從戲劇沖突和人物心理的曲折波瀾中產生。不能即興地生造出許多與主題無關的、甚至不健康的表演,去適應、迎合某些落后的、甚至是低級的趣味雖討得一陣哄笑,卻將廣大觀眾引入誤解劇本的歧途,這樣的創作態度是很錯誤的。
說到“笑”,使我聯想到喜劇表演問題
喜劇,特別是小喜劇,是目前戲曲舞臺上常見的一種形式。它主要被用來反映社會主義社會中大量常見的內部矛盾,也有反映敵我矛盾的諷刺喜劇等。喜劇是用笑作為手段來達到教育、啟發和鼓舞觀眾的。它的特點是幽默風趣,詼諧浪漫,以輕松愉快的氣氛和色彩取勝。大凡喜劇,都具有喜劇性的沖突,而這種喜劇沖突又是由人物的喜劇性性格和劇本的喜劇性情節構成的。楚劇《葛麻》中的馬員外具有愚蠢、吝嗇的性格,他往往是用愚蠢的妄想、失算的企圖而引起觀眾發笑;漢劇《柜中緣》,是以它出乎意料之外的偶然性因素,構成了“藏柜”“護柜”和“揭柜”的喜劇性情節。由此可見,喜劇中的笑,既不是隨手揀來的,也不是任意運用的,而是有著一定的目的性和思想性的,是喜劇用來刻畫人物性格、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一種手段。有些表演之所以引起觀眾發出一陣陣不正常的笑聲,就在于這笑聲不是來自性格沖突和情節沖突之中,扯了這些題外話,為的是讓導演明確戲劇笑效果的意義,目的還是回到題上來正確對待觀眾。
總之,導演要擺正自己與觀眾的關系;設身處地想觀眾之所想,千方百計讓觀眾接受舞臺上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引導演職員工認真嚴肅地全心全意地為觀眾演出。
二、適應觀眾的要求
導演要熟悉和了解觀眾的要求考慮觀眾的接受能力,以便在藝術形象的表達中適應觀眾進劇場看戲,首先要求看清楚,聽明白。
(一)依次講述交待清楚
把故事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按劇本的順序,一樁樁、一件件地交待消楚,這是觀眾容易看懂的重要因素。導演要注意將事情的起因沖突的結扣情節的轉換等重要環節交待清楚。對于頭緒較復雜以及補敘較多的劇本,要特別注意唱、念的清晰和速度的適當。
故事的發展有因有果有頭,有尾是吸引觀眾相信戲是真實的一個重要因素。傳統戲曲一般具有故事情節曲折、有頭有尾的特點。但不少折子戲或生活小戲,又常常不是這樣,它們往往對以前發生過的一些事件和人物關系采取揉進急劇發展的劇情之中,作極為扼要的插敘、倒敘、補敘等方法加以說明。對于這種情況;導演就應該注意把劇本所提供的有關事件的原由交待得清楚明白。
(二)明白準確一目了然
觀眾看戲,不同于看小說,看不懂的地方還可以回過頭來再看;而戲在進行中,一晃而過,無論是情節的交待,或是唱、做、念、打的表達,都要清楚明了,使觀眾一目了然。切忌模棱兩可、似是而非。唱念吐詞要清楚準確,勿使觀眾費解費聽;動作身段要形似神似,讓觀眾一觸即解。如果觀眾把騎馬看成了走路,把走路當成了做操,那當然是導演與演員的問題,決不能埋怨觀眾對你的藝術不會欣賞。
(三)理解觀眾的心理
導演必須理解觀眾的心理。只有理解了觀眾的審美要求、習慣、能力和興趣,才能用藝術手段去適應觀眾,才可能把戲排得符合常情常規引起觀眾的興趣,調動觀眾的情緒,滿足觀眾的要求。對觀眾心理的理解,一般應注意。
(四)理解與適應
導演在構思的時候,就要用觀眾的眼光對劇中事物進行逐一的衡量:哪些是觀眾熟悉和可以接受的;哪些是足以引起觀眾同情和共鳴的;哪些事會引起觀眾詫異或懷疑;哪些又是觀眾不易接受的事等等。對于觀眾易于接受的東西,導演只要運用藝術手段達到劇本應有的要求就行了。對于那些觀眾不易接受的東西,導演則要運用藝術手段,盡量顯示其真實性,指出事物的必然。
(五)情緒的調劑
劇中所發生的事直接刺激觀眾,引起各種情緒反映。由于觀眾情緒的節奏是隨著戲劇節奏而轉換的,因此,戲的節奏要注意由淡到濃、由淺入深疏密相間、動靜相襯,即有張有弛、有激有抒、有緊有松,使情緒螺旋式上升。如果直線上升,反而會削弱強度。一味強烈,使觀眾過于緊張而感到疲倦受不了;一直平淡無奇,則又使觀眾引不起興趣和感到提不起精神。觀眾需要的是張弛有度、激抒相間的舞臺情緒,導演應根據劇情,適當考慮調劑觀眾的情緒。掌握剛進場坐下來看戲的觀眾心理,要處理好開場,誘導和激起觀眾對于即將展開的戲劇沖突的關心和注意;戲進行過程中,要不斷引起觀眾的興趣,藝術處理上要注意起伏跌宕。大戲,每場結尾要很好處理,造成“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懸念,切忌冷場。
(六)對觀眾的預示
對于舞臺上即將發生的事件,總應先給觀眾打個招呼,以免事情發生使觀眾感到突然不可信。劇作者常用的懸念、鋪墊、前呼后應等手法,均能起到這種作用。
導演對觀眾進行預示的常用方法有:
必要的重復。重要的關鍵必須再三重復臺上要做什么,必須事先預告觀眾你將做什么;做的時候,你又須告訴觀眾你在做什么,做完之后,又須告訴觀眾已經做了什么。這樣才能引起觀眾注意,并牢牢記住。
舞臺上的事情稍縱即逝,而一語忽略未聞,常至后文盡失意義。為了使觀眾對舞臺上發生的某種情形、某種態度、某種行動或某種論調不致忽略劇作者往往采取多次重復的方法,第一遍是給全神貫注的觀眾聽的,第二遍是給一觀眾聽的,第三遍是給少數粗心大意沒有聽清,第二遍的觀眾聽的如《雷雨》中三次提到請電燈匠修電線,并由仆人告之電死一條狗為魯四風后來觸電而死作了鋪蟄,顯示了這個非常事件的某種必然性使觀眾感到真實可信。導演對于劇本多次重復的關鍵地方,要用強調的藝術手法加以處理,導演在藝術處理上運用重復的方式顯示事物的必然,同樣是具有藝術魅力的。
總之,通過直觀,使藝術創作者和藝術欣賞者之間建立正常的交流,這是戲劇作者、導演、演員必須掌握和遵循的一條重要規律。如果說,劇作者的心目中要永遠裝著欣賞者,那么,作為導演,更應當是如此。張懷堂同志在談到他在考慮表現手段時說:我必須“再三從最普遍的觀眾角度,檢查這些手法,看看他們是否能接受能欣賞。先叫觀眾看懂了,再叫他們喜聞樂見,然后才談到感動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