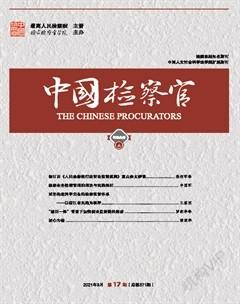對認罪認罰后惡意上訴行為的抗訴模式改進
廣東省人民檢察院課題組
摘 要: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告人上訴的原因是多樣的。針對其中的惡意上訴行為,是否應該規制、如何規制,在理論與司法實踐中均爭議較大。檢察機關對于惡意上訴行為的抗訴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現有立法框架內,可通過控制文書送達解決抗訴時間不足的問題。同時,應建立上訴理由檢察機關快速審查機制,最終實現認罪認罰案件提高訴訟效率的制度設計初衷。
關鍵詞:認罪認罰從寬 上訴原因 抗訴模式 量刑建議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運行至今,司法實踐中仍存在部分案件一審認罪認罰后被告人又上訴的現象。此類情況浪費了大量司法資源,并未實現提升司法公正效率等制度設計的初衷。認罪認罰后又上訴的現象應否受到規制、如何規制,從實踐到理論都存在巨大分歧,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一、認罪認罰案件上訴原因分析
以D省為例,2019年1-12月適用認罪認罰后又上訴的有1569人,上訴率約2.0%;2020年該類案件上訴的有2370人,上訴率約2.6%,無論是上訴率還是案件數量都不算低。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告人上訴的原因是多樣的,不能簡單將認罪認罰后上訴現象與被告人不認罪認罰、惡意上訴相等同。必須對上訴原因具體區分,才能對癥下藥、精準解決問題。
(一)一審判決量刑重于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
這種情況的深層原因是量刑建議有待進一步精準化,檢法之間溝通尚待加強。如筆者辦理的一起案件,被告人李某某成立了雄霸公司,組織員工謊稱可以幫助客戶以人才引進等方式入戶廣州,詐騙800余名被害人共計5000余萬元。全案共計25名被告人,一審檢察機關與包括該案主犯李某某在內的21名被告人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但一審判決對其中9名被告人判處了量刑建議幅度以上的刑罰。一審宣判時,多名被告人強烈不滿紛紛上訴,同時看守所與被告人同倉在押的其他犯罪嫌疑人也表示“司法機關不可信,再也不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了”。該案中上訴的表面原因是一審法院未采納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導致被告人預期落空,但細究深層次的原因:第一,檢法兩家在認識有分歧時溝通不暢,本案一審中公訴人雖然與承辦法官溝通后共同擬定了量刑建議,但在法院合議庭及其他領導不認同量刑建議時,承辦法官并未再次向檢察機關提出異議,更未建議檢察機關調整量刑建議。第二,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有待進一步精確化,筆者作為二審檢察員審查時,發現一審的量刑建議不夠細致,缺乏證據支持。該案系共同犯罪,且被害人眾多、社會危害性極大,提出量刑建議時必須準確區分主從犯,對眾多從犯提出量刑建議時亦須從入職時間、獲取的薪資及提成、騙取被害人的數量、退賠情況等綜合考量。但細查一審量刑建議的根據,承辦人對眾多從犯的量刑情節的表述均為“1.認罪認罰,可減少10-30%;2.從犯,可減少20-50%”,為什么對有的人減少30%,對有的人減少50%,并沒有列出事實依據。雖然此類情形占用了大量司法資源,也未實現認罪認罰的制度初衷,但主要原因在于司法機關本身,應從加強檢法溝通、提高量刑建議采納率入手,不在本文探討的規制被告人上訴權問題研究范圍內。
(二)一審判決后事實、法律發生變化
主要情形有:第一,定罪情節發生變化,如同案犯到案,導致主從犯的認定發生變化,或者同為主犯但被告人在犯罪中的作用發生變化。第二,量刑情節發生變化,如有待司法機關查實的立功情節已被查實,被告人所檢舉揭發的案件已被立案、被采取強制措施,或者公訴、審判的相關材料、法律文書在一審判決之后才提供的,導致被告人上訴。第三,相關法律、司法解釋發生變化,判決后法律所規定的入罪標準、量刑數額變化,導致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從而引起上訴。上述情況屬于有合理理由的上訴,且在實踐中無法避免,亦不在本文探討之列。
(三)認罪認罰違背被告人意愿
實證研究發現,部分認罪認罰案件被告人在上訴時稱并非自愿,表現為在上訴狀內提到“偵查人員強迫、威脅,甚至刑訊逼供”,稱“受到檢察官的欺騙、強迫”;也有少數情況是值班律師釋法、幫助不到位,致使被告人對認罪認罰產生了錯誤的認識。對于被告人違背自愿性所作出的認罪認罰,2019年“兩高三部”共同頒布的《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下稱2019年《指導意見》)已經明確規定不但要審查被告人的自愿性問題,而且需要轉換程序的應及時轉換程序,存在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應依照法律規定處理。
(四)利用“上訴不加刑”原則的惡意上訴行為
此類情況又分為兩種情形:第一,被告人對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法律后果非常清楚,對其所犯罪行其實并無異議,但是先通過認罪認罰換取較輕的量刑,然后再利用“上訴不加刑”提起上訴企圖得到更輕的量刑。此類情況的上訴狀理由雖然大多數是“量刑過重”,但不排除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等其他理由上訴。第二,“技術性上訴”。此類情況多發于一審宣判后剩余刑期不長的被告人身上,有的被告人不愿意去監獄服刑,于是利用上訴拖延訴訟時間,以達到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剩余刑期不足3個月留所服刑的目的。
綜上,由于前三種情況引起的認罪認罰后又上訴現象,被告人上訴都有合理、合法的原因,不屬需要規制的情形。而第四種情況造成了浪費司法資源、拖延訴訟效率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有違司法誠信,如果放任不加規制而其他被告人紛紛效仿的話,甚至會導致認罪認罰制度目的落空。本文所討論的正是如何規制認罪認罰案件中違反司法誠信的惡意上訴、技術性上訴行為,即廣義的惡意上訴行為。
二、對于惡意上訴行為的實踐應對及其局限性
(一)檢察機關應對惡意上訴行為的實踐
司法實踐中,為應對被告人認罪認罰后又惡意上訴的行為,部分地區的檢察機關在抗訴模式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具體做法是,檢察院在被告人惡意上訴的同時提起抗訴,抗訴理由主要有:第一,“這一行為違背了具結書,而具結書是有法律效力的,這也使得被告人的具結是一種‘虛假認罰,帶來了‘不當得利,可以通過抗訴權予以制約。” [1]第二,一審判決的依據是被告人認罪認罰,而被告人提起上訴表明一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發生變化,因此需重新量刑。法院一旦采納了檢察建議,二審改判加重了對上訴人的刑罰,則取得了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雙重效果。首先,惡意上訴的被告人并未真實認罪、悔罪,取消其不應取得的量刑優惠更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其次,可以警示其他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勿濫用上訴權,起到一般預防的作用。例如D省C市R縣檢察院辦理的鄭某某詐騙一案,一審判決后,鄭某某對《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反悔,僅以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饒平縣檢察院認為鄭某某無正當理由提出上訴,不應認定其認罪認罰并對其從寬處罰,遂提出抗訴,C市檢察院支持抗訴,開庭審理后,C市中級人民法院采納了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從而起到“抗訴一案警示一片”的效果,減少不必要的上訴,提高司法效率。
(二)抗訴應對模式的局限性
目前我國對于認罪認罰案件被告人反悔上訴采用抗訴應對模式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受制于上訴時間,有的被告人在收到判決以后的第9天、第10天才提起上訴,檢察院沒有時間提起抗訴。調研時,很多檢察機關都反映收到被告人的上訴狀后已過抗訴期,無法及時提出抗訴。第二,受制于審判機關的裁判傾向,一部分法院及法官并不認可檢察院針對認罪認罰后上訴行為的抗訴,認為此種情況并不屬于一審判決確有錯誤,檢察院提起抗訴于法無據,甚至認為“一旦被告人上訴就啟動抗訴程序以此增加被告人刑期,這在某種意義上剝奪了被告人上訴權”[2],還有觀點認為一審判決的量刑根據是被告人的認罪認罰具結書,在該時間點上被告人并未反悔認罪認罰,因此一審判決并無錯誤,不能因為被告人之后的上訴行為而認定一審判決確有錯誤,因此往往駁回抗訴,對檢察員的抗訴意見不予支持。調研發現,2020年D省檢察機關對認罪認罰案件共提出刑事抗訴226件,上級檢察機關支持抗訴124件,法院采納抗訴意見的僅有30件,采納率為24.19%。如D省Z市檢察機關辦理的葉某某等五人開設賭場一案,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后,司法機關對其多次釋法說理,但葉某某仍然堅持以量刑過重為由上訴,其隨意反悔的主觀惡性明顯,但二審法院并沒有采納抗訴意見,仍然維持原判。
三、檢察機關抗訴模式的改進
立法者出于保障人權、確保案件公正等考量,并未對認罪認罰案件的上訴權進行限制。為此,司法實踐中的應對措施只能在既有立法框架下進行嘗試與改革,需要對抗訴模式進行優化與改進。
(一)抗訴模式的立法依據以及法理基礎
司法實踐中對于抗訴模式的認識并不統一,致使二審法院采納率不高。有觀點認為在認罪認罰案件中只要判決量刑與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一致,即使被告人上訴,檢察機關也不應提出抗訴,抗訴模式于法無據、不合法理。因此有必要消除分歧、統一認識:
第一,針對惡意上訴行為,檢察機關提起抗訴于法有據。部分反對者認為,被告人認罪認罰后又上訴,其具有悔罪的權利,不能以此認為一審判決確有錯誤。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對刑事訴訟法規定“一審判決確有錯誤”的理解過于狹隘。2014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和改進刑事抗訴工作的意見》以及2017年《人民檢察院刑事抗訴工作指引》等多部司法解釋性質文件均明確規定,“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屬于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認罪認罰之后沒有合理理由又上訴的,被告人上訴這一事實正說明了被告人不認罪認罰,因此應當屬于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所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綜上,被告人在一審程序中利用認罪認罰換取的量刑優惠幅度比較大,而之后上訴表明其不再認罪認罰的,檢察機關可以根據被告人不再認罪認罰這一新的事實與證據證明一審判決確有錯誤并依法抗訴。“抗”也是為了“不抗”。尤其是對為了避免移送監獄服刑,留在看守所服剩余刑罰的“技術性上訴”,抗一案警示一片,杜絕不該有、被利用的“技術性上訴”,不能放任鉆制度的空子。
第二,抗訴模式具有法理基礎。部分贊成檢察機關抗訴的觀點認為,被告人先認罪認罰以獲取較輕刑罰,之后再利用上訴不加刑原則提起上訴,其動機不純。[3]因此“檢察機關抗訴有利于震懾上訴動機不純的犯罪分子,同時更好地維護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司法效果。”[4]此種觀點遭到部分學者及審判人員的詬病,認為在刑事訴訟中所應查明的是客觀事實,而非主觀動機,檢察機關苛責上訴人的內心有誅心之嫌,故二審檢察員關于上訴人認罰動機不純的出庭意見,已經超出了刑事訴訟所應考察的范圍。[5]
檢察機關在發表檢察意見時以動機不純進行說理,確有不妥之處。因此我們必須明確認罪認罰從寬的依據是什么?根據刑事訴訟法以及2019年《指導意見》,認罪認罰的“從寬”既是實體從輕,又是程序從簡。部分學者認為從寬的依據是自首、立功、退賠等刑事實體法已經規定的量刑情節,這顯然是不全面的。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認罪認罰可以從寬”正是體現了刑罰的并合主義——即刑罰正當化根據既包括報應,亦包括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認罪認罰的時間、退贓以及賠償情況等均是衡量行為人人身危險性以及再犯可能性的重要依據。“從寬”亦體現了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的并合,認罪認罰情節屬于綜合了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的一個獨立認罪情節,2019年《指導意見》已經明確規定了認罪認罰從寬幅度的把握“認罪認罰的從寬幅度一般應當大于僅有坦白,或者雖認罪但不認罰的從寬幅度。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節,同時認罪認罰的,應當在法定刑幅度內給予相對更大的從寬幅度。”較之單純的自首、坦白情節,認罪認罰之所以在量刑上從寬幅度更大,正是在于被告人認罰,這里的認罰既包括被告人對實體量刑的接受,亦包括其對程序從簡的配合。因此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告人沒有合理理由而上訴的,表明其已不再具有認罪認罰這一量刑情節,原審判決也因此失去量刑依據,檢察院通過抗訴來收回上訴人不應再獲取的量刑優惠正是追求公正的應有之義。
(二)通過調整文書送達時間解決抗訴期限過短問題
針對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訴的時間較晚導致檢察機關來不及抗訴的問題。實踐中,在檢法達成共識、配合較好的某些地區,有的法院采取了變通做法,即先向被告人送達判決書、裁定書,后向檢察機關送達。[6]此種做法還可進一步細化,針對刑事訴訟法第202條規定的“當庭宣告判決的,應當在五日以內將判決書送達當事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法院可以當庭將判決書送達被告人,然后在宣告以后第5日再將判決書送達檢察機關;定期宣告判決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宣告后立即將判決書送達”,但“立即”亦是一個有彈性的時間,先送達被告人再晚幾日送達檢察機關(一般亦以5日以內為宜),亦不違反法律的剛性規定。通過這種變通做法,可以使檢察機關的抗訴期限屆滿時間晚于被告人上訴期限,給檢察機關留出一定時間準備抗訴文書。例如D省J市人民檢察院和D省J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刑事審判、公訴工作進行會商后形成會議紀要,明確規定在“不超出法定審限情況下,法院在宣告第一審判決、裁定后,應將判決書、裁定書及時送達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法院可以將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否上訴的相關信息和材料與判決書、裁定書等文書一并送達檢察院”,從而有效解決了提起抗訴時間不足的問題。
(三)建立上訴理由快速審查機制
被告人提出上訴后,并非必然啟動抗訴程序,上級檢察機關應當建立認罪認罰案件上訴理由的快速審查機制。檢察機關收到上訴狀后,由檢察官或檢察官助理通過遠程視頻提審等方式,向被告人核實其真實的上訴理由,實踐中經過親歷式訊問,檢察官一般就可以確定上訴人的真實理由,甄別是否屬于技術性上訴以達到留所服刑的目的,還是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具體是對哪些證據有異議[7];稱認罪認罰違背其自愿性的具體表現是什么,在哪個階段被脅迫或是被欺騙,有沒有值班律師的法律幫助;稱發現新證據的應該提供新證據的名稱或提供線索請求法庭調取。大多數沒有合理理由的上訴人在接受訊問的過程中,都會無法自圓其說,最終承認其真實的上訴理由。通過上訴理由快速審查機制,二審檢察機關確定被告人屬于無正當理由上訴的,應當支持下級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建議二審法院取消被告人由于認罪認罰獲得的紅利,一定程度上加重被告人的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