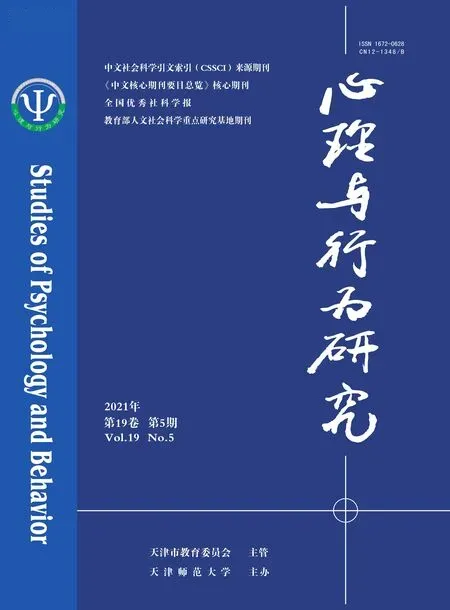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關系的元分析*
賈曉珊 朱海東,2
(1 石河子大學師范學院,石河子 832003) (2 石河子大學心理應用研究中心,石河子 832003)
1 引言
兒童青少年期是個體人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關鍵階段,由于這一時期的特殊性,兒童青少年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2019年,國家衛生健康委、中宣部等12部門聯合印發《健康中國行動—
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動方案(2019—2022年)》,幫助兒童青少年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可見,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已成為我國社會的關注熱點。在影響心理健康的眾多因素中,社會經濟地位是可能的因素之一。關于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系,許多研究者已對此進行了探討(夏婷, 李靜, 郭永玉, 2017; Chen et al., 2016)。然而由于各研究間被試群體不一、地區分布不同以及相關測量指標的差異,對二者關系尚缺少系統研究。因此,本研究計劃采用元分析對我國兒童青少年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關系及相關調節因素進行定量分析,以期更全面地闡釋二者的關系。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指個體或家庭所掌控的財富、權力和相對社會地位(Mueller & Parcel, 1981)。兒童青少年的社會經濟地位通常指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分為客觀社會經濟地位(objective social status)和主觀社會經濟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兩類(Kraus,Horberg, Goetz, & Keltner, 2011)。前者涉及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等客觀指標(Taylor,Kemeny, Reed, Bower, & Gruenewald, 2000)。考慮到有兒童可能不了解家庭收入情況,也有研究者選用上述指標之一作為客觀社會經濟地位的衡量指標(Feng & Guo, 2017; Zou et al., 2018);后者則是個體主觀上對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的認知(Adler,Epel, Castellazzo, & Ickovics, 2000)。鑒于許多研究結果表示社會經濟地位的客觀評價標準和主觀判斷結果有所差異,有研究者建議應同時納入以上兩類社會經濟地位,共同考察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關系(Kraus, Piff, & Keltner, 2011)。
心理健康是個體應對正常生活壓力和富有成效地工作,實現自我價值,為周圍的人和事物作出貢獻的幸福狀態(Galderisi, Heinz, Kastrup,Beezhold, & Sartorius, 2015)。早期研究多探討負性心理健康結果(Vaillant, 2012),隨著積極心理學發展,研究者提出了心理健康兩因素模型,認為對個體心理健康的評價應包括積極心理狀態和負面精神病理癥狀的測量兩方面(Suldo & Shaffer,2008)。當前有關心理健康的實證研究中,積極心理狀態多涉及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和自尊等積極情緒;負面精神病理癥狀多為焦慮、抑郁等消極情緒或整體評估負性癥狀(曾偉楠等, 2017;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其中多數研究僅涵蓋某一類心理健康結果,較少綜合考察這兩類指標,且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的具體研究結果也不完全一致,仍有待探索。因此,基于心理健康定義和心理健康兩因素模型,并結合以往心理健康元分析所包含的測量指標(李松, 冉光明, 張琪, 胡天強,2019; 劉文, 于增艷, 林丹華, 2019),本研究將納入以上兩類心理健康結果。
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關系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已受到廣泛關注。在理論層面,家庭壓力模型和家庭投資理論清晰闡述了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系,認為家庭社會經濟狀況可能對孩子成長發展帶來影響,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能為后代提供更多發展資源,構成成長的積極條件,這對其心理健康起到一定促進作用(Bradley & Corwyn, 2002; Conger,Conger, & Martin, 2010)。實證研究也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兒童青少年其主觀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較高,負面心理癥狀較少(劉志侃, 程利娜,2019; Zou et al., 2018);低社會經濟地位兒童青少年的焦慮和抑郁問題則相對明顯(B?e et al., 2014),且這種影響可能延續到成年期(Feinstein & Bynner,2004)。此前,國外一項元分析表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有待提升(Letourneau, Duffett-Leger, Levac, Watson, & Young-Morris, 2013)。國內雖有許多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結果(程剛, 張大均, 2018; 譚東超, 2019; 殷華敏, 牛小倩, 董黛, 牛更楓, 孫麗君, 2018; Feng & Guo,2017),但由于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差異,國外背景下對二者關系的元分析結果可能并不能直接推及中國被試群體,需本土研究加以探究,以獲得更為客觀和更具綜合性的結果。
除探討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的相關關系,本研究還考慮了影響二者關系的調節因素:(1)社會經濟地位層面。上文提到,社會經濟地位的主、客觀層面與心理健康關系存在差異。隨著兒童青少年認知發展,社會化程度加深,原生家庭的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關系有所減弱,主觀認知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其心理發展影響更大(Demakakos, Nazroo, Breeze, & Marmot,2008)。這一變化可能對二者關系起調節作用。(2)心理健康結果指標類型。關于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積極和消極指標的關系,不同研究之間差別較大,社會經濟地位與積極指標的相關從0.09到 0.39(陳艷, 薛雨康, 連帥磊, 谷傳華, 戴紅波,2018; 張映球, 吳東燕, 王才康, 2015),和消極指標的相關從?0.38到0.05(胡牡麗, 王孟成, 蔡琳, 朱熊兆, 姚樹橋, 2012; 梁書玉, 2015)均有報告。有必要分析不同結果指標類型的調節作用。(3)被試群體。社會經濟地位在整個生命周期中對個體的影響不是一成不變的(Chen, Martin, & Matthews,2006)。研究發現當代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整體好于中學生(辛自強, 池麗萍, 2020)。不同學段的被試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關系是否存在差異需要驗證。(4)地區分布。根據我國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可分為東中西部和東北四大經濟區(國家統計局, 2011)。區域之間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存在差異,或許會對生活于其中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況產生影響。有必要分析這一調節效應。(5)社會發展。隨著社會變遷,個體心理健康水平會發生變化(黃賜英, 2003)。社會環境和經濟水平的變化伴隨著個體積極心理水平下降,消極心理問題增多的現狀(辛自強, 2014)。亟需探索這一因素的調節效應。
綜上所述,本文擬基于中國社會背景下對兒童青少年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相關研究進行元分析,對二者在這一群體中的關系形成全面認識;并深入考察研究相關特征,如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層面、心理健康結果指標類型、被試群體、地區分布和社會發展是否調節二者關系。
2 研究方法
2.1 文獻檢索與篩選
使用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百度學術、Web of Science、ProQuest、SpringerLink、PubMed 數據庫,檢索截止到2021年8月國內外有關中國兒童青少年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的研究。中文檢索詞為:社會經濟地位、社會階層、心理健康、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自尊、抑郁、焦慮、消極情緒。英文檢索詞為:socioeconomic status,social class,mental health,subjective wellbeing,life satisfaction,positive affect,self-esteem,depression,anxiety,negative affect。
文獻篩選標準為:(1)兒童青少年社會經濟地位和心理健康實證研究;(2)文中詳細報告了樣本量和相關系數,部分未報告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總體相關系數的研究采用各維度相關系數均值作為效應值;(3)對象為中國兒童青少年,年齡范圍為6~25歲(劉富麗, 蘇彥捷,2017);(4)對于使用同一樣本和研究內容的文獻,只納入其中一篇。最終納入文獻62篇,其中中文文獻45篇,英文文獻17篇;獲得獨立效應量126個,包含被試111117名。
2.2 文獻編碼
對納入研究進行編碼:作者姓名;出版年代;樣本量;社會經濟地位(主觀和客觀);心理健康(積極和消極指標類型);被試群體(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地區分布(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社會發展(以文獻出版年代為指標)(李松等, 2019)。文獻中每個效應量僅編碼一次,如某文獻包含多個效應量,則進行多次編碼。為確保編碼準確性,由兩位編碼者獨立編碼,二人編碼一致性為0.98。對編碼不一致之處進行核查并達成一致。
2.3 統計分析
使用CMA 3.0進行數據分析,以相關系數r為效應量。元分析模型選擇根據異質性分析結果判斷。若Q值顯著,或I2大于75%時各研究異質,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反之,采用固定效應模型(Higgins, Thompson, Deeks, & Altman, 2003)。使用失安全系數(Fail-safeN)和Egger’s檢驗共同判斷出版偏倚問題。
3 結果
3.1 異質性檢驗
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進行異質性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兩類指標Q值均顯著,且I2大于75%,說明研究間異質性較高,應選擇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

表1 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關系的隨機效應模型分析
3.2 出版偏倚檢驗
采用失安全系數和Egger’s檢驗確定出版偏倚問題。結果如表2所示,積極和消極指標的失安全系數分別是5637和5500,均大于規定標準(5k+10);Egger’s檢驗結果差異不顯著(ps>0.05)。說明不存在明顯的出版偏倚問題。

表2 出版偏倚檢驗
3.3 主效應檢驗
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對社會經濟地位分別與心理健康積極和消極指標進行主效應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社會經濟地位和心理健康積極指標的效應值為0.19,社會經濟地位和心理健康消極指標的效應值為?0.13。隨后,對所得效應量進行敏感性分析,移除任意一個樣本后,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積極指標的效應值在0.19~0.20之間波動,與心理健康消極指標的效應值在?0.12~?0.14之間波動。表明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關系的穩定性較好。
3.4 調節效應檢驗
3.4.1 亞組分析
采用亞組分析檢驗影響社會經濟地位和心理健康關系的調節變量(社會經濟地位層面、結果指標類型、被試群體和地區分布)。結果如表3、表4所示,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層面顯著調節社會經濟地位和心理健康關系(QB=6.19,p<0.01;QB=5.11,p<0.05),其中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相關性要高于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相關性。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積極指標的關系受到不同結果指標類型的調節(QB=2.89,p<0.001),其中社會經濟地位與自尊相關性最高(r=0.21),而心理健康消極指標的調節效應不顯著(p>0.05)。此外,被試群體和地區分布的調節效應均不顯著(ps>0.05)。

表3 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積極指標的調節效應檢驗

表4 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消極指標的調節效應檢驗
3.4.2 元回歸分析
為檢驗社會發展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關系的調節作用,以出版年代為自變量,以社會經濟地位與兩類指標的相關系數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社會發展顯著調節了二者關系(ps<0.001),隨著社會發展,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積極指標和消極指標的相關均會減弱。

表5 社會發展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的回歸分析
4 討論
4.1 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系
本研究對我國近十年來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實證研究進行了元分析。結果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積極指標顯著正相關,與心理健康消極指標顯著負相關,這與國外相關元分析結果一致(Letourneau et al., 2013;Pinquart & S?rensen, 2000)。同時,該結果也支持了家庭投資理論和家庭壓力模型,兒童青少年所處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會對其心理健康產生一定影響(Conger et al., 2010)。當前研究表明,對于我國兒童青少年被試,相關理論依然適用,并且得到了相一致的結論。需要注意的是,這一結果無法澄清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的因果關系,在對二者關系做出推論時需謹慎論述。此外,當前研究還發現較之消極指標,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積極指標相關性更高,即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心理健康的促進作用大于其消極影響。這說明心理健康是包含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一種整體狀態(Greenspoon & Saklofske, 2001)。以往研究多側重探討低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青少年發展的消極作用(Greitemeyer & Sagioglou, 2016; Russell &Odgers, 2020),這啟示心理健康工作者僅致力于消除負面心理癥狀并不意味著心理健康的實現,同時注重對其積極心態的培養可能更有助于心理健康整體水平的提高。這不僅符合積極心理學所提倡的應更多關注與個體發展有關的積極力量,也為當前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發展提供了新思路。
4.2 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關系的調節效應
本研究考察了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層面、心理健康結果指標類型、被試群體、地區分布和社會發展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關系的調節效應。結果發現,社會經濟地位的主、客觀層面對二者關系起調節作用,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相關性高于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關系,這與以往相關研究結論一致(de Almeida Ferreira, Camelo, Viana, Giatti, & Barreto, 2018;Greitemeyer & Sagioglou, 2016)。從社會認知視角看,個體通常從對客觀物質資源的占有程度和主觀感知兩方面來判斷自身的主、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胡小勇, 李靜, 蘆學璋, 郭永玉, 2014)。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在客觀指標基礎上還涉及個體內部認知過程,能體察到更細微的社會信息,因此與個體身心健康相關更高(Quon & McGrath, 2014)。并且相對于客觀社會經濟地位,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可塑性更強,從主觀層面提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更具實踐價值。
心理健康積極指標類型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關系起調節作用,消極指標類型不起調節作用。其中,社會經濟地位與自尊相關性最高。自尊作為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之一,是個體通過社會比較獲得的對自我價值的體驗與評價,這一過程很可能受到社會經濟地位影響(Coopersmith,1967)。研究表明,自尊是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個體主觀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中介變量(黃明明, 陳麗萍, 2020; 朱曉文, 劉珈彤, 2019),這說明較于其他積極指標,自尊與社會經濟地位的聯系較為緊密。這也提示研究者今后關注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的關系時,個體自尊水平是需要重點考察的因素。
被試群體的調節作用不顯著。雖然兒童青少年也劃分出不同學段,其心理健康狀況整體來看有些微差異,但這一差異并未達到顯著水平。或許是因為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同屬于學生群體,尚未獨立,對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的判斷暫且來源于家庭和周圍環境,而這些因素一般較少發生變化。我國近些年對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視也可能改善了其心理狀況,故不同學段兒童青少年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關系不起調節作用。
地區分布的調節效應不顯著。以往也發現不同區域進行的社會經濟地位和心理健康的研究結果較為一致(馮永輝, 李慧, 諶夢桂, 2020; 劉志侃,程利娜, 2019; 周佳惠, 2019),這說明二者關系相對穩定。雖然區域之間的確存在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但所研究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并不僅僅受到經濟這一因素影響。研究發現,簡單增加收入并不能提升個體生活幸福感,教育醫保、健康、人均住房面積、政治參與等均會影響生活滿意度(宋麗娜, 西蒙·阿普爾頓, 2014; 姚偉峰, 2013)。近些年國家對中西部地區支援力度加大,尤其對偏遠貧困地區的幫扶,也可能縮小區域之間人們的心理健康水平差距。
社會發展的調節效應顯著。隨著社會發展,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相關性趨向減弱。根據Chen,Matthews和Boyce(2002)提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健康關系的假設模型,認為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起初很大,隨時間推移其影響逐漸減弱。這或許可為該結果提供支持。此外,現有元分析考察社會發展一般基于文獻出版年代,而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較為廣泛(李松等, 2019;吳玫瑰, 2015)。隨著社會發展,一些因素諸如社會發展帶來的文化沖擊、互聯網技術進步和社會關系變化等對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影響更為顯著(井世潔, 2018; 桑志芹, 肖靜怡, 吳垠, 2016)。這也提示研究者今后納入社會發展這一因素時應考慮得更全面,而不僅是根據文獻出版年代作出分析。
當前元分析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雖然本研究盡可能保證了效應量之間的獨立,仍不可避免一些研究同時包含多個效應量,今后可采用三水平元分析模型,進一步細分研究間誤差來源,以使研究結果更準確;研究將社會經濟地位分為主觀和客觀層面,而主觀社會經濟地位也包含個人對家庭和學校地位的感知,未來可進一步探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層面與心理健康的關系。
5 結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間存在顯著相關,社會經濟地位與心理健康積極指標關系密切。此外,二者關系還受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層面、心理健康積極指標類型和社會發展的調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