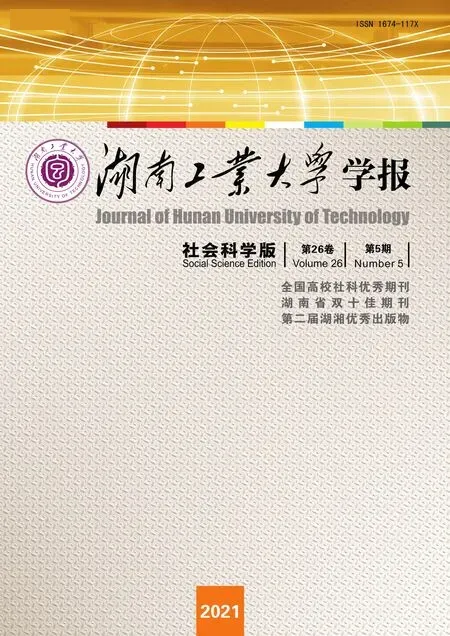我行山川異、風煙英雄同:《上甘嶺》與《金剛川》比較
白 蔚
(沈陽航空航天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 沈陽 110136)
1956年12月,我國第一部抗美援朝題材電影《上甘嶺》在全國公映,引起轟動效應,成為一代人的觀影記憶。2020年10月,作為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的第一部作品,《金剛川》上映,引發廣泛關注,成為年度現象級作品。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其它戰爭題材電影相比,抗美援朝題材電影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的沉寂,直到2020年才重新與觀眾見面。這一戰爭題材電影,不論是對本土觀眾召喚歷史記憶、建構民族認同,還是在跨文化的影像傳播中展現中國對于構建和平發展世界新秩序的卓越貢獻,都具有特殊的意義。在新時代,如何表現抗美援朝這一經典題材,引發了電影創作界與研究界的關注。《上甘嶺》與《金剛川》兩部作品暌隔已久,遙相呼應,既體現了中國電影人對時代主題的主動回應,也反映了國家意志下主旋律電影的價值訴求,其創作主旨、敘事方式、人物塑造、意識形態投射等方面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筆者擬對其進行比較分析,為深化這一戰爭題材電影的研究拋磚引玉。
一 敘事方式
(一)封閉性的線性敘事與多視點的復合敘事
《上甘嶺》采取了傳統的封閉性的線性敘事方式,電影以八連從七連接收上甘嶺陣地始,以八連把陣地移交給下一個連隊終,同時利用電影的蒙太奇手法表現了同一時間的不同空間——前線戰斗的第一線和師部指揮所,既有“戰壕真實”(戰壕戰爭) 也有“指揮部真實”(沙盤戰爭)。電影是建構時間和空間的藝術,德勒茲說:“偉大的電影作者用運動-影像和時間-影像進行思考,而不是用概念進行思考。”[1]39《上甘嶺》遵循了傳統戰爭電影的類型規律,即在規定情境下完成任務、化解沖突,以特定的時間與空間敘事呈現了戰斗任務的艱巨和戰爭的殘酷。
《金剛川》也延續了規定情境下化解急迫戲劇沖突這一戰爭電影的類型規律,并借助電影工業的技術手段將其推向極致。與《上甘嶺》不同的是,《金剛川》突破了傳統的線性敘事方式,嘗試了多視點的復合敘事,特別引入了“對手”的他者視角。《金剛川》創新性地從“士兵”“對手”“高炮排”三個視角復現同一時間里不同空間的戰斗情景,三個視角互有交叉又彼此照應,共同呈現了志愿軍戰士誓死護橋、修橋的壯烈場面,復調敘事力求達到一唱三嘆的效果,使觀眾的情感不斷與人物發生碰撞和共鳴,并最終在張譯飾演的張飛以殘軀與美軍飛機對決這一情節中達到高潮。
(二)聚焦戰爭中的普通人的小切口低視角敘事策略
兩部電影都取材于真實的戰役,都選擇了對戰爭全局產生重大影響,且無論殘酷性還是重要性在戰爭史上都具有代表性的戰役;但二者都沒有展現戰役的全景,而采取了小切口敘事策略,“以小透大,就是小切口看大背景”[2]58。《上甘嶺》鎖定一座山一條坑道——上甘嶺陣地,《金剛川》鎖定一座橋——金剛川上的橋,用以小見大的手法把抗美援朝戰爭的宏大主題凝縮在一個特定的空間和時間上。《上甘嶺》的鏡頭語言回避了戰場上敵我雙方的正面對決,主要描繪八連在異常艱苦危險的條件下堅守坑道24天的故事,雖然降低了對戰爭場面的還原度,稀釋了戰爭場面奇觀對觀眾的視聽刺激,但并沒有稀釋觀眾的情感;消解了戰爭的血腥和野蠻,卻沒有消解戰爭的殘酷,反而將觀眾引向對人物命運的關切和精神價值的體認,使觀眾感受到強烈的情感沖擊和心理震撼。電影還巧妙地借助聲音敘事強化觀眾的情感體驗。當衛生員王蘭在坑道內給戰友們唱歌,歌唱家鄉、歌唱祖國、歌唱我們生長的地方,電影在歌聲響起的同時出現了祖國家鄉的美好畫面,與戰場的艱苦空間環境形成鮮明對比。盡管“向觀眾傳達的更多是記憶的感知而非存在的實體”[3]45,但它“關涉的不僅僅是個人情感,更攜帶著共性的集體情感”[3]43。它使觀眾與片中人物一起從戰場中暫時抽離,憑借想象與記憶喚起對親人的思念、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電影《金剛川》中也出現了在戰役爆發之前金剛川水波不興的寧靜景象,以及在戰爭結束多年后和平年代的金剛川山川蔥郁的壯美景色,這兩幅場景與戰場畫面形成強烈視覺對比,使觀眾自然生發對和平幸福生活的熱愛,領會電影要傳達的保衛和平的主旨。與《上甘嶺》不同的是,《金剛川》直接表現了戰爭中的激烈搏殺場景。其通過近景鏡頭、固定鏡頭讓觀眾直面淋漓的鮮血、慘烈的犧牲,帶給觀眾強烈的視覺沖擊,迫使觀眾思考戰爭中的人類生命個體價值。
抗美援朝戰爭是在敵強我弱的力量懸殊對比下贏得的勝利,其殘酷性在古今中外戰爭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戰爭史詩片。福柯曾經這樣問道:“我們能不能不用英雄化這個傳統程序,去拍一部戰斗電影呢?這就回到一個古老問題上來:歷史怎樣才能把握自身的話語,把握過去發生的事情?”[1]290這兩部電影回答了福柯的疑問:二者都放棄了傳統戰爭體裁的全景架構,不從宏觀視角表現戰爭全貌,而是采取了低視角,即聚焦戰爭中的普通人,以戰壕里的普通士兵的視角,親歷戰爭的每一個時段,強化個體在戰爭中的生命體驗和感受。人物雖然是普通人,但因為沖突鋪展在一個獨特的空間中,便具有了典型意義。低視角的降維敘事,使觀眾更容易與片中的普通人共情,更真切地體驗戰爭的殘酷。
二 人物塑造
(一)在集體主義的英雄群像中塑造個性鮮明的人物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時任上海電影公司經理的袁文殊,身在制片一線,對電影創作上的教條主義的消極影響深有感觸:“機械地和片面地強調了作品的政治內容”導致作品成了政策條文的圖解,特別是“有些人一說話就是思想意識、階級立場,滿口大道理,令人無從置辯,其用心雖好,卻不符合藝術規律”,“如在《南征北戰》中的連長這個人物,由于他的性格關系,當他開始還不了解上級的戰略部署的時候,對部隊的撤退表示不滿情緒,后來經過上級的教育和實踐的結果他才明白過來。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有人就極力不同意把連長描寫成有不滿情緒的人物,他的理由是怕給人誤會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和下級軍官的政治水平與紀律性等等,結果便把連長的情緒盡量的減弱,一直減到失去人物性格為止”[4]。
電影《上甘嶺》的創作適逢雙百方針發布前后,它克服了之前電影創作上的概念化和公式主義傾向。其既完成了意識形態傳播的政治任務,又不是簡單地圖解政策條文,而是用生動立體的人物塑造說服觀眾感動觀眾,使觀眾明確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質和勝利的根本原因。
上甘嶺戰役“慘烈程度世所罕見,美軍調集大炮、坦克、飛機,向我志愿軍兩個連據守的約3.7平方公里的陣地上,傾瀉炮彈190余萬發,炸彈5000余枚,陣地上所有草木蕩然無存,山頭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焦土。戰役持續鏖戰43天,我軍擊退敵人900多次沖鋒而巍然不動,最后取得勝利”[5]。毛主席了解到上甘嶺的英雄事跡后,親自指示要將上甘嶺戰役拍成電影,借以宣傳教育人民。從電影劇本的寫作到拍攝成片,主創人員都懷著明確的政治宣教的使命感,但他們卻并沒有因政治上的創作價值取向削弱對影片人物性格的塑造。從師長到連長、指導員、班長到衛生員和普通一兵,他們力求把每個人物都塑造得真實豐滿,既可親又可敬。影片塑造的集體主義的英雄群像中不乏性格鮮明的個性人物。影片中的場景既有壯烈的戰斗場面,也有溫馨的日常生活。影片通過細節描寫,充分展現了志愿軍戰士豐富的人性內涵——鮮明的民族立場、戰友之間的兄弟情誼與嚴格的組織紀律性統一,昂揚的斗爭精神與飽滿的家國情懷統一,黨性與人民性統一。
影片中,師長批評八連連長張忠發冒險行為,但在八連困守坑道物質供應極為困難時,他特意讓炊事員送去兩個蘋果,表現了上級對下級的關心愛護。七連孟指導員雙眼受傷仍堅持不下陣地,當他得知八連從陣地撤下后,因為不了解這是師部為保存實力所作的指令,他異常激動地指責張忠發:陣地是同志們用血換來的,一定要守住。當他理解了上級命令和戰略意圖后,主動積極配合八連長在坑道中進行思想工作。衛生員王蘭開朗熱情,對戰友有著本能的熱愛,但她畢竟是個初上戰場的新兵,并沒有殘酷斗爭的經驗。因為坑道內嚴重缺水,她負責照料的傷員為了把寶貴的水留給有戰斗能力的戰友,都拒絕飲水,王蘭非常難過。雙目失明的孟指導員察覺出了她情緒低落,主動開導她。王蘭說自己從小膽小,如果一個人在坑道內肯定會害怕,孟指導員說:“害怕時,你就想你是一個戰士,一個光榮的人民軍隊的戰士,就沒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之后,敵人向坑道投放毒氣彈,她臨危不慌,表現得機智勇敢。觀眾從中可以看到人物的成長轉變過程。
八連長張忠發是電影《上甘嶺》著力塑造的核心人物,和《金剛川》中的關磊一樣,都是個性鮮明的有“瑕疵”的英雄:不怕犧牲、勇敢頑強、身先士卒、性情急躁,有個人特殊的喜好和習慣。張忠發一緊張就要喝水,戰斗越激烈越愛喝水,因此跟隨他的楊德才總是隨身背著兩個水壺。關磊愛抽煙,因為在戰場上抽煙違紀被降了職。同是有“瑕疵”的英雄,張忠發與關磊卻有顯著區別:張忠發能夠自覺調整改變個人喜好以服從大局服從紀律。他在戰斗的開始環節,雖然不理解放棄表面陣地爭奪撤入坑道的上級命令,仍然嚴格執行命令,正如他在教育衛生員王蘭時所說的:“這是戰場,要絕對服從命令,沒什么價錢可以講的。”當坑道被隔絕斷水后,楊德才想留一壺水給連長,被張忠發斷然拒絕。相反,關磊自恃曾是張飛師父兼上級的身份,強行改變上級分工安排,和張飛調換了炮位,對張飛的領導拒不服從,雖然被處分也沒有悔改。
(二)用對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金剛川》有意識地用人物對比關系塑造人物形象。影片中,張飛與關磊形成強烈的反差,張飛在關磊面前表面看似怯懦,實際他是出于對戰友兼師父的關磊的關心。兩個人身份的互換,強調了人民軍隊組織紀律的重要性。美軍飛行員希爾和他的隊友也形成了反差,希爾狂妄自信,隊友卻厭戰甚至有些畏戰。
《金剛川》既表現了同一陣營內部人物之間的差異,也通過兩個幸存士兵的旁白,表現了敵我雙方人物的對比。同是這場戰爭的親歷者,志愿軍戰士小胡在回憶時說,“俺們都才十七八歲,俺們這些人,真的沒有一個怕死的”,志愿軍戰士視死如歸、御敵于外是為了保護身后的人民;美軍飛行員史密斯在旁白中說,“我想回家,我不想死”,戰爭給這個曾經的資深飛行員造成了心靈創傷,在未來的生活中他再也不敢坐飛機,因為每次坐飛機就會想起這場災難。通過這種對比,既展現了戰爭中的普通人性,傳達出人類向往和平的共同價值關懷,也表達了電影的主題:志愿軍為什么贏得了勝利,犧牲是為了保衛和平;“犧牲精神是由信仰產生的,所以戰士們都不怕死”[2]64。
三 意識形態投射
(一)表現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和人民軍隊的鐵的紀律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擁有飛機、坦克、汽車等先進武器裝備,又有強大的空軍和海軍的協同作戰,后勤補給也非常充足,其物質條件遠遠超過志愿軍,但依靠黨的堅強領導、依托祖國人民的志愿軍,憑借著人民軍隊的鋼鐵意志和大無畏精神彌補了物質條件的不足,戰勝了擁有強大裝備的美軍。兩部電影都再現了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戰斗的艱苦和壯烈,表現了志愿軍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主動呼應了意識形態詢喚,表達了強烈的意識形態訴求。因為敘事方式的巧妙和人物塑造的成功,觀眾觀影時并沒有感到意識形態的概念化表達,反而能夠自覺接受并認同電影的意識形態投射。
《上甘嶺》中,張忠發派一個小戰士輔助衛生員工作,小戰士很認真地問“我和她,誰領導誰?”張忠發回答他:“她領導你。”這一看似閑來之筆頗有點喜劇效果,觀眾從中既感受到小戰士淳樸可愛的軸勁,也看到組織紀律的重要性:哪怕只有兩個人,要統一行動時也必須服從命令聽指揮。電影多處表現了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和人民軍隊的鐵的紀律,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通過政治動員、思想政治工作體現出來。《上甘嶺》中,師長和政委在給八連下達戰斗任務前,先給八連長張忠發講戰局,解釋任務的重要性;在八連奉命撤出陣地后,耐心向張忠發解釋保存實力的重要性;在發起主峰爭奪戰之前,向張忠發講述再次奪取上甘嶺的戰略意義。楊德才正是因為聽到了師長和連長的談話,領會了戰斗任務的重要性,才主動請纓挑戰最危險的爆破任務。《金剛川》中,步兵劉浩急于代犧牲的戰友立功,他接到協助工兵連修橋的任務時,忍不住抱怨:“怎么又是我們連啊?我們是來打仗的,又不是來修橋的!”高連長教導他:“修橋也是打仗!”《上甘嶺》中,張忠發看接連派出幾個戰士都未能順利炸毀敵人火力點,便不顧自己指戰員的身份,親自冒險上陣。他雖然立功了,卻被連支部批評,師長也教育他:“在這樣殘酷的斗爭面前,更需要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勁不行。”在影片中,觀眾看到,通過政治動員、政治建軍建立起的高度的組織紀律性不是把戰士變成盲目服從命令的工具,而是讓他們深切領會自己的行動的意義和價值,自覺遵守紀律,緊密團結在一起。
(二)展示政治上動員軍民的重要作用
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政治動員造成了強大的政治攻勢,有效地宣傳和發動了人民群眾,激發了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在全國上下形成了支援抗美援朝的熱潮,為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堅強后盾。這是上甘嶺戰役取得勝利的原因,也是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的原因。正如彭德懷在《關于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中指出的:“我們之所以在朝鮮前線贏得了如此偉大的勝利, 我國人民的全力支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
“這個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復復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7]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會作《論持久戰》報告時,明確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2020年10月,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講話,也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人民軍隊的力量,根基在人民。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我們都要匯聚萬眾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在愛國主義旗幟感召下,同仇敵愾、同心協力,讓世界見證了蘊含在中國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讓世界知道了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上甘嶺》中,陣地交接有序,戰斗中傷員幫忙裝子彈,缺水時卻拒絕喝水;后方將士以生命為代價運送物資,師部炊事員冒死送上來的兩個蘋果全連分享;當敵人把毒氣彈投入到坑道的危急時刻,衛生員毫不猶豫地把最后一塊毛巾捂在了連長的臉上,自己卻中毒受傷。《金剛川》中,步兵過橋,工兵架橋、修橋,步兵協助工兵修橋,高射炮兵為部隊過橋提供有效保護,步兵和工兵同時幫助高射炮兵警戒敵機……最后步兵連、工兵連、炮兵連團結協作,齊心合力架起一座人橋。如同電影中小胡那句旁白:“戰場上就是這樣,你也不知道對面的戰友是誰,但他就在那里為你犧牲。”同心協力、緊密團結的隊伍展現了團結起來的中國人民的磅礴力量。志愿軍戰士不是散兵游勇,也不是草莽英雄,在張飛這個“莽撞人”背后矗立著億萬人民的鋼鐵長城。志愿軍戰士很清楚地知道,當他跨過鴨綠江,他的背后,是祖國和人民,是祖國和人民給予了他們驚天地、泣鬼神的力量。
《上甘嶺》中,爆破英雄楊德才在走出坑道后有一瞬間的駐足回眸,他對戰友(也是對觀眾)自豪地高呼:“讓祖國人民聽我們勝利的消息吧!”這一瞬間點燃了觀眾的愛國情感,將觀眾情緒推向了高潮,也點出了電影的創作主旨。
四 創作主旨
(一)以奇跡呈現手法展示無神論者創造的神跡
《金剛川》的導演路陽說,“從上個世紀初到現在,我們經歷了很多的苦難,但中國人都頑強地走過來了,創造很多奇跡。我想這部電影就是這種精神的縮影。它告訴我們,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無論面對任何形式的艱難險阻,都會不計代價地一往無前,這種精神要傳遞下去。”[8]這種精神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跡,兩部電影都以奇跡呈現的方式表達了這一主題。《上甘嶺》中,師長夸贊八連創造了奇跡,因為“共產黨領導下的戰士一個人能頂幾個、幾十個、幾百個”。《金剛川》引入“對手”視角來呈現奇跡:“中國人不信神,但可以創造神跡”。
《上甘嶺》對敵軍做了概念化處理,片中沒有出現一個具體的敵軍角色,鏡頭拉近敵軍時也是虛化,或直接把鏡頭對準敵人的槍口。對敵方的符號化處理,與當時的現實條件有關,更與電影的創作主旨密切相關。《上甘嶺》遵循了戰爭電影劃分明確的敵我陣營的類型規律,建構出以正義之師反對侵略戰爭的善惡分明的價值分野,在塑造我方志愿軍戰士豐滿立體的人物形象的同時,虛化敵方,有意識地淡化了戰爭的殺戮意味,凸顯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質: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人民;侵略者將戰爭強加到了中國人民頭上,中國人民不得不以弱抗強、以戰止戰,用勝利贏得和平。
而在《金剛川》中,符號化的敵人變成了鮮活的生命個體——具體的“對手”。“對手”中既有消極的參戰者——美軍飛行員希爾的同伴,厭倦戰爭,渴望回家,根本不知道參與這場戰爭有什么意義,卻無可奈何;也有積極的參戰者——美軍資深飛行員希爾,狂妄自大也不乏勇氣,甚至也有某種“信仰”,打著基督教討伐異端的“信仰”的旗號,念誦著《圣經·啟示錄》中的句子。西方文化中關于正義戰爭的傳統包含了基督教討伐異端的所謂圣戰精神。“被譽為基督教‘正義戰爭之父’的圣奧古斯丁指出,戰爭本身并不是邪惡,作為懲罰為非作歹者的手段,它可以被用來對抗真正的罪孽。正義戰爭因此成為基督教價值觀的一部分,戰爭被看做是對惡的限制。”[9]基督教經典中不乏戰爭的隱喻。《啟示錄》是圣經中的最后一部預言,以象征性的文學語言,描繪了一場規模巨大、代價沉重、犧牲慘烈的人類劫難,預示上帝與魔鬼、神的子民與異教徒、光明與黑暗的正邪較量,上帝以這場劫難懲戒不信神、褻瀆神的邪惡勢力,從而見證神跡。念誦著《圣經·啟示錄》的希爾儼然是“基督的戰士”,自認為是代表正義和神的旨意來對中國人進行“最后的審判”的。金剛川上的激烈較量由此演變成了美國基督教文明與華夏文明的碰撞。狂妄自大的希爾代表著西方文化的傲慢與偏見,也表征著基督教文明建立在一神教基礎上的排他性和對抗性。希爾目睹隊友的飛機被志愿軍高炮擊落后,決意為隊友復仇,脫離編隊擅自向志愿軍高炮發起決斗式的攻擊,此時,戴上美國西部牛仔帽的希爾又從“基督的戰士”變成了美國西部片中的牛仔英雄——美國精神的化身。牛仔英雄的西部開拓,是挾科技優勢進行的暴力征服與文化輸出,其背后是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的價值觀念。這一開疆拓土的征戰過程,使牛仔的帽子浸透了印第安人的血淚,而這一次,自恃武器裝備先進、扮演征服者的“牛仔”,自己的鮮血沾染了牛仔帽。戰斗的結果,欲代神懲罰不信神的“異教徒”的美軍,卻見證了無神論者創造的神跡。電影借美軍視角昭示觀眾:華夏文明沒有一神教傳統,不崇拜對象化的人格神,但并不缺乏信仰。頂天立地的中國志愿軍戰士以向死而生、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宣示了對國家民族對人類和平的大愛,彰顯了“大寫的人”的價值和尊嚴。正如毛澤東所說“六億神州盡舜堯”,可以參贊天地、創造神跡的“大寫的人”本身就是神人同質的,他們不需要在人的世界之外再構建一個神的世界。
(二)用“勝利”與“犧牲”自覺回應時代主題
電影《金剛川》的英文名是“犧牲”——The Sacrifice。導演管虎在接受采訪時說“每個個體的犧牲都是值得的。”如果說上甘嶺的主題是“勝利”的話,《金剛川》的主題就是“犧牲”。上甘嶺站在愛憎鮮明的民族國家立場上告訴觀眾,我們為什么會勝利。它主動回應了冷戰時代兩大陣營對峙的主題,直接將價值訴求指向國內的觀眾,極大地激發了中國觀眾的民族情感,“它與同時期世界各國戰爭名片相比并不遜色”,“它將中國戰爭片創作推向一個新高峰”[10]。電影《上甘嶺》建構了一代中國觀眾的歷史記憶,“上甘嶺”成了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代名詞。
與《上甘嶺》不同,《金剛川》誕生于全球化時代,它的價值訴求不僅指向國內的觀眾,也指向世界電影市場,除了致力于建構本民族的歷史記憶和國家認同之外,它還試圖實現電影的跨文化闡釋與傳播。電影創作人選擇犧牲這一主題,是因為這一主題更能體現個體在戰爭中的生命體驗,更有利于召喚人類共通的情感。管虎說:“我依然相信情感的力量,不論是中國觀眾還是外國觀眾,只要是人,我堅信應該都能從電影里感受到人類共通的情感”[2]61;“敘事命題不能僅僅拘泥于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沖打仗,它可以作為一個厚實的背景,但是真正重要的還是人,是人在戰爭中的生命體驗,這點對所有觀眾、對電影都會有極大的啟發,我想這是戰爭電影的魂魄”[2]66。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作為主旋律電影的戰爭電影要呼應這個時代主題,既要體現國家意志與民族精神,塑造國家形象與民族身份認同,又要反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尋求電影商業化時代的普遍價值共識。對此,《金剛川》做出了積極的探索與嘗試。“時代更要求我們的電影類型要重視人,重視生命個體在戰爭中發揮的作用。”[2]66管虎的這個認知體現了中國電影人對時代主題的自覺回應。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所有的藝術都內嵌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它們具有文化的內容。為了理解這一意義的內容,僅僅研究普泛的人類價值和情感是不夠的,還需要將藝術置于特定的時空和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11]。人類的共同價值、人性的普遍情感一定是具體化的、情境化的。戰爭電影脫離不了戰爭的特殊語境。在戰爭的特定語境下,個體很難成為康德所說的“人是目的”,往往要服從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或人類生存的總體需要超越個體,乃至犧牲個體。人以強大的理性自覺超越個體的經驗性情感,恰恰證明了人的崇高和偉大。
如何表現戰爭中的人性?怎樣認識歷史中的人?唯物史觀從“現實的人”出發,給我們提供了一把理解歷史的鑰匙。“人的統一性不能建立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生物人類學基礎上,我們應尊重他們人‘活’的客觀性。人是名符其實的‘類’存在物,人的‘活’不單是一個單純的物種行為,它深蘊著人類和地球的統一性,他的‘活’應當使萬物被照亮,而不是使萬物暗無天日。以這種‘活’、‘生’的世界為基礎,就必須對現代性(西式)啟蒙心態下的全球意識予以重審。”[12]西方世界價值觀主導的全球化將人類引入了現代性的陷阱,自覺超越種族、地域、國家和意識形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正在文明互鑒中形成。中國電影人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兩個大變局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主旋律電影如何從人類總體生存發展的倫理維度出發,既回應國家意識形態詢喚,又傳遞人類共同價值,還有非常廣闊的探索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