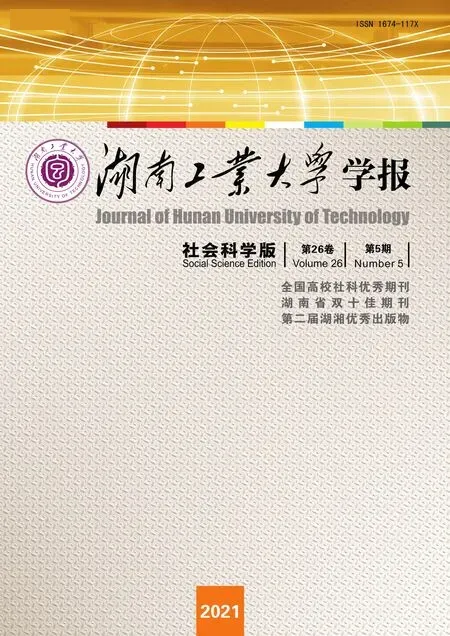“美美與共”的審美理想境界
——論屈原賦的生態美
吳廣平,鄧康麗
(1.湖南科技大學 中國古代文學與社會歷史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2.湖南科技大學 人文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生態美學推崇的美是人與自然整體和諧的生態美,生態美的第一重體現便是“主體的參與性和主體與自然環境的依存關系”[1]。這里“參與性”和“依存關系”都在強調生態美并非一種單純的美的形態,諸如藝術美、科技美、社會美等具有獨立性質的美,而是一種關系之美。在生態審美的維度中,人與自然始終處于一種相關相依的聯系狀態,不能獨立其中任何一方來完成審美過程,兩者的審美聯系不可分割。在這樣的理念背景下,生態審美打破了人與自然主客對立的審美關系,踐行一種“主體間性”的審美(或稱“交互主體性”),即“同時承認并張揚自然主體和人主體,并特別強調這兩類主體之間的聯系的關聯性原則”[2]128。在這種審美中,自然審美是其審美的第一要義和目的[2]213,自然審美是指“自然對象的審美屬性與人的審美能力交互作用的結果,兩者缺一不可”[3]。這表明在這樣的審美中,審美活動中的各方是平等的、融合的,而非獨立的。
生態審美的審美觀與中國古典哲學智慧“天人合一”觀天然相契。“天人合一”觀正是一種同時強調“天”“人”以及“天人關系”的樸素哲學觀,是一種宇宙人生通融合一的觀念。屈原所處的那個時代正是“天人合一”觀的形成期,是時,幾乎所有形而上的思想觀念、文學藝術都是在“天人合一”觀的范圍中進行的闡述和表現。在屈原賦中,屈原對自然美的表現實質是將自然美與人格美、人情美耦合,創建出一種“美美與共”的審美理想境界,從而賦予自然美更深刻的意蘊。
一 物我合一,情景交融
在楚辭之前,《詩經》的無名詩人們就多運用“草木鳥獸”等自然物來比興,其中感物緣情的表現手法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文人及大眾的審美傾向,并迅速反映在當時的文藝創作中。誠如劉勰所言:“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4]65
《詩經》之比興主要在自然感興、言志抒情方面給后世文人留下寶貴的審美經驗。自然感興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一種感性的聯系,形成“物我一體”的審美思維,因此超越了主客之隔,成為后世文人的審美智慧。言志抒情則將人的情感意識與審美意識融合,形成不可捉摸的審美直覺,給人一種朦朧飄渺的美感體驗。屈原繼承和發展了前代詩人的比興手法,在感興和抒情的基礎上,賦予自然美更多的審美內涵,發展出具有象征性的自然意象。且看《離騷》下面一段: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5]2。
這里的江離、白芷、秋蘭、木蘭和宿莽是屈原賦中經常出現的香草意象。詩人以江離、白芷、秋蘭為衣著服飾,早上去山里拔取木蘭,傍晚去水洲采摘宿莽,這些看起來像另一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樣態。然而,詩人的筆鋒卻突然驟轉,時間意識急入,江離、白芷、秋蘭、木蘭和宿莽與詩人被同時置于時間的維度中,都歸原為一種時間性的存在。日月輪回,春秋代序,芳華一瞬,光景不待。在時間的意義上,一切生命仿佛稍縱即逝,一切生之努力都似乎徒勞,詩人對“年歲之不吾與”的恐懼和對“草木之零落”的感慨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此時的香草既指代香草本身,又代表著詩人自己,既是具有審美性的自然物,又象征著某種人格,與前面的“修能”形成呼應。在這一段話中,詩人并未描寫江離、白芷、秋蘭、木蘭和宿莽的審美特征,而是將這些香草直接以一種獨立的形式——審美意象,與詩中的“我”形成對照,又與詩中的“我”合為一體。詩人將自身對時間、人生的思考融入審美活動中,豐富了這些自然物的審美內涵。又比如: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愿俟時乎吾將刈[5]8。
在這幅圖景中,蘭、蕙、留夷、揭車、杜衡和芳芷既保持著它們本來的自然風貌,又象征著不同的社稷人才。眾芳爭妍、欣欣向榮的風貌所對應的正是楚國人才濟濟、國家昌盛的情形,這又是一種二元合一的表現方式。
在屈原賦中,屈原對自然美的描寫趨于一種意蘊豐富的象征表現,所塑造的審美意象具有獨立自足的審美意蘊。與《詩經》對自然美的形象感悟不同,屈原筆下的香草是一種審美提煉后的象征意象——它們已然具備獨立自足的審美意蘊,是不言自明的美的化身。從其本質看,它們是一種升華了的“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原是英國美學家克萊夫·貝爾作為一種視覺美感概念提出的。他在《藝術》中說道:“在各個不同的作品中,線條、色彩以某種特殊方式組成某種形式或形式間的關系,激起我們的審美感情。這種線、色的關系和組合,這些審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稱之為有意味的形式。”[6]文學、藝術就美感而言是相通的,視覺藝術中的“有意味的形式”是指通過線與色的搭配來表現的美感形式,而文學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則是指文學家通過語言文字表現力對現實進行提煉升華所形成的美感形式,比如詩歌中的意象、意境。對此,李澤厚指出:“由寫實到符號化,這正是一個由內容到形式的積淀過程,也正是美作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過程。”[7]屈原賦中的自然意象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其形式和內涵體現出物我合一的獨特審美意蘊。比如《橘頌》篇寫道: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缊宜修,姱而不丑兮[5]133。
《橘頌》被稱為“詠物之祖”,是中國詩歌史上最早的詠物詩,詩中的“橘”與《詩經》中自然物只作烘托、起興的審美形態相比要成熟很多,它不再是一種短暫的情感鋪墊或者提示,而是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自然物。橘樹是一種地區性物種,它只在南國才能長成橘樹,是楚地特有的物產,《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8]屈原首先抓住橘樹“深固難徙”的屬性特征,感慨其“受命不遷”的自然本性。然后遞進深入,細致地描寫橘樹的枝葉、花朵、刺棘、果實、色彩等特征,夸贊其美好繁盛的樣態。從其描寫的層次來看,屈原對“橘”進行了全方位的肯定和贊美——從內在的“壹志”到外在的“姱”,由內到外美善兼備,是天地間最美麗的樹。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對橘樹的審美觀照與屈原對自我的認識和定位,即“內美修能”“內厚質正”“文質疏內”是非常一致的。很顯然,屈原對橘樹的觀察和描寫,滲透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因此,屈原在《橘頌》的后半部分寫道: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愿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5]134。
朱熹點評此段為“申前義以明己志”[9]。屈原在歌頌橘樹的同時,也在歌頌他心中的理想人格,表達他自己的崇高志向。這種心理恰如H.加登納所言,作家總傾向“先把自己鑄入到一個強有力的、自信的個體身上去”[10]。橘樹與詩人,在生命本質上都有著同樣的質感厚度和紋路曲折,在生命境界上均是不改初心、獨立于天地、繁茂而美麗,所以《橘頌》既是在頌橘,也是在頌人,前后對照,相互呼應,物我合一,異質同構,使“橘”這一自然意象的內涵充實而豐富,令人印象深刻。
從上述來看,屈原對自然美的呈現主要表現為自然審美意象的建構。中國傳統美學中的意象,是一個多義并存的美學概念,它是意與象、虛構與現實交融合一的產物,但其實這個美學概念還有更深層的內涵,它蘊含著精神個體與精神客體之間息息相通的一體性,誠如葉朗所言:“意象世界顯現的是人與萬物一體的生活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世界萬物與人的生存和命運是不可分離的。這是最本原的世界,是原初的經驗世界。”[11]64他又說:“當意象世界在人的審美觀照中涌現出來時,必然含有人的情感(情趣)。也就是說,意象世界必然是帶有情感性質的世界。”[11]64由此可見,意象的本質是人的心靈與自然物的合一,是“情”與“景”的交融統一,是一種理想化的審美形式。屈原“以心靈體驗生機,通過人與自然的協調相濟進入了一種‘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境界”[12]。結合屈原賦來看,其中的自然意象往往是自然美與人格美的合一,呈現為物我合一的審美理想境界,不管是單獨成篇的《橘頌》,還是分布在各篇詩賦中的香草意象,審美中都滲入了 “比德”的內涵。愛默生曾說,一個崇尚自然的人,會覺得“屬于自然的美就是屬于他自己心靈的美。自然的規律就是他自己心靈的規律。自然對于他就變成了他的資質和稟賦的計量器”[13]。屈原顯然意識到了這兩種美的互通性和相似性;他常常打破兩者的界限和桎梏,使人與自然物既能相互轉換,又可以融為一體,這種物我不分的審美形態在其筆下十分常見。
屈原將自己的生命意識投射于自然之中,又將自然內化于自己的人格精神中。在屈原賦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主人公形象,他或披葉戴花,或餐英飲露,或滋蘭樹蕙,或芷葺荷屋,或沐蘭釀桂,或乘豹從貍,等等,過著一種親近自然、融于自然的生活。香花香草的清白之體、芳馨之性、繁茂之態、堅韌之質,正對照著屈原自己的生命境界:“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離騷》)“茍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離騷》)“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離騷》)“茍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九章·涉江》)“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九章·橘頌》)“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九章·橘頌》)詩人與自然事物這種超現實的生命聯系,也有如《離騷》中靈氛所言 “兩美其必合”,自然美與人格美也因這種耦合而相得益彰。
除了塑造這些物我合一的自然意象,屈原還精于構造一種情景交融的自然意境。游國恩說,楚國“有九嶷衡岳的高山;有江漢沅湘的長流;有方九百里的云夢澤;有坼吳楚,浮乾坤的洞庭湖;森林魚鱉,崖谷汀州,鶴唳猿啼,水流花放,無一非絕好的文學資料。”[14]59又說:“屈原便是善于利用地理來做文章的頭一位。”[14]60結合屈原賦中的自然描寫來看,誠如其言,屈原確實是將楚地大部分的名勝、名物都統攝于其筆下,構造出非同凡響的審美意境。比如《九歌·山鬼》: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后來。表獨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閑。……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5]61。
這些描寫詩句雖不繁復,內容卻凝練飽滿,充分展現了江南之山的俊秀和清幽。那獨立之高山、遼闊之浮云的豁然景致,和“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朦朧意境,無不在烘托此山的俊秀;山中幽篁遮天、猿狖啾鳴、風聲颯颯、木葉蕭蕭,也無不在襯托山的清幽。在這俊秀和清幽的景象中,又飄蕩著一股綿長不絕的懷思和哀怨,山之景象與人之情態渾融無間,構成飄渺幽弘的意境,恍若夢境。
屈原擅長以象征、通感、比喻、暗示等描寫手法,在實象中造境,在境象中抒情,入景生情,融情于景,其筆下呈現出亦實亦幻的審美意境。比如《九章·涉江》: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5]100-101。
屈原流放時途徑溆浦,此時離首都郢都已相去甚遠。冥冥深林、荒山野嶺的陌生景象觸發了詩人的情緒,而途中山高蔽日、山下多雨的天氣和煙云霧靄的情景又給人造成一種不可遏制的壓抑和孤獨,寒冷和凄涼的境遇催化了詩人內心的傷感。從這一段文字所塑造的情境來看,它的空間逼仄狹窄,它的氛圍幽暗詭異。詩人置身這樣一處陌生之地,來路不可退,前途非大道,于是迷茫、孤獨、彷徨、困惑、恐懼。加之失去家園帶來的傷痛,舊痛添新愁,通通向詩人內心襲來,又都從詩人內心彌漫開去,因此其目之所及與心之所感融為一體。這種情景交融的意境恰如明代藝術家祝允明所說:“身與事接而境生,境與身接而情生。”[15]在屈原賦中,這樣的審美意境處處可見,比如: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5]50。(《九歌·湘夫人》)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5]115。(《九章·懷沙》)
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5]142。(《九章·悲回風》)
此外,屈原還善于用意象組合的方式來構建詩歌的意境,以實寫虛,化虛為實,虛實相生,在審美法則的支配下,營造出一種綺麗靈妙的審美意境,如《九歌·湘夫人》: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為帷,薜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5]50。
這是一座水上搭建的“百草香屋”,是為湘水女神的降臨而精心準備的“居室”。整座居室由香草搭建,荷葉為蓋、溪蓀為壁、紫貝做壇、桂木成棟、木蘭做橑、辛夷為楣、白芷鋪房、薜荔為帷,還有一些其他用作裝飾和布置房屋的香花香草。從最終呈現的審美效果來看,如此繁花似錦、精妙絕倫的構建和布置,仿佛是將《詩經·蒹葭》的“所謂伊人,在水一方”[16]和海德格爾推崇的“詩意地棲居”以藝術的表現形式合二為一了。戴叔倫說:“詩家之境,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間。”[17]“百草香屋”不僅是一種美的形式,而且還具有深厚的思想意蘊。王逸對此注解道:“屈原生遭濁世,憂思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筑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眾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也。”[5]53溷濁而稱惡的世界令屈原無所適從,奸佞小人的誹謗排擠更令他無法立足,因此,屈原在詩賦中為自己構建理想居所,以此屋的美麗和芳香來象征自己守節好修的“居世”態度和芬芳高潔的人格境界。從這種意義而言,“百草香屋”不僅是情景交融的表現,亦是自然美與人格美合一的體現。
老子云:“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18]“道”藏于“象”中,但非“象”,要把握“道”,必須打破“象”的局限,才能得其環中,因此屈原并不重視對物象的逼真刻畫,而是在恍恍惚惚、朦朦朧朧中追求某種本原的狀態,即物我合一、物我不分的狀態。在其筆下,一切客觀世界的障礙都不復存在,萬物交合并生,詩人的知情意與自然的真善美相合,超然象外的審美體驗油然而生。這是人與自然同契相通的結果,更是古代生態智慧“天人合一”觀與詩人的審美理想完美融合的表現,既真實,又夢幻,耐人尋味,令人神往。
二 虛實相合,人神一體
從宇宙的角度來看,自然蘊藏著天地運作之規律、萬物造化之形式,其生機之象、變化之態、和諧之美,互相交融,一氣同流,創化出宇宙生態無盡之靈秀。即使到科技文明如此發達的現代社會,人類文明也不能完全掌握自然規律,窮盡自然的神秘性,更無法創造出如自然形式這般精妙絕倫的形物,而只能師法自然或者從自然那里獲取靈感來源。自然的神性內涵正是因為這種人類無法企及的創化高度被人類接受的。從審美的角度來看,人對自然的美感體驗到達一定程度時,便會產生與宗教體驗相似的敬畏感、崇高感,這是因為“它們都是對個體生命的有限存在和有限意義的超越,通過觀照絕對無限的存在、‘最終極的美’‘最燦爛的美’(在宗教是神,在審美是永恒的和諧和完美,中國人謂之‘道’‘太和’),個體生命的意義與永恒存在的意義合為一體,從而達到一種絕對的升華”[11]135。故有學者認為,人對自然的美感體驗除了具有超功利性和愉悅性等一般屬性外,還具有神性特征,而要達到這種神性體驗,只有當美感層次達到“萬物一體”境界時才會產生[19]。這正是自然之神性美產生的淵源。
因為巫覡文化的影響,屈原的精神意識中保留著信仰自然的宗教意識。這種宗教意識對現實的超越性和對自然的超理性態度,使屈原能夠憑借一種超然的直覺和想象,穿透自然之象,見到一種絕對的美和真。《九歌》是屈原賦中最具巫神色彩的作品,詩中的自然描寫充滿泛神的思想,因此也是最能體現自然之神性美的作品。這是一組基于民間創作基礎上的祭祀詩歌,所祭之神以自然神為主,有日、云、山、川四種自然神(《東君》是祭祀日神,《云中君》是祭祀云神,《山鬼》是祭祀山神,《湘君》《湘夫人》《河伯》是祭祀川神)。自然種種不可思議的變化、力量和創造,在認知能力非常有限的古人看來,是一種無法解釋的神秘,一種讓人頂禮膜拜的神力,一種讓人嘆為觀止的“大美”。在這種情形下,人們的行動經驗和想象代替認知行事,將自然的變化與人類行動經驗類比,將對自然的敬畏和驚奇之感轉化為對自然的神性體驗,虛實相合,人神一體,那些耐人尋味的自然現象變成了某位神靈在顯示神跡。基于這樣一種原始宗教的心理氛圍,詩人屈原擺脫了傳統現實主義創作思維的桎梏,打開神話世界的大門,以玄妙之思、化工之筆描寫了一系列靈光飛揚的自然神以及它們的故事。
在《九歌》中,自然神的本質建構是人神一體,即人性與神性的合一;人性方面包括人的行為活動和情感活動,神性方面則主要指自然的美與力量帶給人的超自然體驗。屈原善于以神靈顯隱變幻之行跡來解釋和描繪自然現象,在自然之中別構一種虛實相合的靈奇之境,以此來表現自然萬物的靈變創化之妙。其在《九歌》中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
第一,對自然本相之美進行細膩而靈動的描摹。比如《云中君》:“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5]44這是對“降神”前的想象,詩人以為云神即將降臨,因而發出靈光。根據我們的生活經驗可以知道,其實這只是一種自然現象,即云受到陽光之朗照后變得明朗發光的情狀。然而在古人眼里,它成了神明顯現的征兆。無獨有偶,海德格爾也曾用他細膩而生動的哲學語言對這種云貌進行過描寫:“云盤桓于敞開的光華之中,而敞開的光華朗照著這種盤桓。云變得快樂而成為明朗者。”[20]云作為“明朗者”的狀態正是云“爛昭昭”的狀態,這兩種描繪在本質上是相通的。自然現象以一種奇異的表象給人神性的、虛幻的美感,刺激人的思考和想象,人又將這種感受和體驗融入對自然現象的觀照中,從而獲得一種更深層的美感。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神性的展現并未使自然神的形象脫離自然的本來面貌,而是在自然現象的基礎上為其鍍上一層奇異的靈光,使自然美在這種靈光的照耀下以某種形式涌現出來,是“如所存而顯之,即以華奕照耀,動人無際矣”[21]式的美。
“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5]44王逸對此注釋道:“夫云興而日月暗,云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5]45此處描寫的依然是云的變化貌。風起云涌,或聚或散;天光云影,或隱或露。云的動態變化在詩人筆下化作了神靈出沒的表征,這不僅是一種詩意的想象,也是一種生命共感的體現。卡西爾說:“美感就是對各種形式的動態生命力的敏感性,而這種生命力只有靠我們自身中的一種相應的動態過程才可能把握。”[22]云的變化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生命的運動行為,詩人以自身的人性經驗來對照云的變化蹤跡,將其解釋為云神的藏露動作,但由于這種自然現象不可測知,云的變化因此在詩人眼中煥發出可與日月齊光的神性之光。
詩人繼續寫道:“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云中。”[5]44此句也是對云之變化貌的描寫,陽光的投射與云的漂浮,相互影響,于浮光掠影中構成了這種忽“降”忽“舉”的情狀。詩人將此種情狀想象為云神對“降神”的徘徊和糾結,也與人的活動十分擬合;“猋”一字的使用,既彰顯某種靈動之意,又符合云變化豐富的特征,可謂神來之筆。
蔣驥評《云中君》為:“此篇皆貌云之辭。”[23]可謂一語中的。屈原以一種超現實的角度來呈現云之變化帶來的神韻和美感,整篇《云中君》短短數十字,就將云的自然特征——舒卷自如,波詭云譎——描寫得活靈活現、妙趣橫生,給人一種奇異而靈動的美感。
第二,從自然事物的整體形象出發,抓住其主要特點,進行生動的描繪。比如在《湘君》《湘夫人》《河伯》中,湘君、湘夫人是“湘水之神”,河伯是“黃河之神”。
湘水在南方,有著江南水鄉特有的那種柔美與恬靜,因此是: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5]46。
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5]50。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5]50。
遠觀,湖水澄明如鏡;細察,江水汩汩流淌。清風揚波,水泛漣漪,湘水之神翩升于這煙波幽境之中,柔波似語,繾綣纏綿,動蕩吐納間,江南水鄉之容態盡顯無遺。黃河居北方,有著北國風光那種壯美式的滔滔莽莽:
與女游兮九河,沖風起兮橫波[5]60。
與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5]60。
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5]60。
河神所到之處,波濤滾滾,奔涌澎湃如神發力;流冰紛紛,冰道塞川如神垂跡。力的壯美與神的行跡相合,將大河非同凡響的壯闊氣勢展露無遺。
在這兩相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屈原在描繪南北之水時,精準把握它們的性質特點,以不同的方式來展現南北水川的情狀面貌。兩種描寫一柔緩一洶涌、一優美一壯美,對照異常鮮明,在突出展現南、北之川不同面貌的同時,又為其增添神性的成分,使得湘水之態、黃河之勢顯得愈發傳神了。
第三,屈原還利用神話的內容和形式來展現自然的形象,比如《東君》。《東君》是一曲日神的頌歌,《東君》以太陽在天空中的“運行軌跡”為依據,融入神話成分,形象地描繪了太陽東升西落的情景: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辀兮乘雷,載云旗兮委蛇[5]58。
這一段是寫旭日東升的情狀。在《山海經》中,日出的地點有很多,湯谷扶桑是其中的一個地點。書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24]《淮南子·天文》中也有記載:“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25]文中太陽神馭馬騎龍的情形也是源于“日乘車,羲和御之”的神話典故。對此,《離騷》中也有“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的描述。當東方第一道晨曦刺破黑夜,漫漫長夜褪去,光明降臨人間,大地顯現,萬物蘇醒。這樣的日出景象在古人眼中是一種非常壯觀的天象。光明與黑暗的強烈對照直接刺激人的感官本能,在黑夜中沉睡的生命活力因為光明的到來而重新亢奮,仿佛晝夜之間經歷了一場生死的輪回,由黑暗進入光明猶如由死亡進入重生。這樣的神性體驗使太陽在古人眼中充滿神圣的光輝,太陽也因此被古人視作人間光明、希望、正義的化身。正如詩中寫道:
青云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5]58。
天狼星位于東南方,是神話傳說中有名的災星,北斗七星則方位不定,因形狀酷似古人舀酒的斗的形狀而得名。詩人結合當時的天文知識,借用神話的想象,將太陽西落的情狀生動地描繪成“射天狼”“援北斗”的情形,仿佛是太陽神為人們除暴安良后,用“北斗”痛飲了一勺桂花酒。至此,太陽神正義凜然、萬丈豪情的英雄形象就赫然呈現在人們眼前了。
由于太陽與人們的生存活動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是自然之中最早受到人們信仰和祭拜的神靈,所以“日食”現象在古人看來是非常兇險的征兆。張樹國認為《東君》就與古代“日食”現象的發生有關,《東君》的祭歌儀式實乃“日食禳救活動”[26]202-208。他進一步解釋道:“日食這種現象的發生,是由于月球運行太陽和地球之間,成一直線,太陽為月所掩而造成,多發生在朔日。但在原初意義上,古人不可能認識到日食就是‘陰侵陽’、‘月掩日’之說,而寧可相信日食的原因是太陽神和猛獸搏斗造成的,這個猛獸便是天狼,所以伐鼓擊鐘以及下文的‘舉長矢兮射天狼’便是這一心理支配下的巫術行為。”[26]206可見,是大自然的變化靈機賦予古人神性的感受體驗,古人再將這種感受體驗轉化為對自然的認識,在這樣的情形下,自然的形象就必然附上一層虛虛實實的神性光輝了。
第四,借用想象之臂來塑造自然神,以瑰麗譎怪的想象來展現自然神。比如《九歌》中的《山鬼》是一首祭祀山神的祭歌。在先秦時期,人們對鬼神并不做嚴格的區分,鬼神一體,鬼即神,都是古人祭祀的對象。易重廉就曾說過:“在古人的意識里,鬼神之分,的確是不嚴格的。……《九歌》中有《山鬼》,標明為鬼,人們卻目之為神。……《九歌》本身,鬼神早已不分。”[27]孫作云曾作《九歌山鬼考》特意考證,認為屈原《山鬼》的祀主即巫山神女[28],郭沫若、陳子展、馬茂元等楚辭學家也都贊成這一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屈原沒有沿襲以往的山神形象進行創作,他在對巫山之神采的感性審美中,憑借自己的想象去發揮和創造。從最后呈現的《山鬼》來看,此時的“山鬼”與《山海經》中面目丑陋粗鄙的山神形象已完全不同,此處的“山鬼”形象宛如一位婀娜多姿的美麗少女。詩中寫道: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5]61。
屈原筆下的山鬼——巫山神女以高山泉水為生活背景,衣以薜荔、石蘭為裝,飄帶以杜衡、女蘿為飾,含睇宜笑,窈窕作態,出行以豹貍為騎、香木為車,在石泉處飲水,在松柏下休憩,衣食起居皆自然,形象氣質儼如自然的精靈。這一形象的塑造,幽峻中藏著娟秀,娟秀中又帶著某種野性,無疑對應著江南之山清幽秀麗、怪石嶙峋的特征。詩人匠心獨運地將巫山之生機神韻、靈秀精華集于“山鬼”一身,濃而不艷,質而不俚,富含靈氣。
從審美的角度而言,自然神是自然理想的化身,其形象不僅反映自然本身面貌的美和精妙,而且也凝聚著古人對天地自然、世間萬物的審美意識和審美經驗。從后者來說,自然神儼然是天地靈氣日月精華的澆鑄,是自然美的化身。要塑造這樣一種美的形象,就不僅要使其光輝璀璨,還要使其生動豐滿、有血有肉。孟子言:“充實之謂美。”[29]如果只是塑造自然神的外在形象,而沒有充實其內在,便不能使其形象樹立起來,更無法建立楚人所看重的人神關系。為了充實這些自然神的內在,使其形象“美之可光”,屈原為這些自然神注入了許多人類情感的內容,這也成就了這些自然神的獨特之處。在詩人的筆下,所祭之神雖都具有自然神力,卻與一般威嚴肅穆的神明形象迥然不同;它們皆平易近人,富有人情味。詩人歌頌云神“云中君”的輝煌燦爛,但也同時表現出“云中君”的性格多變;詩人歌頌水神“湘君”“湘夫人”的安柔和靜,但也同時將“湘君”“湘夫人”之間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隱含其間;詩人歌頌太陽神“東君”的光明偉大,但也同時展現了“東君”的勇武多情;詩人歌頌河神“河伯”的波瀾壯闊,但也同時展現了“河伯”的友好和善;詩人歌頌山神“山鬼”的俊秀清幽,但也同時表現了“山鬼”的美麗多情。屈原以“情”深入自然之象,又以“情”凸顯自然的創化,這些繾綣的懷思、為民除害的正義感、攜手的情誼和孤獨的哀怨,全然是人的情性、情緒和情感。這樣,自然之中滲透著人情,而人情之中又漫溢著自然的氣息,自然與人情在審美的境界中交響共鳴,恰如宗白華所言,詩人“以心靈映射萬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現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30]
從屈原筆下的這些自然神來看,自然的神性美表現為虛實相合、人神一體,屈原讓自然性、神性和人性在一種理想形式中實現和諧的統一,在自然“美的形式”和“真的本質”中注入生命的活力,做到“酌奇而不失其貞”[4]48,從而塑造出如此有血有肉、生動豐滿的自然神形象。
屈原賦的自然意象、自然意境、自然神形象體現了生態美學所推崇的人與自然是共生整體的關系,且富有古典浪漫主義的底蘊。這種別具一格的生態美呈現主要源于詩人將自己與自然置于一種廣闊無限的聯系中。具體而言,就是屈原在審視自然事物時,其審美活動是同時在兩種維度中協調而成的:一種是現實維度,一種是想象維度。前者作為審美的客觀基礎,后者則是審美的靈魂和精髓,表現為一種包攬無垠時空、跨越物種界限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兩種審美維度不是相互對立,而是交叉同行。現實世界常常與想象世界混為一體,在屈原賦中就呈現為一種萬象同一、“美美與共”的審美理想境界。其本質和核心就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這為我們當下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提供了古老智慧。
由自然形象到自然意象、自然意境、自然神,是從客觀到主觀的過程,因為自然作為相對客觀的存在,人無法與自然實現交流,而把自然作為一種意識化、人格化的對象時,人與自然便擁有了共同的情志和語言,人就可與自然無障礙地交流,甚至其交流的豐富性超越了現實世界的其他交流,物我合一的自然意象、情景交融的自然意境、虛實相合人神一體的自然神形象的出現,都是這一豐富交流過程中所得到的自然形象。從生態美學視野來看這種獨特的自然形象,它們正是古代生態智慧“天人合一”觀的藝術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