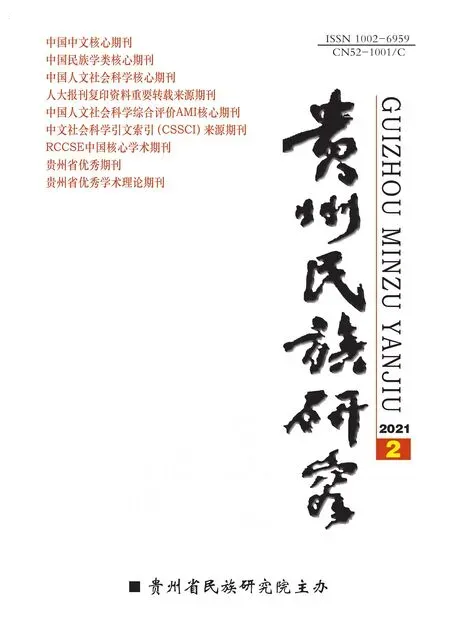府衛分制:明代行政設置中的一種特殊“插花地”
——以明代貴州為研究個案
謝景連
(凱里學院 民族研究院,貴州·凱里 556011)
明朝開國初年,地方機構設置仍依元舊制,設立行中書省或中書分省,但行中書省的長官稱參知政事和平章政事,在所管轄區內具有“無所不統”的大權。這與朱元璋所要建立的高度集中權力于中央的國家體制相互矛盾。因此,需要改革這一地方行政設置。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宣布改革行省領導體制,設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共同組成省級政權機構,分別執掌行政、司法和軍事。三司相互牽制,互不統屬,旨在相互制衡,犬牙相制。然而,洪武年間,貴州并非獨立的行省,但朱元璋為了鞏固貴州地方的穩定,確保其作為云南大后方的戰略地位,在貴州境內遍設衛所,旨在從軍事上控制貴州地方。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貴州正式建成為獨立的行省,但境內的平溪衛、清浪衛、鎮遠衛、偏橋衛以及五開衛仍屬湖廣都司統轄,永寧、烏撒、赤水等衛又寄四川永寧宣撫、烏撒軍民府境內,從而出現了府和衛并非同屬貴州行省統轄的現象,筆者稱其為“府衛分制”現象。
府衛分制現象在明代的行政設置中較為普遍,文中僅以明代貴州為例,討論明代貴州府衛分制現象產生的原因,并以“插花地”視角來展開分析,揭示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明確其實質。
一、通滇驛道貫通、拓修與貴州建省:府衛分制的出現
總體而言,明代從湖廣經貴州通滇驛道的貫通、拓修和府衛分制的出現,是明廷經營西南戰略的產物。自忽必烈偷襲云南獲得成功后,包括元朝在內的其后各王朝,開始清醒并意識到,一旦云南失守,中原地區就會處于游牧民族的弧形包圍圈之內[1]。從而可知,云南對于各王朝國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要確保中原地區的穩定,先需穩定云南,已成為明代及其后統治者的共識。
朱元璋平定中原之際,云南仍然處于元朝所封梁王的統治之下。梁王自恃地險路遙,不肯投降,成為明朝的心腹大患[2]。為了避免蒙古汗國包圍南宋的故事在明代重演,朱元璋決定用武力平定云南。但要平定云南,需要找到通往云南的最佳通道。歷史上,雖從巴蜀經青藏高原東沿進入云南是一條現成的通道,但此通道容易被游牧民族所截獲。因此,從中原抵達云南,最理想的路線是從湖廣出發,穿貴州全境,直達云南,這樣可以有效規避游牧民族的擾亂。加之當時已經有一條從湖廣沅江中游出發,穿越貴州腹地,抵達云南的間道存在,只需擴展這條間道,處理好貴州境內各大土司與少數民族的關系,既可成為通滇國防大動脈。經過慎重考慮,明廷決定貫通與拓展此通道。
因資料闕如,我們無從知曉明洪武年間到底新修或拓修了哪些具體的驛道。但根據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嘉靖《貴州通志》、萬歷《貴州通志》 《明實錄》 《寰宇通衢》等相關文獻資料的記載,明洪武年間,貴州東線的驛站有:貴州驛、龍里驛、新添驛、平越驛、清平驛、偏橋驛、鎮遠水馬驛、清浪驛、平溪驛九個驛站。再結合萬歷年間郭子章《黔記》的記載“自常德府至本省會城,計二十五程,共一千五百一十里。常德府:府河驛、桃源驛、鄭家驛、新店驛、界亭驛、馬底驛;辰州府:辰陽驛、船溪驛、辰溪驛、山塘驛、懷化驛、盈口驛、羅舊驛;沅州:沅水驛、便水驛、晃州驛”[3]。湖廣段共計16驛站,貴州9個驛站,剛好對應郭子章“記二十五程”的記載。這些驛道,我們無從知曉是否都是在平定云南以前就已經開通,但從湖廣辰、沅至普安的道路已經打通,為洪武十四年(1381年) 明朝大軍進軍云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善后經營云南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清代,貴州驛道的布局更加完善,乾隆年間,鄂爾泰等人修纂的《貴州通志》中對當時“通滇驛道”貴州東段有了更詳細的記載:“自省城下至玉屏縣、共十二驛”。分別是“皇華驛、龍里驛、新添驛、酉陽驛、楊老驛、清平驛、重安江驛、興隆驛、偏橋驛、鎮遠驛、清溪驛、玉屏驛,共490里。”[4]
為了平定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年) 九月,朱元璋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云南。傅友德等既受命。朱元璋頒發詔諭,曰:“云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朕嘗覽輿圖,咨詢于眾,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云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5](P20)是年十二月,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等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右江[5](P22),平定云南。但作為云南大后方的貴州不能鞏固的話,大軍一退,云南又成“孤懸”。朱元璋在《平滇詔書》中就明確指出了“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不能守也”[6]。為了加強對貴州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年) 正月,朱元璋設置了貴州都指揮使司,治貴州宣慰司,以顧成為使,其民職有司仍屬湖廣、四川、云南三布政使司[7](卷八)。朱元璋設置都指揮使司的目的旨在利用軍事對貴州加以管制,確保征滇大軍后繼有援和驛道的暢通。
遍設衛所,也是明廷控制貴州地方的具體舉措。從洪武四年(1371年) 置貴州衛、永寧衛開始,朱元璋沿著湖廣通云南驛道沿線,從東到西,設置了平溪衛、清浪衛、鎮遠衛、偏橋衛、興隆衛、清平衛、新添衛、龍里衛、貴州衛、貴州前衛、鎮西衛、平壩衛、普定衛、安莊衛、安南衛、普安衛等16衛。其中平溪衛、清浪衛、鎮遠衛、偏橋衛(還包括不在通滇驛道上的五開衛、銅鼓衛) 等衛隸屬湖廣都司。為了強化對驛道兩側縱深的控制,以及對勢力強大土司的監控,明廷還陸續設置了都勻(隸屬四川都司)、畢節、赤水等衛所[1](P4)。
洪武年間,貴州雖置有都指揮使司,但作為一個獨立的行省,則缺少相應的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因此貴州還不能算是單一的行省機構。明永樂年間,思州、思南兩大土司內訌,相互仇殺,明成祖朱棣見狀,于永樂十一年(1413年) 派兵討平,廢思州、思南宣慰使,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貴州宣慰使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烏羅、新化八府,為貴州建省掃清了主要障礙,于是,貴州才得以建成獨立的行省。
朱元璋在貴州設立衛所時,因貴州尚未建成獨立的行省,故而,朱元璋把湘黔驛道貴州東部的平溪衛、清浪衛、鎮遠衛、偏橋衛以及五開衛等衛交由湖廣都司統轄。永樂十一年(1413年)貴州建省后,或因遵循明太祖朱元璋“犬牙相制”祖制,或因貴州地瘠民貧,無法滿足衛所所需軍餉等因,永樂皇帝并未改變府衛分制現狀。由此可見,府衛分制現象的出現,其實是隨著明廷戰略重心的轉移,基于國家話語體系下而形成的,是國家政治力量介入后的直接產物。
二、府衛分制:一種特殊的“插花地”
查閱相關文獻得知,“插花地”一詞晚至清道光年間才始見于文獻典籍中。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十一月,時任貴州省安順府知府的胡林翼上奏“辦理插花地建言書”中首次使用“插花地”一詞,并將插花地歸納為三類:“華離之地”“甌脫之地”以及“犬牙之地”[7](卷十九)。胡林翼的此種分類,是基于行政疆界的形狀而進行的分類。近年來,隨著插花地問題的研究走向深入,在原有分類原則的基礎上,相關學者按照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分類法,又將插花地分為“傳統插花地”與“現代插花地”,其中傳統插花地包括民族型插花地、軍事型插花地、移民型插花地、經濟型插花地、政治型插花地;現代插花地包括民族自治型插花地、工礦區插花地、城市新型插花地、以及20 世紀50—70年代計劃經濟時期,因國家的計劃安排及“大煉鋼鐵”“上山下鄉”等運動而形成的一些特殊類型的插花地[8]。而在明代開辟西南的過程中出現的府衛分制現象,若按照胡林翼的分類,未將其納入到插花地的范疇來。基于現有插花地的分類體系,將其視為一種特殊的軍事型“插花地”。
明代學者王士性載:“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貴竹地,故清浪、鎮遠、偏橋諸衛舊轄湖省,故犬牙制之。”[9]民國《貴州通志·前事志》同樣也有類似的記載:“而湖廣都司所轄在貴州境內者,又有偏橋、鎮遠、清浪、平溪、五開衛及千戶所。”“而貴州之永寧、烏撒、赤水等衛又寄四川永寧宣撫、烏撒軍民府境內”等方面的記載[10]。明廷之所以將貴州東部的偏橋、鎮遠、清浪、平溪、五開等衛歸由湖廣都司管轄,把永寧、烏撒、赤水等衛寄四川永寧宣撫、烏撒軍民府管轄等情,一是出于行政管轄中的“犬牙相制”原則所致,二是因設立上述衛所時,貴州尚未建成單一行省,故而就將上述衛交由周邊的省管轄;到了永樂十一年(1413年) 貴州建省后,卻又因財政困難,無法供給衛所所需的軍糧以及行政開支所需經費,故而為之。且上述情況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也未改變。
文中之所以將府衛分制稱之為一種特殊的插花地,原因在于,從插花地的視角來看,行政疆界需要整齊劃一,行政疆界或機構的管轄權需要歸屬同一行政機構,若行政疆界中存在著“犬牙”“華離”或“甌脫”等情,或行政疆界中的領域或機構未屬于該行政機構管轄的,皆可稱之為“插花地”。永樂十一年(1413年),貴州建省后,若按照明代正常的行政機構設置來說,貴州省內的“府”“衛”皆應歸貴州管轄,但朝廷處于“犬牙相制”“相互制衡”的目的,卻將偏橋、鎮遠、清浪、平溪、五開等衛劃歸湖廣都司管轄,把永寧、烏撒、赤水等衛寄四川永寧宣撫、烏撒軍民府管轄,故而出現了上述衛雖身處貴州轄境中,但貴州卻無管轄權,而貴州寄在四川的三衛,四川又無權管轄狀況,那么,這種情況,自然就是一種特殊的“插花地”。
三、清理撥正:明代貴州地方官員對待府衛分制的態度
府衛分制現象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因政治、軍事等原因而出現的產物。產生之初,確實能解決一些政治和軍事問題,但在其后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其弊端日益凸顯,因而,貴州地方官員不得不向朝廷奏請,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并將其弊端紛紛陳述在其奏書中。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鎮遠知府周瑛因府、衛地近而分隸兩省,不便地方管理,奏請“地方事宜疏”。
為以合府衛以卻苗蠻事。
照得本府原系湖廣所轄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故地。國初開創西南境土,乃設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邊衛以控蠻夷,以通西南道路。永樂十一年,朝廷以宣慰司田琛等構惡,詔削其官,創設貴州布政司,分其地為思州、思南、石阡、銅仁、烏羅、新化、黎平等八府,俱屬貴州。平、清、偏、鎮等四邊衛仍屬湖廣。正統十四年,本府地方苗賊生發,民兵不能獨制。而四邊衛以屬湖廣,非申報各上司不敢擅動。為因阻隔江湖,文書往返動經數月,遂致賊勢滋蔓,攻城陷堡,殺戮人民,反勞朝廷遣將調兵,始克平定。后獻議者以本府地方沖要,乃于清浪設鎮守參將一員,及撥湖廣武昌等一十三衛所官前來協守。近來苗賊入境,百姓望救,急在旦夕。主將亦以湖廣為礙,不敢輕動,湖廣官司或又從中而牽制之,主將未免徘徊顧望矣。臣等聞兵速則可得志,勢分難以成功,主此不改,恐禍變之生,不但正統十四年而已也。夫分府、衛以屬兩省者,是名犬牙相制,互相犄角,指臂相使,互相運用,古人皆已行之。合無從此計議,查照洪武初年事例,將本府三司一縣割屬湖廣,或復照今日事體所宜,將平、清、偏、鎮四邊衛割屬貴州。庶幾父子兄弟相為一家,手足腹心相為一體,緩急調度,不致掣肘,地方便益[10](201-202)。
從周瑛的奏疏中可以看出,明初設立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邊衛的目的是“以控蠻夷,以通西南道路”,但因貴州當時尚未建成單一的行省,加之上述四邊衛距離湖廣行省近,故而劃歸湖廣行省管轄。永樂十一年(1413年),貴州建成為獨立行省,包括鎮遠府在內的府盡數劃歸為貴州管轄,但平溪、清浪、偏橋、鎮遠等四邊衛仍屬湖廣都司管轄。奏書所述,明廷之所以將府、衛分屬兩省管轄,旨在“犬牙相制,互相犄角,指臂相使,互相運用”。這一行政格局導致的直接后果是,正統十四年(1449年),鎮遠府境發生苗民叛亂,府內能調動的民兵,因勢單力薄而“不能獨制”,平、清、偏、鎮等四邊衛雖兵力雄厚,但“非申報各上司不敢擅動”,從而導致,雖有大軍進駐,但無軍隊調用權。即使要調用的話,也需向各司申報,但“因阻隔江湖,文化往返動經數月”,延誤戰機,最后致使“賊勢滋蔓,攻城陷堡,殺戮人民”。“近來苗賊入境,百姓望救,急在旦夕。主將亦以湖廣為礙,不敢輕動,湖廣官司或又從中而牽制之,主將未免徘徊顧望矣”。
周瑛的這一描述,將府衛分制的弊端暴露無遺,試圖去改變這種格局,因此,奏請“將鎮遠府三司一縣割屬湖廣”,或“將平、清、偏、鎮四邊衛割屬貴州”。但因周瑛的建議,最終不符合朝廷“犬牙相制”原則,未被朝廷采納。
隆慶元年(1567年),時任貴州巡撫的杜拯,也察覺到了府衛分制所帶來的弊端,因此,會同御史王時舉疏請將湖廣沅、靖二州及六衛、四川三土司并黔,若能采納此建議,便能達到“十便”的益處。原文如下:
沅、靖二州,與平、清、偏、鎮、銅鼓、五開六衛之去湖廣,酉陽、播州、永寧三土司之去四川,俱二千余里,遙屬于二省,而兼制于貴州。服役者興遠道之嗟,蒞事者無畫一之軌,民情政體,甚不便也。革數州縣土司專畀之貴州,其便有十:
齊民賦役自遠而移之近,勞費省于舊者數倍,一便。
郡縣專心志以聽一省之政令,無顧此失彼之慮,二便。
軍民力役彼此相濟,無偏重之累,三便。
科貢悉隸本省,禮遇資譴有均平之規,四便。
司道政令有所責成,郡縣不敢以他屬為辭,五便。
府衛互制,悍卒豪民禁不敢逞,六便。
歲征緩急可無失程,盜賊出沒易于詰捕,七便。
土酋之桀,各相牽制,不得肆其毒螫,八便。
僻遠之區,監司歲至,吏弊民瘼,可以咨詢而更置之,九便。
釋兼督之虛名,修專屬之實政,體統相安,事無阻廢,十便。
臣愚以為三司所呈聯近屬以全經制,其說可行也。
臣等又看得各省會城府縣并置,豈徒備官,要以親民悉下情耳,乃貴州獨闕焉。軍民之訟牒,徭役之審編,夫馬之派撥,盜賊之追捕,藩臬不能悉理,往皆委之三司首領與兩衛指揮及宣慰司。夫三司首領類皆異途,操持靡定,政體未諳,指揮則尤甚矣。委牒方承,即懷私計,防緝未效,反貽厲階。宣慰則尤矣。逞其恣睢,日事贖罰,破人之家,戕人之命,往往如是。是故土民爭欲增建府治,而該司議程番府附省會,其說可行也[10](P301-302)。
奏疏將貴州東部府衛分制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即楚屬平溪衛、清浪衛、偏橋衛、鎮遠衛、銅鼓衛、五開六衛插入貴州,酉陽、播州、永寧三土司屬四川管轄此等插花地的弊端。杜拯認為,若能“改隸貴州”,便能取得上述“十便”,并進而指出,“十便”想法的產生,并非心血來潮,而是“皆碩畫也”。但由于杜拯當年將要離任,加之其建議還是不符合“府衛分制、犬牙相制”的原則,此疏依然未獲施行。
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直隸巡按御史蕭重望條陳安黔五策,其中“拓疆圉”一策中指出,“黔省蕞爾單弱可慮,擬待事定,割楚之偏、鎮、平、清以專黔轄,又割蜀之永寧、烏鎮以拓黔壤,但版圖久定,恐有窒礙,應通行三省總督詳加商榷。”[5](P970)兵部復議:“列土分疆,版圖久定,不加會議,猶恐楚、蜀別有窒礙。應通行三省總督、撫、按衙門詳加商榷,要見所議割地之事,如果安便可行,即酌定改正,不得私意執拗。倘有未便,亦明白聲言,具奏定奪。前件,臣等查得黔省本蕞爾之區,而平、清、偏、鎮四衛又屬于楚,永、播、烏、鎮土司又屬于蜀,似應割屬黔中以便控制。但今地方多故,一改革間,彼此相互推諉,恐致誤事。俟寧謐之日,通行三省另議。”[10](P408)從兵部的復議中,可知,因“地方多故”“恐致誤事”等因,這次割平溪衛、清浪衛、偏橋衛、鎮遠衛屬黔的事情又被擱淺了下來。
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 12月,湖廣、川、貴三省總督李化龍在平定播州楊應龍叛亂后,向朝廷上奏《播州善后事宜十二事》,尋又上奏《黔省善后事宜八事》。其中在《黔省善后事宜八事》奏疏中的“一事”就是建議將黎平府、永從縣改隸湖廣,鎮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改隸貴州。其原文如下:
楚、黔接壤、撫屬錯綜,如黎平府永從縣,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五百里而遙,反屬于黔;平、清、偏、鎮四衛,近黔之鎮遠,去楚二千余里而遙,反屬于楚。即云犬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諉。頃者,酋犯偏橋而楚不能救。比者,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救。即黔有播患,而黎平、永從無一夫一粒之助,非不欲救助也,鞭之長不及馬腹,勢也。合無以黎平一府,永從一縣改隸湖廣,鎮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改隸貴州。文武官軍俸糧,歲費公用,悉仍其舊。則軍民合為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即有寇警,誰能諉之[10](P519-520)?
李化龍《黔省善后事宜疏》中所涉及的八款都是事關播州平定后,貴州如何善后的問題,且該疏是與貴州巡撫郭子章商議后的決定,都認為“俱在可行”。疏中也將貴州轄境的“鎮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屬于湖廣管轄的弊端再次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酋犯偏橋而楚不能救”“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救”。且該弊端也是路人皆知的事了,但稽之舊制,或許是出于戰略方面的整體考量,也未能施行。
縱觀上述奏疏,府衛分制這種特殊插花地的弊端,下至地方官員,上至朝廷大員、甚至皇帝本人,都知道其弊端,尤其對地方管理甚是不利。但明廷或許稽于“犬牙相制”的舊制,或出于整體戰略的考慮,一直未能有效解決貴州府衛分制的情況,直至明亡。最終,這一情形直到清代“裁衛所歸并府縣”時,才得以有效解決。其中,鎮遠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歸并鎮遠縣;偏橋衛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 歸并施秉縣;五開衛于雍正三年(1725年) 歸并黎平府;平溪衛、清浪衛于雍正四年(1726年) 歸并思州府;永寧、烏撒、赤水三衛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分別歸并永寧縣、威寧縣、畢節縣。至此,明代貴州境內的府衛分制現象才徹底得到解決。
此外,除府衛分制這種“插花地”的弊端被明代貴州官員指出外,對明代貴州行政疆界其他類型的插花地也被當時的貴州官員紛紛指出。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 巡按貴州御史蕭端蒙以“貴州地方與湖廣、四川、云南、廣西諸省疆土參錯,奸宄迭生,邊圉之患,無歲無之”[10](P298)的緣由,奏請“請特建總督重臣疏”,疏中雖主在請設“湖川貴總督”,但卻將行政疆界中的“插花地”的七弊一并托出,望朝廷能予以清理撥正。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巡撫貴州都御史郭子章在請終養之際,奏上《臨代條陳地方要務疏》,其中將重安司插花一事的弊端描述得清清楚楚,“重安距黃平遠,猶馬之腹,即長鞭有所不及。屬之清平,其近也,只猶舌之唇,唇之厚薄燥濕,舌一舐便知之。”[10](P589)
四、結語
“插花地”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不僅古代有之,現今亦然;不僅中國有之,國外亦有。雖然“插花地”的名字遲至清光緒年間才正式出現,但據譚其驤先生考證,早在戰國時期,中國就已經存在了“插花地”現象。“插花地”現象類型多樣、成因復雜,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插花地”現象不是自然現象,而是立足于國家行政疆界區劃的設置或調整才出現的社會現象。國家行政是插花地得以出現的主導因素,但也并非唯一因素,文化生態、地方建構以及人的能動因素等皆是插花地形成的影響因素。對插花地的社會影響和利弊得失評價也是各抒己見,大部分研究認為“插花地”的弊大于利,但也有學者認為,立足于現實需求,“插花地”也有相當的益處。
文中探討的明代貴州出現的府衛分制現象,確實是伴隨著明廷經營西南的戰略所致。從政治層面看,若未有明廷對西南地區的經營與拓展,以及明代三司分制的政治制度,就不會有府衛分制現象的產生。因此,國家權力是插花地得以產生的主導性因素,可以說,“插花地”是伴隨國家行政機構的設置或調整而出現的社會現象,若沒有國家行政設置或調整,就不會有“插花地”的產生。對于“插花地”的評價,也是考察“插花地”時必然要關注的問題。從上文地方官員的奏疏來看,府衛分制這類插花地確實是有百弊而無一益處,但若從朝廷的整體戰略角度來看,府衛分制卻可以“犬牙交錯”相互制衡,達到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的目的。因此,我們在審視插花地問題的時候,需要從多維度的視角,給予符合其內涵和本質的解釋,才能明了其內在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