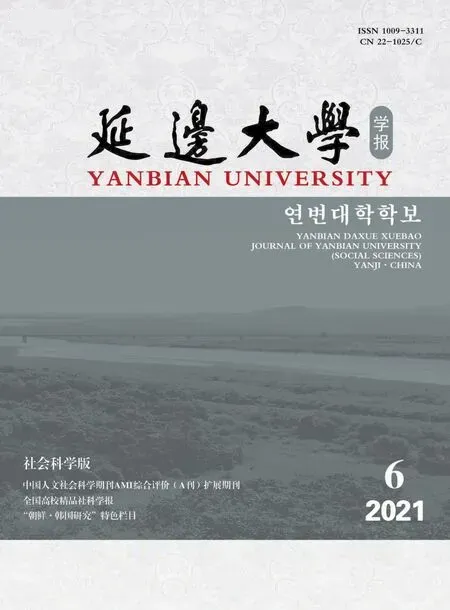中國流亡時期李相龍漢詩研究
張英美 金善華
縱觀韓國文學創作史,用漢字寫作一直是儒學學者的基本能力。即使在1443年創制韓文后,韓國儒學者們也仍然堅持用漢文寫作。19世紀末20世紀初,韓國掀起了國語運動,在整個東亞發生巨變的動蕩時局中,漢文創作也依然延續其脈絡,并始終在韓國文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10年后,眾多愛國志士流亡到中國繼續參加獨立運動,積極進行漢文文學創作,因而漢詩成為抗日文學的重要類型,成為流亡中國的韓國文人直抒喪權辱國之憤懣、報國無門之憾恨、恢復國權之期盼的重要手段。
這一時期,用漢文積極進行文學創作的志士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以活躍在上海、南京一代的文人金澤榮、申圭植為代表。金澤榮的漢詩憂時憫亂,有濃厚的感傷氣氛,抒發濃烈的以文保國的個人意志。申圭植則是在中國南方一代開展獨立運動的典型代表,他加入“南社”的目的在于尋求當時中國的主流政治勢力對韓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支持,其詩作有著大量的、與中國文人直接交流的抒寫。另外一批人以一直在中國東北地區帶頭開展獨立運動的抗日志士李相龍為代表,其漢詩創作集中體現了當時東北地區韓國獨立運動風貌。他通過中國經歷開展創作,并通過創作構筑了特有的文化意識,即對世界和時代的認知。且其一直堅持古體詩創作,作品風格沉郁頓挫、蒼勁有力,頗有杜詩遺風。可以說他既是以筆為刀發表戰斗檄文的革命戰士,也是將戰斗精神和革命思想落實到漢詩創作中的儒學義士,是當時韓國流亡詩人中進行獨立運動的主要人物,同時也是當時古體漢詩創作的代表性人物。
本文以李相龍在中國流亡時期創作的漢詩為研究對象,通過探究其行跡,考察當時的歷史事件如何投映在他的文學作品中,進而審視流亡中國的韓國儒學知識分子的漢詩創作所具有的特殊歷史價值。
一、流亡中國歷程與《石洲遺稿》
李相龍在1858年生于一個書香門第,家族世代為官,是當地的名門望族。初名為李象羲,字萬初,號石洲,相龍是流亡中國后改的名字。他最初學習性理哲學,并逐漸成長為嶺南地區著名的儒學大家。1886到1896年,倡導儒教的李相龍逐漸開始關注義兵運動并陸續開展了形式多樣、目標明確的恢復國權的斗爭。1905年乙巳條約后,曾一度親自組織義兵斗爭,但在1908年2月因日本軍隊突襲宣告失敗。在深刻認識到義兵抗爭的局限性后,他開始尋找新的突破口。1910年,韓國淪為日本殖民地后,在國內著手恢復國權變得舉步維艱。于是,1911年1月5日,時年53歲的李相龍帶領一家50多口人,流亡到了中國吉林柳河縣三源浦鄒家街。
在流亡地,李相龍積極投身到設立耕學社(1)“耕學社”1911年4月建立,是在中國吉林省柳河縣三源浦孤山子建立的韓國獨立運動團體。時任社長為李相龍,由其起草了“耕學社”設立趣旨文(綱要)。1912年建立扶民團,任會長,1914年設立西路軍政署,任督辦。([韓]安川著:《新興武官學校》,首爾:韓國教育科學社,2014年,第138-142頁;[韓]申斗煥:《石洲李相龍漢詩研究》,《韓文學論集》2011年第33輯,第129-130頁。)、建立新興武官學校(2)新興武官學校是韓國獨立運動時期李會榮在中國吉林省通化柳河一帶創辦的第一所武官學校,建校10余年,為抗日前線輸送了2 000多名新生力量。新興武官學校離不開李相龍的大力支持。等團結在華韓國人的工作中,并致力于以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革命活動。當時,在華韓國人的共同目標是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為整合所有的獨立運動團體,他受邀參加了1921年在北京召開的軍事統一會議。(3)即1921年4月在北京組織的韓國獨立軍團體代表會議。會上批判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外交獨立論,推崇了獨立戰爭論。1925年,被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任命為第一任國務令,但最終辭去職務,重新回到東北地區領導獨立運動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1932年5月,李相龍逝世于中國吉林省舒蘭縣,終年74歲。除了擔任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國務令在上海活躍約6個月外,其余時間他都在通化柳河縣一帶進行武裝斗爭。然而,經歷了22年漫長的流亡生活之后,他最終沒能看到祖國光復,在臨終之際對兒子李濬衡留下遺言:“只要我們的國家一天不被解放,就不要將我的骨灰帶到韓國。”
現存的李相龍遺稿集《石洲遺稿》,是其獨子李濬衡回國后,收集其生前的詩文和其他著述,花了整整10年時間整理和編輯的抄寫本,其影印本收錄于韓國高麗大學1973年出版的《石洲遺稿》(4)《石洲遺稿》收錄漢詩410首、辭1篇、疏1篇、書195篇、呈文4篇、告文1篇、序4篇、記3篇、輯說3篇、趣旨文4篇、辨1篇、祝辭1篇、說11篇、告由文1篇、祭文5篇、墓碣銘1篇、行狀4篇、傳1篇、雜著6篇、附錄里包括行狀1篇、《泣血錄》(上)挽詞78首、祭文34篇、《泣血錄》(下)祭文58篇。中。此外,一些沒有發表的漢詩和遺文,收錄于1996年出版的《石洲遺稿后集》(5)《石洲遺稿后集》中收錄了詩14首、書74篇、祭文8篇、雜錄5篇、謾錄1篇、記疑1篇、遺事1篇。中。兩部文集共收錄了李相龍漢詩424首,其中以中國經歷為基礎,寫于流亡期間的漢詩為214首。它不僅很好地展現了李相龍從傳統儒學者變成近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軌跡,同時也是韓國流亡志士在中國進行的獨立運動史的生動證言和歷史遺產。更重要的是,該文集也可作為中國漢字文化在韓國延續其脈絡的重要文獻資料。
目前,國內沒有對李相龍文學作品進行研究的相關著述。韓國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史學和文學兩個方面。后者主要以通過其作品考察其思想和時代面貌的研究為主。其中,有以李相龍全部漢詩為研究對象,圍繞作家分析其對時代的認識的研究;(6)[韓]金潤圭:《試論20世紀初漢詩的文學史特征——以石洲詩為中心》,《東洋禮學》2007年第17輯,第25-70頁。也有以李相龍詩歌為對象,側重于他的流亡生活對其詩歌影響的研究;(7)[韓]申斗換:《石洲李相龍漢詩研究》,《韓文學論集》2011年第33輯,第121-157頁。還有從文本語言學觀點出發,分析李相龍詩文學,重點考察其在中國流亡地的活動和國權恢復相關活動的研究。(8)[韓]扈光秀:《石洲李相龍流亡漢詩文本和互文性》,《中國人文科學》2005年第31輯,第558-595頁;《石洲漢詩“滿洲紀事”和“思故鄉”的文本性研究》,《中國人文科學》2006年第33輯,第237-259頁。除此之外,近期發表的學位論文(9)[韓]申素允:《石洲李相龍漢詩中出現的事物認知及意義》,碩士學位論文,韓國慶北大學,2018年。也可以說是其代表性成果。總之,多側重于李相龍在韓國獨立史上的地位及其文學造詣的論述,而對于李相龍的流亡者身份、以中國經歷為基礎的漢詩創作特征的探究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二、流亡體驗與民族意識
李相龍生活在一個西方列強入侵導致原有價值體系崩塌、新倫理觀尚未確立的思想混亂的時期。他是一位能夠適應時代變化,在每個關鍵時間節點靈活轉換救國運動應對方略的獨立運動家。起初他選擇了“義兵戰爭”這一武裝斗爭的救國方略,后來認識到沒有接受過常規武器和軍事訓練的義兵與用近代武器武裝的正規軍進行戰斗是盲目的。他認為之所以會面臨喪失國家權力的危機,是因為教育的缺失。此后,在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的影響下,他開始投身于愛國啟蒙運動。《石洲遺稿后集》中收錄的一篇《孔教微旨》就是簡略整理了梁啟超對其導師康有為學說的介紹。儒教的宗旨是孔子的大同思想,雖然它繼承于孟子的民本思想,但此后荀子的學說支配了中國學術思想界,孔孟學說一度中斷。康有為后來通過多種著述,以孔子的大同思想為武器掀起了中國儒學界的革命。李相龍在體驗流亡時期,受到這種大同思想的影響,并接受了20世紀20年代社會主義的平等思想,這些都可以在其流亡詩中窺見一斑,其詩文展現了客居流亡的流離之苦,又如實記述了他為獨立所做出的種種努力。
李相龍漢詩一方面發揮著儒學實踐和文化交流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向外界傳遞著韓國嶺南儒學派的世界觀及其處世哲學。流亡前的創作與他的最初身份無法割裂,詩作流動著清雅、幽靜的美感,文筆細膩、情韻悠長,獨具古典韻味。比較典型的是他的詠物詩,詩作中表現出了儒學家的傳統文學修養,并表達了想要立身揚名的情感。流亡后的詩歌作品無論在形式還是主題上,都呈現出新穎多樣的發展趨勢,表現出了深刻的民族意識、時代意識和抗日意識。亡國國民的身份,移居中國的經歷,使其創作多以現實生活和民族解放運動為主題,詩歌內容中時事或軼事占據了較大比重。由此可見,文學作品也是反映作家所處現實狀況的媒介,流亡前李相龍是一位忠實地記錄生活、認真地開展文學創作的文人和儒學家,而流亡后的李相龍,則是其流亡旅程和抗日斗爭經歷的記錄者,其流亡漢詩是亡鄉悲歡的現實寫照。
李相龍基于流亡生活體驗創作的漢詩,主要包括離鄉旅程、異國客愁、亡國之痛、關照現實的悲情等多種主題。從思想內容上又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展現自己在流亡地創作心境的詩,主要是以家人和親戚為中心,為延續儒教正統而創作的抒情詩;第二類是哀悼友人去世而創作的挽詩;第三類是游歷中國的紀行詩;第四類是在流亡旅程和流亡地所見、所感、所想而創作的詩歌。其中最多的是描述流亡旅程和定居地的詩,記述為恢復獨立國權而奮斗的抗日旅程的詩占很大比例。
對于流亡者來說,生活困窘是無法回避的困境。李相龍出身名門,從小生活優渥,但迫于國破家亡的悲慘困境,他帶領一眾家眷踏上流亡之路,這其中包含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一方面他要接受從富足安定到貧困流離的心理落差,竭力為整個家族尋求一線生機,另一方面他還為備受蹂躪的故鄉悲傷憤恨,立志為恢復國權而全力斗爭。在饑寒交迫中掙扎的他,詩歌中流露出來的是對過去的懷念、對現實的接納和對未來的期待。
山河寶藏三千里,冠帶儒風五百秋。何物文明媒老敵,無端魂夢擲全甌。
已看大地張羅網,焉有英男愛髑髏。好住鄉園休悵惘,升平他日復歸留。
——《去國吟》(10)[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24頁。
這首詩與梁啟超離開中國時創作的《去國韻》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對流亡地充滿著期待,然而,首先等待他們的就是殘酷的現實,離家去國的悲傷情緒真切地表現在詩中。但詩人并沒有喪失信心,祖國在他心中是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所在,如今這些美好盡毀,破碎的場景不忍卒讀,無力改變之時,暫且安頓下來,不要過于惆悵,總有一天會帶著希望回到故國。與傳統古體詩中的思鄉之情不同,流亡漢詩中的思鄉,除了對記憶中美好事物的懷念,情感重點往往放在對破壞這些美好的人與事的痛責上,以及對未來斗爭勝利的堅強決心和吶喊,詩中往往流露出強烈的斗爭精神和回歸意識。
朔風利于劍,凓凓削我肌。肌削猶堪忍,腸割寧不悲。
沃土三千里,生齒二十兆。樂哉父母國,而今誰據了。
既奪我田宅,復謀我妻孥。此頭寧可斫,此膝不可奴。
出門未一月,已過鴨江水。為誰欲遲留,浩然我去矣。
——《二十七日渡江》(11)[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25頁。
《二十七日渡江》這首詩是1911年1月27日越過鴨綠江時創作的,詩中描繪了刺骨寒風如劍一般無情地割走他身上的肉,繼而表達出割肉之痛可忍,背井離鄉的游子斷腸之痛孰又可知的心境,斥責故鄉肥沃的田地和房屋都被搶走了,還要覬覦我的妻子。詩人堅定著寧死不做亡國奴的信念越過鴨綠江,表明不會為任何人躊躇而堅決離去的決心。全詩突顯了殘酷侵略與頑強抵抗的尖銳矛盾,在此類離開故國時所創作的作品中,哀傷憤慨的悲壯美充斥著全詩。和其他的流亡者一樣,對流亡地飽含期待、希望在現實面前崩塌,被苦難、饑餓以及作為一家之主的壓力所包圍的無力感,都為他的詩增添了一份哀傷美。
破屋三間掩莽榛,經年未掃沒勝塵。風紙喧來何國語,氷牀凍作別人身。
鼎冷蘇郎啗有雪,廚空句踐臥無薪。上天豈是尋常意,偏俾男兒飽苦辛。
——《懷仁縣北山賃空宅為暫留之計》(12)[韓]李濬衡:《石洲遺稿》, 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 1973年,第25頁。
《懷仁縣北山賃空宅為暫留之計》表現的是渡江后的流亡旅程更加艱苦,他們要忍受東北地區的嚴寒。在多年無人居住、布滿灰塵、擋風紙嗡嗡作響的破敗茅草房內,躺在冰冷的床上睡覺。身體凍僵已經沒有知覺,但他認為這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考驗,并借中國的蘇武和越王勾踐來比喻自己的處境,堅定了流亡斗爭的決心。
布衾年久冷如霜,遠客無眠秋夜長。故國魂歸云萬疊,窮山家住木千章。
黃金盡逐賓朋散,白發偏驚歲月忙。未死難忘惟一事,腰間時吼怒龍光。
——《大牛溝秋夜》(13)[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27頁。
《大牛溝秋夜》首句用環境的艱苦來襯托現實的煎熬,二三句分別用夢境和現實、過去和現在做對比,表現出思念祖國又不得不面對現實的苦悶。結尾句言明至死難忘的志向——為了獨立而斗爭,就像插在腰間的龍川劍一樣。這首詩表達出堅定的流亡斗爭意志,這既是在流亡地克服生活之苦的意志,也是為了定居而做出的苦苦掙扎。
元朝五十五番新,此日堪悲去國身。萬壽蓬宮回寶甲,百年楸壟廢精禮。
明知薪膽終存越,肯效袖椎誤擲秦。七尺極寒元細事,諸生學藝最關神。
——《元朝》(14)[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27頁。
《元朝》詩中,詩人引用“臥薪嘗膽”和“朱亥袖椎”的典故,表明自己如今縱是可悲的“去國身”,也要學習中國古代義士,忍辱負重、籌劃救國之策。如今身體饑寒交迫備嘗艱辛,但皮肉之冷暖本來就是瑣碎的事,對學生們的教化才是重中之重,只有學生們學到了知識,革命才會后繼有人,復國才有希望。全詩流露出在流亡地堅定生活下去的意志、籌謀反攻的堅強決心和復國必勝的堅定信念。
“對大多數流亡者來說,難處不只是在于被迫離開家鄉,而是在當今生活中,生活里的許多東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鄉其實并非那么遙遠,當今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對故鄉一直可望而不可即。因此,流亡者存在一種中間狀態,即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于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15)[巴勒斯坦]愛德華·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20年,第61頁。這段文字非常準確地描述了流亡者的生存狀態和處世心態,這種態度通過文學作品反映到現實中來。從李相龍流亡初期的漢詩來看,描寫嚴寒和貧苦的詩句特別多,這是他作為流亡者最初與家鄉割裂開來的撕扯之痛,被迫流亡心懷悲憤,現實一再提醒他前方充滿艱難險阻,貧寒交加的肉體困頓是其充滿悲憤焦慮的思想在現實生活中的投射。因而在懷鄉感傷的同時,李相龍只能通過與流亡人士的交流,吐露自己生活和思想的困境,抒發身為異國人的苦悶和喪失國家的悲憤。作為獨立運動家,他堅信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為了將祖國改變成自己理想中的狀況而獻身和努力。
三、斗爭實踐與聯合抗日
作為流亡者,除了生活空間的變化,還要面對政治體制不同所帶來的陌生感與疏離感。這一掙扎狀態從表面看表露為極為感性的回憶或回歸故鄉的意識形態,但其實深深扎根于克服流亡、實現光復的強烈意志之中。這種意志會直接轉化為對獨立斗爭的堅定信念,流亡可以說是獨立意志這一情感的行為外化。
李相龍定居中國東北地區時期的活動大致可以概括為四類:第一,維護在華韓國人的社會經濟穩定;第二,組織建設自治機構,使其成為獨立運動的根據地;第三,設置民族教育機構、進行教育活動,為此,建立了包括新興武官學校在內的很多團體;第四,設置兵營,以便為新興武官學校畢業的青年們提供系統的軍事訓練。可見,李相龍的流亡生活與獨立運動是交叉重疊的,這在他的漢詩中表現為頻繁出現的地理名稱,如通化、柳河、三源浦、朝陽鎮、下松崗、磐石、舒蘭、干溝、吉林、樺甸等。借助詩的形式,把真實經歷的重要事件按照時間和轉移方位順序進行陳述,既是對歷史事實的忠實記錄,又是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悲慨之情的揭露。
倭騎跳踉兩旅團,所過屠殺血成瀾。
貫盈爾罪天應厭,惡報昭昭待后看。
——《聞日兵所過燒殺延琿等地盡化灰燼》(16)[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32頁。
《聞日兵所過燒殺延琿等地盡化灰燼》中,詩人聽聞日軍燒殺擄掠無惡不作,所過之處生靈涂炭、血流成海,延吉、琿春等地化為灰燼,詩人痛斥日軍犯下如此滔天罪惡為天理所不容,天道循環、報應不爽,日后定然自食惡果。全詩充斥著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為的憎恨,又表現出抗爭無果,只能借助天道、報應等理念來求得暫時的安慰。
李將兵機敵手無,五團聯合討頑胡。
從此中東關系密,驕倭不敢進安圖。
——《倭寇連絡胡匪劫掠安圖知事以李青天為討匪司令聯合五團發向縣街》(17)[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32頁。
《倭寇連絡胡匪劫掠安圖知事以李青天為討匪司令聯合五團發向縣街》中,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作者以有效抵抗事件為例證,發出“只有中朝兩國聯合抵抗才能取得勝利,傲慢的倭寇才不敢貿然侵入”的號召。接著在《敵兵東西挾進安圖知事屢請我軍退避不得已暫移東崗》中寫到“縣官憂懼敵兵強,固請移軍別處藏;實力未完時未到,不妨暫退向東崗。”(18)[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33頁。安圖縣的知事擔心敵兵強悍,勸我軍隊先轉移到其他地方躲起來,詩人認為實力確實尚不足夠,時機也不成熟,于是順應了知事的想法,答應向東江離去。充分體現了李相龍從現實出發,采取了暫避鋒芒、保存實力的迂回抵抗策略。還把日軍的暴行比喻成瘋狂的狗,痛斥道“狗性冥頑猶怕死,見人虛始猖狂”“禍福皆從身上發,勿須驚動自招殃”,(19)[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33頁。并勸誡他們禍福相依,他日的災禍皆由自己的行為而起,警告他們不要恣意妄為招來禍患。接著,他又如實地表達了對中國人的贊揚與感激之情,在中國人的幫助下,韓國的獨立軍戰士們成功躲避了倭寇掃蕩。“槍砲森圍搜索急,一身無地可圖生;鄰婦翼藏堪警世,華娃高義越常情。”(20)[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33頁。這首詩中講述了倭寇大肆搜捕時,一位鄰家的中國婦女用裙子遮住獨立軍將士,救了他一命的故事。中國婦女的勇敢與義氣足以感動世人,高尚的情操已超越國界。
這些流亡詩,很好地展現出中韓聯合意識,即在中國的獨立運動并不僅是韓國亡命之士的責任,還體現出中韓兩國共同擊退日本侵略的聯合抗日意識。李相龍聽到孫中山逝世的消息后,創作了挽聯來緬懷:
推翻獨裁帝制,為東洋革命領袖。
提倡三民主義,啟后日大同基礎。
——《挽孫中山先生》(21)[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49頁。
挽聯闡明孫中山先生是打破獨裁和專制制度的東洋革命領袖,為提倡三民主義的日后大同社會奠定了基礎。用簡潔的語言概括了先生生前的功績,作品寫于1925年,當時李相龍已經年過花甲,獨立運動讓他殫精竭慮,身體也日漸老去,依然沒有看到復國的希望。這位中國革命領袖的逝世,對當時的東亞革命者是個沉重的打擊。因而李相龍沒有再發出豪言壯語,而是陳述了事實,希望后人能夠看到前輩在黑暗中指出的道路,堅定地走下去。
李相龍一直以中國東北地區的韓國人為中心組織開展獨立活動,因此,他的流亡詩中沒有體現與中國文人交往的痕跡。但是,他以呈文的形式寫了《中華民國國會提議書》《呈柳河縣知事請入籍文——代韓僑作》《呈柳河縣知事文》。《與吉林總督筆話》《韓僑所請聽不聽之利害》等文章是他向柳河縣知事和吉林總督請愿加入中國國籍,并一直為韓國移民在中國的生活保障問題做著不懈的努力。他的這些文章,使流亡中國的韓國文人能夠在生活和斗爭中更好地融入中國文化,在促進中韓文化交流等方面發揮了積極推進作用。
四、文化體驗與精神感悟
李相龍在中國流亡期間為了民族解放運動走遍了東北地區,每到一個地方就用詩歌來抒寫自身的處境和異域風情,采用以物喻人、以古諷今、對比等手法,抒發著囿于現實、壯志難酬的憤懣,但同時又被古代義士的拳拳報國心所鼓舞,有著堅持到底、永不氣餒的抗日決心。其紀行詩可分為三類:一類是輾轉流亡地區時創作的,一類是行經北京時創作的,還有一類是寫于上海臨時政府第一任國務令任上。
《滿洲旅游次李紫東正模松京懷古韻》(22)[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32頁。是其游歷長白山、開原、遼陽、鳳凰城、懷仁、寧古塔、遼西、吉林、興京等地的組詩,真真切切地吟詠出身處異國的思鄉情懷。如描寫長白山“插天白岳雪長飛,三面滄溟遠作池”,而“圓柵家家上夜燈,甲杯洗進乙杯仍”描寫了開原酒家場景,則被視為散發著他鄉風土人情的名句。“淤泥河外柳連天,秉義殷師此碇船。生死一心方是圣,幽宮今在亳蒙邊”吟唱的是一個無處可去的游子的悲傷和思念盡情地撒在了異國他鄉。“一曲悲歌萬斛淚,松江落日酒初醒。吾東不乏金興武,會見長歌入漢城。”(23)[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30頁。讓人想起遠在故鄉的親友,充滿著鄉愁的黃昏讓凄涼之情在異國游子的心中回蕩。
李相龍流亡紀行詩真實記錄了作者走遍中國山川的所見所感,如前往北京旅途中的紀行詩《過山海關》和《望萬里長城》。
汽輪暫逗眼簾寬,名勝中州第一關。宇宙如空前面海,云煙長鎖兩邊山。
唐宗駐蹕連環古,秦帝須仙寶鼎寒。日出扶桑何處是,狂氛蕩漾欲無還。
——《過山海關》(24)[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35頁。
《過山海關》強烈地表達了對日本的蔑視之情,“扶桑”隱喻日本。李相龍面對雄偉壯闊的山海關,聯想到中國歷史上以唐太宗、秦始皇為代表的帝王,他們能征善戰、開疆拓土、戰功赫赫、一統天下,剛剛“崛起的扶桑”與之相比渺小而不值一提,表達了對日本不能正確判斷自己實力、瘋狂擴張行為的輕視,同時,也流露出對中國在東亞反法西斯戰場上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的期待。
費力耗財筑土城,何如團合眾心成。
當年若改牛毛政,黔首應無赤幟迎。
——《望萬里長城》(25)[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35頁。
《望萬里長城》中李相龍看到萬里長城發出疑問,耗費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修筑長城,不如團結眾人之力抵御外敵。1921年北京之行,他目睹了各團體紛紛解散以及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存在的種種弊病,他思考如何引導眾人團結。“牛毛政”指像牛毛一樣多而無效卻束縛著百姓的錯誤政治制度,實則是對眾團體各自為政、不能一致對外現狀的指責。
到了北京,李相龍游覽了北京的名勝古跡有感而發創作了關于北京的紀行詩:
圖書亂鋪文華殿,鐘鼓無聲五鳳樓。
幼主安知軍國策,媾和老將弄好籌。
——《入皇宮》(26)[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36頁。
《入皇宮》前兩句用文華殿散落著書籍的荒誕景象來表現與紫禁城有關的亡國歷史,再無皇帝出行鐘鼓之聲的五鳳樓,喻示皇室已經不復存在。后兩句描繪了中國帝制終結的關鍵時間節點,年幼的宣統面對軍機國策一無所知,以醇親王為首的政界官僚們玩弄著有利于自己的權謀,推動了亡國進程。李相龍由過去聯想現實,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因此,他坐在皇帝曾住過的乾清宮內說:“自見易主,都城宮殿空處,自不禁慨然與感也”,(27)[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47頁。即該詩是從自己作為亡國遺民的角度,看到有著相同歷史的紫禁城,實屬情難自禁,借景抒情,宣泄悲憤。
作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特邀國務令,他在天津乘坐愛仁號艦船到上海的途中,在山東海遇到風浪。吟誦了如下詩篇:
山東海路最多艱,風浪翻空噴雪山。
泛入水天相接處,此行應占上仙班。
——《山東海遭風》(28)[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47頁。
山東的海路險道最多,被狂風卷起的風浪就像從雪山中噴出的雪一樣,漫延至水天相接的地方,這次巡行應該算得上神仙班列。身處滔天風浪,尚能玩笑吟誦。“帝遣黃龍試禹船,中流發嘆至今傳。豈是圣人心不懼,力難容處只聽天。”(《風浪危險舟中戲吟》(29)[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47頁。)稱一人之力難以對抗天意,實則是對自己無法改變獨立運動的現狀的無奈,最終因意見不合他辭去國務令一職,回到自己居住的流亡地。
除此之外,李相龍漢詩中經常借用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來弘揚流亡志士堅守理想、英勇不屈的偉大精神,如:“入島吾非齊壯士,渡江誰是楚漁夫。諸君勿以衰頹棄,致力他時不愛軀。”(30)[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26頁。(《寄呈李半翁笑云》)詩中借隨田橫而死的五百義士——“齊壯士”類比流亡志士,進而表達整個流亡志士群體為爭取國權甘愿犧牲的堅強決心。其他諸如魯仲蓮、嚴子陵、越王勾踐,清廉謙讓的伯夷、叔齊,在匈奴被扣留19年的漢朝使臣蘇武,刺殺秦始皇的荊軻,宋代隱匿者陳摶等中國的豪杰之士,都在李相龍漢詩中一一呈現。他們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精神品質,深深地嵌入了詩人的理想世界,這些人物既是精神領袖,又是形象自喻,借助他們,詩人在面臨喪權辱國、恢復無期的困境面前,依然頑強地維護著自己的儒學風尚和堅定的意志。
詩人雖然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但是獨立運動始終沒能拿出統一戰線方案,李相龍在歲月面前感嘆自己的無力。
吾非勇士是書生,事業難期智力成。
白首風埃還自笑,扁舟歸釣五湖汀。
——《滿洲紀事》(31)[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43頁。
《滿洲紀事》中描寫了李相龍苦苦掙扎了十多年以后,面對復國無望和自己年已遲暮的現實,他寫道“我不是勇士,是書生,能靠智力完成事業這件事是令人期待的。但在這風塵世間,已然白發蒼蒼垂垂老矣,面對現實我反而笑了出來,坐著一葉扁舟,想著要不下午回去釣個魚吧”。因此,他漸漸不再出席政治活動。李相龍晚年時期創作的漢詩,更多的是描繪隱逸生活的景象或對親情及友情之愛,這種愛則蘊含著流亡族裔之間的互助互愛意識。
五、結語
李相龍作為出身高貴的儒學學者,在經歷了喪權辱國、抗爭失敗的痛苦掙扎后,轉戰中國東北地區開展獨立運動。是那個時代的文人志士,一邊為恢復國權而英勇斗爭,一邊通過創作發出痛苦吶喊和精神感召的典型代表。其流亡漢詩是作為離家去國的流亡者身份,在中國語境下、以特殊的中國經歷為基礎創作的,其詩作具有政治上抵抗外敵入侵、文學上應對西方文化侵略、文化上堅守傳統漢文學強烈意志的鮮明傾向。
同時,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他的詩歌呈現出深刻的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和繁盛的古典風采。比如,他在《甲寅元朝》中寫道:“神龍變化淵將躍,精衛工夫海欲填。早晩時機應到手,只嫌鬢發異前年。”(32)[韓]李濬衡:《石洲遺稿》,首爾: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28頁。此詩將《易經》乾卦之九四“或躍在淵”和《山海經》中“精衛填海”的故事進行化用,表達出做事要韜光養晦、積蓄力量,時機成熟方能取得成功的人生哲理。這其中蘊含了中國古人的處世哲學和文化理念,可見詩人吸納了中國傳統文化并具有了自己獨特的精神感悟。
另外,其詩歌呈現著現代中韓文學交流的一個斷面。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流亡文人通過詩歌對抗侵略,積極倡導中韓聯合抵抗入侵,是當時流亡志士致力于恢復國權的堅強意志在文學領域的投射,其作品的中韓合作思想表現尤為明顯,在韓國現代流亡文學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有著特殊的文化交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