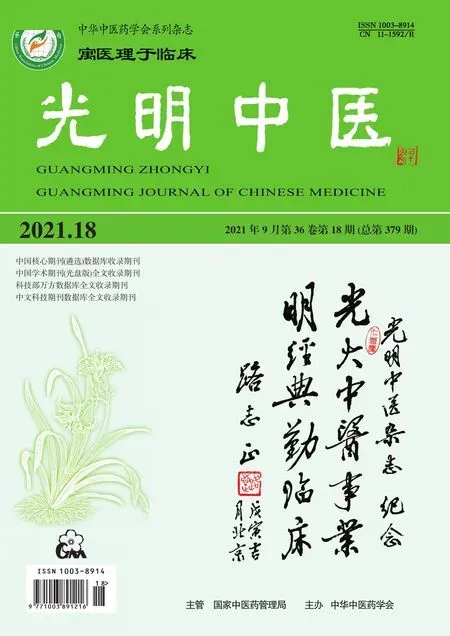陳士鐸運用補中益氣湯解析*
胡鑫才 賀 丹 張光榮 張政杰 郭榮傳
陳士鐸,字敬之,號遠公,浙江山陰人,為明末清初的著名醫家。陳氏一生著述頗豐,然流傳至今者僅《石室秘錄》《外經微言》《脈訣闡微》《本草新編》《辨證玉函》《洞天奧旨》《辨證錄》《辨證冰鑒》《辨證奇聞》,而后3種屬于同書異名、異版[1]。國醫大師張燦玾曾有言[2]:“先祖嘗云:大凡諸病用常法治療無效時,可于《石室秘錄》中檢方一試。后吾在臨診時,遵守此訓,獲益良多”。據李今垣[3]統計,《辨證錄》全書共計用方1643首,其中古方計114首,占6.3%,陳氏自制方占93.7%。所用古方比例較小,而所用古方中,對李東垣補中益氣湯評價甚高,曾言[1]“夫東垣先生一生學問,全在此方,為后世首推,蓋不知幾經躊度精思,而后得之也,豈漫然哉”。本研究以分析陳士鐸運用補中益氣湯為切入點,學習其觀點與經驗,為擴大臨床應用補中益氣湯適用范圍啟發更多的臨證思路。
1 陳士鐸著作中補中益氣湯臨證運用總覽
在現存的陳士鐸著作中[1],共記載30例運用補中益氣湯的案例,具體為《辨證錄》15例、《洞天奧旨》9例、《石室秘錄》6例,其中有2例在治療過程中根據病情變化又對初診所用補中益氣湯進行了加減。因此,補中益氣湯共使用32次,其中有4次僅列方名,未明確具體藥物劑量。28次有具體藥物劑量的用方中,每味藥的劑量跨度較大。如黃芪,從1錢5分到1兩不等,多數用量為3錢;又如升麻,從2分到5錢,甚至有去而不用者,多數為4分、5分;人參、白術用量從1錢到1兩;其他藥物劑量范圍分別為:當歸1錢到5錢,陳皮2分到1錢,柴胡3分到1錢,甘草1分到2錢。以上8味藥中,黃芪、人參、白術、甘草為必用之藥。大抵黃芪、人參、白術的劑量與病證所在部位有關,上焦者用量偏輕,下焦者用量偏重,中焦者則用量中等。記載的30例醫案,涉及的病癥有冬月傷寒、頭痛、春溫、痙痓、癥瘕、癆瘵、小便不通、內傷、不孕、妊娠惡阻、胞衣不下、腳疽、骨痿瘡、內外臁瘡、傷守瘡、胎窬瘡、臍漏瘡、凍瘡、水漬手足丫爛瘡、瘡瘍腫潰、血痢、痿證、氣虛下陷等。具體使用時均有藥物加減,所加藥物有萊菔子、茯苓、金銀花、熟地黃、牡丹皮、山萸肉、生姜、紅棗、炮附片、肉桂、玄參、桑葉、防風、白芷、茯神、炮姜、黑干姜、神曲、貝母、桂枝、蔓荊子、川芎、天花粉、白芍、麥冬、黃芩、半夏、牛膝、金釵石斛等。病患服藥途徑多樣,除了病患自己服藥,在治療小兒病證時還可讓病兒之母服藥,患兒食母乳以治病。如胎窬瘡(乃初生小兒背上或有一二孔也),認為此等小兒,是臟腑不足,少氣少血,善后治療時用補中益氣湯,“與母吞服,兒食其乳”[1]。
2 陳士鐸對補中益氣湯的認識
常規將補中益氣湯作為補氣類方劑,其有補中益氣、升陽舉陷的功效。李東垣立本方以治氣虛發熱,病由飲食勞倦、損傷脾胃所致[4],陳士鐸認為補中益氣湯治內傷之神劑,提陽氣之圣藥[1]。李東垣立本方有言:“夫脾胃虛者,因飲食勞倦,心火亢甚,而乘其土位,其次肺氣受邪,須用黃芪最多,人參、甘草次之……胃中清氣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黃芪、人參、甘草甘溫之氣味上升,能補衛氣之散解,而實其表也;又緩帶脈之縮急……氣亂于胸中,為清濁相干,用去白陳皮以理之,又能助陽氣上升,以散滯氣,助諸甘辛為用……陽旺則能生陰血,更以當歸和之”[5]。陳氏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認識到本方可大補血,通過大劑的人參、黃芪來生氣血,而氣血旺盛則更利于氣血流通,如言“補中益氣湯原是大補氣血之神劑,多用參、芪尤為補氣,氣旺而血自旺,更能流行也”[1]。陳氏贊同李東垣柴胡、升麻升提之說,且更進一步說明兩者升提的不同點,“妙在用柴胡、升麻于參、術、芪、歸之內,一從左旋而升心肝腎之氣,一從右旋而升肺脾胃命門之氣,非僅升舉上、中二焦之氣也”[1]。使后世對本方補氣并升提的作用特點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方劑中藥物的用量及藥物間的比例對方劑功效影響較大,如陳氏體會到,“方中用柴胡原能祛邪也,少用之于補藥之中,則能提氣以衛正;多用之于補藥之中,則能益氣以祛邪,故用至三錢,而風難再留矣,何必更借重他藥散風之多事哉”[1]。
另外,李東垣的立方本旨是“脾胃一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芪以益皮毛而閉腠理,不令自汗,損其元氣”[5]。而陳氏則認為人參、黃芪、白術之間相互配合,才能夠發揮補中益氣的持續作用,言“人參得黃芪,兼能補營衛而固腠理,健脾胃而消痰食,助升麻、柴胡,以提氣于至陰之中,故益氣湯中無人參,則升提乏力,多加黃芪、白術,始能升舉。倘用人參、白術而減去黃芪,斷不能升氣于至陰也”[1]。可見,李東垣是以黃芪益肺固表止汗,陳氏認為黃芪本身具有升提的作用。
3 陳士鐸對補中益氣湯中藥物的認識
補中益氣湯由黃芪、人參、白術、當歸、升麻、柴胡、陳皮、甘草等藥組成,陳氏對黃芪、人參、白術的功效作用認識與現今的看法基本一致,具有益氣健脾等功效。獨特的認識在于認為黃芪[1]其功用甚多,而其獨效者,尤在補血……故氣虛之人,毋論各病,俱當兼用黃芪,而血虛之人尤宜多用。惟骨蒸癆熱與中滿之人忌用,然亦當臨癥審量……氣逆之虛,必用人參,而不可用黃芪……若氣雖虛而無逆,則久病正宜黃芪,未有不服之而安然者也。人參[1]的特殊之處在于,能入五臟六腑,無經不到……人參氣味陽多于陰,少用則泛上,多用則沉下。故遇肝腎之病,必須多用之于補血補精之中,助山萸肉、熟地黃純陰之藥,使陰中有陽,反能生血生精之易也。而認為白術尤利腰臍之氣[1]。
對其余幾味藥的認識則另有獨論。如世人多認為甘草在方劑中不過調和,在方中處于無關緊要的地位,甚至出現有人每方必加甘草以調和。但陳氏認為甘草[1]實可重用以收功,而又能調劑以取效,蓋藥中不可缺之藥,非可有可無之品也。考《脾胃論》補中益氣湯原文,黃芪與甘草等量而用且為單味藥劑量最大的藥味。不過陳氏使用補中益氣湯時,甘草明顯比黃芪用量小,當為佐使之用。當歸,具有補血活血、調經止痛功效,在補中益氣湯中作為佐藥發揮補血功用[4]。而陳氏認為,當歸[1]其性甚動,入之補氣藥中則補氣,入之補血藥中則補血,入之升提藥中則提氣,入之降逐藥中則逐血也。而且用之寒則寒,用之熱則熱,無定功也……當歸是生氣生血之圣藥,非但補也。認為當歸在此是有益于氣血兩生,即是從氣血互生互化的關系來認識的。
以上所論藥物偏于補益,陳氏對柴胡、升麻、陳皮的功用認識別具只眼。柴胡[1],用柴胡以提氣,必氣虛而下陷者始可……柴胡提氣,必須于補氣之藥提之,始易見功……蓋升提之力,得補更大……補中益氣湯之妙,全在用柴胡,不可與升麻并論也。蓋氣虛下陷,未有不氣郁者也。惟郁故其氣不揚,氣不揚,而氣乃下陷,徒用參、歸、芪、術以補氣,而氣郁何以舒發乎。即有升麻以提之,而脾胃之氣,又因肝氣之郁來克,何能升哉。得柴胡同用以舒肝,而肝不克土,則土氣易于升騰。升麻[1],能升脾胃之氣……升麻與柴胡,同是升提之藥,然一提氣而一提血……柴胡、升麻同用之補中益氣湯者,各升提其氣,兩不相顧,而兩相益也。柴胡從左而升氣,升麻從右而提氣,古人已言之矣。然而柴胡左升氣,而右未嘗不同提其氣,升麻右提氣,而左亦未嘗不共升其氣,又兩相顧,而兩相益也。陳皮[1],和中消痰,寬脅利膈,用之補,則佐補以健脾;用之攻,則尚攻以損肺。宜于補藥同行,忌于攻劑共用……夫補中益氣湯中用陳皮也,實有妙義,非取其能寬中也。氣陷至陰,得升麻、柴胡以提之矣。然提出于至陰之上,而參、芪、歸、術,未免盡助其陽,而反不能遽受。得陳皮,以分消于其間,則補不絕補,而氣轉得益。由此可見,補中益氣湯的功效固然依靠人參、黃芪、白術、甘草等味,但脫離了升麻、柴胡、陳皮、當歸則不能安全穩定地發揮其提氣升陷的作用。
4 陳士鐸對補中益氣湯的靈活應用
補中益氣湯原為治內傷而設,陳氏廣其用,所治病癥不限于內傷。如治冬月傷寒[1]、遇春而頭痛[1]、春月感冒風寒[1]、痙病[1]等外感病證,用補中益氣湯加減而取得良好療效。分析其因則為外感病之中,亦有內傷之病,正不可拘于外感,而不思變通之方。正是陳氏認識到補中益氣湯,在補正之中而仍有祛邪之效,故兼用之而成功。治內科似實而虛的病癥,如癥瘕[1]、小便不通[1]等,皆因氣虛下陷,又據不同具體病癥進行化裁,如“癥瘕之塊,未必無痰涎之壅。加半夏入于陳皮、甘草之中,則消痰而又不耗氣,同群共濟,發揚陽氣之升,即有邪結無不散矣”。小便不通是因“脾胃虛而九竅皆為之不通”,病機變化不涉及其它,治療以原方即可。
肥胖婦人不能受孕,常規認為此為痰濕內盛所致,陳氏則深入分析其成因,認為“婦之濕,實非外邪,乃脾土內病也”[1]。因此,治療以急補脾土、瀉水化痰,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而且治本病時重用白術,這是陳氏在治療痰濕病癥時的常用活法。如治妊娠惡阻[1],出現足腫等水濕之癥,也是重用白術、茯苓,陳氏認為“夫重用茯苓于補氣之中,雖是利水,仍是健脾清肺。凡利水之藥,多耗氣血,茯苓與白術補多于利,所以重用以分濕邪,即所以補氣血耳”。可見陳氏靈活應用補中益氣而又有其法度。又如治清氣下陷難升所致的胞衣不下[1],方中當歸用量明顯增加,此為顧及產后的生理病理特點而化裁。
陳氏不僅在內科、婦科病癥中運用補中益氣湯,外科病中使用也不少。《洞天奧旨》是一部外科專著,其中記載了多個用補中益氣湯治療的病癥,如骨痿瘡、內外臁瘡、傷守瘡、胎窬瘡、臍漏瘡、凍瘡、水漬手足丫爛瘡、瘡瘍腫潰等。陳氏治療外科病癥,需大補氣血時常以補中益氣湯,另以大劑金銀花為其特點。認為金銀花性補,善解陰毒,得參、芪而其功益大[1]。另外,在內服湯藥的同時,外用膏藥、散劑或艾灸等內外合治。
5 學習陳氏后的驗案舉例
陳氏記載的運用補中益氣湯未見有治療頭面病癥。通過研究陳氏對補中益氣湯的論述,曾用本方化裁治療頭部皮膚病而取得良好療效。現舉1例如下。
李某,男,39歲,2018年9月13日初診,病歷號2018091301037362。患者2月余前無明顯誘因出現頭部皮膚起散在紅疹伴疼痛及膿性分泌物,曾服中藥(具體不詳)無明顯緩解,皮疹發作無明顯加重因素。刻下:頭部皮膚散在起紅疹伴疼痛及膿性分泌物,部分結痂,食欲佳,睡眠安穩;飲水量偏少,無口干口苦;大便日行1~2次,成形,不干,色未察;小便無所苦,有時尿黃;軀干四肢皮膚不癢。走路稍長即覺下肢累,上4樓即氣急。能出汗,下肢無汗。脈略弦緩;右不流利,寸關偏沉弱,尺略旺;左略細。舌略暗紅,苔白底、根略黃厚膩。體型中等,咽無濾泡。既往史:11年前頭皮及全身皮膚癢,服中藥后好轉。偶飲酒,吸煙日均10支,無運動鍛煉習慣。否認過敏史,母親有高血壓病。診斷:毛囊炎。辨證:氣虛營瘀,濕熱毒表證,氣下陷。治以補中益氣升陷,通營祛濕解毒,以補中益氣湯為基礎方。藥用:生黃芪18 g,黨參15 g,炒白術10 g,岷歸尾10 g,陳皮6 g,藿香10 g,酒赤芍10 g,甘草10 g,忍冬藤15 g,土茯苓15 g,柴胡5 g,升麻15 g。予7劑。水煎沸40 min,每日1劑,每日2次,飯后1 h溫服。
二診日期2018年10月8日:服藥4劑后頭皮紅疹消退,未再發;素入睡難,無多夢。脈略緩;右不流利,寸關偏沉弱,尺略旺減;左略細弦。舌略暗紅,苔白底,根略黃厚膩。2018年9月18日查肝功能、血糖、糖化血紅蛋白,結果均正常。處方:生黃芪30 g,黨參15 g,炒白術10 g,岷歸尾10 g,陳皮6 g,藿香10 g,酒赤芍10 g,甘草10 g,忍冬藤15 g,土茯苓15 g,柴胡5 g,升麻15 g,綠萼梅10 g,生地黃10 g。予10劑。水煎沸35 min,每日1劑,每日2次,飯后1 h溫服。1年后隨訪,頭部皮疹未再發。
按:患者氣虛氣陷體現在稍勞即感氣急、下肢累,脈緩(無運動鍛煉習慣),右脈寸關偏沉弱。在補中益氣升陷的同時,以甘草、忍冬藤、土茯苓、升麻解毒祛濕,岷歸尾、酒赤芍通營活血。服藥后病癥好轉,但左脈仍見細弦、入睡難,陳氏曾言氣虛未有氣不郁者,因此加綠萼梅加強解郁并加大黃芪用量,生地黃養陰清虛熱。以上治療方案均源于學習陳氏經驗后的運用。
6 小結
陳士鐸對補中益氣湯推崇備至,認識深刻,運用自如,應用補中益氣湯治療的病證范圍廣。認為補中益氣湯全方藥味之間配伍嚴謹,具補中益氣、升陽舉陷之功,且各藥在此方的作用均缺一不可。如人參、黃芪、白術、甘草具益氣之功,但無升麻、柴胡不足以升提陽氣,而僅有升麻、柴胡則升提無力。人參、黃芪、白術之間也構成了一個相須為用的組合,人參保障升提有力,黃芪、白術保障生氣升氣,三者不可或缺。具體應用之時,根據病變部位和具體病機及兼夾病癥進行藥量比例的調整,其中又有一定的規律可循。補中益氣湯是大補氣血之劑,而不囚于補氣升陷之論,因此在外科病癥的陰證中多有使用。總之,學習陳氏對于補中益氣湯的認識和運用經驗,有助于擴展靈活應用補中益氣湯,擴大本方應用范圍。而不限于治療氣虛發熱及內臟下垂等病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