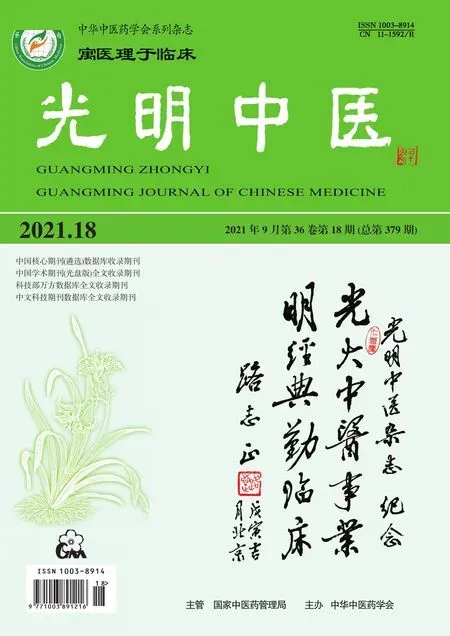黃芪治療原發性高血壓研究進展
李若愚 刁建煒 張蘊慧
黃芪味甘,性微溫,歸脾、肺經,有補氣升陽,固止表汗,利水消腫,生津養血,行滯通痹,脫毒排膿,斂瘡生肌之效,是臨床常用的補氣藥。也因黃芪的補氣作用,使人們在其降壓作用上存在誤解:即為補氣藥又何能降壓?然而,黃芪在臨床上治療以氣虛為主的原發性高血壓有很好的效果,同時越來越多的基礎研究證實了黃芪含有降壓成分。
1 原發性高血壓發病機制
1.1 西醫學認識西醫學認為原發性高血壓主要與發生縮血管物質作用力增強,舒血管物質作用力減弱有關。其主要活性物質有腎素、心鈉素、交感神經系統、一氧化氮合酶/一氧化氮、內皮素、胰島素、同型半胱氨酸。除了這些內源性物質之外,原發性高血壓的發生還與飲食、氣候、吸煙、家族性遺傳、種族差異、鹽敏感性這些環境與遺傳因素有關[1]。現在臨床上主要應用的降壓藥物主要有通過減少心排出量和降低外周血管阻力的利尿劑,抑制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RAAS)系統的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ACEI)和血管緊張素Ⅱ受體阻滯劑(ARB),阻滯鈣離子通道的鈣離子通道阻滯劑及降低心排出量的β受體阻滯劑。
1.2 中醫學認識原發性高血壓為現代醫學病名,中醫學古典文獻中無相應病名,因此與高血壓相對應的中醫病名一直未確定,既往多數醫家根據“頭暈”“頭痛”等高血壓病常見臨床癥狀將其歸為“眩暈”“頭痛”“眩暈”“頭風”“肝風”范疇[2,3]。原發性高血壓的發生發展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諸如先天稟賦不足、七情所傷、飲食失節、內傷勞損、生活環境及方式等。其形成機制論述不一,防治各異。2002年《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將高血壓分為肝火亢盛、陰虛陽亢、痰濕壅盛和陰陽兩虛證4個證型。原發性高血壓病因病機復雜,目前沒有統一的辨證分型。現代大量研究表明原發性高血壓還有氣虛痰瘀、陰虛陽亢、肝腎陰虛等證型[4,5]。
2 黃芪治療原發性高血壓的基礎研究
2.1 有效成分分析黃芪的有效成分主要包括多糖類、三萜皂苷類、磺胺類和其他微量元素等成分[6]。李小玲[7]行大鼠實驗認為,黃芪多肽可減少心肌局部血管緊張素Ⅱ(AngⅡ)生成,且高劑量組比低劑量組更明顯,為黃芪有效降壓的主要成分。而陳國輝等[8]則認為黃芪主要降壓成分為γ-氨酪酸 (GABA)。
2.2 降壓機制
2.2.1 黃芪的降壓機制與其抑制RAAS系統有關鄭彩云[9]認為黃芪降壓機制為通過降低血漿中內皮素(ET)、AngⅡ含量,進而抑制RAAS系統,從而降血壓。眾所周知過度激活的RAAS系統是形成高血壓的主要原因之一,指南[10]中作為第Ⅰ級治療使用的ACEI與ARB類藥物作用機制便是抑制RAAS,黃芪與之作用類似,更加佐證了其降壓有效性。另有研究表明黃芪有效成分降壓可能與升高血液中血心鈉肽(ANP)含量有關。劉曉睿等[11]用40只原發性高血壓大鼠(SHR)研究黃芪有效成分對其降壓作用中發現,黃芪有效成分對AngⅡ和ET影響不明顯,而對ANP升高明顯。ANP是一種由心房合成、貯存和分泌的活性多肽,具有強大的利鈉、利尿、舒張血管、降低血壓和對抗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和抗利尿激素作用。證明實驗結果的差異可能與給藥方式或試劑類型有關,但其二者實驗均證明黃芪降壓機制為抑制RAAS系統。此外,陳國輝等[8]認為黃芪的降壓渠道可能為通過一氧化氮-可溶性鳥苷酸環化酶-環磷酸鳥苷 (NO-SGC-cGMP) 介導的信號轉換通道, 調節血管平滑肌細胞 (VSMC) 的功能, 從而調整血壓同時對冠狀動脈有直接擴張作用。
2.2.2 黃芪降壓機制可能與其利尿作用有關利尿劑作為我國指南推薦的5大類降壓藥之一,通過減少心排出量和降低外周血管阻力降壓,在臨床治療高血壓病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韓旭等[12]認為黃芪煎劑具有利尿作用,其0.5 g/kg的利尿效價與氨茶堿 0.05 g/kg 或雙氫氯噻嗪0.2 mg/kg相當,而且在動物實驗中持續時間長,連續用藥7 d未產生耐受性。而中醫學對黃芪的認識中早就有了利水消腫的作用。《本草綱目》記載“小便不通。用黃芪二錢,加水二碗,煎成一碗,溫服。小兒減半”。《中藥學》[13]中也記錄了其利水消腫的作用“本品既能補脾益氣治本,又能利尿消腫治標,故亦為氣虛水腫之要藥”。
2.3 降壓特點
2.3.1 血壓調節具有雙向性黃芪不但可以治療原發性高血壓,在治療低血壓中有也廣泛應用。熊成熙等[14]認為運用黃芪升壓湯治療低血壓患者臨床療效佳、無毒副作用,在其治療的121例低血壓患者中有效率達到了84.29%。黃芪對血壓的調節作用是雙向性的。孫正華等[15]通過檢索大量文獻得出結論,黃芪對血壓具有雙向調節作用,輕用升壓,重用降壓。帥眉江等[16]總結臨床用藥經驗,總結出黃芪降壓要點與用藥劑量、辨證施治、藥物炮制、藥物配伍密切相關,并指出黃芪用于降血壓劑量應在30 g以上為佳。而黃芪對血壓的雙向調節作用,既小劑量黃芪升血壓,大劑量黃芪降血壓,其具體作用機制特別是大劑量升血壓的作用機制就目前查閱的文獻來看,無論中醫或是西醫均未給出合理的解釋。查閱中醫經典,發現《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有記載:“壯火散氣,少火生氣”,馬蒔在《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中注:“氣味太厚者,火之壯也。用壯火之品,則吾人之氣不能當之而反衰矣……用少火之品,則吾人之氣漸爾生旺,血亦壯矣”。而由此后代醫家將壯火與少火引申出補益藥物劑量的大小[17],該理論與黃芪的雙向調節作用極為相似。但黃芪之大量莫過于補陽還五湯,而原書卻稱其證為“因虛致病”,黃芪功效取之“補”而非“散”,查閱其他文獻卻也不見以“壯火散氣”治療高血壓病的案例。究竟黃芪的降壓作用與“壯火散氣”有無關系,亦或是“壯火散氣”能否治療高血壓病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2.3.2 黃芪對原發性高血壓腎臟損害有較好防治效果預防和治療靶器官的損害是治療原發性高血壓的根本目的,其中高血壓腎損害作為發達國家引起終末期腎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治療原發性高血壓中不可忽視的一環。而黃芪在預防與治療原發性高血壓帶來的腎臟損害有其特有優勢。湯歸春等[18]認為黃芪通過促進Na+、K+-ATP酶活性的作用,改善血液黏度,抑制血小板的聚集,降低脂質過氧化產物丙二醇, 升高血漿超氧化物歧化酶等作用機制,對高血壓腎臟損害起到較好的防治效果。趙玉娟等[19]認為治療原發性高血壓時常規降壓方案聯合黃芪注射液可有效降低尿微量白蛋白的排泄,黃芪可起到協同保護腎臟的作用,是值得推廣的有效方案。倪小玲等[20]認為在治療高血壓腎臟損害時,黃芪聯用西藥比單用西藥治療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并且具有價不高、療效好、毒副作用小等優勢。
2.3.3 黃芪降壓平穩性與安全性大量研究表明血壓變異性增加可通過各種機制造成心腦腎等靶器官損害[21,22],因此長期平穩降血壓對長期降壓治療至關重要。陳治奎等[23]認為黃芪基本無急性降壓作用,長期應用單味黃芪可抑制SHR血壓進一步升高。實驗結果,SHR給藥組中8周血壓下降幅度為8~11 mm Hg,與0周比較無顯著變化,但有較明顯下降趨勢,且越高劑量組者下降越明顯,而SHR對照組自3周開始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P<0.01)。而正常血壓大鼠(WKY)中并未出現明顯的降壓或阻止血壓升高的作用。
3 臨床研究
3.1 補脾以益氣血歸脾湯出自明代醫家薛己的《正體類要》,在治療高血壓病中主要用于氣血虧虛型,此類高血壓病患者氣血虧虛,清陽不展,腦失所養,故以予歸脾湯補益氣血,調養心脾。黃芪在此方中行甘溫補脾益氣之效,脾健氣足,氣血充盈,眩暈得減。同時諸多研究發現該方對治療老年高血壓合并焦慮抑郁有較好效果。殷珺等[24]認為歸脾湯中黃芪、當歸共行生津安神、補氣益血之效,以改善局部微循環,與其他藥物配伍聯合,從而達到降低血壓和改善焦慮、抑郁、失眠等癥狀的效果。季學綱[25]更為系統的使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17)、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和生活質量評量表(SF-36)評價該方對老年高血壓患者抑郁、焦慮、生活質量的影響,結果HAMD17評分、HAMA評分均較對照組改善明顯,且SF-36量表試驗組較對照組升高明顯(均P<0.05)。
3.2 補氣以助化瘀補陽還五湯出自清代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在治療高血壓病中主要用于氣虛兼有血瘀型。此方中重用黃芪以取其大補脾胃之源氣,使氣旺以促血行,正如明代張景岳所說:“氣血不虛則不滯,氣虛則無有不滯”。氣行則血行,血行則眩暈得減。庾劍鴻[26]認為次方中重用黃芪使元氣大補,使氣盛血行無阻,從而達到止暈降壓效果。其實驗中西藥聯合補陽還五湯組血壓達標率為92.86%明顯優于單用西藥血壓達標率為73.81%(P<0.05)。補陽還五湯在臨床上治療高血壓合并腦血管疾病應用廣泛。何郁鵬等[27]認為補陽還五湯可以明顯降低H型高血壓合并急性腦梗死患者的血漿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并通過改善患者血液流變學及神經功能來提高患者的生活水平。此外,李猛等[28]認為黃芪還具有保護血管內皮細胞、預防和治療動脈粥樣硬化和降血脂的作用,其實驗選用補陽還五湯和生脈散配合西藥治療高血壓合并頸動脈斑塊患者疾病緩解率達90%,優于單純應用西藥治療的73%(P<0.05)。
3.3 補氣以助升陽補中益氣湯為李杲的名方,在治療高血壓中主要用于氣虛型,《靈樞》有言曰:“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其基礎為下虛上實,故宜補氣升陽為主[29]。黃芪在此方中為君藥,取其補中益氣、補氣升陽之功。劉彤等[30]認為該方中君藥之黃芪可補中益氣,配合升麻、柴胡可引其上行,阻止眩暈。其臨床實驗也表明補中益氣湯和并西藥治療高血壓,效果優于單純西藥治療。宋傳景等[31]納入5個隨機臨床對照試驗,共360例患者行Meta分析,結果為OR=2.43,95%CI:1.68~3.51,其結果亦為支持補中益氣湯治療高血壓病為有效結果。
3.4 補氣以助滋陰八味降壓湯是名老中醫周次清教授根據“八物降下湯”化裁而來,本方從益氣養血、滋陰降火方面入手治療高血壓病,方中黃芪益氣配陽以助陰,有“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而后瀉其陽”之意。孟志剛等[32]認為八味降壓湯配方顆粒不但具有降低血壓作用,而且具有降低血液黏稠度的作用。其試驗結果其總有效率為81.2%,全血高切黏度、全血低切黏度、血漿黏度、紅細胞剛性指標較治療前下降(P<0.05)。
3.5 補脾以助化濕妊娠期高血壓應用藥物控制一直是備受爭議的,現有的臨床研究表明,對于輕-中度妊娠期高血壓患者應用降壓藥物并不能有效改善其不良出生結局[33,34],但如果減少或停止降壓藥的應用,則會加大其不良出生結局與形成重度高血壓的可能[35,36]。而對于重度妊娠期高血壓患者,過度降壓是危害母嬰的危險因素[37]。這就對降壓藥的安全性與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黃芪注射液的臨床研究表明其不但有良好的降壓效果,而且有較高安全性與改善妊娠結局的作用。黃芪注射液主要成分為黃芪,其適應證為本品用于益氣養元,扶正祛邪,養心通脈,健脾利濕。用于心氣虛損﹑血脈瘀阻之病毒性心肌炎、心功能不全及脾虛濕困之肝炎。妊娠期高血壓中醫證型不盡相同,但脾虛濕盛型在各年齡段都占有相當比例[38]。黃芪注射液之所以對妊娠期高血壓治療有效,多是取其補氣以健脾之功效。范中燕[39]認為黃芪注射液聯合鹽酸拉貝洛爾注射液干預妊娠期高血壓不但能顯著降壓,對α2-微球蛋白、尿素氮、尿肌酐及尿酸的降低作用明顯,而且能切實改善妊娠結局。
4 討論
在現代醫學方面,大量研究表明黃芪降壓機制明確,臨床與動物實驗療效確切,切實可以治療原發性高血壓。因其降壓機制主要為抑制RAAS和促進排尿,故在中西醫結合治療原發性高血壓時,西藥可優先選用CCB類或β受體阻滯劑,以達到多種降壓藥物聯用的目的,從而獲得更好的臨床療效。此外,因黃芪無急性降壓作用,故其降壓作用平穩,相對安全。而相應的,因黃芪不具備急性降壓功能,故其不能作為高血壓急癥的首選降壓方案,但因其具有對靶器官的保護作用,黃芪仍有在高血壓急癥中應用的價值。
在中醫學方面,黃芪治療的證型主要有氣虛、陰虛、血瘀、濕盛、清陽不升,而究其根本均與脾虛氣虛有關。中醫講究辨證論治,雖然黃芪降壓機制明確,但以現在的臨床研究,黃芪多適用于虛癥患者,尚未有相關研究表明其可治療實證眩暈病。
黃芪對于血壓的雙向調節作用,單論升壓或是降壓,現代醫學與中醫學均有各自的解釋,然而對于大劑量黃芪降血壓,小劑量黃芪升血壓的經驗說法卻沒有理論支持,至于是否對應《黃帝內經》中提到的“壯火散氣”也缺少足夠的實驗證據。若未來能證明“壯火散氣”法行之有效,那在臨床上無異于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