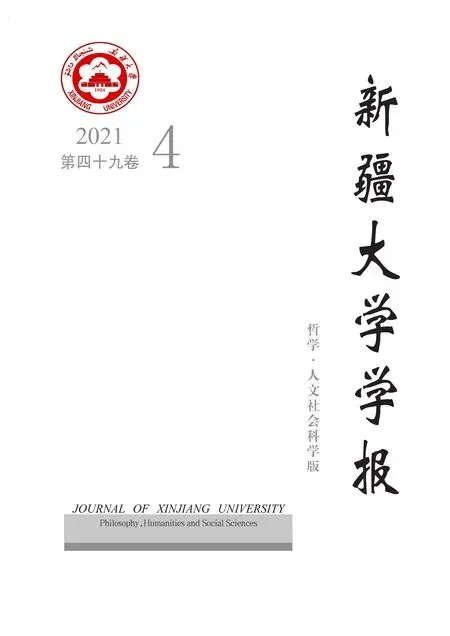論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華文明沃土的制度保障*
管守新
(新疆大學 學報編輯部/新疆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新疆 烏魯木齊830046)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與生活的地方。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族人民互相學習、互相借鑒、共同進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與風俗習慣。這些文化與風俗習慣在不斷的民族融合與社會變革過程中之所以能夠保留下來,并得以繼續發揚,是與我國歷代中央政府所秉持的“大一統”的天下觀及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所實行的特殊政策分不開的。
一、中國各民族認同“大一統”天下觀的文化基礎
中華民族是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華夏(后稱為“漢”)族為主體,不斷融合其他民族而逐漸形成的。中華文化也是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由各民族文化在不斷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在此過程中,由于華夏(漢)族的人數不斷增多,活動地域范圍宜居,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影響力較大,認為自己的“國家”居于“天下之中”,稱之為“中國”;又是經濟文化發達之區,冠帶禮儀之邦,故又自稱為“華夏”;①《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六,杜預注,孔穎達疏曰:“夏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參見《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148頁。把居于自己周邊、認為“落后”于自己的民族或部落籠統地稱為“四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從而產生了“夷、夏之別”的思想觀念。從上所述可以看出,這種區分觀念產生的基礎,不是基于種族與民族,而是基于文明。
雖然“內諸夏”“外夷狄”的思想觀念貫穿于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敘述之中,但是由于中華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華夏與夷狄等各民族不斷融合的結果,因此,當西周建立后,隨著眾多部落、邦、國,或分封,或羈縻,置于周王統屬之下后,就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1]卷十三《北山》的“大一統”的天下觀。這一思想,不僅被歷代漢族執政者所接受,而且也被少數民族執政者所接受。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共識,是因為它被看作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2]卷十七《漢紀九》,555。一方面它強調了君王“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3]卷十二《洪范》第六《周書》。“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是無論哪個民族的執政者都樂意接受的。如匈奴執政者在統治了中國北方的廣大地區后,即自稱“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②參見[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傳》,載《二十四史》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896、2899頁。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4]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3780因此,當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中國”)后,為了證明自己“天子”地位的“合法性”與“正統性”,無不強調他們與華夏(漢)同源,或與華夏(漢)有著某種親緣關系,如十六國時期的匈奴人劉淵之所以把國號定為漢,即說自己是“漢氏之甥”,是在繼承漢業。①參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一百一《載記第一·劉元海》,載《二十四史》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649頁。北魏的建立者鮮卑拓跋氏自稱為黃帝之后;北周的建立者鮮卑宇文氏自稱為炎帝之后;清朝的建立者滿族為了消弭“夷夏之防”的區隔,諭說:“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5《]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四十,順治五年八月壬子,諭禮部等,都是此意。由此,他們也自覺肩負起了維護國家統一的責任。比如,前秦氐族首領苻堅在統一中國北方后,即以“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6]卷一百十四《載記第十四·苻堅下》,于是發兵南下,意欲一舉消滅東晉,統一南北。另一方面,隨著統轄范圍的不斷擴大“,夏“”夷”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斷加深,儒家思想影響的不斷深入,為了維護王權的尊嚴與民族的統一,獲得各民族的認可與支持,在思想上又逐漸產生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7]卷六《顏淵第十二》,85的思想意識。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基本采取“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7]卷八《季氏第十六》,121-122的自愿向化原則,并不一味以武力相加。不同時期、不同政權治下的不同屬民,即便有地域、稱謂的不同,也就如清朝雍正皇帝所說:“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8]天朝中華一統。”[9]無論華夏、夷狄、同姓、異性、本部、藩屬,都是一家人。只不過二者的關系是,“中國,根干也;四夷,枝葉也”[10]卷一百九十五《唐紀十一》。所以,當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南匈奴已經歸服漢朝,北匈奴單于遣使請求和親,并請求率領西域各國“胡客與俱獻見”的時候,漢朝政府就明確指出:“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11]卷八十九《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在漢朝政府搜選五經飽學之士,加強對期門、羽林等官員進行儒家文化教育學習時,“匈奴亦遣子入學”[12]卷四十五《漢紀三十七》,1450。對于普通民眾而言,無論是何民族,來自哪里,處于哪個政權的治理之下,能夠被一視同仁公平對待、相互尊重、和睦相處,則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于是就形成了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的全國大一統的思想觀念。從而也就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中心,各民族文化共存、交融的中華文化體系。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執政者在制定國家政策時,鑒于自身發展的經歷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情況,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逐漸形成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因俗而治”的邊疆施政政策。也就是在不改變、尊重當地少數民族社會制度、風俗習慣的基礎上,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制定當地的政治管理制度,從而達到“因俗施治”的目的,以保證地方社會的安寧與國家的統一。
二、“因俗而治”政策在新疆②本文所用“新疆”的范圍,是指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所定的范圍,而歷史上的“西域”所指的范圍,則是包括今天的新疆及其周邊的廣大地區,因此,為了敘述的準確,文中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實際情況,“西域”與“新疆”并用。的實施
漢朝統一西域后,根據西域地區的實際情況,在設置西域都護、派兵屯田并保護派駐機構與官員及來往使者、商旅安全的同時,保留了當地社會的組織結構與各級首領的地位,由中央政府給他們頒發金印紫綬或銅印墨綬“,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4]卷九十六下《西域傳第六十六下》,3928。“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2]卷二十一《漢紀十三》,686把他們納入漢朝的官吏體系,享受漢朝的俸祿與不時的“賞賜”,而這種“歲時賞賜,動輒億萬”[12]卷四十五《漢紀三十九》,1515,其中“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余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12]卷四十五《漢紀三十九》,1529,并由他們管理當地的具體事務。這與匈奴在西域設置“僮仆都尉,匈奴蓋以僮仆視西域諸國,故以名官。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2]卷二十《漢紀十二》,658的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所以,在東漢建立之初,西域“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相反“,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4]卷九十六下《西域傳第六十六下》,3930。成了西域諸國人心向漢的重要社會基礎。漢朝政府正是通過他們,使“漢之號令班西域矣”[4]卷七十《鄭吉傳》,3006。
唐朝統一西域后,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先后設置安西都護府與北庭都護府兩大軍政管理體系,管轄天山南北及中亞地區軍政事務。在靠中原較近、漢族居民較多的東部地區,實行與中原地區相同的州縣制度。在西部其他民族聚居的地區則采取“分置酋領,統其部落“”因其俗而撫馭之”[13]卷七十三《安北都護府》的羈縻府州制,即在這些地區按照部落或地區的大小,設置羈縻府、州、縣,保留各部落或地區首領的地位與權力,任命他們為都護或都督、刺史、縣令等官職,享受國家相應俸祿,肩負國家相應使命,接受唐朝法令約束。唐朝政府通過這種方式,把政令植入周邊諸族社會內部,分割了諸族君長的統治權。①參見王義康《因俗而治與一體化:唐代羈縻州與唐王朝的政令法令》,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4卷第4輯,2019年,第54-62頁。唐朝也因此對“聲教所暨,皆邊州都護、都督所領,著于令式”[14]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給予這些地區極為寬松的政策,在他們保持對中央政府忠誠、履行守邊職責的前提下,各羈縻府、州、縣除向安西、北庭兩大都護繳納有限的財物,以保障都護府的部分開支與給養外,其它地區性的具體事務均自行處理。
清朝統一新疆后,借鑒前朝治疆經驗,在實行軍府統治的前提下,在烏魯木齊及其以東的東疆地區,實行與中原地區相同的州縣制度;在北疆的蒙古族、哈薩克族等游牧民族中,以及歸服清朝較早的哈密與吐魯番的維吾爾族地區,實行與蒙古地區一樣的札薩克制度;在南疆與伊犁地區的維吾爾人中,實行傳統的伯克制度,但卻不得世襲。通過制定《蒙古律例》《回疆則例》等律法,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他們的權利與義務,在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使清朝的政策與法令得以貫徹實施。
在這種管理體制下,不僅少數民族上層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被納入到政府的官吏體制中,享有相應政府官員的權利,確保了其地位與待遇,增強了其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而且本民族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與文化,也從法律制度上得到了尊重與保護。就是在新疆地區處于割據狀態時,這種慣性也得以延續,這在《二十四史》等有關新疆歷史的文獻記載與出土文物中,我們既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區繼續通行的情況,也可以看到新疆當地不同文化、風俗習慣精彩紛呈的呈現,就是很好的例證。
三、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文化保護政策的制定及其在新疆的實踐
中國共產黨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從建黨初期就主張民族平等,并付諸實踐。在1922年7月于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在“蒙古、西藏、回疆(即新疆——引者注)三部實行自治”[15]。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把黨的民族政策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在強調保障少數民族權力的同時,強調“蘇維埃政權更要在這些民族中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16]。在大會通過的《關于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中指出:凡是居住在國內的各族“勞苦人民一律平等,享有法律上的一切權利義務,而不加以任何限制與民族的歧視”[17],并在蘇區付諸實施。1947年5月1日,我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成立。②參見《內蒙古自治政府布告(第一號)(1947年5月30日)》,載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128頁。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以臨時憲法的方式,在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明確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應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眾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18]中國共產黨不僅是這樣提的,也是這樣做的。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為了保障少數民族的權益,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籌建準備工作。1951年2月5日,政務院發布《關于民族事務的幾項決定》,“在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內設民族語言文字研究指導委員會,指導和組織關于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逐漸充實其文字”[19]。保護與發展進入實施階段。
1952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確立了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原則。9月,新疆省第二屆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決議,成立“新疆省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籌備委員會”。次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新疆分局擬定的《新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辦法草案》①參見《中共中央關于新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辦法草案的批語(1953年10月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編《新疆工作文獻選編(1949—2010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06-113頁。,新疆民族區域自治進入實施階段。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經過不斷修訂完善,第四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系。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為。國家根據各少數民族的特點和需要,幫助各少數民族地區加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20]明確了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在這一制度下少數民族所享有的權利和所應該承擔的義務。同年,經中央批準,新疆成立了5個自治州,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6個自治縣,即:焉耆回族自治縣、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木壘哈薩克自治縣、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和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在此基礎上,1955年10月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正式成立。②參見董必武《在慶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大會上的講話(1955年10月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編《新疆工作文獻選編(1949—2010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38-140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新疆得到全面貫徹與落實。
為了使憲法賦予少數民族的權利得到充分的保障,1984年5月31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并于當年10月1日頒布實施。該法全面規定了民族區域自治地方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風俗習慣的傳承,第三十八條明確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地發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點的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等民族文化事業,加大對文化事業的投入,加強文化設施建設,加快各項文化事業的發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組織支持有關單位和部門收集、整理、翻譯和出版民族歷史文化書籍,保護民族的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繼承和發展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21]并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等具體法律中細化規定,加以保障。
正是在上述一以貫之的一系列法律政策的保護下,在我國,“除回族和滿族通用漢語文外,其他53個少數民族都有本民族語言,有22個少數民族共使用27種文字。……截至2017年,全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共有195個廣播電視機構使用14種少數民族語言播出廣播節目,263個廣播電視機構使用10種少數民族語言播出電視節目”[22]。“新疆各民族主要使用10種語言和文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司法、行政、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互聯網、社會公共事務等領域得到廣泛使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的重要會議,提供維吾爾、哈薩克、蒙古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文稿和同聲傳譯。新疆本級和各自治州、自治縣機關執行公務時,同時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語言文字。各民族成員有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選舉或訴訟。以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在課程設置和各類招生考試中均重視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學習和使用。每年一度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新疆使用漢、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5種文字試卷。”“新疆使用漢、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錫伯6種語言文字出版報紙、圖書、音像制品和電子出版物。新疆電視臺有漢、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4種語言電視節目,新疆人民廣播電臺有漢、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5種語言廣播節目,《新疆日報》用漢、維吾爾、哈薩克、蒙古4種文字出版。”[23]以喀什艾提尕爾清真寺、昭蘇圣佑廟、克孜爾千佛洞為代表的109處宗教文化古跡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各族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風俗習慣,都得到了尊重。春節、中秋節、古爾邦節、肉孜節等各民族傳統節日,都能享受法定假期。
為了加強對少數民族文化古籍的保護,1983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與人民政府聯合發布了《關于搜集、整理和出版新疆少數民族古籍的通知》,并于1984年成立新疆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辦公室、2008年成立新疆古籍保護中心,整理出版了維吾爾族古典文學名著《福樂智慧》、哈薩克族醫藥巨著《醫藥志》、柯爾克孜族英雄史詩《瑪納斯》與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等一大批少數民族重要文化典籍。到2017年,新疆“完成古籍整理普查14 980種。已收藏的古代典籍文獻包括漢文字(漢文字、西夏文和契丹文等)、阿拉美文字(佉盧文、帕赫列維文、摩尼文和回鶻文等10多種)和婆羅米文字(梵文、焉耆-龜茲文、于闐文、吐蕃文等)三大系統,共19種語言、28種文字,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天文、數學、醫學、藝術等領域”[23]。已完成1 500多冊少數民族古籍數字化掃描工作。充分反映了新疆各少數民族文化在中國歷代中央政府特殊政策、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尊重、保護與支持下得以保留、傳承與發展的情況。
文化,是指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活動的產品,從人及其實踐活動的角度來看,還是人與世界的對話形式和意義建構。文明,是有史以來沉淀下來的,有益于增強人類對客觀世界的適應和認知、符合人類精神追求、能被絕大多數人認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發明創造以及公序良俗的總和。文明與文化一樣,都建立在人類改造世界的實踐基礎之上。文明本身是指“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和具有較高文化的”[24]形式和實體,沒有文化的積累就不可能有文明的進步,而人類社會文明建設過程亦是在踐行著文化。文明通常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現代意義上還包括制度文明,即物質交換及社會關系的一種自覺、合理、歷時的規約,它構成了人類文明的基本單元,成為在文明多樣性的比較和對話中衡量治理水平的參照。恩格斯說:“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25]新疆各民族接受了中國歷代中央政府在少數民族地區所實行的“因俗而治”政策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就意味著接受了中華文明中的“制度文明”,也即接受了中華文明;認可了國家權力在當地的行使,也就意味著承認了自己是中國的國民。正是在中華文明的寬容、尊重、支持、保護與滋養下,新疆各民族文化長期交流交融,并得以保留、傳承與發展,呈現出枝繁葉茂和欣欣向榮的景象。這正是“中國之治”這一人類文明偉大實踐的真實體現。如果中國歷代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文化采取的不是“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強”[26]卷二十八《漢紀二十》的寬容、尊重與保護政策,而是與之反向的強制同化、甚或是“滅絕”政策,那么,今天,中國還會有56個民族,新疆各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還會保留如此完好并有所發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