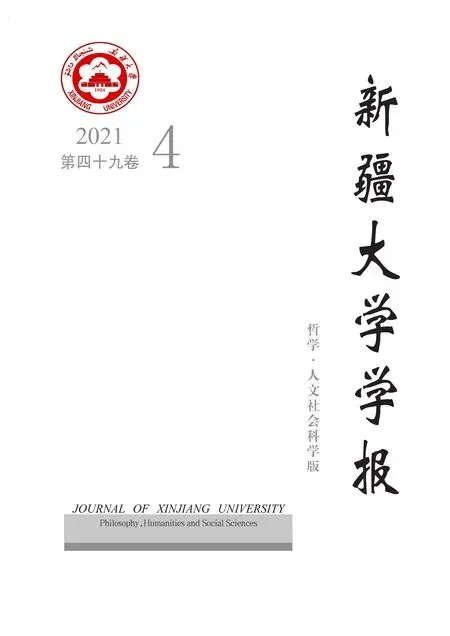葉燮“陳熟生新”思想的共時性思考*
楊 暉,羅興萍
(江南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無錫214122)
葉燮批評明代詩論沒有處理好“陳熟”與“生新”關系,如前后七子重“陳熟”;公安竟陵主“生新”;而近今詩家卻“新而近于俚,生而入于澀”[1]4,在“新”中不見“陳”,“生”中不見“熟”。對此,他將兩者納入傳統哲學“對待”的框架中,提出“陳熟、生新,二者于義為對待”[1]44。表現了對“陳熟生新”的共時性思想。“對待”是明清之交思想家方以智提出的哲學概念,用以指事物相互排斥的雙方。他說:“夫對待者,即相反者也”[2]88,“有一必有二,二皆本于一。”[2]89又說“因對待謂之反因……所謂一切對待之法,亦相對反因者也”[2]94。提出“公因反因”說,極為精粹。“反因”是指對待兩端,“公因”是指兩端的統一,這便有了“吾嘗言天地間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極相反……晝夜、水火、生死、男女……《剝》《復》、《震》《艮》、《損》《益》、博約之類,無非二端”[2]87-88的說法。方以智以為“一不可言,而因二以濟”[2]243,側重于“一在二中”;而王夫之則側重于“二于一中”,即“兩端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于一也”[3]。這是中國傳統哲學“兩”與“一”思想的體現。
中國傳統哲學常“兩”“一”并舉。前者指對待,后者指合一。“兩”與“一”關系,就是對立統一關系。葉燮所謂的“陳熟”與“生新”之義為“對待”,但又“不可一偏,必兩者相濟”[1]44,即兩者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既是沖突的,也是融合的。這是葉燮對“陳熟”與“生新”在共時性中的看法,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對待”的不確定性
葉燮《二取亭記》說:
凡物之義不孤行,必有其偶為對待。棄者,取之對待也。……有棄有取,道之變也。有棄斯有取,有取斯有棄,道之變而常也。[4]卷六《二取亭記》697
凡事物“不孤行”,“必有其偶”,有“正”必有“反”,有“棄”必有“取”,有“取”也必有“棄”。葉燮還說“對待之義,自太極生兩儀以后,無事無物不然”[1]44。此語首見《呂氏春秋·大樂》,后有《易·系辭上》的太極“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卦。八卦定吉兇,吉兇成大業”[5]。此“兩儀”指天地或陰陽。可見,葉燮之“對待”來自于古人陽陰兩端的觀物方式①張岱年:“古時人見萬物萬象都有正反兩方面,此種兩極的現象普遍于一切,于是成立了陰陽二觀念。所謂陰陽,其實即表示正負。更發現一切變化皆起于正反之對立,對立乃變化之所以起,于是認為陰陽乃生物之本,萬物未有之前,陰陽先有。”參見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6頁。。這被馮友蘭稱之為“一物兩體”。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任何事物都有與之相反者存在,諸如陰陽、男女等各以對方為前提。“有一必有二,二皆本于一”[2]89正是葉燮眼中的“對待”。
“對待”的雙方不僅互為前提,而且還相向運動。葉燮在《題雪窗紀夢后》中說:“世間萬法不出事理二者。為事與理,各各對待而成。我與物,真與幻,悟與迷,覺與夢,皆對待也。……無我則無物,無真則無幻,無悟則無迷,無覺則無夢,無則俱無,斯對待絕。”[4]卷二十二《題雪窗紀夢后》,832強調了對待雙方相互依賴的關系。他將“陳熟”與“生新”的運動方式描述為“夫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1]44體現了他對“陳熟”與“生新”不確定性的看法:
一是陳熟與生新的相互運動。有“厭”方有“趨”,“趨”是向自己對立面方向運動,即厭“陳熟”必趨“生新”;而厭“生新”則又返趨“陳熟”。而任何事物無時無刻都在“陳熟”與“生新”之間搖擺,或由“陳熟”趨“生新”,或由“生新”趨“陳熟”。“熟”與“生”,物極必返,否則必死,如《詩人玉屑》所說的“一戒乎生硬,二戒乎爛熟”[6],以及元人方回提出“熟而不新則腐爛,新而不熟則生澀”的觀點①方回在《桐江續集》卷三十三《恢大山西山小稿序》中提出:“他人之詩,新則不熟,熟則不新。熟而不新則腐爛,新而不熟則生澀。惟公詩熟而新,新而熟,可百世不朽。”參見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編《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94頁。。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大綱》中揭示其運動的機理,認為是“對待”之雙方“相摩相蕩,相反相求”之故②張岱年:“至《易傳》乃以對待合一為變化反復之所以,認為所以有變化而變化所以是反復的,乃在于對待之相推。凡對待皆有其合一,凡一體必包含對待;對待者相摩相蕩,相反相求,于是引起變化。”參見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1頁。。
二是陳熟與生新的“相濟”。葉燮認為事物是運動的,對立雙方不能永遠對立,不能“一偏”,不能“主于一”,而是“相濟”,即是“陳中見新,生中得熟”[1]44。就“相濟”,西晉郭象在《莊子·秋水》注中說:“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7]他認為世上事物就各自而言都是孤立而不相關的,是“自為”的,但事物又彼此并存,不能互缺,彼物的存在正是此物所必須的條件。其實,關于“相濟”的說法還有很多③關于“相濟”的說法還有很多,如江西詩派王直方(1055—1105)《詩話》中說:“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枯乾,能不失二者之間,則可與古之作者并驅耳。”(參見《筆記小說大觀》三十五編(第1冊)《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八·東坡一,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259頁)視“圓熟”和“老硬”相濟。明人謝榛《四溟詩話》卷三:“貴乎同與不同之間。同則太熟,不同則太生。二者似易實難。握之在手,主之在心。使其堅不可脫,則能近而不熟,遠而不生。此惟超悟者得之。”(參見謝榛《四溟詩話》宛平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71頁)他以“同”與“不同”比作“陳熟”與“生新”,“同”者為“陳熟”,無新意;“不同”者為“生新”,無“陳熟”,主張在有“陳熟”與“生新”之間找到最佳的位置,方能為“貴”。清人牟愿相《小澥草堂雜論詩》有:“生字有二義,一訓生熟,一訓生死。然生硬熟軟,生秀熟平,生辣熟甘,生新熟舊,生痛熟木。果生堅熟落,谷生茂熟槁,惟其不熟,所以不死。”參見牟愿相《小澥草堂雜論詩》,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富壽蓀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23頁。,而葉燮對之作出了進一步的闡釋。
葉燮不僅認為兩者相互滲透、相互轉化,而且還引用莊子的“其成也毀,其毀也成”④此語出自莊子《齊物論》:“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參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王孝魚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70頁。一語加以說明。在葉燮眼中,“對待”雙方很難有清楚的邊界,如蔣寅說的,“他(葉燮)力圖取消這類對立概念的恒定價值,只將它們視為需要在具體語境中靈活看待的對象”[8]。葉燮在靈活運動中進一步指出其不確定性。以“美惡”為例。他認為“美生而惡死”“美香而惡臭”“美富貴而惡貧賤”[1]44等并非絕對,而在一定條件下可發生反轉,如人們稱道忠臣關龍逢和比干的死,而不羨慕奸臣江總的長壽,⑤關龍逢,夏代賢臣,因諫桀被殺;比干,殷紂王叔父,官少師,因縷勸諫紂而被戮。江總(519—594),字總持,濟陽考城人,早期戰功赫赫。陳后主時官宰相,但不理政事,飲酒作樂,國家衰敗,君臣昏庸,陳朝滅亡。這是“美生而惡死”的反轉;“幽蘭得糞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則萎,香反為惡”[1]44,這是“美香而惡臭”的反轉⑥《原詩·外篇上》:“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于一者也。其間惟生死、貴賤、貧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惡不死,美香而惡臭,美富貴而惡貧賤。然逢比之盡忠,死何嘗不美!江總之白首,生何嘗不惡!幽蘭得糞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則萎,香反為惡。富貴有時而可惡,貧賤有時而見美,尤易以明。即莊生所云:‘其成也毀,其毀也成’之義。”參見葉燮、薛雪、沈德潛《原詩·一瓢詩話·說詩晬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44頁。。他認為這就是莊子“其成也毀,其毀也成”之義,突出“對待”雙方不確定性。清人俞兆晟說王漁洋論詩“三變”,認為少年學詩“博綜該洽”,推崇盛唐;中年“事兩宋”,“厭故”“喜生”;晚年習讀《唐賢三昧》。①俞兆晟《漁洋詩話序》:“少年初筮仕時,唯務博綜該洽,以求兼長。文章江左,煙月揚州,人海花場,比肩接跡。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韻勝于才,推為祭酒。然而空存昔夢,何堪涉想?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良由物情厭故,筆意喜生,耳目為之頓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長慶以后,已有濫觴;而淳熙以前,俱奉為正的。當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爭相提倡,遠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為空疏,新靈浸以佶屈,顧瞻世道,惄焉心憂。于是以太音希聲,藥淫哇錮習,《唐賢三昧》之選,所謂乃造平淡時也,然而境亦從茲老矣。”參見王士禛《漁洋詩話》,載《清詩話》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5頁。這也是對葉燮“陳熟”與“生新”運動方式的另一種表達。
葉燮在《原詩·外篇上》中說:
對待之美惡,果有常主乎!生熟、新舊二義,以凡事物參之:器用以商周為寶,是舊勝新;美人以新知為佳,是新勝舊;肉食以熟為美者也,果食以生為美者也。反是則兩惡。推之詩,獨不然乎![1]44-45
美惡沒有“常主”,這正是為了說明“對待”雙方之意義因運動而難以確定,正如蔣凡說的,“《原詩》的理論,就是根據事物的發展變化,靈活、巧妙地運用藝術辯證法”[9]。所以,葉燮在運動中去認識對象,破除對立雙方的固定屬性,體現出辯證法的思維方式。
二、消解“陳熟”“生新”的優劣
葉燮的“陳熟生新”有明確的針對性。明清之交的徐增《錢圣月法廬全集序》認為,明代中后期,因王(世貞)、李(攀龍)所尚聲律,復古模擬,陳陳相因,“陳熟”積弊而求“生新”之風興起,便有鐘譚竟陵出。鐘譚竟陵以“生”救“熟”,但未能救詩病在“熟”的毛病,卻反走向詩道之日淪。對此,葉燮在《原詩》中指出“近時詩人,其過有二”[1]34,批評復古之“陳熟”和反古之“生新”各偏一方之弊。他說:
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其詩也,非庸則腐,非腐則俚。[1]34
前后七子專事“陳熟”,沿襲守舊,忠厚和平,渾樸典雅,卻停留于皮毛,誤以為得古人之真傳,其實不過是庸俗、腐壞,為“真虎豹之鞟耳”[1]34罷了。葉燮指出他們忽視詩歌的演變。而與之相對應的反古者則相反。他說:
其一好為大言,遺棄一切,……怪戾則自以為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為李商隱……后生小子,詫為新奇,競趨而效之。[1]34
反古者則看重“生新”,以詫為新奇,卻又陷于“怪戾”“濃抹”,以為“新奇”,便“趨而效之”,其實不過是四不像的鬼怪而已。
葉燮看到以上兩者之弊,認為“以勦襲浮辭為熟,搜尋險怪為生,均為風雅所擯”[1]45,其實質是人為區別“陳熟”“生新”之優劣所致。這是孤立靜止地看待事物,忽視對立雙方的運動。他以傳統之“對待”去面對“陳熟”與“生新”的問題,以審美批評的標準,要求在“生新”中兼顧“陳熟”,“陳熟”中不忘“生新”。葉燮這一思想得到時代的回應。與他同時代的葉矯然②葉矯然又號思庵,生卒不詳,福州閩南縣人,順治九年進士,官工部主事,樂亭知縣,有《易史參錄》《龍性堂詩集》《樂溟集》《鶴唳集》等。在《龍性堂詩話》初集中說:“作詩須生中有熟,熟中有生。生不能熟,如得龍鲊熊白,而鹽豉烹飪,稍有未勻,便覺減味。熟不能生,如樂工度曲,腔口爛熟,雖字真句穩,未免優氣,能兼兩者之勝,殊難其人。”[10]稍后的陳僅在《竹林答問》中也說:“詩不宜太生,亦不宜太熟,生則澀,熟則滑,當在不生不熟之間,……詩不宜陳,亦不宜新,陳則俗,新則巧,當在不陳不新之間,初日鞭蓉,其光景也。”[11]葉燮學生沈德潛《說詩晬語》(下卷)第四十九條中也有“過熟則滑,唯生熟相濟,于生中求熟,熟處帶生,方不落尋常蹊徑”[1]246等,都表在了這層意思。所以,在葉燮看來,應該合理把握“陳熟”與“生新”作為事物的“對待”兩端的動態屬性,不能偏執于一端。
葉燮的“陳熟”與“生新”觀念,破除了詩壇對此的優劣之爭,認為只有兼顧兩者,才真正符合詩歌的審美要求。張岱年先生也曾提到過“兩極”與“兩分”的問題。他說:
凡一類之兩極或兩分,謂之對立,亦曰對待。一類之兩極謂之相反;一類之兩分謂之相非,亦謂之矛盾。統括相反與相非,謂之對立。
一類之性質或事物之最相異者常為兩端,可謂此類之兩極。凡一類之兩極,謂之相反。如黑與白二色為相反。黑與白為顏色之兩極,故為相反。一類亦可直截分判為二分,一類之二分謂之相非。如動與靜,凡存在之物之狀態,非動即靜,非靜即動。動即非靜,靜即非動,如男與女,或雄或雌。一類動物可分雄雌,人分男女。相反之性質或事物,其間有居中者,如黑白之間有灰及紅黃藍綠諸色。凡相非之性質或事物,其間無居中之性質或事物。
相反之二性,即一類性之兩極;相非之二性即一類之兩分。相反之二性,亦即一定范圍內之諸物可兼無而不可兼有者。相非之二性亦即一定范圍內之諸物或有或無者,即不可兼有亦不可兼無者,物之顏色,可黑可白,亦可非黑非白,而不可既黑且白。人或男或女,不可非男非女,亦男亦女。[12]
張岱年指出了“對待”包含“兩極”與“兩分”兩類。前者即“相反”,后者即“相非”。“相反”者彼此間相互參透,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沒有邊界,“可兼無而不可兼有”;“相非”者則此是此,彼是彼,邊界分明,“或有或無者,即不可兼有亦不可兼無”。葉燮的“陳熟”與“生新”尤如“兩極”為“相反”,其居有中間者,即如“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于陳中見新,生中得熟”[1]44,“陳熟”與“生新”相互滲透,彼中有此,此中有彼,而不是如張岱年所說的“相非”。這種在“陳熟”中包含“生新”,在“生新”中包含“陳熟”,自然消解了“陳熟”與“生新”作為獨立的個體存在,即沒有一個絕對的“陳熟”,也沒有一個絕對的“生新”。這一觀點自然消解了兩者誰優誰劣的話題。
葉燮的“陳熟”與“生新”思想具有批判意義。嚴羽《滄浪詩話》認為,“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13],即稱“第一義”的漢魏、盛唐之詩,優于大歷以后詩。這種風格的優劣觀在明代得到進一步的推進,如有明人歐陽玄《梅南詩序》有“詩得于性情者為上,得之于學問者次之,不期工者為工,求工而得工者次之。《離騷》不及《三百篇》,漢魏六朝不及《離騷》,唐人不及漢魏六朝,宋人不及唐人,皆此之以而學詩者不察也”[14]。他以“性情”與“不期工”為上,得出《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唐人詩、宋人詩的代降判斷。稍后的胡應麟《詩藪》有“《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14]。“代降”軌跡是前優于后,這種偏于“陳熟”的傾向被清初的顧炎武總結為“詩體代降”①顧炎武《詩體代降》:“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參見顧炎武《日知錄》(二),嚴文儒、戴揚本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13頁。。
而葉燮的“陳熟”與“生新”思想無疑將兩者拉到平等的地位,認為世間對待之事是運動著的統一體,難以劃清各自邊界,要求在雙方的運動中去把握意義。這種運動中的不確定性自然就消解雙方的優劣之爭。他說:“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于一者也。”[1]44初看它不合于情,也不合于理,正如在生死、貴賤、貧富、香臭當中,人人都喜生厭死,喜貴厭賤,喜富厭貧,喜香厭臭。然而當條件變化了,喜的對象可能成為厭的對象,如前文提及的,龍逢和比干因盡忠納諫而死卻為人稱道,江總長壽而為人稱惡一樣,世間的事物美丑善惡的絕對性消除了。再拿“新舊”與“生熟”概念來說。新與舊,生與熟的意義也非絕對,此時此地為優,彼時彼地為劣,如古代器物以舊為珍,美人卻以新為好;肉以熟為珍,果以生為好。所以,新與舊,生與熟在無條件下是難以區分誰優誰劣的。
稍后于葉燮的詩論家袁枚《隨園詩話》的“厚薄”之論也然。他說:
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為主耳。以兩物論,狐貉貴厚,鮫蛸貴薄。以一物而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為名家。[16]
“厚”就是厚,“薄”就是薄,并無優劣之分,如狐貉貴厚,鮫蛸貴薄,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并無異議。當“厚”為厚,當“薄”為薄,自然為優;但當“厚”卻薄,當“薄”卻厚,自然為劣。所以,“厚”與“薄”兩者本無優劣,而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可能有優劣之分。所以得出杜少陵、李太白、李義山、溫飛卿都為名家,難以道出誰優誰劣的結論。可見,是“美惡”“新舊”,還是“生熟”“厚薄”,沒有什么固定不變的優劣是非。這一不確定也就自然消解了誰優誰劣的問題。
葉燮又以“四季之花”為喻,認為天有四時,四時有春秋,此乃氣之不同,非優非劣。盛唐詩乃春之花,尤桃李的濃艷,牡丹之妍艷,華美貴重;晚唐詩乃秋之花,尤芙蓉叢菊,極幽艷晚香之韻,是各有風韻,并無優劣之分。②參見葉燮、薛雪、沈德潛《原詩·一瓢詩話·說詩晬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66-67頁。葉燮在《原詩》中借孔子以“美”“善”評《韶音》來評歷代詩歌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
葉燮與上面提及的嚴羽、歐陽玄、顧炎武等提出的“代降”思想不同,也沒有走向他們的反面“代升”,而是持各見其美的觀點。“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1]35,其中用的是“仍”,而不是“更”。在葉燮看來,只要有“變”,美的還是美的,善的還是善的,表現了他“詩無一格,雅無一格”[4]卷九《汪秋原浪齋二集序》,740的美學思想。
三、“陳熟”“生新”須“相濟”
針對復古與反古,葉燮提出“陳熟”“生新”須“相濟”的思想,即“于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1]44。對此,葉朗說葉燮“把古人和今人、繼承與創新統一起來了”[17]。張健說“葉燮試圖超越明代詩學的兩極對立而將他們統一起來”[18]。
那么,兩者是如何“相濟”的呢?葉燮說:
學詩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會人。……昔人可創之于前,我獨不可創于后乎?[1]76
在葉燮看來,“不可忽略古人”就是要看到“陳熟”的一面,“不可附會古人”又是要看到“生新”的一面。學習作詩,要學習古人,又不能依附古人,要有所創新,所以,昔人可創新于前,我當然也可以獨創于后。葉燮的“相濟”表現在:一是“不可忽略古人”,繼承優秀傳統,以“陳熟”為基;二是“不可附會古人”,獨創于后,以“生新”為目的。
1.以“陳熟”為基礎,“不忽略”與“不附會”
針對清初文壇之弊,葉燮認為當時的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蒙,要承擔責任。他們無論是沿襲者的模擬,還是耳食者的跟風;無論是不能知詩之源流正變盛衰,還是識蒙而不知所衷,都導致了“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為沿為革,孰為創為因,孰為流弊而衰,孰為救衰而盛”[1]3。為此,他提出學詩者“必取材于古人”[1]18,從學古人而始的觀點,要求學詩者多讀古人書,多見古人。那么,又如何學古人呢?他提出了“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會古人”[1]76。
什么是“不忽略”呢?他說:
忽略古人,粗心浮氣,僅獵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于不見者;古人之字句,有側見者,有反見者。此可以忽略涉之者乎?[1]76
深入學習“古人”,不能僅獲皮毛,而要領悟到不在言的“古人之意”,要看到藏于不見的“古人之言”,還要學習或側見,或反見的“古人之字句”,所以“學詩者,必從先型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1]35。這與韋勒克的對文學史的正確認識,可以避免個人的好惡,是有利于批評開展的思想不謀而合。①韋勒克認為,對文學史的正確認識,可以避免個人的好惡,是有利于批評的開展不謀而合。他說:“一個批評家倘若滿足于無視所有文學史上的關系,便會常常發生判斷的錯誤;他將會搞不清楚哪些作品是創新的,哪些是師承前人的;而且,由于不了解歷史上的情況,他將常常誤解許多具體的文學藝術作品。”參見[美]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38頁。可見,葉燮的詩學觀念也得到二十世紀西方學者的回應。
關于學習古人,葉燮進一步建議,按照詩歌演變的順序,讀《三百篇》、漢魏六朝詩、唐詩、宋元詩,乃“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②《原詩·內篇下》:“讀《三百篇》而知其盡美矣,盡善矣,……繼之而讀漢魏之詩,美矣、善矣,……又繼之而讀六朝之詩,亦可謂美矣,亦可謂善矣,……又繼之而讀唐人之詩,盡善盡美矣,……又繼之而讀宋之詩、元之詩,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矣;吾縱其所如,而無不可為之,可以進退出入而為之。此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而學詩者循序反復之極致也。”參見葉燮、薛雪、沈德潛《原詩·一瓢詩話·說詩晬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35頁。。此讀詩方法可以在宏觀上把握詩之流變,清楚地認識到沿與革,創與因,辨別精華和糟粕。這是學詩者所必須的知識儲備。
同時,不忽略古人包括還要看到古人創新之處。他以為在詩歌史上要看到陸機、左思、鮑照、謝靈運、陶潛等,不襲前人,自成一家,③《原詩·內篇上》:“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為鮑照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之藻繢、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為依傍。”參見葉燮、薛雪、沈德潛《原詩·一瓢詩話·說詩晬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4頁。要求學習集大成者如杜甫,杰出者如韓愈,專家者如柳宗元。他們的創新之處不僅不能忽略,而且還是后人學習前人之處。有更進者,古人的創新精神正是后人學習的重要內容。
什么是“不附會”呢?他說:
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學者,亦有不妨自我為之者。不可學者:即三百篇中極奧僻字,與尚書、殷盤、周誥中字義……;不妨自我為之者:如漢魏詩之字句,未必盡出于漢魏。[1]76
學習古人但決不能盲從于古人,要做到“不附會”。古人詩并非句句精華,字字珠璣,而是有“可學者”和“不可學者”,當取其精華而習之。
時變也未必都能入詩,所以要會辨別,知取舍,做到“可自我為之者”[1]76。“如漢魏詩之字句,未必盡出于漢魏”[1]76,一些典范字句不一定真是典范。因為,“天道十年而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1]4。時變而有詩變。詩之變由他律與自律等因素促成,這就是他所謂的“正變系乎時”與“正變系乎詩”[1]7。時不得不變,而詩也隨之不得不變。故時變而強行附會古人之行為,乃失去其合法性。他說:
上古之世,飯土簋,啜土铏,當飲食未具時,進以一臠,必為驚喜;逮后世臛臇魚膾之法興,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土簋土铏之庖進,可乎?[1]5
在飲食還未精致之時,以“簋”與“铏”盛飯與羮湯,而當各種烹飪之法無所不至,還能用上古時的“簋”“铏”嗎?同理,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康衢,但各種樂器,如琴、瑟、簫、笙、竽、鼓等產生,有美妙的曲譜,還會去聽擊壤之歌嗎?他的“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于極”[1]6的詩學觀念是與“附會古人”[1]76相對立的。他批評明人的復古之竊取古人時說:“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1]9,批評明末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為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1]10。“附會古人”必摹仿古人,尺寸古人。葉燮認為,詩是時代產物,作詩要真正認識理、事、情,培養起自己的才、膽、識、力,要有真感情、真心情、真獨創,如“若腐儒區區之見,句束而字縛之,援引以附會古人,反失古人之真矣”[1]76,批評了附會古人之舉。
可見,學習古人要“不忽略”與“不附會”。同時,他還進一步提出也不要附會“世人”,要有自己獨特之處,不附會古人,以著作自命,將進退古人,但如果議論是非而受世人影響也是愚蠢之事,而應該出入古人之間,達到古人為我所役的目標。
2.以“生新”為目標:以創辟之人為創辟之文
葉燮說“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1]76就是要把“古人”融化在“今人”之中。對此,其弟子沈德潛在《葉先生傳》中曾說到其師葉燮論詩,一曰生,一曰新,一曰深。雖然弟子對老師之詩歌創作的評價有拔高之嫌,但他看到葉燮身體力行,作詩之“言”和“意”都從已出,鄙視隨波逐流的“陳熟”之論。
葉燮重視獨創,他在《與友人論文書》中重申了這一點。他說:
荘、列、司馬遷諸人之文,為之于周、秦、漢以前,以創辟之人為創辟之文,稱作者可也。……仆嘗論古今作者,其作一文,必為古今不可不作之文,其言有關于天下古今者,雖欲不作而不得不作。……古來作者有言謂之立言,以此言自我而立,且非我不能立,傍無倚附之謂立,獨行其是之謂立,故與功與德,共立而不朽也。[4]卷十三《與友人論文書》,764
古今之作者,必為“不可不作”,或雖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這就是“自我作詩”。葉燮指出,“傍無倚附之謂立,獨行其是之謂立”,說前人沒有說過的,即要有“生新”。敏澤也認同葉燮,認為“一個時代應該有一個時代的詩歌,一個作家應該有一個作家自己不可重復的特色:‘自成一家’”[19]。針對有人說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1]8的話題,葉燮則說他“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藉《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1]8。陳子昂之詩能名揚后世,是因其“能自為古詩”[1]8。然終因他蹈襲漢魏詩,乃至與阮藉《詠懷》詩極為相似,不能盡脫漢魏窠臼,失自家體段,所以終不能自成一家。這是葉燮對陳子昂評價不高的原因。而相對應的是左思和鮑照則受到葉燮的青睞。他說左思、鮑照離魏并不遠,但前者不見曹、劉余習,后者不見建安本色,“千載后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1]7,正是因為有“生新”,有獨創,正如他所說的“相似而偽,無寧相異而真”[1]33。詩歌創作為求“真”而可以“相異”,“昔人可創之于前,我獨不可創于后乎?”[1]76要想創作出優秀的可傳之詩,就不能如陳子昂之“尚蹈襲漢魏蹊徑”[1]8,而要如左思、鮑照,挑戰前人,讓后人贊賞。
由此可見,“自成一家”[1]4是葉燮的評詩標準。如豪杰之士雖然出自“風會”,但并不隨風會而行,而是“能轉風會”[1]7,引導時尚。縱觀詩歌流變,能稱豪杰者,都是“不肯沿襲前人以為依傍”[1]4,而開一代風氣之先。葉燮稱杜甫融古匯今,無人能與之媲美,說他“包源流,綜正變”[1]8,既有漢魏詩的渾樸古雅,六朝詩的藻麗秾纖、澹遠韶秀,但又無一字與漢魏、六朝詩相同,這就是獨創。除了杜甫,葉燮還認為韓愈和蘇軾與他們三足鼎立,韓愈“無一字猶人”[1]51,蘇軾的點鐵成金,都體現出獨創之勢。陳運良指出:“葉燮對于那些善于創造的詩人,特垂青眼。”[20]因為他們都有創辟之詩,乃“千載后無不擊節”[1]7。可見,“陳熟”不可去,“生新”可追求,打通古今是作詩的成功之路。葉燮說:“后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后人,何以竟其引申乎?”[1]34我們不能簡單地重復過去,在“陳熟”中必須見到“生新”。
就葉燮的“陳熟生新”,郭紹虞說:“演變與不變,是他讀昔人詩所悟得的結論;成熟與生新,是他從這結論中所定的理想的詩境,他于明代七子詩風,病其陳熟,而于公安,竟陵詩風,又病其生新。陳熟之因,即因其學五古必漢魏,學七古及諸體必盛唐。其病在不知詩的演變,而懸一成之規以繩詩。生新之因,又因其抹倒一切體裁聲調氣象格律諸說,獨辟蹊徑,而入于瑣屑滑稽險怪荊棘之境。其病又在不知詩自有不變之質,而故趨新奇。所以他說:‘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于陳中見新,生中見熟,方全其美。若主于一,而彼此交譏,則二俱有過。’”[21]郭紹虞先生之論,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