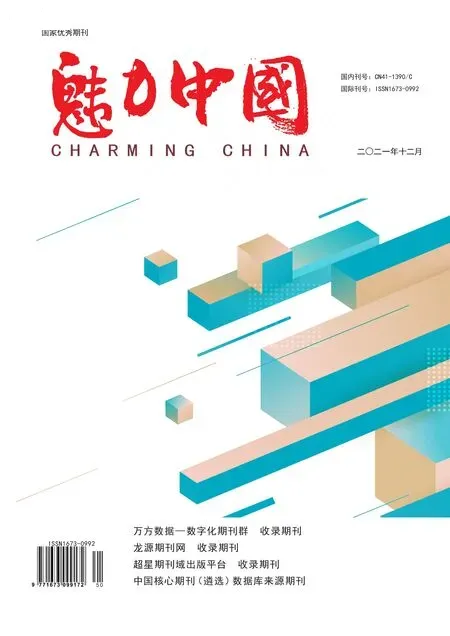從悲劇美學的角度淺析影片《地久天長》
翟淑昕
(大連藝術學院,遼寧 大連 116000)
《地久天長》作為第六代導演王小帥近年來最受關注的影片,曾被英國《衛報》評為“2019 年度全球十佳影片”之一。該片聚焦于生活在中國社會大變革時期的工人家庭,講述了一段跨越30 多年的悲劇故事,描繪出那個年代的人物充滿悲劇性的人生。在美學的視域下,悲劇不單單是現實中悲劇的再現,更是作者對悲劇理解的主觀表達。盡管《地久天長》是以現實主義為基調的影片,但是作為一部精雕細琢的藝術作品,其在盡可能還原社會現實的同時,還帶有獨特的悲劇美感,使得欣賞者在欣賞的過程中可以體悟到悲劇美學深厚的精神價值。
一、悲劇沖突的發生
悲劇沖突必將首當其沖地在悲劇中發生是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中的論斷,因為悲劇發生雙方的立場都帶有一定價值意義上的普遍性和正確性,但與此同時也都存在片面性,這種不可調和的片面性會導致沖突發生。在影片《地久天長》中,沖突不僅體現在個人與自我之間的內在沖突,還體現在個人與他人、社會之間的外在沖突。
(一)個人與自我的沖突
德國著名非理性主義哲學家叔本華在他的代表作《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中提出,主體的生命意志主導了世界,一切問題的根源在于主體的意志。而當個人選擇與自我意志發生沖突,便產生了痛苦的悲劇。《地久天長》中,盡管痛失獨子的劉耀軍收養了周永福,失去親生骨肉的痛卻依舊沒有被填平,這也令他無法正確的處理與周永福之間的父子關系,劉耀軍的內心仍保持著對親生孩子的渴望。沈茉莉懷孕的消息,讓常年壓抑在畸形心理下的劉耀軍陷入了強烈的自我沖突,一方是親骨肉所代表的傳宗接代之欲,一方是一起經歷風雨的妻子王麗云所代表的夫妻恩義之情,當劉耀軍選擇了王麗云,也是選擇了親手終結滿足自我欲望的機會。劉耀軍的選擇不僅僅是血緣與責任之間的選擇,更是在傳統父權觀念與自我感情間進行的決斷,無論結局如何,選擇都必將失敗,折磨也會一直存在。
(二)個人與他人的沖突
個體在社會生活實踐中必定會與另一個體相聯系,雙方在互相聯系的過程中也必會因利益問題產生不同的矛盾沖突,處于社會現實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沖突也就無法避免。王麗云和劉耀軍在發現懷二胎后曾有隱瞞并偷偷保住孩子的行為,這是他們對自己利益的維護,但這種維護卻侵犯到計生單位副主任李海燕的利益,因為王麗云超生的行為必然會牽連到她。當王麗云懷孕真相被李海燕得知后,代表著不同立場的雙方便產生了沖突,與此同時,計生委與好閨蜜之間的抉擇也導致了李海燕個人內心的沖突,但閨蜜情最終沒能抵過現實利益,李海燕強行帶著王麗云墮了胎,在這場沖突中維護了自己的利益,但代價卻是一個生命的逝去,不禁令人唏噓。
(三)個人與社會的沖突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強調是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共同構成了悲劇,象征放縱感性的狄俄尼索斯與象征光明理性的阿波羅分別代表自由的個人與嚴謹的社會,二者之間的沖突也是個人與社會的沖突。當渺小的個體的抉擇與強有力的社會大環境產生沖突,必然會導致小人物命運的悲劇。《地久天長》里的每一個人物,都與所處時代產生過劇烈的沖突,無論是愛好新潮因跳舞被判“聚眾淫亂”而關進監獄的新建,還是懷著二胎被強行墮胎的王麗云,抑或是在下崗潮中被迫下崗的無數工人,都曾在與社會產生沖突的過程中體驗過無比的痛苦。個體的生命體驗被結構性的社會制度所規訓,在強大社會力量的無情壓迫下失去心靈的支柱,導致了精神世界無助與崩潰,進而形成個體人生的悲劇。
二、悲劇美學視域下的闡釋
自充滿沖突的悲劇由古希臘誕生之日以來,無數美學家都曾在在美學領域對悲劇美感進行過帶有鮮明個人特色的闡釋,王國維的“壯美”說與朱光潛的“崇高感”便是其中經典,除了對探究悲劇美感之外,對于悲劇中展現的命運的必然性與欣賞悲劇時產生的悲傷之情的探討也備受重視。《地久天長》作為一部帶有濃厚悲劇色彩的影片,在其中充斥著悲劇美學的元素。
(一)“壯美”的無處不在
王國維認為悲劇的美感大多是“壯美”,是一種生存的意志被打破后消逝,繼而使個體失去意志目的所產生的美感,這往往設置在“好人蒙難”的情節中,在個體生存環境與命運悲劇的互文作用下,悲劇的“壯美”之感得到充分的體現。劉耀軍與王麗云的二胎沒能保住,他便將生活的重心放到了劉星一人身上,在劉星身上寄托了他全部的愛與期待,但是劉星卻在水庫溺死,劉耀軍自此失去了生存的意志,他收養周永福,想讓周永福來扮演劉星,可因為被悲慘的命運蹂躪過后性情大變,他無法與養子溝通,周永福也逃離了這個壓抑的家,劉耀軍第三次痛失孩子。就在絕望時,沈茉莉腹中的孩子成了劉耀軍最后的希望,但對王麗云的責任感讓他最終選擇了放棄,自此,劉耀軍完成了四次意志的破碎,內心的痛苦也達到了頂峰。四次失子所體現出的“壯美”,是個體被迫放棄一切后以無可奈何之情面對人生所產生的,帶有一種破碎又不失莊嚴的色彩。
(二)“超我”的崇高敘事
朱光潛認為,悲劇的崇高感在于它能在描繪小人物的悲慘遭遇的同時,表現人本身的偉大,王麗云與劉耀軍失子后的種種行為就帶有這種崇高感。盡管自己失去了兒子,王麗云依舊在李海燕提到沈浩時,編出劉星回外婆家的借口讓李海燕轉達,以安撫沈浩。在得知劉星去世真相后,兩人從未產生應有的瘋狂,反而將苦難默默承受,讓沈英明夫婦不再提起任何相關的事,以免影響沈浩的未來。長大成人的沈浩上門坦白時,作為苦主的夫婦倆反而繼續安慰沈浩,哪怕他們依然沉浸在悲傷中,也沒有怪罪沈浩。盡管失去兒子的痛苦導致他們的內心無比壓抑,多年來都無法釋懷,甚至間接導致了劉耀軍出軌,他們依舊自始至終從未指責過他人。影片選擇站在“超我”的道德層面對兩個人物進行刻畫,帶有一種崇高敘事的特征,作為小人物的夫妻二人經歷了非同一般的悲慘遭遇,卻仍時刻閃耀著人性的偉大光輝。
(三)必然性的悲劇命運
自古代起,中國的悲劇變有著相似的內核,那就是帶有必然性的不可抵抗的悲劇性命運。在大多數悲劇中,命運的強大仿佛能壓倒一切,個體只能被命運裹挾著沖進時代的長河,除此別無選擇。《地久天長》便設置在這樣的情境中,在那個工人集體下崗的年代,王麗云的下崗是上級帶有偶然性的選擇的結果,同時也是她作為那一時期沒有任何背景的工人無可抵抗的命運,是一種必然。李海燕到死也無法解脫也是一種必然,當她偶然得知劉星溺水的真相卻為了自己的孩子而將事情埋在心底,選擇懷著愧疚生活時,這種無法釋懷的愧意也必然會將她慢慢搓磨,直至死前還對于王麗云的孩子念念不忘。沈浩多年的無法忘懷也是如此,因為心懷愧疚,記憶在腦海中從未褪色,反而愈加鮮明。在必然與偶然這對辯證關系中,偶然成為故事的推動力,必然確定了故事的走向、成為了悲劇的前提,這是中國悲劇的一大特色。
(四)“移置”的悲傷之情
海德格爾認為人作為“此在”與世間萬物(“存在者”)一同寓于存在之中,人能夠通過想象進行橫向超越,達到物我同一,立普斯在美學上將這種同一稱為“移情”,欣賞者與作品情感狀態的合一便蘊含了移情的種子。《地久天長》講述的是上世紀那一特殊年代的故事,它采用了盡可能還原現實的手法進行拍攝,有利于欣賞者與影片人物之間達成悲傷之情的“轉移”。在痛失獨子后,王麗云不是崩潰的大吼大叫,而是在眾人散去之后轉過身偷偷哭泣,這一情節的設置令欣賞者從一位“旁觀者”變成了“分享者”,將自己與王麗云“縫合”在了一起,在完成身份轉變的同時也完成了悲情的“轉移”。悲劇審美體驗的達成,“移情”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悲劇價值的流露
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一書中講:“悲劇通過讓人面對困難的人物而喚醒人的價值感。”也就是說,只有在直面苦難人物的悲苦人生之后,個體才能在產生悲憫情懷的基礎上對一些現象的發生進行反思,進而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
(一)“憐憫”情懷的形成
“凈化”論認為在個體對悲劇進行審美體驗時除了愉悅感還應有教育作用,欣賞者在“憐憫”之情誕生后不應僅僅停留在共情,還應有所體悟。《地久天長》在描繪處在大環境下的小人物悲慘命運的同時,也抓住了其性格上的閃光點進行突出強調。心地善良的王麗云、敢愛敢恨的美玉、心懷愧疚的沈浩等,他們性格中那些美好的部分在欣賞者觀賞影片的過程中會對欣賞者產生影響,激發欣賞者對美好品格進行追求的欲望。
(二)“團圓”背后的“悲憤”
自“新文化”運動開始,由于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悲劇對“大團圓”結局的偏好,“中國無悲劇”論在美學界持續泛濫。直到80 年代,陳瘦竹才在《論悲劇精神》一文中提出,“大團圓”的中國式結局會產生“悲憤”這一獨特的審美體驗,“大團圓”結局這才擺脫“粉飾太平”的污名,名正言順成為中國悲劇的特色。只有在經歷“風雨”后,才能得知所得之珍貴。《地久天長》的結局中,周永福終于與劉耀軍、王麗云和解,要帶著女友回家,雖然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團圓結局,但經過對兩人三十多年里種種痛苦經歷的刻畫,影片帶給欣賞者的不是徹底放松,而是一種略帶沉重的釋懷,是一種讓欣賞者情不自禁去品讀、去反思的復雜之情,而不是淺薄的闔家歡樂。
伴隨著消費主義與現世主體的不斷崛起,“崇高”與“壯美”在文藝作品中正不斷被告別,作為美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悲劇對于喚起欣賞者的憐憫與悲憤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應受到大眾的重視。作為悲劇美學的最佳表現形式之一,悲劇電影應做到有思想、有深度、有內涵,能給予受眾以思考和感悟,影片《地久天長》便貫徹了這一原則,將故事設置在自帶沖突性的時代,以失獨這一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主題探討悲劇中事件發生的偶然和悲劇命運的必然,在給予觀賞者審美體驗的同時也起到了警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