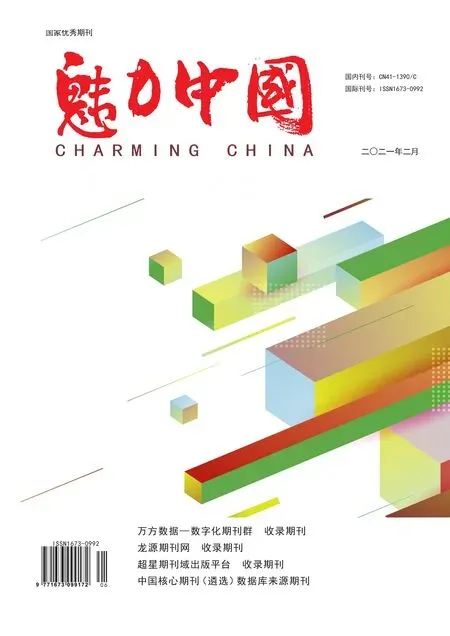中國山水畫形式語言的表現認識
蔣沖
(魯迅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遼寧 沈陽 110004)
肌理是指物體表面的組織紋理結構,即各種不同的紋理變化,是表達人對設計物表面紋理特征的感受。應用于繪畫中,肌理是物質材料與表現手法相結合的產物,在藝術實踐中,依據審美取向和對物象特質的感受,利用不同的物質材料,不同的工具和表現技巧創造出的一種畫面的組織結構與紋理。山水畫中的皴法是依照不同山石的差異地質構造和樹木表皮的差別形態,加以歸納總結而創造出來的表現程式。我認為這正是山石畫法中的不同肌理構造。而在后期山水畫中加入的筆墨,所尋求的暈化效果和厚重感等,也恰恰是對創造繪畫肌理方法的轉變。
一、中國山水畫的肌理起源
(一)山水畫的肌理萌發
最先的山水畫是作為人物畫中,補充畫面背景出現的,后來才發展成為獨立的畫科。雖肌理構造無處不在,但早期山水畫并沒有刻意地去加入,早期山水畫的主要表現為形式為先用線條勾勒輪廓,然后通過敷色來豐富。是從人物畫學來的。山水畫到了盛唐時代更趨繁榮,金碧青綠山水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當屬李思訓、李昭道父子。他們繼承和發展了隋代展子虔金碧青綠山水畫的傳統,用色更加典雅富麗,用筆則增加了皴筆筆法,使形體表現得更加飽滿。這是開啟了山水畫肌理的大門,皴法語言。
(二)山水畫肌理的發展
展子虔到李思訓時期是皴法肌理的從無到有,伴隨山水繪畫的成長,五代時期,董源 荊浩的繪畫作品中,則將皴法推向了成熟階段,因董源生活在金陵一帶,此地多山巒江澤,山勢平緩,起伏連綿,且為土質。這類環境締造了披麻皴的出現。而荊浩常年隱居太行山,則依據環境,畫出了折帶皴。皴法的發展,肌理的認識,代表著畫家們對事物內在的二次認識與了解,通過特殊的手段,創造特殊的肌理來表達自己的繪畫語言形式。
二、山水畫內在肌理的變革與走向
(一)前后匯通:學古傳承發展
以筆情墨趣為主的中唐山水畫,僅用墨色來描繪山水始于王維。王維在皴法中加入筆墨,使得筆墨與之相結合,是皴法肌理與筆墨肌理的雙重碰撞,從而開始了山水畫肌理的下一個方程式。荊浩主要繼承和發展了王維所開創的水墨山水畫法使傳統水墨畫技法形式得以確立,有筆有墨,筆墨相濟。關仝創造了獨特的繪畫風格,他的特點是巨石堅硬、厚實、凝重,山體、樹木豐厚茂密,景象壯闊,關仝畫樹不用線勾,這種表現手法更具生命力。而樹上常畫些樹枝枯梢,用筆方面則快捷縱放,下筆尖利。
(二)內外融合:借鑒西方繪畫
劉海粟早年作品多為油畫,后才以中國畫為主,善寫意山水及花鳥,運筆狂放,所畫山水多用重墨潑彩,還喜好層層重涂、重重積染。陸儼少的畫從生活中來,是一種概括與提煉,他以高超扎實的師古筆墨技藝為根基,加以革新的智慧手段,將山水畫由傳統引向現代。晚年的陸儼少思想并不保守,曾在西畫家的指點下,運用過丙烯色。張大千的潑墨潑彩,李可染的紅色意象山水,傅抱石的皴法等,他們注重于探究水墨效應的發展。
(三)現當代山水畫中肌理的創造與運用
為了追求更多樣式和更具沖擊的畫面效果,現當代山水畫創作中,產生了多種技法。用以形成肌理,譬如在畫面墨色濃濕時,選好局部進行撒鹽,鹽有吸水效果,可吸走部分墨、色,自然形成撒鹽肌理。在畫樹干、巖石的時候,我們可以采用揉紙法。這樣在紙張上作畫時能夠通過改變繪畫承載體的變化,來達到特殊的效果。還有膠礬,拓印,扎染法等等。不計其數的方法一方面體現了現代智慧以及多元化的氛圍,另一方面則表達了現當代畫家為革新創新中國畫,使畫面產生特殊的肌理效果。材料的變化并不是最終的目的,而是為了新的畫面語言表現,創造新的血液來完成中國畫的變革。
三、當代中國畫形式語言的思考
中國畫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創作上,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社會意識和審美情趣,集中體現了中國人對自然社會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政治,哲學,宗教,道德,文學方面的認識。它是用中國畫所獨有的材料工具,依照長期形成的表現形式及藝術法則而創作出的繪畫。隨著社會發展不斷發生著變化,在當今多元化文化的氛圍中,中國藝術創作發生了巨大變化,開始對古代繪畫成就中傳統成分開始現代轉化,其中包括為適應題材的表現采取的手段,將特殊材料和技術運用于創作,達到產生不同的藝術效果等,在現代水墨畫中最難表現的是現代視覺經驗,這經驗先于藝術的經驗,所以需要特殊的手法去創造特殊的肌理效果去表達,去吸引觀者,當然肌理的效果也并不是新奇險怪就好,而是通過視覺圖像發人深思,予人啟迪,用現代的方式,把握古代。
總結
對傳統的質疑,思辨甚至背離與虔誠的信仰形成強大而緊張的合力,共同推動了中國畫的現代進程。在當代國際文化版圖之中,中國畫已然向異質文化開放,自由多樣的媒介和手法,植入傳統元素或精神特質的創作,已超越筆墨技法和水墨媒介的限制。立足當下,應找到屬于自己的繪畫符號,精神層面對傳統加以思考,對其解構,重構。表現自身對當下生活和社會現實的觀察和體驗。獲得具有時代的特色的畫面語言。這才是藝術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