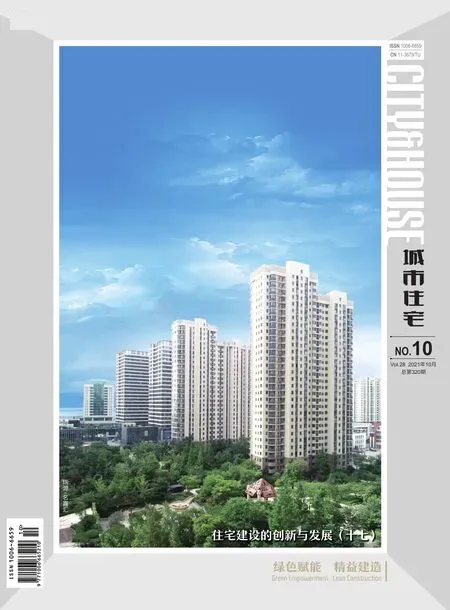解析少數民族建筑的地域性文化元素應用
——以鄂倫春族民居“斜仁柱”為例
郜英洲
(寧夏大學土木與水利工程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1 古老的馴鹿人——鄂倫春族
1.1 歷史淵源
“鄂倫春”這一名稱初見于清代初期文獻。《清太祖實錄》中首次提到“俄爾吞”,后在康熙年間改稱“俄羅春”,此后經多次演變,才比較統一地稱為“鄂倫春”,寓意為馴鹿的人。鄂倫春族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鄂倫春自治旗、布特哈旗、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以及和黑龍江省呼瑪等地區。自2000年以來,鄂倫春自治旗境內的鄂倫春族作為其主要部分,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總體人口呈上升趨勢(見表 1)。

表1 鄂倫春自治旗境內鄂倫春族人口增長趨勢
鄂倫春族屬于北方少數民族中的一支,人口稀少,但是民族文化非常豐富。鄂倫春族雖然沒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卻有自己的語言。鄂倫春語屬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通古斯語支,現在主要使用漢語及漢文。
1.2 文化形式
1.2.1 狩獵文化
鄂倫春族的狩獵文化是在17世紀中葉以前就已形成,早先的鄂倫春人主要分布在貝加爾湖以東、黑龍江以北的地區,后遷至大小興安嶺地區。而新遷而來的且依然依靠大自然而生存的鄂倫春人,初期是以“烏力楞”為單位集體狩獵解決衣食問題,而后大致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仍處于原始的游獵社會,另一部分則以飼養馴鹿的鄂溫克獵民為主。
1.2.2 早期薩滿教
早期的鮮卑信仰薩滿教,在鄂倫春族中也發現了類似于薩滿教信仰的痕跡。鄂倫春人以狩獵而生,依靠大自然的饋贈,鄂倫春語中的“德樂查”和“白那查”分別是他們對太陽神和山神的稱呼。雖然現今鄂倫春人的意識形態已發生較大改變,但仍有老鄂倫春人保留著用手指蘸酒彈向空中來祭祀山神的習俗。
1.2.3 光文化
鄂倫春族的光文化讓族人相信,薩滿的太陽神會指引其狩獵和生活,這一點在鄂倫春族傳統民居“斜仁柱”上有所體現。“斜仁柱”建筑圍護由片制的樺樹皮或獸皮構成,當鋪設至頂端時會留出一圈不作圍護。其作用之一是在溫度較高時利于室內外的空氣交換,并排除室內煙氣;作用之二便是對于光的使用,鄂倫春人在狩獵時會跟隨樹林中的斑駁光影安排行進路線,他們認為這是太陽神對其的饋贈。
1.2.4 火文化
鄂倫春人視火為生命,在長期的游獵生涯中,火更是充當了重要的生活工具。他們崇拜火甚至敬火為神,每年6月18日還會舉辦篝火節,除祭祀火神外,更是展現鄂倫春民族風情的重要活動。
1.3 常見的建筑樣式
1)住所——斜仁柱 傳統的鄂倫春族以狩獵作為主要生活方式,常年居無定所。為了適應這種不斷遷徙的生活,便形成了斜仁柱這種最原始的傳統民族建筑形式。
斜仁柱也被稱為“仙人柱”或“撮羅子”,在鄂倫春語中是樹干房屋的意思。建筑整體造型呈圓錐樣式,主要由若干根圓木搭建而成,外圍通常會覆蓋鐵克沙(一般由樺樹皮、獸皮制成),頂端留有采光通風的開口,夏季敞開,冬季加蓋圍子以作保暖。
2)儲存倉庫——奧倫 奧倫是鄂倫春族人存放糧食和物品的倉庫,通常會搭建在離游獵中心較近或狩獵時的必經之路,距離族群約5m。整體造型簡單,主要由立柱、橫木搭建框架,然后以半圓形架子構成頂部,覆蓋樺樹皮、松樹皮等。
3)狩獵棚舍——祜米汗 祜米汗是一種臨時搭建的棚舍,主要供鄂倫春人在外打獵時使用,臨時承擔居住功能,建造材料主要為樹條和樺樹皮,與斜仁柱相比,建造工藝較粗糙,無內部方位、座次等布局形式。
2 鄂倫春族代表建筑——斜仁柱
2.1 建筑布局及民俗
2.1.1 鄂倫春聚居模式
由于鄂倫春族的游獵性質所形成的“游”和“居”的關聯,是鄂倫春聚居模式的重要體現。從“游”到“居”的核心點的穩固,體現的是核心點的凝聚力和輻射力。
而對于“游”與“居”的關聯構架如下:以居所為核心點的定居模式,輔以“游”的線路及其他輔助空間的排列布置,形成新的同等級核心及不同等級核心點之間的連線。
“游”與“居”相輔相成,形成功能面以及關系網,在聚落空間演化過程中,將游獵文化表現得淋漓盡致。
2.1.2 建筑內部空間布局
鄂倫春族從原始社會到17世紀40年代由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的變化,形成不同的家庭空間單元。在父系氏族占統治地位以后,對斜仁柱中的方位以及座次進行比較嚴格的規定。與門相對的正位被稱為是“瑪璐”,是男客人的席位,右側的“奧璐”是老年夫婦的位置,左側的“奧璐”是年輕夫婦的位置,再分列兩側安排兒女等晚輩的座席。此外,圓形平面中央立放一口吊鍋,供全家取暖烹飪(見圖1)。

圖1 “斜仁柱”內部空間布局(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2.1.3 建筑相關民俗
鄂倫春族建造的斜仁柱樣式多次出現在其族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過程。如出生時,鄂倫春族人使用樺樹皮作搖籃,將其懸掛在斜仁柱頂部的橫桿上;結婚時,新娘會在新婚前一夜隨新郎在事先搭建好的斜仁柱內過夜;死亡時,鄂倫春人將逝去親人的物件放置于高處倒錐形樹杈之間,以示回歸自然。
2.2 建筑建造方式
搭蓋斜仁柱是先用2~3根粗實的“阿杈”(意為主干)架好形成門框,然后將6根較細且長5~6m的“托拉根”(帶杈的樹干)搭在“阿杈”上,相互咬合,使整個骨架牢固。然后將從樺樹上剝下來的“塔路”(樺樹皮)像鐵瓦一樣一張壓一張地覆蓋在斜仁柱的骨架上,用繩索捆牢。剝下來的樺樹皮通過縫合,每片高、寬均約1m。由于樺樹皮較厚,斜仁柱內部較暗,只能從斜仁柱頂端的通煙口和東南部的門進光。
人們會在斜仁柱頂端縫制一塊皮子,白天打開利于通風散熱,使光線進入室內。夜晚將其放下,扣住頂端,形成封閉的室內空間,起到保溫隔熱的作用(見圖2)。

圖2 “斜仁柱”建造流程(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2.3 衍生建筑——蒙古包
斜仁柱的建造歷史可以追溯至原始社會,幾十根木桿綁扎成為圓錐狀骨架,后在外表覆蓋樺樹皮或獸皮。這一方式幾經演變,在公元前7世紀已呈穹廬狀。公元前5世紀基本定型,并成為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寓所。
3 東北地區鄂倫春族建筑與現代建筑的融合
3.1 民族現代民居現狀
東北地區鄂倫春族在1951年成立鄂倫春自治旗后就開始遠離森林,逐漸適應城鎮市井生活,狩獵文化作為民俗保留下來,大多鄂倫春人已住進磚石房屋。在脫貧攻堅征程中,鄂倫春自治旗于2020年正式實現脫貧摘帽,國家級貧困縣的歷史一去不復返。
高科技的建造手段以及現代的建筑材料催生“千村一面”式的保障性磚房,斜仁柱傳統民居已經淡出了鄂倫春人的生活,保留下來的僅有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庫圖爾其廣場上佇立的42個大小不同的混凝土斜仁柱。
此外,位于大楊樹鎮的多布庫爾獵民村,其游客中心設計雖保留“阿杈”交接的樣式,但整體形制已與普通木屋無明顯區別。
3.2 地域性文化符號的提取
1)一味地推崇原貌,現代建筑材料的濫用 在庫圖爾其廣場上佇立的42個橘紅色斜仁柱,雖保留原民居的“阿杈”交接形式,利用混凝土材料的高強度特性,在高度和空間尺度上都進行了大幅度改進。但究其根本,僅僅是對斜仁柱原貌的模仿,仿造建筑外在形態,忽略建筑表皮以及建筑頂端的鏤空部位。玻璃窗、鋼架網以及用涂料粉刷的鄂倫春族圖騰樣式,缺少鄂倫春族的真實精神,這也是新型斜仁柱缺失地域性文化符號的主要原因。
2)對民族傳統文化認識度不夠 新建造的現代斜仁柱并沒有理解原有建筑存在形式的社會性、人文性和自然性。鄂倫春人將信仰保留在建筑中,以光“照亮”自己的生活,用樺樹皮表達民族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生,這也是當今建筑設計中鄂倫春族傳統民居與現代建筑融合過程中所缺失的地域性。
4 鄂倫春族傳統民居與現代建筑融合設計方案
4.1 人文性
將鄂倫春族的民俗民風凝練成3條故事線索:線索一是鄂倫春人的生活,包含游獵文化、光文化、薩滿祭祀等不同民族文化;線索二是鄂倫春人的一生,包含鄂倫春人的出生、結婚、日常生活以及死亡;線索三是傳統文化符號的消逝,包含鄂倫春族的樺樹皮工藝以及其他民俗文化活動等。
4.2 自然性
4.2.1 保留樺樹皮等主要營造形式
從鄂倫春族對山神“白那查”的崇拜中,可以提取樺樹皮作為新建建筑的外表皮及內部裝飾,用樺樹皮構建固定的尺寸模數,使用連接構件將其拴掛在建筑外部,夏季若要增加建筑散熱面積或新開門窗,可將拴掛的樺樹皮取下(見圖3)。

圖3 “斜仁柱”在現代建筑設計中的應用形式(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4.2.2 保留頂端通光孔
太陽神“德樂查”對于鄂倫春人的狩獵和生活具有重要的影響,如今對于光的利用契合這一民族文化和精神。使用光作為不同功能空間的標志節點和建筑觀展流線的布置依據,能夠進一步使鄂倫春族的傳統文化與建筑結合,從而形成更有敘事性的展覽建筑(見圖4)。

圖4 鄂倫春族光文化在現代建筑設計中的應用形式示意(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4.3 社會性
高水平的科技發展和快節奏的生活頻率,讓人越來越多投入到以經濟為重的城市建設,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逐漸被人們遺忘,亟待被重新喚醒。展覽館保留原有的民族建筑形式,在設計過程中對民族文化的保留和引申,對民族精神的暗喻,都會成為對少數民族建筑地域性文化元素的新理解。
5 結語
建筑應該更多地反映民族的文化內核和精神。少數民族建筑的傳統樣式在當今社會中大多被新的建筑材料、建筑樣式所取代。從鄂倫春族民居斜仁柱的現狀中可以窺見大量的少數民族建筑已經缺失了傳統建筑文化的內涵和精神。
對鄂倫春族建筑的研究,不僅能夠保留傳統民族文化和精神,使其得到更好的繼承和發展,同時也能為地方城市尤其是對少數民族地區城市建設帶來更多可以借鑒的設計手法,形成更具多樣性的城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