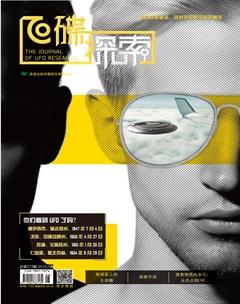濕漉漉的太空“入侵者”
塞思·肖斯塔克
如果你正在尋找地外生物,那么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專家會告訴你,雖然其他液體也可能孕育出生命(這時候你也許會想到氨和液化天然氣),但水總是首選。歸根結(jié)底,就地球而言,我們認為生命首先出現(xiàn)在海洋中,并且對其大洋中的出生地一直都很滿意,30多億年來,它們一直待在那里。
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可以估計出,大約有1萬億顆其他行星散布于整個銀河系中。于是,我們很自然地猜測,在這1萬億顆其他行星中會有一些同地球一樣潮濕,其中有些還可能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生命。但是最近對小行星的研究(它們就像太陽系里的“野孩子”)使得人們對上述看似合理的場景頓生疑竇。這項研究同時也開啟了另一種可能性的大門,即大多數(shù)溫度適中、如地球般大小的行星,也許干巴得就像英國幽默一樣。
這一切都取決于地球是如何獲取水的。地球表面積的2/3碧波蕩漾,其大洋的平均深度約是3200米。據(jù)此我們可以推算,地球上的水總共有約132.5億億立方米。這么多的水的確令人震撼,但是,要說明的是,這么多的水只占地球質(zhì)量的約0.02%,而這大概與你的頭發(fā)占你身體其他部分的比例相同。但對地球來說,水是必不可少而又極不尋常的標志。
然而,覆蓋地球表面的這層薄薄的液體,一開始并不是地球表面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我童年時代讀過的地質(zhì)學書籍中,就有插圖描繪了戲劇性的一幕:火山將蒸汽噴射入史前大氣層,而彼時的地球還是一個死氣沉沉、毫無生機的世界。這表明我們居住的星球自出生之日起就已經(jīng)在其表層下儲備了足夠的水,只等著“樂于助人”的火山刺破地球的表層,將其噴射到地表。在一個孩子看來,這一切肯定是合情合理的。
但事實并非如此。
地球是由內(nèi)爆云中小的灰塵顆粒形成的,而內(nèi)爆云同時也形成了我們的太陽。雖然這些灰塵顆粒的混合物中肯定有水,但由于太陽光的作用,它們都是以蒸汽的形式存在的。對,你理解得沒錯,地球一開始是熱氣騰騰的。這是沒辦法的事,因為當時地球的重力很弱,無法使那些“渾身濕透的云”沉下來。
現(xiàn)在繪就了地球表面山川大陸的水,則是來自其他地方。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許多天文學家認為這個其他地方就是彗星。彗星常常被我們描繪成一個“臟冰球”,根據(jù)這一說法,你身邊的海洋就是“彗星果汁”了。
但是這一觀點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再流行。因為你很難想象,怎么可能有足夠的彗星專門繞道到我們的星球(彗星通常只出現(xiàn)在太陽系內(nèi)偏遠的地方),并將它們的“水貨”交付給地球。
現(xiàn)在人們傾向認為,那些在電影中經(jīng)常威脅星際飛船的、黑暗的、難以發(fā)現(xiàn)的巖石——也就是小行星——才是地球表面水的來源,而它們是通過撞進地球來做到這一點的。盡管在你的印象中它們是干燥、花生狀的大石頭,但它們也含有大量的水冰。
當然,需要大量的小行星才能造就一個像地球這樣的藍色巖質(zhì)行星。我們假設小行星的直徑平均為1.6千米,有1/5是水,要填滿大西洋、太平洋以及地球上所有被“藍色墨水”覆蓋的區(qū)域,將需要大約50億顆這樣的小行星。
那么,是什么使得這些濕漉漉的巖石變成了瘋狂的“神風特攻隊隊員”,墜落到地球的呢?我們給出的可能是:被木星和土星怪異的舞姿驅(qū)趕到地球附近的,時間是太陽系開始形成后的四五百萬年,即大約45億年前。當時,原始塵埃顆粒導致新生的木星和土星呈螺旋狀向內(nèi)旋轉(zhuǎn)。最終,它們得以盡可能地接近太陽,出現(xiàn)在現(xiàn)在的火星軌道上。如果你能親眼見證這次行星之間“背對背的換位舞步”,會看到木星在天空中像一個大盤子,而不是現(xiàn)在這樣的一顆明亮的星星。
這對巨人行星之間的舞蹈撼動了小行星,使得它們中的很多來到了離太陽足夠近的地方,從而使它們與地球相撞成為可能。它們與地球融合時留下的“傷疤”,形成了今天地球上碧波蕩漾的海洋。這種不正常的態(tài)勢并沒有持續(xù)多久,大約50萬年后,木星和土星退回到它們目前所處的位置,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用以界定外太陽系的位置。但是,它們親手為地球打造水層的任務已經(jīng)完成了。
現(xiàn)在,所有這一切都還只是一個溫和而有趣的故事。真正的問題是:這只是一個還說得過去的故事嗎?其他恒星周圍的行星,也會經(jīng)歷類似的一系列事件嗎?還是說,我們的太陽系非比尋常,其他系外行星都是焦土一片、死氣沉沉?
我們不知道。地球的確是有些特別,也許還相當特別。但是許多天文學家,對“除了錯綜復雜的‘巨行星舞蹈’這一機制可以為巖質(zhì)行星提供水外,還可能有其他機制也能做到這一點”感到樂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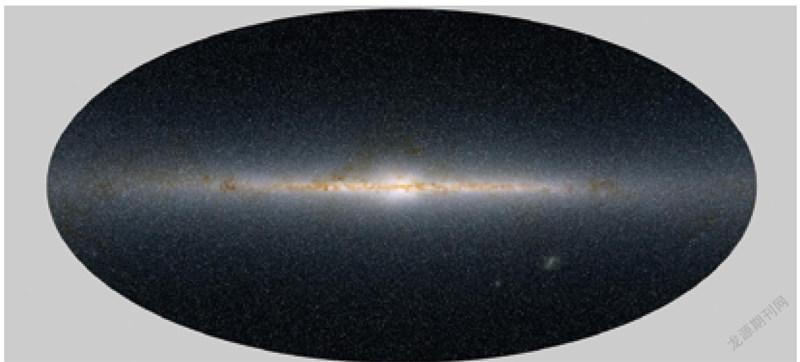
基于mass的觀測數(shù)據(jù)繪制的銀河系紅外線畫像
博爾德城西南研究所的行星科學家凱文·沃爾什曾致力解開地球水的來源之謎。他指出:“雖然地球歷史似乎的確很特別,但我們真的不知道,它是否就是那么不同尋常。此外,行星上沉積著水的場景也不難想象,它們中既有小行星也有彗星。”
沃爾什說,要確認這樣的場景是罕見的還是常見的,需要時間。只有當我們建造起足以查實地球大小的行星上是否有水的大型望遠鏡,才達到可以斷定行星上是否存在水的條件。同時,對那些想與其他生物分享宇宙的人士來說,你們只能寄希望于銀河系有許多大洋,而不只是地球上的七大洋。(譯者注:現(xiàn)在,西方科學界的相當一部分科學家,主張將我們熟知的地球上的四大洋細分為七大洋,分別是南太平洋、北太平洋、南大西洋、北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和南大洋。因為這一觀點有其科學性,所以現(xiàn)在西方主流地圖很多都采用七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