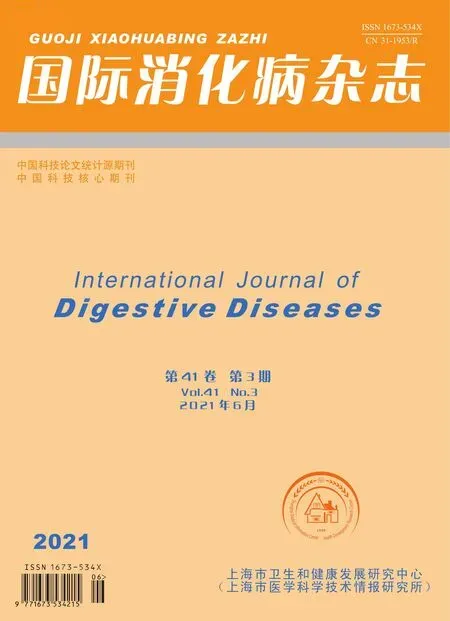CD26與炎癥性腸病關系的研究進展
郭 蕊 羅 娟 繆應雷
炎癥性腸病(IBD)包括潰瘍性結腸炎(UC)和克羅恩病(CD)兩種類型,其病因尚未完全明確,目前仍缺乏有效的診療方案。反復發作的癥狀和高昂的治療費用給IBD患者帶來了生理、心理雙重壓力,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質量。探究IBD的發病機制,開發新的有效診療方案任重道遠。有研究發現,與健康人群相比,IBD患者的血清可溶性CD26(sCD26)水平下降,而作為淋巴細胞膜表面抗原的CD26表達水平升高;且sCD26水平與IBD疾病活動度呈負相關[1]。另有研究表明,高血清sCD26水平可提示治療反應良好[2]。動物實驗顯示sCD26抑制劑具有減輕腸道炎性反應的作用[3-4]。上述研究提示CD26參與了IBD的發生、發展,可能成為新的IBD治療靶點。本文就CD26的水解、非水解作用與IBD的相關性,以及CD26在IBD臨床診療中應用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CD26的結構和功能
CD26是一種高度糖基化的Ⅱ型跨膜蛋白,相對分子質量為110 000,由兩個同源亞單位組成,主要結構包括由6個高度保守的氨基酸組成的胞內區、由22個氨基酸組成的跨膜區和由738個氨基酸組成的胞外區。胞外區分為N端糖基化區、C端水解區、富含半胱氨酸區這3個結構域。N端糖基化區可與腺苷脫氨酶(ADA)、微囊蛋白-1(Caveolin-1)結合,膠原蛋白、纖連蛋白、纖溶酶原和鏈激酶可與富含半胱氨酸區結合。CD26胞外區可被剪切、釋放至血清,具有水解作用,這種sCD26又被稱為二肽基肽酶-Ⅳ(DPP-Ⅳ)。CD26廣泛表達于體內多種組織器官,主要發揮兩種功能:(1)絲氨酸蛋白酶水解功能 作用于氨基末端第2個為脯氨酸或丙氨酸的多肽,并剪切氨基末端前的兩個氨基酸,改變底物的生物活性;其底物具有多樣性,目前研究已發現的是胰高血糖素樣肽(GLP)、神經肽、血管活性腸肽等[5]。(2)非水解作用 即受體和共刺激因子功能,參與細胞信號轉導,誘導T細胞活化和細胞遷移、黏附、侵襲等病理、生理過程[6]。由此可見,CD26參與了代謝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惡性腫瘤的發生和發展。
2 CD26的水解作用與IBD
2.1 CD26在IBD中對GLP的水解作用
在受CD26水解作用調節的底物中,被研究得較為深入的是GLP。進食刺激腸道L細胞分泌GLP,主要是GLP-1和GLP-2,從而促進胰島素釋放,延遲胃排空,控制血糖水平。GLP在體內的半衰期極短,主要由sCD26水解失活或由腎臟清除。近年來研究發現GLP還參與了免疫調節[7],這使得GLP和sCD26備受關注。Keller等[8]發現活動期IBD患者的胃腸排空延遲且GLP-1水平升高;Xiao等[9]發現IBD組患者血液中GLP-2活性形式GLP-2-(1-33)水平較健康組顯著升高,而sCD26水平較健康組顯著降低。上述研究表明IBD患者的GLP水平發生了改變。
目前對GLP-1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糖尿病、動脈粥樣硬化方面,而在GLP-1與胃腸道的關系方面則鮮有研究。Yusta等[10]發現GLP-1基因敲除小鼠的腸道微生態紊亂,且IL-1β、IL-6、IL-12、三葉因子1(TFF1)、TFF2表達異常。Anbazhagan等[11]用GLP-1治療由葡聚糖硫酸鈉(DSS)誘導的結腸炎模型小鼠,雖未觀察到腸道炎性細胞浸潤程度減輕,但觀察到腸上皮杯狀細胞破壞程度明顯減輕;此外,GLP-1治療組小鼠的腹瀉情況緩解,DRA蛋白表達升高,DRA蛋白在維持細胞內外離子平衡,防止腸道液體丟失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GLP-2可維持腸道黏膜屏障,參與腸道炎性反應。GLP-2的促生長作用較表皮生長因子、生長激素、胰島素樣生長因子更強,并具有腸道特異性[12]。Drucker等[13]用GLP-2類似物治療由DSS誘導的IBD模型小鼠,發現其可顯著逆轉小鼠的體質量降低,并可使小鼠結腸及腸腺體長度增加,以及黏膜炎性反應減輕。Gu等[14]用DSS誘導建立小鼠IBD模型,治療組予重組GLP-2二聚體,對照組予生理鹽水,結果顯示治療組小鼠的體質量增高,腸道炎性反應減輕,腸壁通透性較對照組降低,干擾素-γ(IFN-γ)、TNF-α、IL-1β、IL-6等促炎因子表達降低,結腸組織中Nod樣受體蛋白3(NLRP3)炎性小體及環氧合酶-2(COX-2)蛋白表達降低,髓過氧化物酶活性減弱。GLP-2的治療作用在由TNBS和乙醇混合液誘導的IBD模型小鼠[15]、IL-10-/-模型小鼠[16]、人類白細胞抗原-B27(HLA-B27)轉基因模型小鼠[17]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驗證。2006年一項GLP-2類似物Teduglutide治療CD的Ⅱ期臨床試驗納入了100例克羅恩病疾病活動指數(CDAI)為220~450分的CD患者,隨機給予患者3種劑量(每日0.05 mg/kg、0.10 mg/kg、0.20 mg/kg)的Teduglutide或安慰劑皮下注射治療8周,8周后CDAI評分<150分視為治療完全緩解,CDAI較基線下降100分視為治療有應答,結果顯示Teduglutide組的緩解率為55%,安慰劑組的緩解率為33%,且緩解率與藥物劑量呈正相關;由于該試驗中劑量梯度分組較少,故未發現Teduglutide的最佳治療劑量[18]。
上述研究結果表明,GLP可能成為IBD的潛在治療靶點。然而,GLP在人體內的半衰期極短,主要由sCD26水解失去活性,由此推測可通過抑制sCD26的水解活性延長GLP的半衰期,以達到減輕腸道炎性反應的目的。有研究建立了小鼠IBD模型,比較sCD26抑制劑治療組與安慰劑組的療效,發現sCD26抑制劑治療組小鼠的疾病活動度低于安慰劑組,腹瀉、直腸出血、體質量下降等癥狀較安慰劑組明顯改善;腸道細胞增殖加快,腸壁厚度較安慰劑組增大;此外,sCD26抑制劑治療組小鼠的腸道腺體缺失、炎性細胞浸潤、杯狀細胞破壞程度均減輕,促炎因子釋放減少,GLP水平升高且半衰期延長[3-4]。由此可見,sCD26抑制劑可通過抑制GLP水解發揮減輕腸道炎性反應的作用,sCD26抑制劑可能是潛在的IBD治療藥物。
2.2 CD26在IBD中對其他物質的水解作用
除GLP以外,CD26還可作用于其他底物,如神經肽Y(NPY)、血管活性腸肽(VIP)等。研究顯示NPY、VIP可能是胃腸道保護因子[19]。Baticic等[20]為觀察結腸炎機體中CD26是否參與調節神經內分泌因子,分別給予野生型(C57BL/6)小鼠及CD26-/-小鼠直腸注入TNBS和生理鹽水構建IBD組和非IBD組,結果顯示由TNBS誘導的兩系小鼠的炎性反應相關病理學指標之間無明顯差異,僅野生型TNBS組小鼠的Lieberkuhn隱窩的寬度恢復較慢;野生型TNBS組小鼠和CD26-/-TNBS組小鼠的血清、結腸、腦中的VIP水平及血清NPY水平均升高,CD26-/-TNBS組升高幅度更大;在炎性反應急性期和恢復期,野生型TNBS組小鼠的結腸和腦中NPY水平升高,而CD26-/-TNBS組小鼠僅結腸中NPY水平升高且升高幅度較野生型TNBS組小鼠小。該研究結果提示:(1)血清、結腸、腦中神經內分泌因子變化的差異表明IBD發病機制中腦-腸軸調節的存在,sCD26參與調節IBD機體神經內分泌因子變化,恢復期野生型小鼠較CD26-/-小鼠更需要NPY水平升高,提示CD26基因缺乏對于結腸炎可能存在潛在的保護性作用;(2)與野生型小鼠相比,CD26-/-小鼠并未顯示出明顯的腸道炎性反應減輕,CD26-/-小鼠腦中NPY水平的變化,表明sCD26在IBD中的調節機制復雜,不僅僅是水解作用。
3 CD26的非水解作用與IBD
CD26的非水解作用與其結構密切相關。CD26是T細胞活化所需共刺激信號來源,T細胞表面CD26與抗原遞呈細胞(APC)表面Caveolin-1連接,促使Caveolin-1胞內區結合的Toll相互作用蛋白(Tollip)和IL-1受體相關激酶-1(IRAK-1)解離,IRAK-1磷酸化,介導APC表面CD86表達上調并結合T細胞表面CD28,協同活化第一信號,活化抗原特異性T細胞。此外,CD26胞內區尾部可結合CARMA1的PDZ區域,激活NF-κB,誘導T細胞分泌IL-2[4]。CD26胞外區的富含半胱氨酸區可結合膠原蛋白、纖連蛋白,介導T細胞遷移[21]。眾所周知,IBD存在復雜的特異性免疫調節過程[22]。CD26的非水解作用可能參與了IBD的免疫紊亂。目前關于敲除CD26基因對小鼠結腸炎影響的研究報道存在爭議。有研究認為CD26-/-小鼠造模會表現出更為嚴重的結腸炎性反應[23],而另有研究顯示CD26-/-小鼠結腸炎病理表現與野生型小鼠之間雖無明顯差異,但其結腸炎癥狀較野生型小鼠輕[24]。細胞分子層面的研究采用DSS誘導CD26-/-小鼠建立結腸炎模型,發現髓過氧化物酶活性增強,NF-κB亞單位p65水平升高,脾臟CD8 T淋巴細胞占比升高[25]。不同于CD26對于T細胞活化、遷移作用的理論,也不同于前述研究的結論即sCD26抑制劑可緩解小鼠結腸炎,敲除CD26基因并未表現出對于結腸炎的保護性作用,敲除CD26基因與使用sCD26抑制劑對于結腸炎結局的影響具有差異性。有研究顯示sCD26抑制劑Teneligliptin除可抑制GLP水解外,還可直接與CD26競爭Caveolin-1的結合位點[26]。此外,有研究發現CD26-/-結腸炎小鼠體內絲氨酸二肽酶-9表達升高了約1倍,使得體內sCD26樣水解作用即絲氨酸蛋白酶對相關底物的水解功能并未受到CD26表達缺失的影響[27]。由此可見,CD26在IBD機體中不僅可通過影響底物水解水平起作用,其非水解作用也非常重要,具體作用有待深入研究揭示。
4 CD26與IBD的臨床診療
研究顯示血清sCD26水平與IBD疾病活動度[1]、治療反應性[2]相關,提示臨床上檢測血清sCD26水平可協助評估IBD活動度及預測療效。Yazbeck等[28]采用改良13C同位素呼氣分析法測量sCD26水平,這一無創、簡便的檢測方法為血清sCD26的臨床檢測開辟了道路。目前IBD治療主要是依靠生物制劑、糖皮質激素、免疫抑制劑、水楊酸類等藥物減輕腸道炎性反應。sCD26抑制劑具有促進腸黏膜修復的作用,可能成為IBD的一種輔助治療方案。除IBD外,目前sCD26抑制劑在短腸綜合征、腸易激綜合征、結腸癌、糖尿病、動脈粥樣硬化等疾病治療中的應用也在研究中[29],這對于有復雜合并癥的IBD患者的藥物研發具有提示作用[30]。
近年來,應用sCD26抑制劑是否會升高糖尿病患者的IBD發病率引起了廣泛關注。Kim等[31]檢索了2005年至2013年的美國保險理賠數據,比較了分別以sCD26抑制劑聯合二甲雙胍與以非sCD26抑制劑聯合二甲雙胍作為起始降糖治療方案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發病風險,發現在以sCD26抑制劑聯合二甲雙胍治療的患者中,包括IBD在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發病風險明顯下降。2018年英國一項納入141 170例糖尿病患者的觀察性研究顯示,sCD26抑制劑升高了75%UC患病風險[32]。2019年一項薈萃分析納入了16項有關sCD26抑制劑對IBD發病率影響的研究,共198 404例患者,結果顯示sCD26抑制劑暴露并未導致IBD風險顯著升高[33]。2019年一項隊列研究對比了895 747例服用sCD26抑制劑的糖尿病患者的IBD發病率,發現短期sCD26抑制劑治療并不會升高IBD風險[34]。目前CD26對IBD的影響尚未明確,今后需開展大規模前瞻性研究揭示。
5 小結
CD26與IBD的相關研究顯示,CD26可通過水解作用和非水解作用調節機體細胞因子的生物活性,介導T淋巴細胞的活化、遷移,參與IBD的發生、發展。CD26可能成為IBD診斷和治療的新靶點。然而,目前研究多集中于闡述CD26對GLP類似物的水解作用對IBD的影響,對CD26與IBD發病機制關系的相關研究尚有限,sCD26抑制劑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有待臨床觀察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