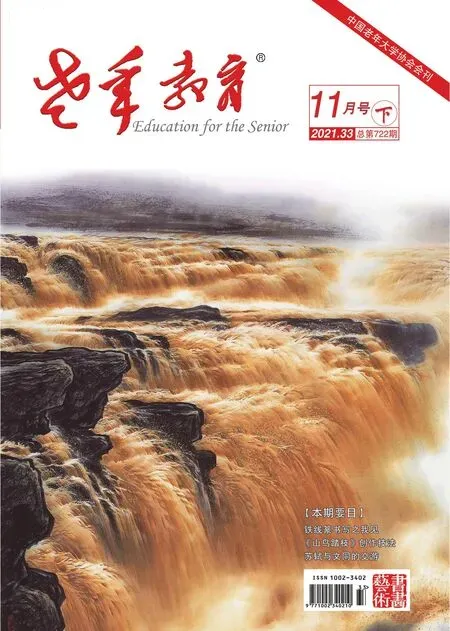孫過庭《書譜》書學理論與寫法分析(十八)
□ 楊 勇
論書體
《書譜》涉及對各種書體的認識,強調辨別各種書體,指出各種書體用途、特征、規律的區別,以及從各體書法不同的功用出發分析其不同的風格特征。如“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藝術需要各種養料,故“镕鑄蟲篆,陶均草隸”,要把各種不同風格的東西加以融會貫通,重視各體間的相互聯系。“草不兼真,殆于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從真、草二體的比較中引出其筆法、字形上的相通與相異之處。融諸體之長,觸類旁通,是書家成功的重要因素,歷代書家概莫能外。學書者若能融會篆之“婉通”、隸之“精密”、草之“流暢”、章之“簡便”,自然能成大家。而且,孫過庭認為專精一體對書法學習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畢竟每個人精力有限,只有以有限的精力聚焦于一種書體上,才有可能做到極致。所以,我們可以涉獵廣泛,但需找準自己的專攻點,這需要一種理性精神。
各種書體在妍質方面有所不同,這是歷史原因,不必厚古薄今。孫過庭對鐘、張、二王的評價不以古今、質妍等觀念為標準,而主張一種趨變適時的審美觀。他認為草書自有其特性,“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回互雖殊,大體相涉”。關鍵在于把握好草書的特質,使其很好地再現“達其性情,形其哀樂”的審美效果,而不是糾纏于“古質”與“今妍”孰高孰低。
論風格與鑒賞
在書法風格方面,孫過庭注重書法風格的多樣性。人與人的性情不同,進而有了不同的書法風格。“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不遒,剛者又倔強無潤;矜斂者弊于拘束,脫易者失于規矩;溫柔者傷于軟緩,躁勇者過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滯澀,遲重者終于蹇鈍,輕瑣者淬于俗吏。”表面上是批評九種不同的不良風格,進一步分析則是因為人的審美取向不同,從而會追求不同的書法風格。孫過庭追求的是和諧的中庸之美。他主張骨氣與遒麗兩者兼得。當然,在兩者之中,孫氏似更看重骨氣。因為骨氣偏多,無非“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猶不失為書;反之,若遒麗居多,則便不成其為書法了。這種傾向不僅是由于孫氏繼承了魏晉以來書論史上重視骨氣的傳統,也反映了盛唐時代追求清新、剛健之美的審美傾向。
對于書法作品而言,孫過庭一方面標舉參差錯落之美,要求點畫變化;一方面追求終篇協調,表現出以中和為尚的審美趣味。因而,孫過庭對不同風格采取兼容并包的態度。他盛贊王羲之書法“會古通今”,即指出其博采眾長、兼取各體的特點。孫過庭在論述具體書家時也反復提出要能“兼善”“兼通”各體,可見其欲綜合各種書風而融會貫通的藝術思想。
關于書法批評及鑒賞,孫過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對當時的批評風氣深感不滿,指責了三種批評態度:有的人昧于所見而信于所聞,習慣于跟風批評,這種現象可謂“人云亦云”;有的人以自己的年紀與職位炫耀,隨意訾議他人,這種人可謂“倚老賣老”;更多的人迷信古董,鄙薄現代,一見緗縹古書,則贊不絕口,這種弊病可謂“貴古賤今”。孫過庭對這些現象深加譏諷,進而提倡書法批評中的獨立思考精神:“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于耳目也。”他以為評書也要具有蔡邕識琴、伯樂相馬那種見微知著、不為時尚所囿的精神。
孫過庭提倡書法批評要切于實用,不做浮泛空洞或玄虛莫測的議論。他批評一些論書著述:“或重述舊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茍興新說,競無益于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體現了他強調獨立思考與有益實用的原則。雖然孫氏對前代書論的檢討未必公允,卻體現了實事求是與不囿于前說的精神。他認為批評的目的在于從紛繁復雜的書法創作中總結規律,以期有助于現世與后代學書者。清王文治《論書絕句》中說:“細取孫公《書譜》讀,方知渠是過來人。”孫氏理論之所以能超越六朝而成為書論史上的重要著作,與他本人對批評的認識是分不開的。
其實,孫過庭對書家的要求不外乎“思”“學”二端。“思”,指書家通過自身各方面的修養而達到對藝術的徹悟。王羲之晚年“思慮通審,志氣平和”就是這種境界的體現。同時,他極重視“學”的作用,即“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實為甘苦之言。
孫過庭在書法理論方面的成就巨大,凡是研究書法者,無不奉《書譜》為圭臬。在全文3700余字中涉及書法發展、學書師承、重視功力、廣泛吸收、創作條件、學書途徑、書寫技巧等各個方面。唐代是一個各方面都繁盛的朝代,書法一方面強調技法的重要性,同時張揚其“表情”性質與“風骨”,從而構成唐代書法的整體面貌。孫過庭在《書譜》中倡導的技與道的“中和之美”和助人倫的教化作用,不僅使我們看到《書譜》墨跡所流溢的藝術之美,同時也體會到書法背后、文字內容在書學理論上的里程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