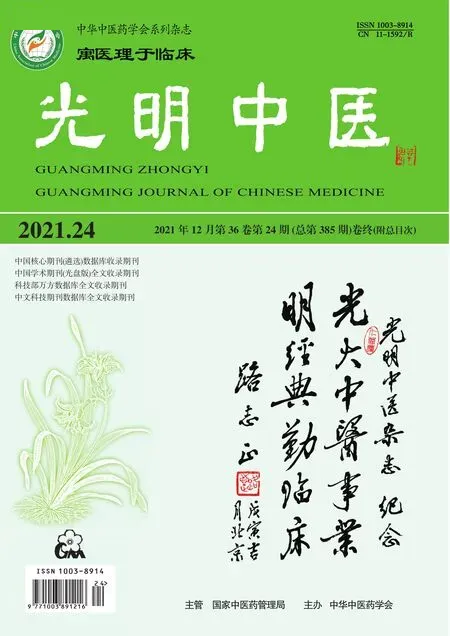論氣指稱事態時序性處理方式的預設和途徑*
嚴名揚 黃 悅 謝明坤 郝振芬 唐臻一 王 寧
筆者深信,表現在中國古典學說里的中國文化精髓正是這種“秩序和進步”[1]。如果“進步”是指在各具體學科或領域中,組織秩序的形式優化和現實合理;那么,可以這樣認為,中國文化的精髓始終聚焦于對“秩序”的考察。正如《國語·周語》:“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秩序作為事態發生過程的體驗內容的組織形式,是內容,也是形式。如果以事態把握在意識活動過程中的體驗流的形式來限定“秩序”;那么對秩序的關注產生的認知視野的轉換將進入一個新的話語體系[2]。如此假設:傳統哲理的中醫藥術語“氣”指稱“事態時序性處理方式”,簡稱“序式”。此對秩序的強調區別于現象學對秩序的先驗意向性分析[3]和“論秩序”[4]。
1 氣指稱事態時序性形式考察的預設
通過對中醫“氣”語詞指稱的概念性和時序性事態對象化的分析,“氣”作為時序性事態的把握、組織形式,并以此形成客體對象被初步證實;且中醫一般術語與思辨形式在以復雜事態時序性把握的形式中構建中醫藥所面對此客體對象認知的存在實體,即形成語詞的指稱對象[5,6]。為進一步在此事態時序性處理方式的視角下探討氣一元論思維中的一般性術語實踐與語詞命題,相關的預備考察擬先從該視角的預設和背景展開。
1.1 預設的背景伴隨文明交融的“西學東漸”,由近代新文化運動發端,秉持徹底訣別于傳統的“初心”而開展的白話文等運動使得現代漢語在語言學上更趨于西方現代性的話語表達形式,以實現語言表達式的邏輯合理性與科學精確性[7,8]。于此,漢語言中諸如“意會與言傳”“指事會意象形”等形式屬性,在嚴格的概念定義后分離,形成益于思想把握、表述、交流、傳播的實體;但隨之而來的還有因語言現代性的表達式使漢字符號化,排斥、懸置或忽略了漢字詞本身所具有的意指方式和漢語言所承載的傳統哲理,導致因諸如玄思、謬誤、詭辯而生的誤解與迷失[9]——因具體范疇內的客體無法通過否定自身而訣別范疇;即使這種使客體消亡的訣別實現了,也只是他域中形成不同的新客體而已,原客體還在原范疇之中[6];就如“經歷了5000多年的艱難困苦,中國依舊在這兒”[10]一樣。
在此,我們不去討論帶有具體時代特點和歷史使命的“新文化運動”所采取各式文化運動的現實意義,而只是將其作為我們即將深入的領域及針對現代性問題所采取的探索性工作的部分背景。歷史的發展使得每個時代均具有其獨特的現代性,一種歷史屬性與現實環境交織的現代性問題,使處于現代性之中的每個獨立個體必須理性面對。
一定程度上,對于現實中的個體使用現代性的話語體系試圖述說傳統哲理的形式與內容,尤其是對中醫理論體系進行邏輯的、現代性的科學探討,以此證明某種基于文化的根基性存在,并在現實中實現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合法性是極具挑戰的任務。為實施這些目標,基于現有認知體系的新境界企圖被展現,以期在現代漢語背景下進行傳統哲理在具體的同一論域中有意義的分析。
1.2 預設的內容事態時序性形式,或秩序的形式(以下簡稱“序式”)的處理方式以對事態把握所表達的順序、秩序的序列方向性形式為考察的客體對象,并在感知的初始階段參與意識內容的實現[11],使體驗內容的質料通過序列性排列組合而映射、抽象成為知識與智慧。“氣—序式”這種基于漢語言表達的事態認知方式的本質考察在自身的反思中具有自明性與確定性[5]。當然這種標新立異的客體設置不是自圓其說的泛泛而談,也不是簡單地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戲;而是在邏輯的合理性中尋求一般性的出發點,并以中醫藥為理論實踐的載體,在數理的普遍性中構建傳統哲理的話語體系。
而在開展“序式”的考察之前,對即將進入的領域進行一些準備性工作是必需的。我們擬從2個預設出發,以此構建該領域的可能輪廓,并借這些預設展開所要述說的內容。2個預設如下。①意識所及皆有序,有序均有方向性。②事物的序式考察具有類域中的形式和論域中的內容2個相互聯系、對立統一的方面。
這些預設不僅僅只是關于寫作敘述的技術處理,還是規范客體、展開話題的前提。這些預設的推理有的隨著本文的敘述間或明了,有的將一直以預設存在而有待后文論述。在預設論證后,預設本身就成為結論,但我們要避免以預設來論證結論的文字游戲。任何對此2個預設的證偽是消除“先入為主”,達到某種區別于個體意識中既有經驗的先驗性范式,觸及序式考察內容的必然步驟。
2 氣——序式考察的途徑
如果“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第一性的,物質決定意識”[12,13];那么物質是意識永遠無法完全把握而處于超驗的位置上,與菩薩、神、上帝一樣的信仰對象并列。超驗性的“物質”與信仰對象一個主要區別在于,兩者在意識的體驗把握中,對物質的認識是可以被構建、質疑而具有科學邏輯性,而后者是無可置疑的永恒[4]。
意識方向有序性的本質根植于物質和意識關系的第一、第二性的順序形式中。第二性的意識必然指向地反映第一性的物質,具體的意識內容所意指的事實必然體現于對物質把握的客觀存在中;客觀存在的物質決定主觀實在的意識活動所具有的第一、第二性秩序,使得對該有序的指向性進行話語表達必然存在秩序的形式,即序式。
故可以推理出預設①,意識都是有方向性的,也就是具有指向性。意識的指向性具有意識內容在形式上的秩序、順序;無論承載此指向性的意向行為的內容是什么,意向行為的形式方向性具有承載物質決定意識的客觀存在。如果語言是意識的表達,語詞表達是意識活動的描述形式;那么語詞表達不僅具有意義指向性,而且表達行為本身的形式也具有指向的有序性。所以,意識所及皆有序,不僅意識內容是有序的,而且意識形式必然有序。
2.1 序式作為先驗秩序的形式思想的本質,即邏輯,表現著一種秩序,世界的先驗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種種可能性的秩序。它先于一切經驗,必定貫穿一切經驗[14]。作為實際情況的事實是諸基本事態的存在;而諸存在著的基本事態的總和就是世界。基本事態是諸對象(物件、物)的結合;在基本事態中諸對象猶如一條鏈子的諸環節一樣彼此套在一起。在命題中事實的邏輯圖像,即思想——以感官可以知覺的方式得到表達[15]。
2.1.1 連續序列形式的對象化連續序列在因果關系中是一種必然性的連續序列。一切范疇都是行動的方式,通過它們,對象本身才被我們產生出來。如果可以判定X是Y的原因,這就意味著:產生于兩者之間的連續序列并非只是產生于個體的思想之內,而且產生于對象本身之內——主體間性的設立基礎之一。因此,這里不僅有一種一般的連續序列,而且有一種作為對象本身的存在條件的連續序列。連續序列對我們必然表現為和現象不可分離,就像這些現象表現為和連續序列不可分離一樣。所以,是連續序列維系于事物,還是事物維系于連續序列,對經驗都有同樣的結果[16]。
就實體來說,它是被固定的時間本身;因為對于我們來說時間固定下來,實體就會產生,反之亦然——此被固定的時間是以秩序的形式而論的。如果在時間中也存在著一種前后連續的序列,實體本身就必定又是時間里的常住性東西。此作為抽象類的實體在先驗唯心論體系中既不能產生,也不能消滅。因為當某物消滅時,本身必定會遺留某種常住性東西,那一消滅的階段就會由這種東西固定下來。因此,消滅的并不是常住性東西本身,不是事物(于語詞表達中的事態)與連續序列彼此維系的形式,而只是常住性東西的一種規定——實體被定義的一種規定[16]。而在現象學的直觀表象中,直觀充盈的一個不同尺度(規定)的說法指明了可能的充實序列;以此序列更好地認識和完整地把握對象[17]。
常住性東西的本質來源于連續序列的某種形式,這些形式以確定的規定確認實體,并通過語詞表達出來。消滅的規定被新的規定填充,連續序列對事物的維系形式不變。當我們以此連續序列形式為考察對象時,就要求體驗內容置身于現象流和體驗流的序列之中,在語詞表達的事態考察過程中通過因果關系等交互作用,固定此指向的連續序列形式的實體。
實際情況下,對事態的考察必然處于時間性的秩序和跨范疇排序的空間性(內時間性)中,也就是時序性中。可以這樣認為,“世界的先驗秩序”在構成世界的事實或作為實際情況而存在的諸基本事態中,以事態的時序性形式——作為客體的“序式”——呈現時間和空間的連續性;對此客體的存在形式與內容等方面的探討構成本領域的研究課題。
2.1.2 秩序的形式合理性要求序式作為先驗秩序的形式以物質的第一性為基礎。意識活動的思維過程使得對物質認識的能動性在邏輯形式上具有區別于意識體驗的先驗性,一種客觀存在——尤其是在意識活動所示的意向行為在對象化的客體形式中表現出的先于經驗的客觀性存在——以物質與意識的辯證關系優先強調物質決定意識的先驗性。序式作為先驗秩序的形式需關切辯證唯物主義觀,以避免時序考察的物質成為先天賦予的“神的啟示”或意識于腦海中創造的心靈認識。以序式為對象的考察是以物質的客觀存在為出發點,面對意識活動而進行的意向行為的事態序列性考察。
序式的先驗性是對物質決定意識、物質的客觀存在性先于意識的經驗性而言;因為對于辯證唯物主義者而言,總需要確定的途徑、方式來對辯證唯物論的物質第一性進行具體的話語表達。如果認為所有的話語表達都是意識活動而無關乎物質,那么唯心的認知方式如何把握客觀存在的物質呢?這就關乎哲學道路選擇的問題——但有一點應該確定,不同道路所提供的方法論體系在實踐中都專注于現代性問題的解決。
而中醫藥理論的現代性話語表達為此提供了良好的實踐領域;并在此基礎上,對傳統哲理應用下的中醫藥學進行邏輯明晰的科學探索,和在意識活動的考察端進行理性的反思是富有現實價值的,這兩方面在哲學的話語表達中是統一的。序式作為先驗秩序的形式肯定了意識活動在感官的體驗層面所具有的時序性本質。經驗、感知、體驗等意識活動自覺或不自覺地置身于秩序之中;對此秩序的關注表現為對此秩序形式的抽象、概括,而不僅僅只是意識活動本身所意指的內容。
2.2 序式作為實體的內容與形式時序性事態形式的對象化是以事態考察中客觀存在的序列表達形式構建實體,并且通過可能的漢語詞——某“氣”——達到意義的實現[5,6]。事態把握所擁有的時序性形式構建的實體,具有辯證關系的形式和內容兩部分;且內容具有雙重形式,形式具有雙重意義,兩者是對立的統一[18]。
2.2.1 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在話語表達和語詞實現的具體論域中,事態序式考察具有對論域內對象進行話語表達的兩層次描述:內容的形式和形式的內容[19]。對序式-實體的形式和內容的描述遵循如下原則:①有形式必有內容,有內容必有形式,形式和內容相互體現對方的存在。②無組織形式的內容是無法被認識的,無內容的形式是未曾被把握的。③形式和內容的指向是一致的,它們體現對客體(事態)的意向性目的之統一。④由前三點可推出形式和內容在實踐中互為根據、互為意義載體。⑤形式與內容在具體論域中具有對立性:話語表達的語詞具有概括性和模糊性[20,21],所以在學科中的術語需要概念性的準確定義來限定語詞表達的意義,表現出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的辯證關系。復雜形式中的內容表述越簡單、意義越明確;概括性越強的簡單形式的內容表述越繁雜——這是指就被限定的具體論域而言的,因為界定的具體論域由形式與內容所充實——在具體論域被限定的空間中,形式與內容必然存在“厚此薄彼”的對立性。⑥形式與內容還可以角色轉化:以形式為對象進行考察,則“形式”作為客體對象化生上一層次的內容(關于形式的理論);以內容為對象進行考察,則“內容”作為客體對象化生出下一層級的形式(關于內容的理論)。
2.2.2 形式獨立于內容的外在存在形式和內容的意向性統一,在語詞表達的命題中根據話語敘述(言傳)所及的學科內容和自身的組織形式,達到現實世界的意義給予(意會)。正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所保持的沉默一樣;“只可言傳、不可意會”是不可理解的,是對語言的直接否定;即使是一般的肢體語言也是可以意會的。“只可意會、方能言傳”和“言傳之物必可意會”是意識活動通過語詞表達于命題的邏輯前提。
而對傳統哲理和中醫藥理論漢語詞的表達命題、術語的考察在事態的把握中要求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均具有邏輯合理性。一方面,漢語詞命題表述內容的邏輯合理性根植于自然科學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命題形式的邏輯合理性則不僅需在經典的一階邏輯中辨識命題“真假”,而且更需在諸如多值邏輯等廣闊的邏輯領域中構建其話語體系。
同時,形式在上述原則⑥中具有雙重意義,形式就之自身反映而言,也是內容;就不反映自身而言,形式是和內容不相干的外在存在。在事態感知質料的時序性處理方式中,序式考察以感知內容、現象于語詞的表達中回歸于內容,并與所反映的內容形成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而此過程中,體驗質料或現象在意義給予和語詞表達中所必然具有的秩序的形式可應客體化而抽象為對象。
3 氣——序式作為客體被考察的應用
以傳統哲理為背景,試圖利用哲學——馬列哲學、語言哲學和現象學等——的方法探討“一元論”的氣指稱事態秩序性形式的現代性途徑,需在科學和數理等方面開展具體研究的應用。
3.1 序式考察在語詞表達中的命題形式如果懸置體驗質料或現象在意義給予和語詞表達中的內容,而對意義給予和語詞表達的形式進行邏輯分析;那么面對話語表述中的各個語詞命題的邏輯形式就自然地充實于某種秩序之中。氣也正是以對一般性術語和漢語詞命題所反映的事態性序式考察構建“一元論”地位與作用。例如:命題③苔黃有熱;④諸風掉眩皆屬于肝;⑤該病癥所辨證型是太陽中風表虛證;⑥半夏瀉心湯辛開苦降主治寒熱互結之痞證。當在具體的事態考察中,以上述命題表達話語內容時,我們所意指的對象在某種序式的事態考察中完成了語詞意義的實現。但這種意指形式的途徑和方法需要在現代性背景下,實現意指形式的一般性敘述。即使是形式體系的復雜構建,對語詞表達中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性和確定性是明確語詞命題所指客體的基礎。如果在體驗內容對象化的過程中,考察事態的客體缺乏確定性;那么事態把握的語詞命題就表現出意義的不確定,這種不確定的意義就是沒有意義,是意指內容與形式分離所致的“不可理解”。
在此,還必須面對臨床診治中存在的同一病證可以從痰、從濕論治,也可從臟腑、經絡等方面論治,一證多方[22],以及遣方用藥也迥然有異所反映的“客體”不確定性。中醫藥要想被世界認可走向科學前沿,融入主流醫學體系,必須走標準規范的道路[23]。當然,如果所辨病證不是抽象的客體、不是對象化的載體,本學科本身不需要客體的確定性和語詞意義的準確性;那么如何建立所辨病證的語詞表述合法性呢?這將是事態序式考察解決現代性問題的另一方面工作。
3.2 流變客體的對象化解析命題③由2個層次的句法結構構成,第一層次:“苔黃”——舌苔的顏色是黃色——是描述性的客觀事態的反映,觀察客體是自然物舌苔,對象論域是顏色,內容是黃色;第二層次:“苔黃有熱”——黃色舌苔說明存在“熱”——是評價性的事態表述,觀察客體為自然物的人體,對象論域是病癥,內容是有熱。同理,命題④、⑤、⑥也可以在句式的語法結構中呈現出多級層次的事態性表達;這些事態性表述的形式在本文主旨認識觀下,以事態時序性的形式對象化而形成一個連續的客體流——某種客觀存在的合法性原則使得此客體流成為對象、成為客體——如果可能,這類以流變客體在客觀性事態序列性形式考察方式的語詞意義,被賦予語詞“序式”或者“氣”。
從簡單的命題③的句法結構性分析可見,在漢語詞表達的意會特點中,漢語詞命題在語法層次中以語境的轉移使得話語所表達的內容、論域、對象等發生變化。但語詞表達的命題形式和事態表述所具有的一般性原理是普遍性的,即以根基性地面對自然物感知、體驗獲取的第一層次內容是基于自然科學一般性現象、規律的直接呈現。“舌苔是黃色”的事態C客觀存在,此事態指向事實,這是由感知內容中體驗質料的根基性決定的。但對第二層次中“事態C有熱”的事態D是否指向事實呢?則要求在以事態C為對象的觀念化作用下的原信念意義給予途徑具有普遍的邏輯合理性,如此需要回到第一層次中對“熱”進行分析,并且這種分析是在暫時懸置原信念的情況下進行的,以此打破玄思和自我證明,建立原信念的根基性。
當然,在計算語言系統設置中,也可以在限定的語境中對事態C直接賦值為“有熱”,但此技術性處理還是需要更基礎的論證以表明該話語體系的合理性。如以“寒”為賦值的話語表達存在“寒熱”二類域中的邏輯值、“寒熱溫涼”四類域邏輯值、“風寒暑濕燥火”六類域邏輯值等范疇中論述的意義差異性。
3.3 語詞命題的序式考察對命題③語詞元素在第一層面進行反思,就可將語詞表達式直接推向以漢字詞為對象的研究領域;它至少包括以下兩方面:以漢字為對象的語言學領域,和初始體驗質料在明確認知內容和意義給予等認知方式的哲學領域。這些領域的探討存在著各種邏輯可能,并在不同的邏輯形式和方法論中成為不同分支學科的研究內容;而其中采用事態時序性處理方式的考察是本課題選擇的方向。
在復雜事態的復合型命題中,存在一種自覺的反思以背景的形式隱于語詞表達的內容和語法合理性之后。這種“自覺的反思”在對以文本或話語表達于外時,除卻語詞表達的意向目的以外,普遍性存在的對文本形式的評價、描述、判斷的內容將此種反思從背景中顯示出來,可語詞表達為“氣郁而熱”“氣行不暢”“氣勢如虹”“營衛不和”等關于就事態形式性把握的表述——這些也都是關于“氣”的、關于“序式”的呈現。
如對復雜事態的復合命題④“諸風掉眩皆屬于肝”進行分析。假設該命題的現代漢語言表述為“各種因風所致的掉眩癥狀都是由于肝臟的相關病證所致”——先排除病癥與癥狀間的自我證明,即懸置語詞內容;那么命題④針對的根基性是“掉眩”這個客觀事態E,它的二級命題是“此事態E由風所致”的事態F,三級命題是“各種事態F都是由于肝臟的相關病證所致”的事態G。對復雜事態命題④各語詞單元的考察在不同的層級命題中因考察論域、對象與內容的不同,使得此流變形式的客體需要一個整體把握的序式處理方式來建立該復合命題語詞表達的合理性和意義的同一性。對命題④諸語詞元素關系的表達式,不僅僅是簡單的集合⑦,而是類似表達式⑧那樣。
⑦{風,掉眩,肝}
{{掉眩}∩{風}}?{肝}或{{掉眩}∪{風}}?{肝}
正如命題④諸語詞元素所形成的對象類——表達式⑧中各個語詞元素所形成的意義集合——在序式考察中以某種類域間的交互產生關系,進而在復合命題④的目的同一性中建立基于某種邏輯形式的數理模型。而對于命題⑤、⑥等更復雜的命題形式也可以利用類域的交互進行序式考察。復雜事態在語詞表達中的復合命題的序式考察需在以預設②的論證中涉及。
而對命題④的序式考察所展現的表達式⑧是對命題內容懸置后的形式抽象;這種對漢語詞命題所指事態的考察方式在中醫理論體系中,只有“氣”的形式定義才能提供命題中諸語詞元素所表達內容集合類之間的聯系和意義交互——是 “氣”使“風、掉眩、肝”等集合元素間產生關聯,并且這種形式關聯在不同的語境中被賦予推動、溫煦、統攝等功能屬性。對形式的抽象使得類似表達式⑧的表達形式可以獨立于語詞內容,并被“病機十九條”的各內容填充。對此過程的再次反思和抽象,懸置具體表達內容的表達形式成為“氣”作為實體存在的對象,并且原表達式成為“氣”的內容。如此,形成不同層級的對象化的氣,在不同復雜程度的命題中維系該話語在事態性序式考察中的合法同一性。
4 總結
如果我們述說任意事情,那么一個針對任意確定性客體的事件就產生了,在具體的語境中就以語詞命題的形式形成一個事態,屬于客觀存在的事態考察被認定為事實。但理性提醒我們,不能如此輕率地接受這使用簡單語言描述的序式對象,相關的探討需要學術群體的廣泛參與,直至有效地證偽。
在“氣”一元論的臨床實踐范疇中,科學技術與社會人文不是因學科組織秩序的內容而機械分離的;其中對學科處理事態秩序的強調和重視,使得以秩序的形式(氣)為考察對象相較于對專注于秩序的內容(分子機制、代謝規律等)的研究同樣能提供可探索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