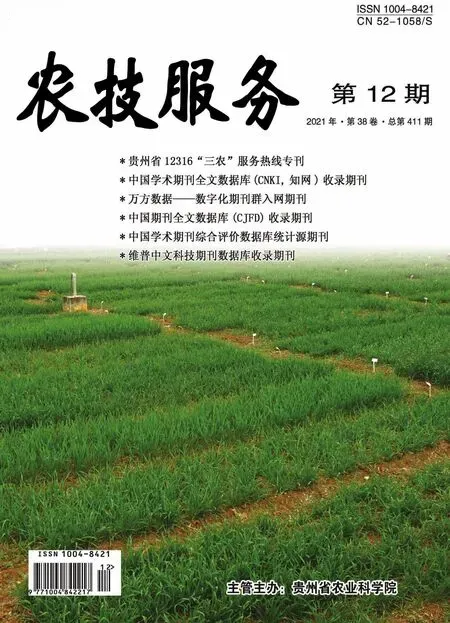農民養老意識的培養意義及特征
邵寶文
(山東華宇工學院 創新創業學院, 山東 德州 253034)
我國為人口大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億人,占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億人,占13.50%[1],體現出我國的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深。隨著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廣大農村年輕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和遷出,使農村人口結構發生變化;《2020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指出,我國鄉村60周歲及以上、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鄉村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23.81%和17.72%[2],農村人口老齡化也同樣在加深。由于城鄉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農村相較于城市在養老、照料看護、醫療等方面資源的不足[3],使農村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更加突出。對此,一方面我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在不斷健全與完善,以適應農村老齡化的現實需求;另一方面,伴隨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帶來農村勞動力遷移、經濟結構、家庭權力結構的變遷,也使農民的養老意識發生顯著變化[4]。養老意識包含個體對養老行為所持有的看法及態度,也是其養老需求的內在體現,對其養老行為的決策,如養老模式的選擇產生影響[5]。因此,研究農村居民的養老意識,對于從養老主體對象的角度進行相應的養老制度安排和模式設計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對培養農民養老意識的意義及農民養老意識的特征進行分析,以期為增強我國農民養老意識,更好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提供決策參考。
1 農民養老意識培養的意義
1.1 促進年輕農民積累養老資源,保障老年生活質量
農民養老資源是指一切可用來作為其養老的經濟資源和精神資源,主要包括贍養人資源、經濟資源、住所資源、健康資源等其他資源[6]。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城鄉差距進一步縮小,一直在農村的農民和進城農民工均有了相對以前更為充裕的養老資源,但由于其本人擁有的社會資源、個人收入差異、生活方式行為不同,養老資源的個體差異較大[6]。同時,相較于城市退休老人而言,我國農民比較缺乏養老資源,特別是隨著大量農村青壯年進城,導致傳統的家庭養老面臨人力緊缺或因養育下一代擠占養老資源等現象出現。對此,需要通過培養較強的養老意識,促進年輕農民在精力充沛和身體健康的年齡階段,根據自身的養老觀念和認識及現有的養老資源狀況,合理規劃自己進入老年后的生活,預先針對性積累自己缺少的養老資源,堅持健康生活方式,維系好子女關系,為養老打好基礎,以保障老年生活質量。
1.2 有助于形成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孝養文化
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的價值觀出現多元化,農業現代化導致傳統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逐漸走向解體,較多80后、90后年輕人走出村莊到城市發展,選擇回鄉發展的多數是已在城市生活多年、即將步入老年的70后、60后,傳統“孝道”文化已無法適應高速發展的現代農村經濟,現代化社會的發展削弱了傳統的“家文化”“孝文化”“父母在,不遠游”類的傳統孝文化已不適應當代社會的發展,僅靠“孝道”等道德觀念已難以約束子女的“孝”行為。因此,需要從農民個人的實際出發,結合個體差異,積極培育農民的養老意識,推進其樹立較強養老意識,更好發揮個人主觀能動性,更明確自己的需求和家庭的相處模式,做好個人規劃,妥善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以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巨大變化,并有助于形成新的孝養文化。
2 農民養老意識的特征
2.1 養老意識多元化
由于農村勞動力遷移、經濟結構、家庭權力結構的變遷,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出現弱化,迫使農民選擇傳統家庭養老之外的養老方式,傳統社會“養兒防老”的觀念已出現轉變,其養老意識和意愿因現實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化[4],進而使農民對養老責任主體的認識發生較大變化,養老責任主體出現多元化發展趨勢[5]。
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家庭結構小型化以及經濟的發展,催生了農民的自我養老意識,使其在養老上既不靠子女和親屬(或無依無靠),而主要靠儲蓄或勞動收入或其他收入(如租金、股金)維持生計[5]。同時,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化元素和社會養老保險事業進入農村,如“新農保”的全面推廣和商業保險的興起,為農民選擇養老方式提供了更多選擇[4]。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盡管水平還比較低,但作為一種正式的策略安排,已經被農民所接受[7]。
農村老人在其家庭權力結構中的地位變化,特別是其家庭權力的減弱,導致其養老意識發生變化,從家庭養老意識逐步向自我養老意識和機構養老意識轉變[5]。機構養老是通過各種福利院和敬老院獲得專門為老年人提供護理、食宿、照料的養老模式。該模式能減輕年輕人照顧老人的壓力,緩解家務勞動所帶來的各種矛盾,使老人得到較為集中的照顧和有秩序的生活[5]。
2.2 家庭養老是主要的養老模式選擇
雖然農民的養老意識呈現多元化,但家庭養老目前仍是我國農民養老的主要方式。傳統的家庭養老,是指以血緣為紐帶,由家族成員對上一輩老人提供衣、食、住、行、醫直至死亡送葬等一系列社會服務行為[5]。盡管家庭規模縮小、代際分離加大,弱化了家庭養老功能,但由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長期缺位和農民獨立養老能力較低[7],農民對養老風險的擔心主要來自對家庭資源以及未來保障的考慮[4],加之其養老資源主要依靠家庭提供,特別是其在養老需求上對子女的期望最大,而對政府和法律保障的期望較低[7],因此,家庭保障在養老意識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使其仍傾向于選擇家庭養老。另外,家庭能夠給予老人精神慰藉這一重要效用,使家庭養老具有一種特殊的文化和情感特征,具有一定的穩定性[7]。
2.3 養老意識的代際差異顯著
農民養老意識的代際差異來源于其所處年齡階段的個體需求不同。對于未到養老期的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農民,經濟條件是未來滿足其老年時期基本生活的重要保障,因而其最擔心經濟保障問題[7]。正處于養老期的50年代出生的農民,生活自理能力逐漸下降,子女外出務工導致生活無人照料,因此其最關注生活照料問題。60年代出生的農民即將進入養老期,經濟保障可通過自己、子女和制度共同解決,農村養老服務體系的發展也為解決生活照料提供了安全預期,更關注子女兒孫陪伴的精神慰藉,情感因素對其養老意識具有一定影響。
基于上述原因,農民養老意識的代際差異在其養老策略上得以體現。70后、80后作為改革開放下成長發展的一代,其成長經歷明確使其認識到養老較難依靠兒女,因而在養老上大多對子女無依賴心理,對政府養老和法律保障的期望較大,對機構養老也比較認同,其社會養老意識明顯。另外,從變化趨勢上看,5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農民對子女養老的期望呈逐年下降趨勢,自我養老的比例呈增加趨勢,養老觀念從“依賴養老”向“獨立養老”轉變[7]。
3 結語
先進的養老理念是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和老年人實現自我價值的關鍵。為此,需要培養農民的養老意識,使其對于養老的認識和觀念既不盲目樂觀也不杞人憂天,能夠正確了解自己的養老需求,積累所需的養老資源并培養個人應對養老的能力。
不同年代農民的生存環境、養老資源及養老觀念均有很大差異,從而影響農民對養老風險的判斷,以及養老策略與期望[7]。人力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等養老資源的稟賦水平,影響農民的養老意識,對其養老責任主體和模式的選擇也產生影響[4]。因此,需要最大限度地發掘、優化、利用養老資源,在增加對農村地區養老保障資源投入、擴大農村養老資源供給主體的同時,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保證就業和增加農民收入,增強農民的自我養老能力,推進建立能最大限度滿足農村居民需求的養老保障體系,由個體到整體逐步解決“未富先老”困境,爭取“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