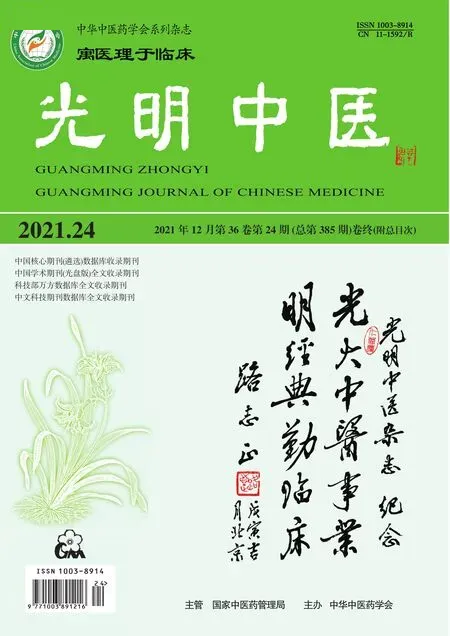仲景見病知源指導下失眠治驗的回顧*
王冠雄 胡鑫才 張光榮
失眠是指即使有合適的睡眠機會與良好的睡眠環境,但對睡眠的時間和(或)睡眠的質量仍感覺不滿意,且明顯影響到日間生活的一種主觀感受[1]。根據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慢性失眠癥的患病率在6%~30%。我國普通成年人群中失眠的患病率在9.2%~11.2%[2,3]。因此探究對失眠的治療顯得極為重要。中醫學自古對失眠已有論述,且因其治療形式靈活、方法多樣,效果穩定,不良作用小而被廣大患者接受。在張仲景“見病知源”理念的指導下,踐行“讀經典,做臨床”的學習方法,始終將經典指導臨床貫徹于實踐。通過運用所學治療1例較復雜的失眠病例取得了較好療效。現對驗案的臨證思路和方法及歷代醫家對失眠的認識進行回顧,以就正于同道。
1 中醫學對失眠的認識
1.1 病名的沿革失眠,在中醫內科學中稱之為“不寐”。《難經》最早提出“不寐”這一病名,《難經·四十六難》載:“老人臥而不寐……血氣衰,肌肉不滑,榮衛之道澀, 故晝日不能精, 夜不得寐也”。有學者考證[4],在現存醫學文獻中,有關此類病證的最早記載見于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和《陰陽十一脈灸經》,始將本證稱為不臥、不得臥和不能臥。縱觀中醫學的發展歷程,不同的醫家和著作對不寐的病名認識不完全相同,主要有:目不瞑、不得眠、不得臥、不能臥、不眠、臥起不安、起臥不安、臥不能安、不得臥寐、不得睡、眠寐不安、寢臥不安、睡臥不安、臥不安席等。并有醫家已將“不寐”列為獨立疾病,如明代龔廷賢《萬病回春·卷之四》列“不寐”。
1.2 對失眠病因病機的認識
1.2.1 古代醫家的認識《靈樞·邪客》有:“今厥氣客于五藏六府……陽氣盛則陽蹺盛,不得入于陰,陰虛故目不瞑”。在漢代張仲景的《傷寒論》中有關失眠的病因涉及到外感內傷兩類,如內傷中提出“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外感中有《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發汗吐下后,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復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的論述。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膽虛實第二》中認為,溫膽湯(半夏、竹茹、枳實各二兩,橘皮三兩,甘草一兩,生姜四兩)治大病后虛煩不得眠,屬膽寒者。宋代許叔微在《普濟本事方》中有云:“平人肝不受邪,故臥則魂歸于肝,神靜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歸,是以臥則魂揚若離體也”。認為邪氣內擾于肝,則血不能歸藏于肝以養人之神魂,所以出現不寐的情況。明代張景岳在《景岳全書·雜證謨·不寐》提出“不寐證雖病有不一,然惟知邪正二字則盡之矣……一由邪氣之擾,一由營氣之不足耳”。更有明代李中梓《醫宗必讀》提出了不寐有氣虛、陰虛血少、痰滯、水停、胃不和等并給出了對應的治療方藥。清代《馮氏錦囊·卷十二》指出“壯年人腎陰強盛,則睡沉熟而長,老年人陰氣衰弱,則睡輕微易知”。總之,古代醫家認為不寐的病機總屬陽盛陰衰,陰陽不交。并將不寐分為虛實兩大類,實者多見肝火、痰熱、瘀血等;虛者多見肝、心等血虛所致的虛煩不得眠,以及熱病后期所致的膽寒不得眠[5]。
1.2.2 現代醫家的認識周仲瑛[5]認為失眠多因飲食不節、情志失常、勞逸失調及病后體虛所致心肝脾腎的陰陽失調,氣血失和。徐云生[6]總結鄧鐵濤治療失眠的經驗,認為失眠病位則以心肝膽脾胃為主,總的病機是陽盛陰衰、陰陽不交。肖相如認為產生失眠的根本原因是“日出不作,日入不息”“心不靜而體不動”,頑固性失眠病機的根本在于陽不入陰,腎虛不藏[7]。《中醫內科學》[8]將不寐的證治分為肝火擾心證、痰熱擾心證、心脾兩虛證、心腎不交證和心膽氣虛證, 分別治以疏肝瀉火、鎮心安神, 清化痰熱、和中安神,補益心脾、養心安神,滋陰降火、交通心腎,益氣鎮驚、安神定志。有醫家從五臟論治失眠[9],治療上可以根據五臟藏神的特點,對癥用藥,重點應調整臟腑氣血陰陽、輔加以鎮靜安神可以取得更好的治療效果。綜上可知,現代醫家認為不寐的產生是以各種內傷因素導致的陰陽不交為基本病機,五臟氣血陰陽失和為特點。
2 見病知源初探
在《傷寒論》原序中有言:“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說明仲景著述的目的并不是把所有疾病的具體治療寫出來,而是想通過著述來告訴后世醫者治病的一般原則和方法,以期達到“見病知源”的目的。如果能夠“見病知源”,即使有些疾病暫時不能治療,也知道尋找治療方法的方向在哪里。仲景臨證注重四診合參,審證求因,故能夠做到見病知源而后治之。其撰寫的《傷寒論》更是深刻體現其臨證理念,如《傷寒論》第16條所云:“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針,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之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雖然仲景此段文字的本意是提出對誤治、逆治的處理原則,但縱觀《傷寒論》全篇,無不體現“脈-證”合參的辨證思維和方法,如書中敘述的“辨病脈證并治法”,主要是講先通過辨脈和臨床證據來認識疾病,而后言治法。其治療疾病的過程是對“病位”“病因”“病機”“病勢”等辨識并鑒別之后再言診斷和治療。因此,原文雖源于誤治逆治,但其指導意義不止于此。此條文突出了“疾病是一個變化的過程”這一生命自然規律,確立了辨證論治的原則。書中提出的六經辨證不僅要求對“病之源”所屬的陰陽表里寒熱虛實有清晰的認識——這是“見病知源” 的重要環節,同時也要對疾病的來龍去脈有清晰的把握。這樣才能在中醫治病“因勢利導”的大前提下,給邪氣以出路,找到疾病痊愈的途徑。“源”一旦出錯,則萬慮皆失。當前現代醫學治療失眠主要采取鎮靜催眠等方法,此舉不僅毒副作用多而且停藥后易反復[10]。而中醫施治則采取調和陰陽、疏肝養心、解郁安神等法,顯現出療效穩定、毒副作用少等優勢。然固守證型論治則屬刻舟求劍而療效不高,認識疾病的來龍去脈方可取得預期的效果。
3 失眠驗案
患者,女,65歲,家庭主婦,于2018年8月15日以“失眠3個月余,消瘦2個月余”為主訴就診。自訴1年前因一次感冒發熱后開始出現胃腸功能異常,主要表現為食欲減退,納后腹部痞滿,后經西醫靜脈點滴用藥等治療(具體不詳)后癥狀略有減輕,但效果不佳。近半年來體質量下降5 kg余,其中近2個月來下降3 kg余。偶眼癢,面部、背部偶有發麻感。3周前不明原因胸痛,現已自行消除。2周前偶有心悸,自服西洋參數次后癥狀消失。咽喉部偶感有物梗阻,吞咽無異常;平素血壓偏低[最近一次90/60 mm Hg(1 mm Hg≈0.133 kPa)],目前血壓在正常水平;平時心事重而容易影響夜間睡眠。現病史:近3個月來因心煩而致睡眠差(大致過程:晚上22點左右睡——凌晨1~2點醒——早晨5點勉強入睡——5點半左右起床——上午10點前后疲乏欲睡——晚上22點左右睡);記憶力減退;吹風扇和冷空調則易引發咳嗽伴流眼淚,每咳久方有少量清稀痰,咳嗽可自行緩解。無畏寒;平素出汗少,出汗不均,主要在頭胸背部,下肢無汗;無口干口苦,口淡、伴有較強饑餓感,洗漱口腔時欲嘔;納食不馨,但能勉強進食,進食量如常;喜熱飲,嗜食咸味;陰雨天降溫等氣候變化時頸背部、膝關節酸痛;大便成形,色褐,前硬后軟,每日1~2次,排便過程無不適;小便清,無夜尿。望診:面色黃,消瘦面容,稍顯憔悴;舌質淡紅,舌尖緣有少數黑瘀點,苔白底,中部左側微浮黃、右側及舌根部黑苔,舌下絡脈短細,不明顯,色偏淡。脈象:脈細弦不流利;左寸不受按,關較浮,尺略沉;右寸關略浮,尺略沉。2018年8月14日某市三甲西醫院電子胃鏡報告示:食管炎(霉菌性?);慢性萎縮性胃炎?。中醫診斷:不寐;咳嗽;虛勞?西醫診斷:失眠;體質量下降原因待查?(食管炎,霉菌性?慢性萎縮性胃炎?)。證候診斷:太陰(脾、肺)氣虛;少陽風飲郁熱,表里相兼;厥陰瘀熱。方擬防己黃芪湯合小柴胡湯加減。處方:漢防己12 g,生黃芪20 g,甘草9 g,白術9 g,柴胡15 g,黃芩9 g,黨參15 g,法半夏9 g,岷歸尾6 g,生姜3片,大棗4枚。5劑,常規方法水煎服。
9月18日二診:患者自述服藥后再吹風未引發咳嗽,食欲增強,上午疲乏欲睡大減,但夜間睡眠無明顯改善,且膝關節酸痛較明顯,其余情況大致同前。脈象:脈細弦;尺沉;左關略不受按;右脈略緩。舌相:舌淡紅略暗,舌尖有黑瘀點,苔淡黃,中后根部厚膩且有少許浮黑點。證候診斷:太陰(脾)氣虛;少陽風飲郁熱,里證兼表;厥陰瘀熱。方擬防己黃芪湯合小柴胡湯加減。用藥:漢防己12 g,生黃芪20 g,甘草9 g,白術9 g,柴胡9 g,黃芩9 g,黨參15 g,法半夏9 g,生姜3片,大棗4枚,丹參9 g,杜仲9 g。5劑,常規方法水煎服。
2019年3月2日三診:患者自述服藥后夜間睡眠略改善,但有時明顯胸口悶痛牽涉至后背正中,且食欲略減退。追問病史得知胸背痛發作之前曾食用雞湯和大骨湯。無咳嗽,大小便情況無變化。舌相:舌淡紅略暗,苔白,中后根略厚膩;黑苔消失。脈象:脈弦略細。2019年3月2日某市二甲中醫院腹部彩超示:膽囊炎。證候診斷:少陽兼厥陰氣郁;食濕內阻。方擬柴胡疏肝散加減。用藥:柴胡10 g,白芍15 g,枳實6 g,青皮10 g,香附10 g,炒麥芽15 g,延胡索10 g,厚樸10 g,炒雞內金6 g,炙甘草3 g。5劑,常規方法煎服。
半個月后電話隨訪,患者自述服完上5劑后癥狀改善明顯,但偶感胸口悶痛牽涉至后背遂自行去藥店購藥5劑服用。再回訪,患者無胸背痛,舌苔正常,體質量恢復,睡眠佳,精神狀態良好。
4 治療思路分析
該患者因睡眠障礙3個月就診,但其起病卻要追溯到1年前。3次就診的時間間隔較長,可以看出患者就醫意愿很低。尤其是第二、三診之間,患者的睡眠問題并沒有明顯改善,是因為胸背痛難以耐受而不得不再次就診。因此,在收集病情資料時要注意了解疾病的起始及發展過程。現對各診次的思路做一分析。
首診:患者因1年前外感發熱出現了食欲減退、飲食無味、嗜睡、疲乏等表現,一般這種屬于表證誤治導致中焦脾胃氣虛之象。從病史中患者咳嗽伴流淚、咳出清稀痰等癥可知有飲邪;其咳久方有少量白色清稀樣痰,說明飲邪不在肺胃,而在少陽焦膜。根據吹風后咳嗽出眼淚且結合脈象可診斷為表氣虛夾風飲,同時患者眼癢、面背發麻之感均屬風的表象。根據心煩不寐、洗漱時欲吐、有咽梗感等癥,結合飲食不馨、精神倦怠,即如“心煩喜嘔,默默不欲飲食”,從患者突出的癥狀可知其少陽病是表里相兼證,即少陽里證內有飲邪郁熱,少陽表證表有風飲。根據心煩失眠以及患者凌晨醒的時間(傷寒論第328條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舌尖瘀點以及脈弦不流利等可知厥陰有瘀熱。據姚梅齡教授臨證脈學[11],脈弦不流利也可提示飲邪,脈細提示氣虛,仲景亦有言“傷寒三日,少陽脈小”,左關較浮提示有少陽表證,右寸關略浮說明太陰少陽有表邪,兩尺略沉說明老年腎氣不足,第二診出現膝關節酸痛明顯進一步印證。舌苔見浮黃、黑苔說明內有火熱之邪。而心煩失眠這一主訴的病因不好確定,有以下3種可能:①由少陽病引起;②可能由厥陰瘀熱引起;③由前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總體來看,此患者雖有三處偏態(氣虛;少陽風飲郁熱,表里相兼;厥陰瘀熱),但這三者的輕重緩急不一樣。雖然患者目前最突出的癥狀為睡眠紊亂,但根據病史可知,患者的食欲差、體質量明顯下降等造成睡眠紊亂。因此追尋疾病的起病情況,認識其來龍去脈,而后按照“見病知源”理念和仲景辨治的一般先后順序:先表后里、先氣后血、先陽后陰,方可“因勢利導”獲得預期療效。故應首先治療太陰里虛和少陽病這2個證候,其次才是厥陰瘀熱。故第一次治療先擬用防己黃芪湯合小柴胡湯加減。防己黃芪湯功效益氣固表,健脾利水,主治表虛衛氣不固,風濕(水)傷于肌表,水濕郁于肌腠所致的風水。此處借用以治風飲,可祛患者已有之風飲,并益氣健脾,助患者恢復脾氣和衛氣,構建體表防御力,抵御外來寒風之邪。其中漢防己祛風利水,黃芪益氣固表,兼可利水,兩者相合,祛風除濕而不傷正,益氣固表而不戀邪,使風濕俱去,表虛得固;白術補氣健脾祛濕,既助防己除濕行水之功,又增黃芪益氣固表之力。小柴胡湯為和解少陽的代表方劑,既可祛表邪又可化痰飲、清里熱,同時補益中氣,可令其表里之邪均除,恢復正氣。其中柴胡苦平,入肝膽經,透泄少陽之邪,并能疏泄氣機之郁滯,使少陽在表之邪得以疏散;黃芩苦寒,清泄少陽里熱,柴胡之升散得黃芩之降泄,兩者配伍為和解少陽的基本結構;中焦痰飲上泛,胃失和降,以法半夏、生姜化飲降逆止嘔;岷歸尾性溫活血止痛力強,并可兼顧厥陰之瘀阻。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邪從太陽傳入少陽,緣于正氣本虛,故又佐以黨參益氣健脾;再佐入姜、棗,調和營衛;甘草和中,兼可調和諸藥。兩方并用,諸藥相伍,祛風化飲健脾與和解少陽并用,扶正與祛邪兼顧,使風飲俱去,樞機得利,食欲增強,疲乏欲睡大減。但首診治療只考慮解決疾病的源頭,針對失眠不會有大的改善。
二診:通過患者自述(受風不再咳嗽等)及舌脈診可知其表證已解,太陰病和少陽表證好轉,少陽里證未見明顯好轉,但腎氣略虛,遂加入補肝腎的杜仲,并將升散的柴胡減量,使柴胡和黃芩按1∶1入藥。同時考慮到第一診后患者睡眠沒有改善遂將性味偏溫的當歸尾換成既清血分熱又活血,味苦、性微寒的丹參,這樣可以避免藥物對失眠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因脾胃之氣的恢復尚需時日,故其余用藥暫時不變。此時病源已得處理,適當調整表里藥物的比例,另需兼顧血分瘀熱。故用藥后夜間睡眠略有改善。
三診:此次就診距離上診的時間較長,患者素有脾胃氣虛,后因飲食不節,出現了胸背痛、食欲略減的情況,結合彩超檢查考慮為“膽囊炎”。考慮患者是在經過前兩診的治療后,機體進入自我修復的過程,但少陽病尚有殘余之時,此時患者食用油膩之品,突然加重膽囊的負擔,故導致此病的發生。綜合前兩診的治療可以認為現在患者睡眠不佳主要是少陽厥陰氣分郁滯所致。根據舌象和神的變化可知厥陰之郁熱較為輕微。因此本次方擬用柴胡疏肝散加減以疏肝行氣,活血止痛,消食化濕。又可兼顧少陽膽經。方中取柴胡,入肝膽經,條達肝氣,透邪外出;白芍斂陰養血柔肝,與柴胡合用以補養肝血,條達肝氣,可使柴胡升散而無耗傷陰血之弊,為調肝常用組合;厚樸燥濕消痰,下氣除滿;此外方中陳皮、延胡索、枳實、香附可增強疏肝行氣、活血止痛之效。故服后肝膽條達,氣血通暢而痛止,營衛自和而寐安,諸癥亦除。
整個治療過程,首先要根據四診信息判斷患者的證候,即對其病因、病位、病機和病勢要有清晰的認識。然后遵循表證為先,病源為先的一般原則加以治療方可做到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取得理想的療效。以本病案為例,該患者雖以失眠為主訴來就診,但其體內疾病關系略微復雜。根據仲景“見病知源”等理念,先治療其源頭之證和在表之證,即太陰和少陽兩經的病證。姚梅齡教授曾強調表證與許多內科病證關系密切,而中焦脾胃是藥物進入人體發揮作用的一個關鍵中轉站。因此只有當表證已去且脾胃功能得到一定的恢復后,再進一步深入去治療少陽和厥陰的里證,方能獲得預期的效果。否則,若在首診就針對睡眠障礙治療,表證不解除、脾胃運化功能不能恢復,飲邪停滯,藥物很難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5 小結
本次治驗是讀經典、用經典的一次實踐。當代中醫科班出身的中青年大夫在治療內科疾病時,很多不會想到用傷寒方和溫病方,更少將解表法用于內科病初起及感受外邪引起急性發作者,以致臨床療效不理想。尋其原委,發現對于許多雜病是由外感病誤治失治所造成的,許多雜病的初起階段和急性發作階段往往是外邪犯表觸發的,等等諸如此類的理論與事實均不了解。此種現狀,不僅與經典著作學習得不深不透有關,同時和人為地將外感時病與內科雜病一定程度的割裂亦有關。這是沒有注意到仲景所說的“見病知源”,而更多的是去套證型的思維在誤導。中醫治病要經過辨證后方可“見病知源,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只有正確認識疾病,認識疾病最初的來源,分層次、按步驟治療,使機體“陰陽自和者,必自愈”,著眼于“以平為期”。例如此例患者雖以失眠為主訴來就診,但不能簡單地去治失眠這一內科病候。而應當根據四診信息進行辨證,分析出疾病的起源并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治療。所以最后的臨床療效滿意,患者機體恢復健康。通過這一次的臨床實踐,更深刻地理解了仲景《傷寒論》“見病知源”理念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