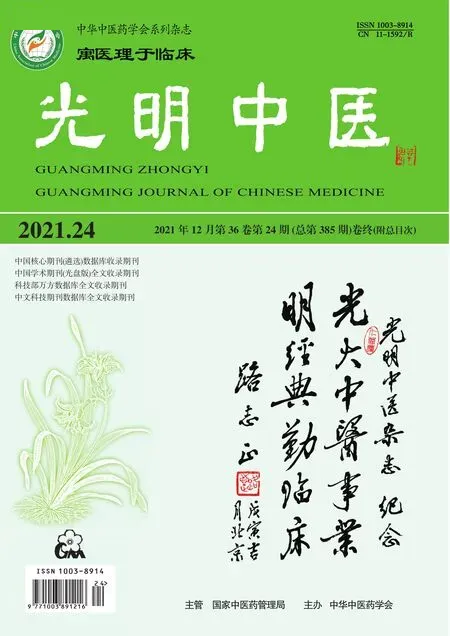中西醫治療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痰瘀互結型研究進展*
周雨姍 蘇士印
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中醫屬“胸痹”范疇,其臨床表現最早記載于《黃帝內經》,《靈樞·五邪》篇有:“邪在心,則病心痛”。其病因病機復雜多樣,西醫認為其病理生理基礎主要是冠狀動脈過度狹窄以及易損斑塊糜爛破裂所導致的急性血栓形成,伴或不伴有血管收縮和微血管栓塞,從而引起冠狀動脈血流減低和心肌缺血[1]。中醫視動脈粥樣硬化為“痰”,視血管栓塞和血流動力學改變為“瘀”,因此痰瘀互結型為ACS最常見的證型。ACS痰瘀互結型患者臨床上常表現為發作性胸痛、胸悶等,可引起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甚至導致猝死,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和壽命。在及時干預和有效治療的情況下,可極大地降低病死率,減少并發癥,改善患者預后。現將近年來對本病的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1 病因病機
1.1 中醫病因病機對于ACS的發病機制,中醫理論認為氣血陰陽的虧虛為發病基礎,夾雜著血瘀、痰濕和外感六淫等病邪,同時也會受到飲食不節、情志不調、年老體虛等因素的影響。對于中老年人而言,素體虧虛、氣血不足,致使血液運行不暢,從而形成血瘀,阻塞經脈血管而發病。機體陰津虧虛、經脈失養,心脈不榮則痛;素日疲勞、耗傷正氣,導致胸陽不足,外感六淫之邪乘虛而入,或陰占陽位,胸陽不足而痛;氣血運行不暢,導致心脈閉塞或攣急,經脈不通則痛;素日飲食不調、過食辛辣、酒肉油膩,導致脾胃虛弱、氣血運行失調,則痰濕內阻、夾雜血瘀阻滯經脈、痰瘀互結從而阻塞心脈則痛;情志不調、肝失條達疏泄,造成氣滯阻于心脈則痛。
首次提出“胸痹”名稱的人是漢代的張仲景,他在《金匱要略》中對該病進行了專門的論述,將其病因病機總結為“陽微陰弦”,即上焦陽氣不足,是為“陽微”,下焦陰寒氣盛,是為“陰弦”,認為此乃本虛標實之證。隋朝醫家對胸痹有了新的認識,巢元方于《諸病源候論》中提出,血脈壅熱,飲水結聚而不散則成痰。他認為“痰”為胸痹發病的重要因素。朱丹溪《丹溪心法》中提到,自郁成積,積而成痰,痰挾瘀血為患,而成窠囊。表明痰瘀互結是人體動脈中斑塊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
當代醫學研究在總結古代經典和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對ACS的病因病機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及研究。唐世球[2]認為胸痹的病因病機主要為氣陰兩虛。張翠英從熱、痰、瘀3方面探討了ACS熱毒痰瘀型的發病機制[3]。張培影則認為,ACS的發病基礎為氣虛痰滯,痰濁瘀阻心脈從而致使心脈攣急是本病發病的關鍵病機[4]。聊城市名中醫專家、聊城市中醫醫院急診學科帶頭人康廣山主任醫師總結臨床經驗,認為ACS痰瘀互結型患者因年衰、飲食不節、起居無常、吸煙酗酒等因素致使津化痰、血生瘀,而痰可生瘀、瘀可生痰,痰濁血瘀相互搏結閉阻脈道而為病。
1.2 西醫病因病機西醫認為,ACS的病機十分復雜,目前普遍認為ACS發生的病理生理機制為動脈粥樣硬化和斑塊破裂[5],由于斑塊破裂和糜爛并發血栓形成、血管痙攣及微血管栓塞等多因素作用下所導致的急性或亞急性心肌供氧減少[6]。袁健瑛等[7]認為,動脈粥樣斑塊的形成和破裂是大多數ACS事件的主要原因,然而非動脈粥樣硬化如穩定性冠狀動脈疾病、冠狀動脈栓塞、冠狀動脈痙攣、心肌橋、應激性心臟病等所致的ACS也占相當一部分,其血管造影未顯示冠狀動脈梗阻。
2 中醫治療
2.1 五臟論治
2.1.1 從肝論治心主血脈,肝主疏泄,“血為氣之母,氣為血之帥”,心肝相關ACS多表現在氣血的運行與生化上。沈金鰲《雜病源流犀燭》認為,肝氣一陽生發,起于厥陰,乘一身上下之氣。肝和則使氣機生發,發育萬物,生化五臟,若衰或亢,則反為諸臟之殘賊也。故應疏理肝膽,調暢氣機,調和氣血。張惠等[8]從肝的疏、補、清、平、暖、搜等6個治療角度,闡述了單味藥及中藥復方在冠心病臨床治療中的運用。龍秀娟[9]認為,肝氣郁結者,當以剛治,疏肝解郁,通行氣血;心肝陰虛者,當以柔治,柔肝養心,滋養陰血。剛柔相濟,氣血調和則痹除疾蠲。主張應用疏肝解郁、涼肝瀉心、柔肝養心、益肝養心4法論治心痹。
2.1.2 從脾論治脾胃乃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虛弱,氣血化生無源,心脈失養,發展成為胸痹,多為虛證;脾主運化,運化失司,痰濁內生,濕性黏滯,阻礙氣血運行,致使氣滯痰凝血瘀等相互膠結,阻塞脈道,影響氣血運行,因實致虛,發展成為胸痹。故從脾論治胸痹,重在扶正祛邪,標本兼顧,若本虛標實,則重在治本。治療本虛,應調脾胃而養營血,方用歸脾湯調理心脾,養益營血;補中氣而鼓宗氣,選用五味異功散加味益氣補中、理氣健脾。治療標實,當化瘀濕而宣通痹,治用瓜蔞薤白半夏湯或枳實薤白桂枝湯并常合用小陷胸湯通陽開痹,以治標急;醒中州而化濕濁,方用三仁湯加減以醒脾運脾,清化無形之邪,暢通氣機。標本兼顧,則宜溫中陽而卻陰寒,治宜附子理中湯加味,振奮胸陽,下降逆氣,溫通經絡,散寒止痛[10]。閆海慧等[11]基于數據挖掘及分析整理,發現治療胸痹最常用的“底方”分別為四君子湯、枳術丸、平胃散和三仁湯。四君子湯健脾化濕、行氣祛疾;枳術丸健脾消食、活血行氣;平胃散化濕和胃、痰瘀同治;三仁湯理氣醒脾、健脾和胃。客觀準確地反映出條暢脾胃氣機、調節脾胃運化,祛除痰飲濕濁等有形之邪對治療胸痹的作用。李悅[12]通過動物實驗,發現健脾方對ApoE-/-小鼠血清5-HT及5-HIAA有下調作用,為健脾方可對早期冠狀動脈粥樣硬化進行干預提供了實驗依據。
2.1.3 從肺論治心為君主之官,主血,肺為相傅之官,主氣,心肺相互為用,心血的生成有賴于肺的氣化功能。肺為華蓋,主一身之氣,肺氣虛弱,則氣虛行血無力,血行遲滯,臨床表現為胸悶、氣短、唇青、舌紫脈澀等心血瘀阻癥狀;肺主通調水道,若功能失常,可致使水飲內停或痰濕中阻,從而影響血液運行,出現心血瘀阻的癥狀[13]。徐浩等[14]提出三法從肺論治胸痹心痛:補肺益氣法,方選保元湯合丹參飲加減;理肺祛痰法,可在基本方基礎上加用全瓜蔞、陳皮、法半夏、前胡等藥;瀉肺行水法,可在基本方基礎上加用葶藶子、川厚樸、桑白皮等藥。王中男著重通過調治肺氣,使血脈暢通,增強肺對心的治節作用,令氣行推動血行,并輔以心理疏導和飲食起居指導,從而更好地改善心臟功能[15]。
2.1.4 從腎論治水火者,乃陰陽之征兆,心臟屬火、腎臟屬水。心火下降于腎,使腎水不寒而助真陽,腎水上濟于心,使心火不亢而益心陰,此即心腎相交,水火相濟。若心陽衰微,心火不能下交于腎,致水寒不化,上凌于心,而出現驚悸、怔忡、氣短、喘息、水腫等。若腎水不足,或腎陽不足以蒸化腎水,不能上濟心陰,皆可導致心火亢于上,從而出現心悸、怔忡、心煩、失眠、多夢、五心煩熱等病癥。張仲景《金匱要略》中提到了“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的癥狀,治以烏頭赤石脂丸。方中使用烏頭、附片、蜀椒、干姜、赤石脂等辛溫之品,以溫腎散寒、宣陽通痹。胸痹“表現于心,根源于腎”[16]。根據上述理論基礎,胡業彬教授主張從滋補腎氣、活血化瘀入手,獨創補腎逐瘀湯,主要由仙茅、肉蓯蓉、淫羊藿、葛根、杜仲、牡丹皮、丹參、連翹、水蛭等組成,全方寒溫相輔、冷熱相承、升降相調、攻補相存[17]。尹琳琳[18]結合心腎在生理、經脈、病理上的關系,提出了以補腎為主的五法對胸痹進行論治:補腎溫陽法、補腎滋陰法、補腎益氣法、補腎活血法和補腎化痰法。在胸痹的臨床用藥中,多采用熟地黃、太子參、山萸肉等補腎益氣之品,許多現代研究已經指出此類藥物可促進心臟造血、保護心肌、提高機體免疫,有補腎固源之意,并能益精生血,助心行血,使氣和血榮,改善胸痛癥狀[19]。
2.2 外治法孫思邈《千金要方》中提到,湯藥攻內,針灸攻外,則病無所逃。并認為“針灸之功,過半于湯藥矣”。其主張針、灸、藥并重,不拘于一法一方,權衡諸法之長,取長補短,達到整合運用的最佳境界[20]。由此,可在內治的基礎上加用外治法:熨法疏通體表經絡,在其中使用熨背散,通過溫熱體表,使得藥力通過背部腧穴經絡來調節臟腑的功能,以達到治療胸痹的目的;在運用灸法時,多使用足厥陰肝經和足少陽膽經的腧穴,調暢肝膽氣機,進而調達一身之氣,使氣血陰陽調和,氣通則痹止。孫思邈將胸痹心痛分為肝心痛、脾心痛、肺心痛、腎心痛等類別,并根據其所在臟腑選取對應的腧穴進行治療,其選穴大多采取遠端取穴法[21]。
3 西醫治療
ACS的非藥物治療包括盡量避免各種誘因,如過度勞累、情緒劇烈變化、飽餐、寒冷的刺激等,改變生活方式,戒煙限酒,適度減輕體質量,保持樂觀情緒,積極參加室外活動,避免久坐,同時治療高血壓病、高血脂癥、糖尿病等疾病,保持一種自身平衡穩態[22]。
在ACS的治療中,藥物治療仍是基礎和首選的治療方式。張海濤[23]通過分組試驗觀察對比,認為瑞舒伐他汀可明顯地改善患者體內炎性因子水平,并能調節血脂,改善血管內皮功能,以及控制血小板聚集,在一定程度保障了患者的生命安全。巢時敏[24]觀察非ST段抬高型ACS患者分組治療情況,認為卡維地洛在降低GGT、UA方面更有意義,同時在降低不良事件發生率方面,卡維地洛也要更優于美托洛爾。呂萍等[25]在對ACS患者進行分組治療試驗中,發現替格瑞洛試驗組患者的血小板聚集率顯著低于氯吡格雷試驗組,由此認為在ACS的臨床治療中,替格瑞洛相較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療的效果更好,安全性更高。Waqas Ullah等[26]研究發現,對于ACS患者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中,普拉格雷和替卡格雷比氯吡格雷更有效。
4 小結
胸痹為病,本虛標實,多虛實夾雜,本虛常見于氣血陰陽的虧虛,標實則多為痰濁瘀血等有形之邪或氣滯寒凝等無形之邪。在治療上,從五臟入手,卻不偏執某一臟,而是從整體出發,結合五臟,虛者益之,實者損之,冷者溫之,熱者寒之[27]。西醫則從標實之有形之邪出發,對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采用溶栓或介入治療(PCI)方式,盡早開通梗死相關動脈,可以明顯降低病死率,并減少并發癥、改善患者預后。對于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消除誘因之外,還需使用抗心肌缺血、抗血小板、抗凝、他汀類藥物進行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