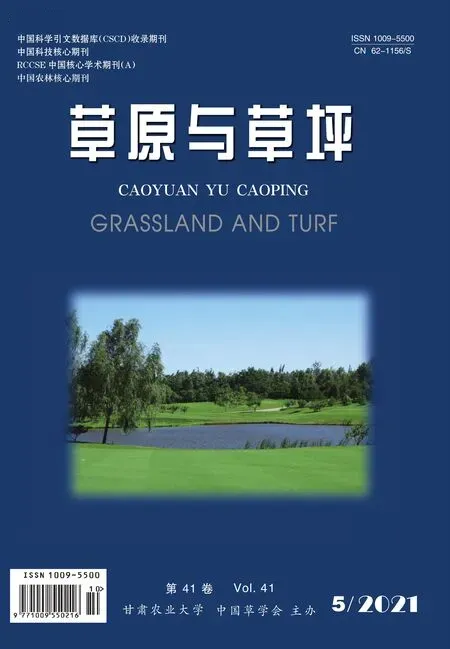不同強度短期放牧對高寒草甸植被特征的影響
高成芬,張德罡,王國棟
(1.甘肅農業大學草業學院/草業生態系統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甘肅省草業工程實驗室/中-美草地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甘肅 蘭州 730070;2.甘肅省草原技術推廣總站,甘肅 蘭州 730010;3.甘肅省農業科學院畜草與綠色農業研究所,甘肅 蘭州 730070)
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稱,對全球氣候變化、人類活動干擾響應敏感,是我國重要的牧區[1]。草甸約占青藏高原面積的33%[2],是當地進行畜牧業生產的基礎,也是黃河、長江源頭地區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由于受全球氣候變化、不合理放牧、過度開墾等因素的影響,高寒草甸退化嚴重,部分地區出現了毒雜草蔓延、地上生物量降低、草原沙化和黑土灘等現象,可食牧草、優良牧草比例逐漸下降[3-7],對當地畜牧業的發展產生了制約[8]。
草地最主要的生物干擾因子-放牧,是影響草地植物群落動態的重要因素[9]。李永宏等[10]認為從區域水平來看,氣候條件、地形特征和土壤特性等環境因子決定了草地牧草生產,但是這些環境因子對同一地域的影響是恒定不變的或有規律變化的,在放牧條件下,植物群落特征與放牧強度關系密切。放牧對高寒草甸植被的影響,前人已進行過大量研究。周興民等[11]通過研究發現,牦牛能通過采食使某一植物在群落中的地位發生變化,最終改變植物群落結構。West等[12-13]研究發現高強度放牧會使植物群落高度和生物多樣性降低。張偉華[14]的研究結果表明,地上生物量、高度、蓋度隨放牧強度增大而減小,其中,優質牧草地上生物量減少速度最快。
因此,本文以高寒草甸為研究對象,通過不同強度放牧試驗,探究其地上生物量變化規律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對禾草、莎草、毒草、可食雜草和毛茛科植被特征進行分析,旨在探討高寒草甸不同功能類群對不同牦牛放牧強度的敏感性、穩定性,為加大草原環境保護力度,提高放牧管理水平,維持草畜平衡,促進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更好實施提供依據。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碌曲縣位于青藏高原東部,地處E 102°42′,N 34°31′,平均海拔3 600 m,年均氣溫為2.3℃,年均日照時數2 300 h,年均降水量為550 mm,主要集中在 5~9月,其中8月最高,為156.9 mm。年均氣溫為1.5 ℃,最低溫為1月-7.4℃,最高溫為8月13.8℃。5月初牧草集中返青,9~10月枯黃,只有約120 d的生長期。
草地類型是高寒草甸類高山嵩草型,主要植物有矮嵩草(Kobresiahumilis)、藏苔草(Carexthibetica)、線葉嵩草(Kobresiacapillifolia)、披堿草 (Elymusdahuricus)、鈍葉銀蓮花(Anemoneobtusiloba)、矮金蓮花(TrolliusfarreriStapf)、翠雀(Delphiniumgrandiflorum)、高山唐松草(Thalictrumalpinum)、鵝絨委陵菜(Potentillaanserine)、老鸛草(GeraniumwilfordiiMaxim)、披針葉黃華(Thermopsislanceolata)。主要毒害草有秦艽(Gentianmacrophylla)、龍膽(Gentianscabra)、黃帚橐吾(Ligulariavirgaurea)、馬先蒿(Pedicularisreaupinanta)、毛果婆婆納(Veronicaeriogyne)、甘肅棘豆(Oxytropiskansuensis)、毛茛(Ranunculusjaponicus)等。
1.2 試驗設計
在碌曲縣加倉村選擇60 hm2禁牧5年的高寒草甸草地為試驗樣地,坡度約為3°,外圍設置圍欄,采用單因素(放牧強度)隨機區組試驗設計。設置4個放牧強度,即:禁牧(對照,G0)、輕度放牧(15羊單位/hm2,G1)、中度放牧(25羊單位/hm2,G2)和重度放牧(35羊單位/hm2,G3),按照1牦牛=5個標準羊單位進行換算,每一強度重復3次,每個小區面積5 hm2,共12個。開始放牧時間為2019年6月11日,10月10日結束放牧,放牧時間為120 d,共選用體重相近、健康無病的成年牦牛225頭,白天自由放牧,夜間趕回圈舍休息。10月11日,在每個小區隨機取面積為1 m×1 m的樣方,重復9次,對樣方內出現的植物種類、物種密度、株高等指標進行測錄。許國成等[16]認為廣泛分布在甘肅草原上的有毒植物以毛茛科、龍膽科、豆科、大戟科、茄科的有毒種最多,本試驗區中出現的有毒植物也以毛茛科最多,群落中毛茛科占比遠大于其他雜類草,為進一步探究毛茛科植物對放牧強度的敏感程度,將樣方內的植物齊地面刈割,按照禾草、莎草、雜類草(分為毒草、可食雜草)、毛茛科分組,先測其鮮重,并于烘箱內65℃烘干測定生物量。樣方中植物種類、密度、高度指標的測定方法如下:
植物種類:記錄在樣方中出現的植物名稱;
密度:數出每一樣方中每一植物植株數;
高度:在樣方內隨機選取每種植物各5株(不足5株者全部測定),測定植株自然高度,計算每種植物的平均高度。

表1 研究樣地設置
1.3 數據處理與分析
(1)物種豐富度指數(D),測定有毒植物物種豐富度:
D=S
隨著我國經濟企穩和轉型升級,跨境資本流動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自2017年12月中旬以來處于升值階段。2017年12月15日到2018年1月9日,人民幣中間價上升了1145個基點。這已基本反映基本面變化。2018年1月央行宣布暫停逆周期調節。暫停當日下午,離岸價與在岸價雙跌,創下近兩個半月的最大日間跌幅。
式中:S為樣方內出現的植物物種豐富度。
(2)生物多樣性指數采用Shannon-Wiener指數(H):
H=-∑(Pi)(LnPi)
式中:Pi為此物種個體數占總個體數比例。
試驗數據整理錄入EXCEL,并用SPSS 26.0軟件在0.05顯著性水平下進行統計方差分析(單因素方差分析)。用 Duncan 法對牧草群落物種豐富度、密度、物種多樣性指數進行多重比較,研究上述指標之間有無差異性。對禾草、莎草、雜類草(毒草、可食雜草)、毛茛科的物種豐富度、密度和株高,用 Duncan 法進行多重比較,研究不同功能群對放牧強度的敏感程度。
2 結果與分析
2.1 放牧強度對高寒草甸地上生物量的影響
牧草按經濟類型可分為優良牧草和雜類草,其中優良牧草主要包括禾草和莎草,研究表明牲畜采食最主要的牧草為禾草和莎草,雜類草包括毒草和可食雜草。試驗發現,高寒草甸地上生物量和禾草比例隨著放牧強度增大而逐步降低,莎草、毒草和毛茛科牧草的比例隨著放牧強度增大而逐步提高。地上生物量在對照區最大,為1 084 g/m2,其中禾草地上生物量占總生物量的19%,莎草占26.98%。重度放牧下地上生物量最小,為632.87 g/m2,其中雜類草地上生物量占總生物量的43.6%,禾草占16.8%,說明在重度放牧水平下牲畜采食性低的雜類草顯現出優勢(表2)。

表2 不同放牧強度下高寒草甸功能群的地上生物量
2.2 放牧強度對植被群落特征的影響
植被群落物種豐富度在中度放牧條件下最高,并且重度放牧顯著低于其他放牧處理(P<0.05)(表3)。此外,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植被群落密度出現先增后降的趨勢,但是三組之間差異不顯著(P>0.05)(表3)。在重度放牧下,物種多樣性指數顯著低于其他放牧水平(P<0.05)(表3)。

表3 不同放牧強度下的植被群落物種豐富度、密度
2.3 放牧強度對不同功能群植被特征的影響

圖1 不同功能群植被的物種豐富度Fig.1 Effects of grazing on the species richness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groups

圖2 不同功能群植被的密度Fig.2 Effects of grazing on the vegetation density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groups

圖3 不同功能群植被的高度Fig.3 Effects of grazing on the plant height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groups
放牧強度不斷增加時,莎草地上生物量占總生物量的比例逐漸增加(表2),物種豐富度和群落密度均呈現先增后減的趨勢,其中物種豐富度在中度放牧和對照組之間具有差異性(P<0.05)(圖1),密度之間差異不顯著(P>0.05)(圖2)。莎草株高隨著放牧強度增大而不斷增加,重度放牧與其他3組之間差異極顯著(P<0.05)(圖1)。
根據《中國天然草地有毒有害植物名錄》《甘肅草原植物圖譜》等文獻資料,統計出試驗區出現有毒植物18種,分屬7科,最多的為毛茛科,有6種,其次是龍膽科和豆科(各有3種),玄參科、菊科各出現2種,木賊科、大戟科均只有1種(表4)。研究表明,毒草地上生物量占總生物量的比例隨放牧強度增大而提高(表2),重度放牧條件下物種豐富度最低,與輕度放牧、中度放牧、對照組均差異顯著(P<0.05)(圖1)。在放牧水平下,密度和高度在重度放牧達到最高,其中重度放牧植物株高與輕度放牧差異顯著(P<0.05)(圖3)。

表4 高寒草甸試驗區中有毒植物種類
可食雜草地上生物量占總生物量的比例隨放牧強度的增大出現先增后減的趨勢,物種豐富度依次減小,重度放牧顯著低于其他放牧處理組(P<0.05)(圖1)。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大,可食雜草密度逐漸增大,重度放牧與輕度放牧差異顯著 (P<0.05)(圖2)。與此同時,可食雜草株高呈現出先提高后降低的趨勢,且中度放牧與重度放牧、輕度放牧差異顯著(P<0.05)(圖3)。
研究表明,放牧強度不斷增加時,毛茛科地上生物量占總生物量的比例逐漸增加(表2)。物種豐富度逐漸降低,群落密度密度逐漸增加,但是3個放牧梯度之間差異不顯著(P>0.05)(圖2)。株高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而逐漸增加,在重度放牧水平下達到最高。
3 討論
3.1 放牧強度對地上生物量的影響
本試驗表明,高寒草甸地上生物量隨放牧強度的增大而逐漸減少,優良牧草比例也在降低,雜類草比例依次增加。這可能是因為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牦牛對優良牧草采食頻繁,植被葉面積指數下降,導致被啃食過的優良牧草不能在短時間內得以生長恢復與繁殖,因此,優良牧草比例降低。同時,處于草地上層的禾草減少,為下層植株較小的雜類草和一些喜光的雙子葉植物的生長發育增加了群落透光率,使得雜類草不斷與優良牧草競爭資源環境,抑制了禾草的補償性生長,提高了光合作用速率,干物質積累增加,地上生物量占比增加,出現了牲畜采食性低的雜類草逐漸替代優良牧草的趨勢。
3.2 放牧強度對植物群落特征的影響
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牦牛對土壤的踐踏程度加重,導致土壤表面壓實易板結,此外糞尿排泄也在增加,易造成土壤容重增大[17],對草地土壤的滲透性、通氣性與蓄水能力產生一定影響,進而降低草地植物群落生產力,阻礙優良牧草生長和發育。研究表明載畜率與草地植物生長呈正相關,載畜率較大時,被采食的植物短時間內不能生長繁殖。在重度放牧水平下,家畜為滿足飽腹要求,降低了對牧草的選擇性采食,加之行走的時間和步數增多,植物因被反復啃食、踐踏而變得低矮,植被物種豐富度和密度下降。
本研究表明,禾草和莎草對放牧強度的敏感性相似,群落密度在中度放牧下最大。其原因可能是因禾草營養價值和適口性較高,被牦牛優先采食,導致植物株高變化明顯。適度放牧刺激了禾草生長繁殖,隨著植株高的禾草被采食,下層低矮莎草獲得的光增多,莎草競爭力增強,光合作用速率提高,物種豐富度、密度、株高增加。此外,重度放牧下,牲畜反復啃食、踐踏處在營養生長階段的禾草,導致禾草生長發育被抑制,群落密度、高度在重度放牧最低。在放牧條件下,莎草群落密度差異不顯著,其原因可能是以營養繁殖為主、具有耐牧耐踏特點的地下芽短莖植物是高寒草甸的優勢種,重度放牧對其繁殖無影響。因此,基于以上兩種原因,莎草才得以生長良好,這與周興民[11]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本研究表明,放牧強度不斷增大,毒草、可食雜類草和毛茛科物種豐富度依次降低,重度放牧水平下毒草地上生物量占比最高,毒草和毛茛科株高最高。其原因可能是隨著放牧強度持續增大,優良牧草逐漸減少,當食物資源短缺后,牦牛便會采食適口性差的低矮植物,這些低矮植物主要是毒草和可食雜草,從而使可食雜草、毒草和毛茛科物種豐富度逐漸降低[18],這與王志鵬[19]的研究結果相一致,但與王向濤[9]重度放牧條件下毒草地上生物量和總蓋度最低結論相反,可能原因是試驗區主要毒草高山唐松草(Thalictrumalpinum)、翠雀(Delphiniumgrandiflorum)、馬先蒿 (Pedicularisreaupinanta)、黃帚槖吾(Ligulariavirgaurea)、花錨(Haleniacorniculata)等在8月處于生長旺盛季節,重度放牧水平下,牦牛過度采食優良牧草,使得毒草獲得競爭優勢。此次試驗,毛茛科共有7種,分別是小花草玉梅、高山唐松草、銀蓮花、矮金蓮花、驢蹄草、細葉毛茛、翠雀,其中6種為有毒或微毒植物。重度放牧干擾為毒雜草生長提了供有利的空間、陽光資源,而且有毒植物根系分泌的化學物質會降低其它牧草種子萌發率,對牧草生長起到抑制作用,因此,在重牧放牧水平下毒草和毛茛科株高顯著提高。
3.3 放牧強度對植物多樣性的影響
物種多樣性指數是反映植物群落結構內物種豐富度和均勻性的重要參數。中度干擾理論認為,在中等干擾強度下群落的物種多樣性最高。本研究表明,輕度放牧和中度放牧之間物種多樣性指數并沒有顯著的差異,但與對照組、重度放牧之間差異顯著,就3個放牧水平相比而言,中度放牧條件下的物種多樣性最高,同時,其植被豐富度也最高,符合中度干擾理論,這與江小雷[20]、陳昕[21]、付偉[22]的研究結果一致。這可能是因為在輕度放牧水平下,牦牛的選擇性采食使得位于上層的優質禾草、莎草的生物量降低,為位于中下層的雜類草提供了有利生存環境,造成植物群落物種組成發生變化,進而使得植被物種多樣性發生改變。對于輕度放牧和重度放牧來說,中度放牧具有較高的地上生物量、物種豐富度、密度以及物種多樣性,可能是放牧加速了土壤養分的循環及超補償性的原因[23],同時家畜的踐踏還能造成更多的微生境,有利于競爭力弱的植物。然而,當放牧強度不斷增加,食物資源發生短缺,家畜采食那些適口性差的雜類草,從而使物種多樣性降低[21-39]。
4 結論
牧草地上生物量對牦牛放牧強度具有較強的敏感性,改變了地上植被物種組成,生物多樣性在中度放牧下最高,并且禾草和莎草密度達到最大。而重度放牧則使毒雜草和可食雜類草密度陡增,物種豐富度驟減,毛茛科因大量植物為毒草,在密度上表現出了和毒草相似的趨勢。因此,在高寒草甸利用中,若以單一牦牛為放牧對象,需要合理規劃牦牛放牧強度。適宜強度的牦牛放牧可對草地植被結構與功能起到改善作用,另外,當高寒草甸出現退化時,可采取圍欄禁牧作為有效的恢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