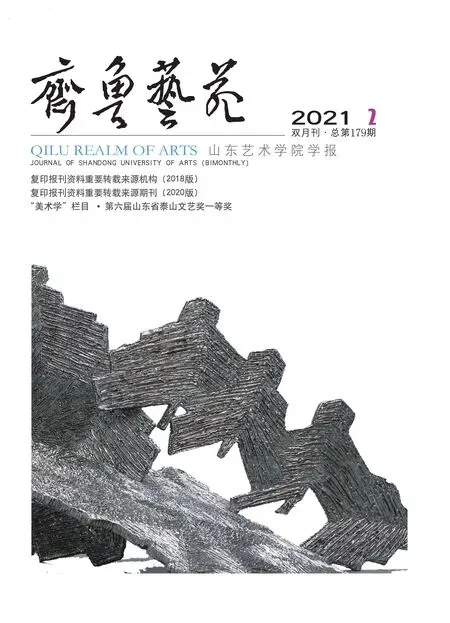略論中國“新主流電影”(2019-2020)
陳旭光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北京 100871)
近年來,中國電影產業,在經過了高速增長的黃金期之后,雖然不斷“遇冷”、遭遇“寒冬”乃至經歷疫情突襲的打擊,但仍然在一種“新常態”下,承上啟下、繼往開來而穩步發展。
總體而言,無論在制作生產還是發行放映層面,中國電影產業都持續了2018年開始的“整體增速放緩”態勢,進入到了一個更加穩定的發展“新常態”,也形成了一種愈加多元的產業結構,顯現出更為豐富的創作生態與樣式類別。國產電影呈現出異彩紛呈的類型格局,電影生產迅速消化吸收市場出現的新潮流、新現象,匯聚而成影響力頗大的《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等“新主流電影”迭加頻出的潮流,而代表電影工業制作水準的幻想類大片《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的成功,更開啟了中國電影“想象力消費”時代的新篇章。
2019年堪稱“新主流”電影之年。依憑國慶70周年的主流文化機遇,2019年的“新主流電影”創作繼續穩步前行,且因與宏大的國族主題親密“合謀”,達成主旋律、商業和平民意識形態的最佳組合。
2020年,遭遇猝不及防的疫情,中國電影產業面臨重大危機,經受了嚴峻考驗。電影行業的發展與重構,也遭遇了面對嚴酷現實的新課題。作為疫情影響“重災區”之一的電影行業,遭受了“停擺”式的重創——影院關閉、影片堆積、拍攝停滯、資金緊縮、產業鏈熔斷——但在重新開放放映之后,中國電影還是迅速恢復了生機,繼續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新態勢和新趨勢。《奪冠》《八佰》《我和我的家鄉》等作品,在疫情未絕的形勢下,依然取得口碑票房雙贏的佳績,有效地引領觀眾重歸影院,奠定了特殊時期中國電影票房登頂世界票房最高點的基礎。
一、“新主流電影”:“大片”與“中小成本電影”的分層和多元化進路
從“新主流電影”或“新主流電影大片”的術語界定和工業、美學定位來看,此類電影是對傳統的電影“三分法”即主旋律電影、商業電影、藝術電影的固有界限之跨越。這些作品“尊重市場、受眾,通過商業化策略,包括大投資、明星策略、戲劇化沖突、大營銷等,彌補了主旋律電影一向缺失的‘市場’之翼”[1](P13-21,187)。而商業化運作的結果,票房的上升與傳播層面的拓展,“也促進了主旋律電影所承擔的主流意識形態宣傳功能的實施,這是作為中國特色大眾文化的主流電影的市場和意識形態的雙贏。”[2](P90-99)因此,“在世紀之初,‘新主流大片’概念的提出并得到相當的認同,達成了某種共識實際上表征了‘三分法’的界限逐漸模糊,逐漸被抹殺被抹平的事實”[3](P13-21,187)。
毋庸諱言,“新主流電影大片”大多屬于大制作,成本較高、制作規模較大、明星較多、奇觀場面較為宏闊,常以真實可信的中國故事、紅色經典塑造國家形象,以表達集體主義精神等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故事為藍本,旨在生產能夠打動人心、喚起國族意識的中國故事和中國人物,正面或側面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凸顯中國氣派、中國風度和中國形象。
無疑,“新主流電影”是近年來學界與業界都頗為重視的藝術現象。盡管“新主流電影”并非一個嚴格、規范的概念。“因為它并沒有明確界定什么類型什么題材才是新主流。但它是對三種電影界限的模糊化和抹平,是電影的某種‘大眾文化化’表征,是對當下多元文化的包容,是對主流觀眾的尊重!它更是一種追求趨向,一種開闊的胸懷,體現了非常包容的文化胸襟”[4](P13-21,187)。但狹義而言,或者說最為引人關注的所謂“新主流電影大片”,作為“在主旋律電影文化基礎上對多元文化資源的有效整合”,是指以《戰狼2》《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為代表的具有較強主流意識形態,但又在視聽效果、動作與情節強度上都做得非常精致,追求商業性、動作奇觀和異域風光表現,票房口碑雙贏的一類電影。當然,“新主流大片”的題材、風格應該是多樣化的,筆者在《戰狼》等行動類“新主流電影大片”熾熱之際就曾經矚望:“新主流大片的風格也應該是多樣化的,不能僅僅局限于政治主流,青年文化等都要被納入,青年文化在正統傳媒上也許不是主流,但在網絡新媒體上無疑早就是主流了。當下的受眾主流不用說是年輕人。我們應該關注目前非主流但很快就會成為主流的一些電影語言、形態、風格等方面的新變化。而這些新變化歸根結底是因為主流電影觀眾的變化,或者說越來越年輕化、‘網生代’化。就此而言,我們也不能對新主流這一概念固步自封,自我封閉——只有這樣,我們所期待的‘新主流大片’也才能保持生命力,才能不斷發展。”[5](P13-21,187)
筆者在分析《中國機長》(2019)的創作得失時,也曾論述并預期經由其表現出來的新主流電影不斷拓展新題材、新領域的態勢:“隨著像《我和我的祖國》這樣的主題更為集中突出,時效性更強的國慶檔影片熱度的退潮,《中國機長》這樣類型清晰,本土化,新主流拓展的視效大片,因其對工業化視聽效果的完美呈現,對創作的‘中國速度’下中國品質的彰顯,災難片的本土化與中國式表達,”[6]總是會得到促使其發展的持續動力。“在《中國機長》之后,中國還會有更多類型定位清晰、類型敘事完整、工業體制完善的新主流電影。”[7](P29-33)
電影發展的事實印證了筆者的預期。2020年中國“新主流電影”的發展,明顯表現出從大投資大市場的大片形態向中小成本形態的轉變,這也是契合了疫情之后電影交流阻斷,資金緊縮的產業現實狀況。因為疫情對經濟發展造成沖擊,疫后面臨流動性資金有限、后續資金不足等經濟問題,電影生產只能把開發重點置于有著多元發行渠道、資金回籠迅速之特點的,“短、平、快”型的影視作品。中小成本、“中等工業美學”電影顯然都會在優先考慮范圍之內。受“全球性”疫情的影響,在多國航線中斷,國際交流不順暢的背景下,我們更不宜做大投資、瞄準國際市場,“走向世界”的大片,包括“新主流電影大片”。因為大片就會耗資巨大、風險甚高,而且必須依托國際市場。
于是,不僅僅《八佰》《奪冠》等“新主流電影大片”在歷史戰爭題材和體育題材上開疆拓土,另辟蹊徑,就是以《我和我的家鄉》《一點就到家》等為代表的中小成本“新主流電影”,也以一種內向化、民生化的清新面目,以勃勃生機之態出現在電影市場上,收獲了票房和口碑的雙贏。
二、2019:“新主流電影”的主潮
2019年最引人注目的“新主流電影”的收獲非《我和我的祖國》莫屬。這部作品是以陳凱歌為總導演,黃建新為監制,以6位不同年齡段導演(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寧浩、文牧野)聯合執導的電影大片。此片講述大歷史環境下的小人物故事,表達了懷舊情緒下的“國家共同記憶”,負載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與情感“詢喚”。國家化的生產制作方式,使之成為繼早年《建國大業》后,“新主流電影大片”的又一典范之作。
《我和我的祖國》是“獻禮片”,而從明星陣容和制作精良的視角來看也堪稱大片。當然,該片更以“獻禮”之名,而使得明星演員和明星導演們不計報酬甚或義務出演或執導,竟然以600萬的成本完成全部制作,堪稱奇跡,其策略與當年《建國大業》如出一轍。組成影片的6部短片都屬于現實主義題材和風格的作品,個別帶有浪漫主義色彩。其中最接近現實或者說現實主義追求力度最強的是陳凱歌的《白晝流星》和寧浩導演的《北京你好》,直接對應國家“扶貧大業”和“奧運”大事。另外4個故事也都是通過具有真實感的小人物瑣碎平庸的日常生活和現實故事,以小見大、講述背后的“不平凡”或大歷史、大現實。無疑,作為中國特色的“獻禮片”,一要有正確、正能量的主題表達;二還要吸引觀眾,一定程度上得適應市場,才能起到獻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慶的任務。因此,《我和我的祖國》通過對細碎生活的現實主義化展現,幾乎以對中國每一個重要階層,每一代表性地域的表現,讓盡可能多的普通觀眾,在觀影中完成國族歷史的想象,進而在想象中獲得國家認同,完成自我個體與國家關系的定位。
《我和我的祖國》通過普通人故事的具象化、戲劇化,藝術性地表現了作為“個體”與國家血肉相連的關系。劇作采用的以主題引領,聚合多個短片情節構成“麻辣燙式”的組合敘事結構,既是充分考察與體現主創人員敘事講述能力高下的標桿,也像《建國大業》那樣利于發揮演員群像表演集聚的明星效應,給予了導演執導調度駕馭的廣闊空間,并讓觀眾在目不暇接中感受到群星璀璨的魅力價值。因為這部作品還以6個導演分別執導一部短片電影的方式來拍攝,更增添了一種導演同臺競技,聽由廣大“吃瓜群眾”品頭論足的味道。它無疑是繼十多年前的“獻禮大作”——《建國大業》“求新求變”的改造過后,“新主流電影大片”出奇制勝的又一新案例。
影片將目光聚焦于重大歷史事件中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看似微不足道,但卻在歷史中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說偶然又必然地,他們注定要“遭遇”大歷史,更是要以別具一格的方式創造大歷史。于是,影片賦予了這些普通人以某種“平民英雄”的氣質,從作為知識分子的工程師、科學家(《前夜》《相遇》),到參與國慶閱兵的飛行員和維護治安的港警(《護航》《回歸》),到普通的出租車司機(《北京你好》)、單純可愛的孩子(《奪冠》)、有過錯的少年(《白晝流星》)等。蕓蕓眾生的喜怒哀樂,與重大事件的集體記憶相結合,且使用了具有“數據庫敘事”特質的6部短片融合方式,使得這部影片所講述的“中國故事”新穎而動人。
當然,與《建國大業》《紅海行動》等作品的“主流”敘事策略不同,《我和我的祖國》并沒有利用奇觀化的動作和明星扎推的場景來書寫這些“英雄”,其策略是在大歷史前為每一個普通人樹碑立傳,與普通觀眾形成更加有效的共鳴和共振,尋求價值觀的傳遞。
此外,《中國機長》《烈火英雄》《攀登者》等“獻禮片”進一步形成了“新主流”電影類型的豐富性。
紀念澳門回歸的《媽閣是座城》和紀念徽班進京的《進京城》雖是中小成本制作方式,但仍然以文化命題來書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國文化、中國精神,依然“擠進”了“新主流電影”之列。“從某種角度看,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富強’‘民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核心價值觀的體現成為‘新主流電影’一個重要的特征。這些表達,一面受到了官方的認可,另一面也感染觀眾。但是,這些電影之所以成為‘新主流電影’,最重要的一點是能夠將這些價值觀寓于小人物的生命體驗之中,使之在他們與觀眾有情感共鳴的經驗中透出,通過書寫個體來書寫群體,通過書寫個人史來書寫當代中國史”[8](P90-99)。
本土化災難大片《中國機長》,“是對新主流大片的一次新拓展,是一部具有類型拓展或本土化意義的災難類型電影”[9](P29-33)。在一個相對獨立、封閉的空間中進行了崇高美學的“平民化”表現,影片的生產則體現了某種“中國制造”的速度與質量,“彰顯著大國效率與大國風范。該片也較完美達成工業與美學的相互融合,為‘電影工業美學’尤其是‘重工業電影美學’”[10](P29-33)的實踐提供了一個重要例證。
在聚焦“小人物”,刻畫“平民英雄”,以“獻禮”名義傳遞主流價值觀等方面,《中國機長》與《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相近,但影片有如下兩方面重要突破。
其一,集體主義精神和職業價值觀的新主題。“影片沒有濃墨重彩刻畫個體英雄,而是聚焦整個機組的團隊協作,這自然是中國式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的顯影。”[11]“影片甚至表達了以往主流電影不多見諸如‘敬畏生命’‘敬畏職責’‘敬畏規章’的理念,呈現出‘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命運共同體價值觀。就此而言,《中國機長》不僅是一部具有類型突破和升級意義的類型電影和新主流電影,也是一部表達新型價值觀的一部安全教育片、職業劇。”[12]
其二,《中國機長》取材真實事件,借鑒但超越了西方災難片的類型模式,具有美國式災難電影的“本土化”意義。以“空難”事件為主構筑情節框架的美國電影作品《薩利機長》作為參照物來看,不難發現,該片核心焦點凝聚在主人公的外在形象與內在心理之上,在探究飛機選擇迫降的合理性等律法制度問題時有大量呈現,諸如災難事故過后,調查部門對于事實細節的盤問質疑,讓薩利自身都感到了迷惑而記憶陷入不確定性之中。電影作品的場景著力于構成行動核心的情節呈示,“真實再現了從起飛到安全落地的全過程并在著陸后的大團圓中戛然而止。這種追求逼真性、體驗性,凸顯‘空間消費’、視聽震撼的場景再現,以及對于機艙玻璃碎裂原因追究的回避,”[13]可以被視作尊重體制的恰當選擇。“因為電影安排在國慶檔放映,有著重要的‘獻禮’任務,國慶檔受眾的情感共鳴和身份認同是壓倒一切的。”[14]
《攀登者》對探險片、冒險片等亞類型電影有所借鑒,在獻禮主旋律的線索中,疊合“愛情片”“青春片”等,在主人公愛情這條敘事線上加入了“青春片”元素,并試圖講述當代或另一個時代特定時間里英雄的故事(無論是群像還是個人)。但過于強大的主旋律動機,使得電影的故事顯得不夠真實流暢。
實際上,《中國機長》《烈火英雄》《流浪地球》雖然也可以有其他歸類,但也不妨歸之為原本類型性就比較復雜,常與其他類型疊合的“災難電影”。這些電影作品都不約而同地運用“災難片”元素,并在災難中以“超現實主義”或“現實主義”的手法塑造著某種中國式的“超級英雄”或平民英雄。具有災難片元素的電影作品,在中國電影產業體系與創作實踐中大量出現,顯示出中國電影工業的巨大進步——畢竟,“災難片”需要大量的特效——一個工業基礎薄弱的電影產業,是無力制作要求宏大場面的“災難片”的。
從2019年中國“新主流電影”發展態勢來看,“新主流”電影試圖以商業電影的模式,發揮國族想象和民族文化認同的功能。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文化產品的形成,對于國家精神的弘揚,國家文化想象的建構,對于個人發展的正向影響都是巨大的。在中國獨特的文化體系、政治體系和電影市場中,“新主流電影”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生產模式,甚至已經初具中國特色類型電影的類型特征。而這些電影的商業特質,也能夠將過于明顯的意識形態策略企圖“隱蔽”起來,有望成為“中國電影走出去”(1)參見陳旭光、肖懷德主編. 電影的目光:中國電影“走出去”戰略研究[M]. 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20.的重要代表。
三、2020:中國“新主流電影”的新態勢與新趨勢
2020年,載負著“走出疫情”的使命和我們的期待,“新主流電影”在形式、類型、主題等方面繼續進行新的拓展與探索,且繼續發揮“大魚帶小魚”的引領示范作用。該年度票房收入排名前5的作品中,有4部是“新主流電影”:《八佰》31.13億、《我和我的家鄉》28.23億、《金剛川》11.19億、《奪冠》8.35億。
2020年的“新主流電影”有新的發展、新的探索,這表現在題材和風格等諸多方面。
相對于以往的《戰狼2》《湄公河行動》這些講述“當下故事”,并以“救援”為主線的作品,《八佰》與《金剛川》直面歷史,甚至直接呈現“被忽視的歷史”。此種直面歷史又不同于《建國大業》《建軍偉業》《建黨偉業》那種關于國家與政黨的宏大敘事。這兩部電影直面的是“人民的歷史”“戰士的歷史”,不同于《中國機長》那種對職業英雄的稱贊,也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國》對歷史關鍵時刻平民英雄的贊揚。總體來講,這兩部作品所關注的英雄,超越平凡人,又是平凡人。兩部作品講述歷史上被忽視的英雄、戰士,對其進行客觀、立體、真實的還原、呈現,不故意“高大全”,而是將每一個戰士的“真實”表現了出來,是一種對真實歷史事件中大寫的“小人物”的描繪,那種魯迅先生說的“中國的脊梁”式的“人”的表現。
《八佰》以四行倉庫保衛戰為故事背景,以“一河兩岸”的對比,反思戰爭、人性和國民性。匠心獨具的符號化隱喻(如那匹戰馬),凝重壓抑的封閉空間敘事,民族啟蒙的主題與真實歷史英雄人物的刻畫,使影片在描摹戰爭時,表現出粗糲而震撼人心的真實慘烈之美。而其最為值得稱贊的是將“戰爭”的慘烈與“都市繁華”平行蒙太奇般地并置在了一起,指稱著國民性批判的意向與現代性“啟蒙”主題。一邊是拼命抗戰,大無畏“捐軀赴國難”的真戰士,一邊是如觀看“雜技”一般甚至“壓注”的“看客”。戰士以生命“啟蒙”對面的“看客”,而“看客”們由“事不關己”到“親力親為”“為之動容”的轉變,表現出民族意識與民族精神的覺醒。影片中的英雄,并非“高大全”的英雄,有些也曾怯懦,甚至想當逃兵,這是戰爭、死亡面前人性的真實展現。這些“不完美”的英雄們,在這場抗擊之中堅持了下來,發生了轉變,成長為了英雄。影片不避“人”的本性,但更加凸顯時勢造就的英雄的可歌可泣。
《金剛川》領命于時事政治需求,以極快的運營效率、極高的工業化標準而制成。該片講述“抗美援朝”戰爭中一群為國奉獻的英雄,戰爭場景營造趨向真實,人物情感表達較為真摯。影片在敘事上對以往戰爭類型有所突破,采用了“復現性敘事手法”[15](P59-61,162),從“士兵”“對手”“高炮排”三個敘事視點講述故事、記錄戰爭。以方言營造歷史人物真實情境的演繹,以輕度的喜劇性描摹悲劇內核,以戰爭主題承載友情與愛情的書寫,也是影片的藝術特色與過人之處。
《奪冠》是中國體育題材電影的新拓展。“藝術表現上混合虛構與紀實,跨越歷史與當下,有著含蓄蘊籍的主題意蘊表達。”[16]該部作品借由女排從教練到隊員形象的結構化呈現,歌頌了她們執著追求與堅韌剛毅的奮斗精神,也在其上標注了時代價值觀念與人們情感寄托的銘文。尤其是影片呈現競技運動中人的尊嚴,弘揚與時俱進的先進體育理念和現代體育精神,既表現愛國情懷,歌頌郎平等人通過體育競技展現中國人的“精氣神”和崛起的國家形象,也傳遞了體育必須結合個人愛好,追求身心和諧等當代文化精神和理念。
不同于以往較為枯燥的傳記片,也不同于既有體育題材電影,《奪冠》融合名人傳記、個人成長與體育賽事、家國命運的復合題材,不僅在多重結構上有探索,在敘事上綿密緊湊,在人物塑造上也處理地比較到位。影片最大程度上再現了歷史中的人和事件,采用真正的體育運動員,并大多以現實中的自我身份作為演員出演,并經常插入真實影像記錄畫面,將真實與藝術進行了高度的融合。
“《我和我的家鄉》與2019年《我和我的祖國》相似,以相近主題的幾個短故事構成影片整體。但與《我和我的祖國》不同的是,《我和我的家鄉》不僅主題從祖國具體化到故鄉,而且強化了喜劇性,使‘新主流’式的宏大敘事轉向普通百姓的民生故事。《我和我的家鄉》《一點就到家》等,一方面,是農村題材電影的升級換代,是扶貧國家主題的藝術表達,而從另一角度看,它堪稱是新主流電影大片的民生化、內向化、‘小片化’。”[17]
《我和我的家鄉》《一點就到家》以當下現實題材,關注民生與社會發展,同時滿足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訴求。對位“扶貧”國家主題,歌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就,反映了當下社會發展與人民生活的真實現狀。
相對于以往主要表現黨、國、偉人、英雄、特殊任務等宏大內容題材的“新主流電影”,以《我和我的家鄉》《一點就到家》為代表的功能屬性與價值理念相近的作品,將切口縮小到“鄉村”,以“鄉村發展”展現社會進步,以老百姓真實的生活呈現,描繪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成果,傳達和諧、發展、振興、脫貧等當下主流意識形態和國家層面關注的時代主命題。
2021年已經到來。2020年的新冠疫情公共衛生危機正在改變這個世界。但“新主流電影”仍然顯露出生機勃勃、清新俊朗的生命力,不負使命,不懼艱難,慨然前行。我們也把美好的祝福和期待,奉獻于“新主流電影”的未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