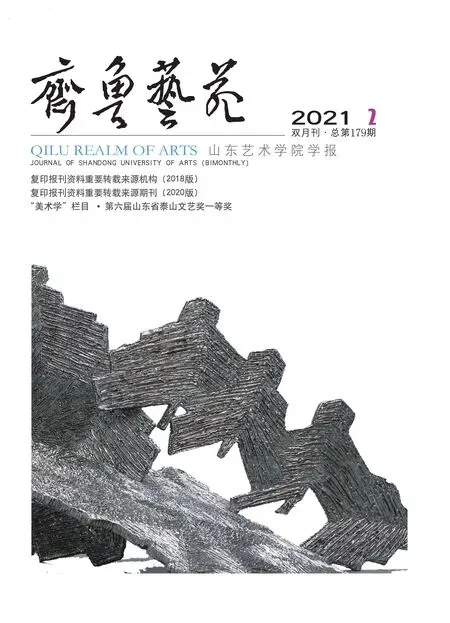“獻禮片”形態(tài)的承續(xù)與超越
——以《我和我的祖國》為例
宋法剛
(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作為2019年國慶檔的現象級影片,《我和我的祖國》不僅創(chuàng)下了主旋律電影的諸多票房紀錄,更以自身對歷史情境的還原與書寫,直接蕩起了觀眾內心的時光記憶、民族自豪與家國情懷,也使其引發(fā)的話題傳播熱議事件,成為一次具有共振意味的集體狂歡。該片由7位各具創(chuàng)作風格且富有市場經驗的導演分別制作,以開國大典、原子彈爆炸成功、女排奧運奪冠、香港回歸、北京奧運會開幕、神州載人飛船返航以及紀念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閱兵等7個歷史高光時刻為線索,全景式地呈現出一幅“新中國”發(fā)展歷程的壯美畫卷。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脫去了宏大敘事的窠臼,轉而以小人物的視角進行情節(jié)構設,使得個體在總體歷史面前的動然一瞬,悉數躍然于銀幕之上,使觀眾之“我”與影片人物之“我”形成指涉、互為觀照。奮戰(zhàn)一線的工程師、默默無聞的研究者、活潑可愛的小男孩、一絲不茍的護旗手、幽默風趣的出租車司機、無私奉獻的扶貧辦主任以及英姿颯爽的替補飛行員等平民英雄,使原本觸不可及的歷史,瞬間幻化成一種可供觸碰的共有記憶。最終,影片以31.14億的超高票房挺進國產電影票房榜單,成為當之無愧的“主旋律”電影星空圖譜中的燦爛“北斗”,而“七星”方陣的制作方式,也為電影工業(yè)體系化構建的形成與發(fā)展,提供了一條更為明晰的路徑。
一、“命題性”與“能動性”:工業(yè)體系下的規(guī)劃與協(xié)調
正如電影理論家約翰·霍華德·勞遜所言:“一部影片是由一系列的章節(jié)組成的,這些章節(jié)是有明確的界限的”[1](P379)。在電影工業(yè)體系中,策劃作為整個環(huán)節(jié)的起始鍵和核心源,是整部電影章節(jié)中的緒論。盡管策劃的重要性無需贅述,但“主旋律”電影的策劃難度卻值得一提。通觀此類電影的創(chuàng)作之路不難發(fā)現,一部分影片匯入傳記式人物書寫的洪流之內;一部分影片則沉入歷史節(jié)點的宏大敘事之中。在此創(chuàng)作語境下,大量的相似創(chuàng)意與敘事雷同使得觀眾觀之乏善可陳。另外,作為夾雜典型意識形態(tài)特征的影片,主旋律電影企圖“在特定歷史社會語境中塑造自我和他人”[2](P76),具有鮮明的說教性與導向性,而這些特性在多元文化泛濫的當下時代,就顯得古板而生硬。正是如此,策劃一檔別出心裁的“主旋律”影片,便顯得尤為必要,但在必要之下卻盡是難以抽離的桎梏與枷鎖。作為一部集錦式的作品,《我和我的祖國》無法脫離策劃這一核心存在而各自獨立完成的創(chuàng)作,但它并未陷入窠臼之內,而是接下了“主旋律”電影的接力棒,成為工業(yè)美學下極具規(guī)劃與協(xié)調的一曲奏鳴。
黃建新導演作為《我和我的祖國》的總制片人,實際上握有了影片的指揮棒。作為《我和我的祖國》的總制片人,黃建新曾經提到,7個導演拍攝7個歷史瞬間的念頭“是他和總導演陳凱歌在2018年10月接到相關主管部門的通知后,反復思考討論,才商議出來最適合這部影片的呈現方式”。作為“作品等身”的導演,黃建新積累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經驗與資源,因此在協(xié)調影片的過程中顯得措置裕如。另外,隨著《建國大業(yè)》《建黨偉業(yè)》《建軍大業(yè)》等獻禮“主旋律”電影的相繼問世,黃建新也摸索出了涉及“主旋律”電影的創(chuàng)作觀念,即通過演員資源的整合,擴大影片影響力,以實現生產與消費的對接。在此種觀念之上,黃建新也考慮通過導演資源整合的方式,實現“主旋律”電影的進一步突圍。盡管這種方法史無前例,但卻得以更為有效地調動起了不同導演的創(chuàng)作能力與激情,更能借導演票房號召力的東風,實現宣發(fā)效應的最大化。另外,這樣的呈現方式,實際上與“新中國”70周年大慶的節(jié)點休戚相關,黃建新直言:“70年,7個導演拍,7和70,挺有意思的,這個想法就出來了。”
與演員的整合有所出入,導演的主觀能動性更強,自身的風格特征亦是難以抹殺。因此,黃建新等人在籌備之初,便“用了兩個月的時間選擇題材”,尋找了策劃團隊來進行選材,選出了二三十個具有“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3](P69-76)的創(chuàng)作理念”的選題,其中包括了航空母艦、汶川地震、南方洪水等重大事件。在眾多事件中,黃建新等人認為事件之間應該存在時間存續(xù)的關系,確立一個明確的時間線,并以此串成一段中國70年的心靈史。黃建新指出:“7和70這個概念,得統(tǒng)一,差不多10年一個,有的稍微跨度長一點,(這樣能)代表不同的時期”。在具體規(guī)劃和特殊設置的拉動下,不同風格的導演,通過內部規(guī)范與斟酌討論,建立起一條與核心相符卻各自成節(jié)的創(chuàng)作鏈條。
二、“小人物”與“大歷史”:產業(yè)經驗與文化價值的完美對接
電影工業(yè)美學的體系既強調電影的工業(yè)屬性,又主張電影的美學價值。因此,電影工業(yè)美學否認大規(guī)模的批量生產,但并不否認經驗復制所帶來的創(chuàng)作動能與美學價值。換言之,電影工業(yè)美學也如同“工藝美術運動”一般,是一種強調“大量的、經濟的制造物品,而又無損于創(chuàng)造性和美質的手段”[4](P187)。《我和我的祖國》的創(chuàng)作,實際上也與電影工業(yè)美學所強調的經驗復制休戚相關。具體而言,7位導演所慣常使用的敘事策略,實際上與該片中“小人物”與“大歷史”的筆調相統(tǒng)一。
總制片人黃建新作為“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創(chuàng)作出一系列反映時代小人物的影片,如《黑炮事件》《站直啰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等。實際上,黃建新的早期創(chuàng)作,吻合了“第五代”導演整體的創(chuàng)作觀念與改革開放初期的文化新風。在特殊的時代語境之下,從歷史拉入個體、將個體指代歷史,成為常有人走的路。另外,黃建新監(jiān)制的“主旋律”影片《投名狀》作為蟬聯金像、金馬的雙料最佳,同樣是以“小人物”與“大歷史”相勾連的方式,進行敘事的。除了總制片人黃建新以外,《我和我的祖國》的總導演陳凱歌,同樣出身于“第五代”導演,經典之作《霸王別姬》,同樣是將“小人物”與“大歷史”進行關聯,使人物命運與時代進程環(huán)環(huán)相扣。除“第五代”導演以外,張一白、徐崢、管虎、薛曉路、寧浩、文牧野等幾位導演,皆擅長拍攝具有“小人物”色彩的影片,對于相關人物描摹與刻畫的把握了如指掌。因此,以“小人物”與“大歷史”相結合的《我和我的祖國》,可以說是工業(yè)美學流程下經驗復制的產物。
盡管如此,影片實際上更是一次歷史的必然選擇。可以說,“小人物”與“大歷史”相結合的方式,既是當下市場的需要,也是時代文化的主流。文化這種“貫穿了所有的社會實踐,是它們相互之間關系的總括”[5](P53)因子,無時無刻不流動在創(chuàng)作者周圍,使之成為創(chuàng)作內容的縮影與模板。放眼于當今社會,被放大的“超級英雄”已經不再是觀眾趨之若鶩的對象,而與觀眾互為觀照的小人物,反而更能撩撥到彼此的心弦。值得一提的是,電影創(chuàng)作中所展現出來的工業(yè)美學價值,實際上建立在創(chuàng)作者對于市場與文化的把握與洞察之上。換言之,作為工業(yè)而言的藝術“商品”,更加不能棄時代語境而獨自逆旅。
《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小人物”,涵蓋了工程師、科研工作者、學乒乓球的小孩、護旗手、出租車司機、退休的扶貧辦主任、飛行員等。他們在特殊的歷史節(jié)點上揮毫一轉,成為“大歷史”的犧牲/奉獻者:工程師犧牲了家庭,完成了開國大典中電動升旗的使命;科研工作者犧牲了愛情,實現了第一次原子彈爆炸的成功;乒乓少年犧牲了懵懂的初戀,完成了為鄰里播放女排奪冠節(jié)目的任務;護旗手戰(zhàn)勝了自我,實現了分毫不差的使命;出租車司機放棄了看開幕式的機會,轉而為少年圓夢;扶貧辦主任拿自己救命的錢,換來了兩位少年的成長;飛行員放棄了親自參加閱兵儀式的機會,為隊友保駕護航。他們作為角色被觀眾凝視,又作為普通的個體讓觀眾投射,成為觀眾“建立起二次認同的他者”[6](P43)。在建立起認同之后,觀眾也隨角色進行轉變,成為勇于戰(zhàn)勝自己的工程師、放下面子收獲力量的出租車司機以及收獲乒乓球夢的少年。劇中角色的成長,不僅使得觀眾“從這種與悅人的一致性和完滿性的幻覺中獲得快感”[7](P92),更使得他們直接成為成長中的個體。
毫無疑問,“作為一種創(chuàng)意文化產業(yè),電影一方面能創(chuàng)造票房即經濟價值,另一方面則還能創(chuàng)造符號價值或象征價值,即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8](P7-15)。《我和我的祖國》正是借產業(yè)經驗完成了內容生產,又實現了文化產業(yè)屬性和文化社會屬性的完美對接。黃建新強調:“每10年都會為重要節(jié)日拍一些電影”。 實際上,這種獻禮式的作品不僅迎合了“我和我的祖國”的個體情緒、民族情緒,更成為黨員教育“不忘初心”活動的優(yōu)質內容。
三、“老導演”與“新導演”:資源合力下的百花齊鳴
美學離不開風格的研究,工業(yè)美學亦不丟失對于風格的考量。風格即是作品因于內而浮于外的整體面貌,它是藝術創(chuàng)作者成熟的天然標志。這部由7位年齡各異、特色各迥的導演共同完成的影片,凝聚著第五代導演、第六代導演及新一代導演們對于歷史的不同側寫方式和獨成一脈的創(chuàng)作風格特征。盡管整部影片都圍繞著大歷史中的小人物,但創(chuàng)作者所選擇的表達方式卻不盡相同。可以說,7位導演以獨特的亮相方式,完成了影片的集錦式創(chuàng)作。因此,7位導演風格上的碰撞,也成為該片值得書寫的關鍵之所在。
首先,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的作品,在《我和我的祖國》中直接“對壘”。《白晝流星》的導演陳凱歌,作為第五代導演的佼佼者,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佳作。《白晝流星》同樣能看出導演身上鮮明的風格氣質,即歷史與個體命運融合的敘事特征以及環(huán)境大于個體的敘事結構。換言之,《白晝流星》中的人,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直接成為群體的特殊指代。與第五代導演的寓言性言說不同,第六代導演則表現出了濃郁的個體化意志。《前夜》的導演管虎,堪稱第六代導演中的怪才,其作品兼具個性化的敘事特征以及商業(yè)化的創(chuàng)作思維。在《前夜》中,這種風格特征繼續(xù)延續(xù),使得工程師的昨昔與今日、各崗位工作人員的妥協(xié)與互助、迫在眉睫的“快”與危難之時的“慢”相互碰撞。另外,極具商業(yè)洞察力的管虎,在作品的處理上幽默風趣、犀利生動,因此,《前夜》也在人文關懷精神的基礎上,帶有鮮明的戲劇張力。
其次,擅長拍攝商業(yè)類型片,尤其是愛情片的兩位導演“狹路”相逢。《相遇》的導演張一白擅長描摹城市男女的鮮活愛情,同樣的,《相遇》亦是兩個城市青年,從邂逅相戀到因故分離,再到公車相遇的故事。當男青年再度遇到久違的愛人,喋喋不休與只字不提、追憶的渴望與眼神的撲朔、奔放的追逐與怯懦的回避,集中在一個景深長鏡頭之下,顯得激情有力。與激情流露的張一白不同,薛曉路在《回歸》中顯得溫情十足。以愛情片《北京遇上西雅圖》成名的導演薛曉路,擅長描摹人物內心情感,其導演的《回歸》,便在這一點上展現得淋漓盡致。當具有不同身份特征的個體,保證回歸“一秒不差”之時,個體內心的情感追溯,也徹底建立完成。
最后,因共同制作一部影片而結緣的三位導演,也在《我和我的祖國》中各顯“神通”。2018年上映的《我不是藥神》,徹底讓新人導演文牧野家喻戶曉,而其背后的兩位監(jiān)制——寧浩、徐崢,也同樣成為被人稱道的前輩典范。《我和我的祖國》也讓原本一盤棋上的三人,各自獨立、盡顯神通。《北京你好》的導演寧浩,擅長描摹草根人物的形象,其作品帶有鮮明的黑色幽默氣質以及荒誕的生命體驗意味。在《北京你好》中,這些典型的風格特征,借出租車司機這一形象,生動地詮釋出來。《奪冠》的導演徐崢,屬于演而優(yōu)則導,但其作品以小人物為著力點,通過詼諧幽默的內容推動敘事。在影片《奪冠》中,冬冬的可愛與懵懂、上海弄堂的市井氣與煙火味、冬冬的情愫與奪冠的激情,都成為牽動觀眾心弦的所在。文牧野導演的《護航》,則展現出了其在“類型化”制作上的天分,女飛行員過去與現在的堅守、愛情與事業(yè)的取舍、個人與集體的抉擇,十分震顫人心。
面對當下電影危機以及影視產業(yè)寒冬,中國導演放棄了風格之爭等諸多爭議,轉而進行合作抱團。這種合作像是一種朋友間的握手言和,但更是創(chuàng)作者對中國電影市場的高度認知,對中國電影未來發(fā)展的深度認同下做出的選擇。
四、“短視頻”與“大制作”:“快時代”下的影像潮流
電影工業(yè)美學強調契合時代、應時而作。這是工業(yè)體系中作品創(chuàng)造于人、服務于人、回饋于人的回環(huán)鎖鏈中,所形成的天然場域。盡管在這條工業(yè)體系中,創(chuàng)造者創(chuàng)造的是一系列非實體的“文化經濟的商品”,但這些“商品”也成為“意義和快感的促發(fā)者”[9](P31)。因此,創(chuàng)作者便不可忽視受眾群體的整體期待和現實渴望。在互聯網時代,“短”便是這種整體期待和現實渴望的集中顯現。隨著“電腦和手機的功能逐漸趨同”[10](P726),視頻的碎片化傾向已經成為大勢所趨,人們更希冀利用碎片時間觀看碎片視頻,從而更為高效地滿足自身的收視需要。在此情景下,短片的制作,便更加貼近了受眾的觀看需求、順應了時代的影像潮流。《我和我的祖國》盡管是一個整體一致、單珠成串的集錦,但仍舊可以分割為7部各自成篇的滄海獨珠。這與早年具有段落結構特征的《愛情麻辣燙》《萬有引力》等影片不同,它不再是“形散神不散”的文字游戲,也不是通過結構性處理后的情節(jié)拼湊,而是幾個故事各自獨立成篇的精彩合集。這樣的短片合集,通過大銀幕的方式呈現出來,不僅對于故事的講述時間,加以重新的界定,更對電影的時間長度,進行了大膽的嘗試與突破。值得一提的是,時間的改變,必定帶來一系列電影元素的改變。
實際上,每一個故事以短片的形式出現,觀眾可以直觀的感受到創(chuàng)作者對于這一選題的情節(jié)壓縮。如《相遇》實際上大大壓縮了方敏這一角色的前史,而將方敏與高遠的愛情凝聚在公交車上的長鏡頭之中;《白晝流星》壓縮了少年成長的轉合,以至于使得米利埃主教式的救贖與觀看飛船返航的心靈重建稍顯斷層。壓縮是創(chuàng)作過程中一次迫不得已的時間重組,但隨著劇情的壓縮,高潮跌宕的情節(jié)也演變?yōu)槎唐缹W的一大傾向:在短片《前夜》中,一晃而過的個體、今夕前夕的對照、家庭與事業(yè)的取舍,都緊湊而連貫的一筆帶過,成為“國”之背后的點點繁星;在短片《回歸》中,升旗手朱濤、女港警蓮姐、外交官安文斌、修表匠華哥,也指代了一個又一個身份各異的群體,成為你我雖各異,心愿卻相聯的“回家”禮贊;在短片《北京你好》中,一張奧運會開幕式門票,鏈接了兩段父子的情感,成為情感救贖路上的通行證。這些情節(jié)性的壓縮與強化,實際上極大程度地服務于短片美學的創(chuàng)作之路,成為銀幕新形式的一次集體展望。
另外,短片的形式,實際上也為工業(yè)內容的產業(yè)化之路,提供了一條路徑。畢竟,合則一團火、分則滿天星的集錦方式,直接便于影片進行二度傳播,即通過網絡形式,實現整合傳播的同時,也實現了各自的碎片化傳播。影片《我和我的祖國》一經撤檔,便于愛奇藝、騰訊、優(yōu)酷等諸多網絡門戶上架,在超高票房的天頂之下,迎來了網播熱度的又一春。值得一提的是,分段化播放、抑或取舍式觀看,成為該片的一大觀影選擇,這也極大地迎合了網絡播放空間的個性化設置。
盡管影片以短片集錦的形式呈現給觀眾,但卻并不同于以往的短片產業(yè)格局,表現出了“大制作”的一面。《我和我的祖國》由華夏電影主控投資,華誼兄弟、文投控股、萬達電影、金逸影視、華策影視等公司聯合出品。盡管華誼兄弟一直不便于告知該片的具體投資金額,但高配置的制作團隊、逼真的歷史場面、高能的攝制安排以及精準的服、化、道設置,都體現出該片精益求精的追求,宣告了本片的“大制作”格局。在“主旋律”獻禮大片的旗幟下,諸多具有頂級流量的明星傾情加入,選擇“零片酬”參演。這樣一來,在整個工業(yè)流程中,原本占投資比例極高的支出內容轉變?yōu)榱悖蛊渌麅热菰黾映杀静⒁源颂岣弋a品質量。換言之,這一舉措使得各投資公司的投資金額大幅度側重于影片制作,電影質量也獲得了顯著提升。值得一提的是,7部影片中制作難度最大的《前夜》,更是直接表現出規(guī)模足、場面大的創(chuàng)作格局,整部短片不僅外景全部采用特效,更是組織了大量的演員參與、游走在畫面之中,以制造開國前夜的興奮狀態(tài)。其他6部影片,雖然在難度上不比《前夜》,但也傾盡了創(chuàng)作者的全力。在這樣的大制作模式下,《我和我的祖國》在國慶檔一路高歌猛進,上映首日便累計票房2.44億元,36小時更是突破5億元的票房大關,最終收獲了31.14億元的票房佳績。
五、“分工化”與“合流化”:產業(yè)形態(tài)下的探索與優(yōu)配
“進入新世紀后,‘文化產業(yè)’成為中國的國家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電影又與‘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連在了一起。”[11](P7-15)實際上,產業(yè)的完善,離不開電影從生產到營銷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它意味著無論最初的創(chuàng)意、策劃階段,還是最后的宣傳、營銷階段,都是電影工業(yè)產業(yè)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合環(huán)節(jié)。電影工業(yè)美學的實現,離不開創(chuàng)作者的分工與合作,甚至可以說,脫離了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共贏約定與互助原則,便不足以稱之為“工業(yè)美學”。換言之,合作是建立工業(yè)系統(tǒng)的基礎,共贏是實現工業(yè)流程的公約。在《我和我的祖國》中,分工的細化更是遠大于一般,它不僅要求各鏈條的具體分工得當,更囊括了7組風格鮮明而具有不同經驗的組合。
在具體的導演主創(chuàng)選擇上,作為總導演的陳凱歌率先被選中,成為整部電影的領頭羊。作為總制片人的黃建新,原本有執(zhí)導一部影片的可能,但他考慮到自己作為總制片人,需要完成具體的制片工作,因此便把這一位置空了出來。黃建新與陳凱歌等人一同,在一份長長的導演備選名單中,篩選出其余6位導演。黃建新指出:“有的導演在戲上不能過來,有的還有某些別的事情,最終就落在了這7位導演身上。這7位導演都挺高興,欣然接受。”通過最初策劃的內容,7位導演選擇了自己樂于且擅長的故事,并分頭同總制片人黃建新以及總導演陳凱歌細談自己對于這一題材的構想、故事的安排以及人物的設置。7位導演再根據具體的構想,尋找合適的編劇,配合自己完成故事的創(chuàng)造。正是由于這種分段、分層的工業(yè)化創(chuàng)作方法,使得7個電影劇本皆于春節(jié)期間順利提交。
在具體的故事創(chuàng)作完成后,接下來的影片拍攝制作環(huán)節(jié)便顯得尤為重要。盡管7部影片僅是時長在20分鐘到30分鐘區(qū)間內的短片,但使用一個劇組線性、連續(xù)的拍攝,卻顯得耗時耗力。因此,黃建新并未考慮一個組“連拍”或者兩個組“分拍”的傳統(tǒng)創(chuàng)作模式,而是采用更具工業(yè)化形態(tài)的分頭制片方式加以創(chuàng)作。實際上,分頭制片的策略,不僅減少劇組與導演之間的磨合期,直接地縮短拍攝時間,更能有效地調動7位導演,選擇適合自身且相對高效的拍攝隊伍。對于總制片黃建新而言,7個劇組分頭制作對于導演而言是釋放,對于自己而言更是松綁。在這樣的調整與設置下,7個劇組分別設置了相應的制片人,且這些制片人皆是導演慣常的合作伙伴,譬如《前夜》的制片人朱文玖是管虎的老搭檔,同管虎合作過《斗牛》《殺生》《老炮兒》等作品;《奪冠》的制片人劉瑞芳、陶虹亦是徐崢的合作伙伴,同徐崢合作過《港囧》《我不是藥神》等作。在這樣的具體分配之下,黃建新只需要對各組的制片人進行管理,完成統(tǒng)籌制片。正是由于流水線式的分工方式,使得《我和我的祖國》的制片于管理而言更具協(xié)調,于制作而言更具效率。
盡管該片顯現出“分工化”的工業(yè)傾向,但也表現出“合流化”的工業(yè)流程。實際上,兩者之間并非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互為協(xié)同的表里。首先,該片的“合”體現在風格上。在以往的電影中,工業(yè)美學的合作流程往往是通過導演、編劇、攝影、后期等各部門的協(xié)調加以實現的。與之不同的是,集合了7位導演創(chuàng)作的《我和我的祖國》,在合作的流程上便顯得更具復雜性。換言之,創(chuàng)作者為了“和”而采取了折中、“平均”的處理方式,這也正與電影工業(yè)美學所強調的“大眾化,‘平均的’,不那么鼓勵和凸顯個人風格的美學”[12](P32-43)相一致。
在《我和我的祖國》中,整部影片都在“追求塑造的就是偉大歷史瞬間中發(fā)揮價值的普通人”[13](P69-76),這也是影片一致性的起點。另外,在宏大敘事和個人敘事之間尋找契合之處,也是創(chuàng)作中不可規(guī)避的難題。影片選擇了幾個相對典型的范式,使7部影片得以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我和我的祖國》通篇都借助歷史素材,打開了真實與虛構間的一扇窗。在《前夜》中,影片的首尾段落,通過相關的歷史紀錄片和新聞素材,使得觀眾從虛構的劇情中,建立起真實的觀念。值得一提的是,在開國大典上,林治遠走向人群、佇立于毛主席身后的素材,是通過修復舊素材并再度著色、摳圖成像所形成。我們也隨著演員黃渤的走進而真正身臨到那段激動人心的歷史高光時刻之中。在影片《相遇》中,導演同樣借助真實素材建立具有真實感的歷史語境,當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畫面出現在方敏與高遠之間,個體的情感與國家的榮辱瞬間建立起了直接的關系,高遠的犧牲變得愈加偉大。在影片《奪冠》中,女排比賽的素材,作為第二敘事時空,直接牽連著冬冬的悲喜,它也同緊張、刺激的冬冬“戰(zhàn)場”,形成了超越空間的共振。《回歸》中香港回歸現場的真實素材、《北京你好》中的奧運會開幕式素材、《白晝流星》中的宇航員真實參與素材以及《護航》中的閱兵式素材無不如是。
其次,《我和我的祖國》還表現出了資源上的“合”。早在《建國大業(yè)》《建軍大業(yè)》《建黨偉業(yè)》等獻禮片上映之際,觀眾便大呼“數星星”。所謂“數星星”,即一語雙關地交代了影片中出現的明星龐大,多如繁星。作為總制片人的黃建新,在此次影片中更是糾集了一眾演員、明星進行參演,明星數量高達50余人。其中,黃渤、張譯、吳京、杜江、葛優(yōu)、劉昊然、陳飛宇、宋佳、王千源、任素汐、馬伊琍、朱一龍、佟麗婭等一眾演員,更是極具票房號召力的一時之選。可以說,這樣的集合,極大程度上利用了明星的人氣,通過明星效應與粉絲經濟的完美搭橋,加大電影的宣傳力度。總制片人更是集合了最具影響力的7位導演,集合創(chuàng)造力的優(yōu)勢,使得整部影片呈現出群星薈萃的觀感,并引之成為大眾茶余飯后的談資。這也是“主旋律”電影,特別是“獻禮片”的價值之所在。更值得一提的是,隨著7位導演的介入,頗具經驗的制作團隊,也紛紛加入其中。可以說,影片在整合導演資源的時候,同時整合了導演的粉絲和人脈,整合了宣發(fā)資源。
最后,影片同樣在營銷與宣發(fā)環(huán)節(jié),表現出集體發(fā)力、共振的事勢。影片由統(tǒng)一的發(fā)行團隊進行統(tǒng)籌發(fā)行,其中包括華夏電影發(fā)行有限責任公司、聯瑞(上海)影業(yè)有限公司、上海貓眼影業(yè)有限公司、新麗電影發(fā)行團隊、五洲電影發(fā)行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光線影業(yè)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等經驗豐富的發(fā)行團隊。在營銷上同樣如是,該片由北京果然影視文化有限公司、霍爾果斯青春光線影業(yè)有限公司、EPK制作、斐然傳播集團等團隊聯合營銷,共創(chuàng)未播先火的氛圍。各營銷公司在網絡平臺上不僅搶占了話題,更是憑借精心制作的預告片,讓中國影迷熱血沸騰。與此同時,憑借《我和我的祖國》熟悉的旋律,以王菲特有嗓音演唱的同名主題曲MV,更是成為宣傳中的焦點。除此之外,“表白祖國”的線下活動,作為產業(yè)鏈條中的一部分,同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功效。
結語:全案整合評估及對中國“主旋律”電影未來發(fā)展的思考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華誕,2019年度的國產“主旋律”電影既不缺乏數量,又實現了質量的飛躍。在娛樂大片橫行的時代下,國產“主旋律”電影不遺余力地發(fā)揮著自身的宣傳與教育使命,實現了傳遞文化自信、發(fā)揚文化自覺的總體目標。值得一提的是,該年度的國產“主旋律”電影表現出整體高票房的走向,而《我和我的祖國》更是以31.14億的總票房成績脫穎而出,伴隨著國慶70周年的激情時刻,顯得余味綿長。《我和我的祖國》可以說是一次“主旋律”電影的突圍,透過這次突圍,我們也不難發(fā)現,“主旋律”電影的創(chuàng)作之路并非獨木一條。《我和我的祖國》既是“命題性”與“能動性”協(xié)調下的結果,又以“小人物”與“大歷史”的形式,完成了產業(yè)經驗與文化價值的完美對接,它還通過“老導演”與“新導演”的同臺演繹的方式,展現出資源合力下的百花齊鳴,它是“短時代”的產物,又是“大制作”的體現。最為重要的是,它通過“分工化”與“合流化”的搭建,彰顯了產業(yè)形態(tài)下的探索與優(yōu)配。總而言之,《我和我的祖國》契合了電影工業(yè)美學的發(fā)展之路,用聚合之火點燃了滿天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