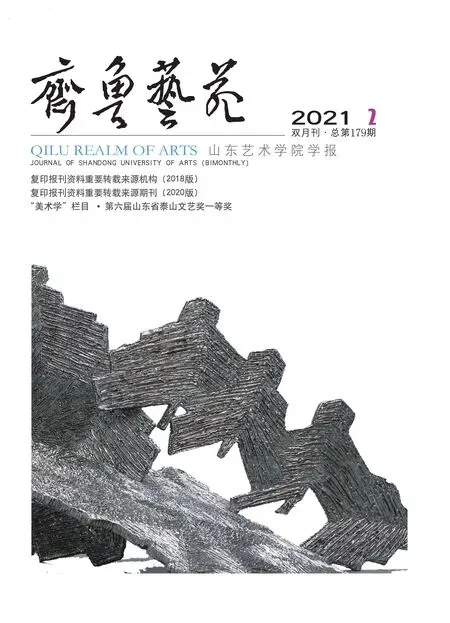電影工業美學視域下的作品呈現
——以《中國機長》為例
潘國輝,張明浩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北京 100871)
近年來,中國影視行業大步向前,年度總票房不斷攀升,中國電影生態版圖呈現出多元、平衡之態勢。但災難類型電影一直未有長足的發展,相對比于好萊塢而言,中國的災難電影在質和量上都相差甚遠,遠未形成一個可持續的類型。[1](P62-77)2019年,《流浪地球》《烈火英雄》《中國機長》的出現,可謂給中國災難類型電影的發展帶來了希望,讓導演與受眾都看到了災難片的現實意義與票房價值,感受到它們在弘揚主流價值觀、塑造平民英雄的同時,也“感動了影院內外的大量觀眾,在中國電影里成就了一種淚水深埋的英雄敘事”[2]。而作為獻禮片,改編自熱點事件的《中國機長》更是對災難、主旋律等關鍵詞進行了融合與超越,在工業呈現的同時,對崇高美學進行了平民化書寫,極具研究意義與借鑒價值。
一、工業呈現:系統化的工業式制作與“體制內宣發”
“電影工業美學”體系大體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側重于文本、劇本,也就是內容層面。第二,側重于技術、工業層面。電影是視聽藝術,需要視聽的震撼力。第三,側重于電影的運作、管理、生產機制的層面”[3](P18-22)。具體到制作而言,電影工業美學要求“在電影生產過程中弱化感性的、私人的、自我的體驗,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標準化的、協同的、規范化的工作方式,力圖達成電影的商業性和藝術性之間的統籌協調、張力平衡而追求美學的統一”[4](P18-22)。《中國機長》所呈現的工業化,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影片系統化、協作化的制作;二是影片對技術高要求;三是影片生產與宣發的協作化;四是影片緊跟體制的宣發策略與工業式宣發布局。
(一)技術、制作層面的工業化運作與自覺
首先,進行技術化探索,進而表現出一種工業化追求。[5](P29-33)據悉,《中國機長》在視覺呈現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劇組花了近3000萬專門搭建了1∶1的空客A319模擬機,并且請來了為《星球大戰》《美國隊長》《雷神3》制作特效的好萊塢團隊,為影片后期提供了強大的技術保障。所以,在飛機遇險時刻的場景中,經由驚險氛圍的營造,給觀眾帶來了震撼的視覺體驗,最大限度地還原了觀眾對真實飛行體驗的感知認同。
不僅如此,影片還自覺進行了技術創新,表現出對“技術化生存”的一種主動探索。“《中國機長》技術負責人王寶撥透露為精準還原當時的情況,此次運用了不少國內首創的技術:首次實現三艙聯動,誤差不超過0.1度,并且首度實現了用平板電腦控制飛機,實時響應速度不超過10毫秒,能夠實現飛機的俯仰、滾轉、顛簸等多個動作的精準操控,確保完美重現當時事件的情景”[6]。所以當表現飛機遇險情景時,電影為觀眾呈現了身臨其境的視聽感受,飛機飛行時的全景呈現、旋轉晃動的鏡頭、逼仄壓抑的封閉空間,緩慢裂開到瞬時爆炸的風擋玻璃、身體懸在半空中的副駕駛員、電閃雷鳴以及槍林彈雨般的冰雹等,一切的鏡頭、特效、聲音,將觀眾全身心地帶入到影片虛擬情境的同時,也是中國電影工業進步和美學升級的有力見證。
同時,《中國機長》還運用了構成杜比影院效果最核心的技術——杜比全景聲(Dolby Atmos)和杜比視界(Dolby Vision),“杜比全景聲打造的左右前后和上方環繞效果,以及杜比視界100萬比1的超高對比度,能夠讓觀眾在杜比影院感受到非常不同于普通影廳的觀影效果”[7]。影片運用“杜比聲”技術,以聲效手段達到了敘事抒情層面的審美訴求。強烈咆哮的風聲、劈里啪啦的冰雹擊打聲、電閃雷鳴聲等增強了影片的敘事張力,為觀眾帶來了感同身受的驚險體驗。
其次,表現出系統、協作、高標準、高要求的工業化制作水準。據《中國機長》IP授權書(1)《中國機長》IP授權書由《中國機長》項目組孫塵老師提供,具體項目采訪以及IP授權書重點內容,參見陳旭光,范志忠主編. 中國電影藍皮書(2020)[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顯示,影片2018年12月創建項目組、2019年3月20日殺青、2019年4月到6月步入后期制作、2019年9月30日上映,由此,僅僅不到一年時間,便完美地實現了“建組-拍攝-制作-宣發-上映”的全環節覆蓋,其中涉及的緊密協作與高效運轉的體系化價值便不言而喻。在演員導演合作方面,演員在劇本完成前便紛紛到組學習,乘務員學習飛行知識、機長學習駕駛知識、導演則負責各方統一調配協調;在飛機制作方面,為真實還原高質量的現實原型,導演與技術人員多次前往國外取經,并且取得了三艙聯動等技術突破;在后期協調方面,飛行顧問、乘務顧問、機場、消防、醫務等各方工作人員與電影制作人員溝通協作,才得以使影片再現真實……諸多實例均直接佐證了影片工業化特質,也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踐行電影工業美學生產制作觀念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制作上的工業化、協同化,還體現在民航公司對影片拍攝的幫助上。作為事件原型的四川航空,對于影片制作的支持可謂是自始至終,從前期出品,到后期發行,都有所涉及。在人員方面,川航機組英雄們與演員們不斷溝通,促使影片對其真實經歷做了完美還原;在培訓方面,川航則為演員們提供了專門的培訓,飾演機務組成員的演員,在四川航空培訓中心接受特訓,川航為其安排了專門的培訓老師;在宣發方面,川航官網緊隨熱勢,助力影片宣傳。另一方面,被眾人稱贊的“萬米高空首映禮”,便是在四川航空3U8803的航班上舉辦。此外,影片的成功離不開整個民航系統的協助,導演多次表示在拍攝過程中,得到了上千民航人的支撐與幫助,如管轄較為嚴格的成都機場、重慶機場,全部開放為攝制組提供拍攝場地。劉偉強也曾在采訪中表示拍的過癮,“你在一個真的飛機上拍,機場給拍,十多部消防車給拍,你還想怎么樣?真的很榮幸能拍這個電影”[8]。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影片與整個民航系統的關系是相互的,民航給了影片以生產制作層面的支撐,影片也給川航甚至是整個民航系統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獲,即受眾的理解、認同與尊重。所以說,影片的工業化不僅僅是影片內部協作式制作,更在于整個民航系統等外在機構對于電影項目的大力協助,于此,內外之間都做到了系統、協作式的工業化生產。
不僅如此,這種生產運作層面的工業化呈現,還體現在生產與宣發的緊密聯動方面。縱觀整個項目業務開發節點,自11月便開始進行評估、市場調研,拍攝過程中便開始進行品牌營銷,上映前已經做好所有準備工作……此種系統化配合生產與協作式的運籌帷幄,可謂工業化生產的典型,一方面影片在上映前不斷調整宣發策略,保證在全線上映時擁有一定數量的粉絲基礎與品牌基礎,進而保證影片受眾;另一方面,制作與宣發調研的同步并行,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影片后期宣發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緊跟體制的宣發策略:真實改編、國慶獻禮與“歌頌平民英雄”的助力
根據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機組成功處置“特情”真實事件改編的《中國機長》,可謂是在“熱點”的保駕護航下取得成功的。毋庸諱言,當下很多影片的宣傳都要與社會熱點話題相結合,而本身便是基于社會真實熱點新聞進行文本重構與影像轉化的《中國機長》,顯然是自帶流量的。在此基礎上,它還擁有著“獻禮片”的頭銜,并且扎根在“歌頌平民英雄”的社會語境下。于此而言,如果說影片的成功與宣發、影片質量等密不可分,那么在宣發過程中,熱點、政策、題材可謂是影片的“自來水”式助力者。
縱觀中國當下收獲高票房的電影作品,無論是現實主義題材的《我不是藥神》,還是“新主流大片”《戰狼2》《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都是基于真實事件進行影像化重構的佳作。但對比如上作品,《中國機長》則表現出獨特性,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影片改編的熱點發生于2018年,時間距離較近;另一方面,對比以往“白血病”問題、軍隊愛國之舉等距受眾較遠的真實事件而言,飛機遇難這一真實事件更貼合民眾實際生活,更接地氣也更具討論意義,因為國民出行是在所難免的事情,所以大眾本身對于這一“社會熱點”的關注度與討論度必然較為強烈。與此同時,真實事件中的職業英雄、平民英雄,也都是日常生活環境里所常見的普通人,更具親和力與話題感。如果說人們觀看《戰狼2》等作品,是從中獲得國家榮耀與民族認同的話,那么《中國機長》背后的熱點事件,便是使受眾感受個體認同與職業歸屬的想象建構。所以,與《攀登者》講述在時間和認同方面距離受眾較遠的登山隊故事相比,改編自“川航成功降落”這一真實社會熱點的《中國機長》似乎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在親和力與話題性上的天然優勢。盡管前者有著吳京、章子怡、胡歌等國際巨星與銀幕翹楚的助力,但影片最初的文本話題性與現實感顯然是不及后者的,而正是基于此種在時間、認同、親和力距離較近的“真實事件”,影片才得以拿到宣發的關鍵詞與突破口——尋找觀眾的“共情之處”。
如果說川航事件是宣發著力的重要地基,那么“獻禮70周年”的定位與“歌頌平民英雄”的社會環境,則是影片成功“出圈”的兩雙有力翅膀。
自項目獲得審批后,便帶著“獻禮”任務與光環書寫的《中國機長》,可謂是以平民/職業英雄的名義,致敬國慶70周年,頌揚每一位兢兢業業、堅守崗位、認真負責的普通人。而“獻禮”的定位與光輝,也在某種程度上,為影片贏得了受眾認可與話題熱度。一方面,各大影院獻禮三部曲的捆綁式宣發策略,使影片似乎成為國慶檔必看片目之一,大部分觀眾似乎都會在三部中選擇兩部或以上進行觀看,以此在社交圈層完成發聲交流,因為相互對比討論、商榷仿佛是人們自我表達的最好方式。正是基于此種社交“場域”,《中國機長》有了一定意義上的直接受眾群體。另一方面,獻禮片作為中國電影生態發展中的關鍵影片類型,對于電影的本體研究、社會研究、文化研究等具有重要意義與價值,而其必然會促進一大批影視行業專家、學者、學生等相關人士加入到這一話語言說的行動之中,正是于此,電影的話題性與現實感,都得到了相應的提升。
于當下社會文化環境而言,《中國機長》立足了“頌揚平民英雄”的社會文化語境,在意識形態、主旋律的表達方面,也十分貼合受眾之心。縱觀當下社會楷模,可以發現,大部分都是出自平凡崗位的平凡人物,為國家和人民無私奉獻、盡職盡責。近年來,一直開展的“感動中國十大人物”評選等系列主題活動,便得以看出當下社會對職業英雄、平民英雄的重視。在此背景下,《中國機長》的創作、宣發可謂如魚得水,無論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川航機務組的高度肯定與贊譽,還是社會大眾對英雄群體事跡與經歷的廣為傳頌,都在直接助力電影的宣發推廣。值得一提的是,影片項目組曾于2019年春節聯歡晚會與全國人民見面,在新年之初便讓廣大受眾產生相關審美期待,無疑是最為廣泛也最為正統的宣發。此種宣發模式可謂前無古人,而其模式成功的背后,離不開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的支持,更離不開“頌揚平民英雄”的社會語境支持。
綜上,從內在真實事件的文本基礎到外在社會語境的認可,《中國機長》的宣發,可謂占據“天時地利人和”,正是此種順勢而為的模式應用,才得以使影片在三強爭霸中立于高地。而此種基于“體制內”且充分發揮其優勢的宣發思路,也恰恰為電影工業美學在同等環節的探索,提供了一種類似“體制內作者”的途徑與經驗。
值得一提的是,該片的工業式宣發,還體現在它的品牌合作以及與品牌之間的雙向緊密協作方面。影片與220個品牌進行了合作,品牌緊跟影片宣發節點、全程深度參與的合作方式,為實現雙贏打下了堅實基礎。在營銷大事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品牌的助力與支持,如“萬米高空首映禮”中,片方為乘客準備的禮物,便是由金士頓與出品方推出的聯名款禮盒及紀念版內存盤等;又如“重慶解放碑線下首映會”中,粉絲便通過華為榮耀智慧屏PRO進行遠程連線參與。與此同時,品牌與電影的密切協同,還體現在二者的深度捆綁式合作上,以WEY高端汽車品牌與《中國機長》的合作為例,品牌前期在海報與TVC等方面與電影緊密相連,并且依靠電影的傳播熱度,又自動發起“征集擔當故事”的活動,進一步增加了作品的曝光度,延長了影片的熱度。綜上,電影與品牌相互配合的宣發方式,也是一種協作化、系統化、整體化的工業式呈現。
二、美學表達:“崇高”的平民化書寫與主流價值觀念的傳達
電影工業美學要求電影制作過程中要尊重受眾、遵循“常人之美”的生產制作理念。作為新主流大片的《中國機長》便在美學方面,呈現出一種“大眾的美”,它不僅將距離普通受眾較遠的“崇高美學”進行了平民化書寫,而且還以小見大,以主流價值觀念認同的方式,完成了對災難母題超越的藝術呈現。[9]
(一)崇高美學的平民化書寫
“崇高是在表現那些在現實中可能是痛苦的或是可怕的東西時所產生的愉悅的體驗”[10](P19)。崇高往往還與犧牲、拯救、英雄等有關,拯救眾人的英雄或神(又或者是人根本無法觸及的事物),都可以使大眾產生一種崇拜感與向往感,這種由無法觸及而帶來的壓力,轉化為的欣賞、向往、崇敬,便是崇高所產生的美感。《中國機長》憑借飛機駕駛員臨危不懼的應變能力、空中乘務員的安全指引與情緒撫慰操作、乘客的有效配合行動、地面各個部門的協調引導處理等多方努力將飛機安全降落,在此基礎上將一個轉危為安的災難事件升華到一個崇高文本。這種崇高的平民美學,賦予觀眾的不僅是個體心靈層次的震撼,更是人類對于敬畏生命、敬畏職責、敬畏規章的深度思考。
影片對崇高美學的平民化書寫,最為顯著的體現在該片對英雄人物進行了日常化的藝術處理,將崇高的主體變為了蕓蕓眾生之中的普通職業人員,進而拉近了受眾與“崇高”之間的距離。
其一,對崇高主體進行群體化書寫。如果說機長劉傳健在故事中作為主英雄的話,那么對于第二機長、副駕駛員來說,他們無疑是輔英雄,甚至航班組的所有人員,在這次飛機事故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在飛機還未落地,民航局、軍隊、醫療、安保、消防等各個部門就已預先啟動,密切配合,響應指揮,為飛機的降落和乘客的安全提供了支持保障。所以,《中國機長》不再強調英雄個體的價值彰顯,而是注重營造一種“生命共同體”,或者說,在這種共同體敘事下,歌頌英雄集體所發揮的強大作用,即:成功往往不是一個人的成功,而是眾人共同努力的結果,這也符合中國傳統團結協作的文化價值觀,因此具有非常強的現實意義。
其二,對崇高主體加以職業化呈現。《中國機長》顯現出來的不是那種超人式、舍小求大的英雄形象,而是帶有職業個人操守,有著良好應變能力的平凡群像。機長劉傳健這一角色的塑造,符合觀眾審美期許,更易于被大家接受。他在突發事件中的成功處理與應變,靠的不是天賦.,而是那種日復一日式的自我嚴格要求和勤奮訓練,把日常的平凡做到不凡。在電影的開篇部分,他堅持洗冷水澡,在冷水中屏住呼吸3分鐘,這些堅持不懈的習慣培養,都為應對緊急危機時刻,提供了強有力保證。很顯然,在這次機體故障中,機長劉傳健以臨危不懼的心理狀態應對,最終將飛機成功降落,靠的就是將平凡簡單的工作,進行了不凡的自我訓練準備,最終將平凡之事轉化為不凡作為。在此基礎上,《中國機長》似乎賦予了英雄新的含義,即:在關鍵時刻用自己扎實的專業技巧和良好的職業操守挺身而出,化險為夷。
其三,對崇高主體賦予非性別化特質。新英雄主義的另一種體現,便是“英雄的非性別化”[11](P159-166),即對女性英雄形象的彰顯。這種女性英雄形象,在近年來的主旋律大片中,也有所體現。比如《紅海行動》中,由海清飾演的夏楠、蔣璐霞飾演的佟莉;《戰狼2》中,由盧靖姍飾演的Richael、余男飾演的龍小云等,都是新時代的女性英雄形象。而《中國機長》呈現出來的,便是乘務長畢男及4位乘務員的職業女性英雄群像。從飛機起飛開始,她們用熱情周到的服務有效應對乘客刁難,到飛機遇險時臨危不懼地指引、調節整個機艙內部人群的情緒氛圍,無一不體現了責任、擔當、勇氣和專業能力。所以,《中國機長》改變了很多人對空乘職業“端茶送水”的刻板印象,向觀眾呈現了一個個女英雄形象,可以說是對以往的“男尊女卑”說法的有力顛覆,對“女人撐起半邊天”說法的再次突破,更是女性群體從“女人到女強人再到女英雄”這一過程的有力佐證。此外,這種英雄的非性別化,也呼應了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男耕女織”的性別協作配合,成就了“英雄必然有美女加持”的人物設置,為《中國機長》在藝術審美層面,形成一道靚麗的身體美學景觀。
最后,對崇高主體實施平民化“升格”。電影在進行人物塑造的時候,沒有著意去刻畫某一鮮明特征,而是把其塑造得更加接地氣,更符合觀眾審美期許的普通人特質。拿機長劉傳健這一角色來說,影片并沒有夸大職業屬性上“高大全”的角色功能,而是把他塑造成了一個凡人。作為一名父親和丈夫,他有著 “暖男”特質;作為一名機長,他顯現出“高冷”的性格和扎實的專業能力。同樣,由歐豪飾演的副駕駛員徐奕辰,也被塑造成了活潑幽默、愛開玩笑的大男孩兒形象,其插科打諢的喜劇風情和機長一臉嚴肅的冷峻,形成了藝術創作上的有力互補。此外,由杜江飾演的第二機長也有著近似“撩妹”的鮮活舉動,其向美女炫耀自己“機長”職位的行為,本身就帶有源自生活與人性本身的豐富蘊含。所以《中國機長》呈現的,不再是傳統電影中有著神性特質的主流英雄形象,而是一個個符合當下現實更被觀眾所認可接受的圓形人物。雖然這樣第二機長、駕駛員的形象,略顯淺薄和輕浮,并且有悖于觀眾認知經驗里“高大上”的職業形象,但這不是編劇的最終目的,而是在緊急事件到來之際,讓人物帶著職業責任和經驗挺身而出,從而完成對英雄價值的再認知,達到英雄精神升華的目的。
(二)主流價值觀念的彰顯與傳達
首先,彰顯了集體精神與職業精神。如前文所述,影片對英雄進行了集體化、平民化、職業化處理,也正是這種處理,傳達出作品背后獨特的中國集體主義文化認同與價值觀念以及職業精神。該片中無論是強調系統整體的重要性,還是未有事后追責的情節設置,都呈現出了中國集體主義精神的內涵價值,一方面突出系統協作、強調團隊合作,與當下強調“人人都是社會一份子,都可建設社會、發展社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相符合;另一方面,于大團圓處戛然而止的設計,與中國百姓所推崇的“大圓滿”“合家歡”不謀而合,進而滿足了受眾審美心理期待,體現出獨具東方意味的圓滿意識。同時,“職業英雄人物群像”的設定,亦在彰顯當下社會對平民價值觀念的推崇,強調時代倫理觀念對“職業英雄”“平民英雄”、職業精神的重視,也為“新主流”大片的書寫拓展開辟了新的路徑。
其次,凸顯“生命共同體”的價值觀念。飛機作為災難的發生地與其承載空間,具有劃分、集合的作用。事發時,封閉空間中的乘客與乘務人員被加入到“災難共同體”的認同序列中,作為災難承受者與自救者的受難人,也便意識到團隊合作與集體協作的重要性。換言之,災難本身便具有“共同體”性質,而災難的化解,更是離不開“生命共同體”的集體協作。當災難可能到來之時,機上乘客躁動不已,但在乘務組的疏導下,開始配合工作,機務人員的一句“我們也想回家,我們也有父母子女”,道出了機務人員/乘客二者的“共生性”,進而隱含著“我們是一個集體,你們需要配合,才可以共渡難關”的深層意義。另一方面,影片以大團圓結局落幕的設置,也隱含著“共同體美學”:機艙乘客與機務人員作為一個“災難共同體”,在危機過后一起攜手渡過難關,亦體現出災難后“共同生命體”的“同生性”。
再次,突出個體價值觀念與生命意識、平等意識。對比《烈火英雄》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義”情節設置,《中國機長》中的人物行動是出于職業素養慣常養成。如上文所述,飛機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是英雄人物被動加入后,為自己生命安全而主動加以營救的實踐行為,但《烈火英雄》中,主人公是主動加入救援拯救人們的非常英雄。由此比起《烈火英雄》中人物,為救大家而舍小家的構設,《中國機長》中為“小家”進一步“救大家”的設計,顯然是更為接地氣、也更為符合當下時代價值觀念的認知。從主人公出發點,便可窺見影片背后的文化內核,前者江立偉是為“義”,是一種擁有家國情懷與崇高追求的職業英雄,而后者是為“己”,為回家團圓,為都能平安,是一種基于最深處的生命意識與平等意識后的職業行為。于此而言,作為獻禮片的《中國機長》,表達此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價值觀念,是頗為大膽的,也是頗為務實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當下社會對職業平等、生命平等的倡導,也在一定意義上,彰顯了影片所力圖傳遞的個體價值觀念與生命意識、平等意識。
最后,表述當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與以往大多數主旋律電影中以“執行特殊任務”為故事出發點的設置不同,《中國機長》的故事出發點是一次平常的工作任務,更為普遍,也更契合受眾日常,體現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理念。以往大多數“新主流”大片中的英雄們,是以“保衛家國”為出發點,而《中國機長》講述的,則是一群受過嚴格訓練的普通職員,依靠其職業素養與專業技能解決工作中遇到的突發事件,進而拯救工作范圍中普通人的故事。影片中主人公行動的出發點是完成工作、順利保護乘客安全。顯然,它沒有以往我們慣常所見的“新主流大片”那樣宏大崇高的主題立意,但它的故事卻更能引起普通百姓的共鳴:盡管前者在呈現反抗敵人、收繳毒販的場景中,給受眾帶以足夠的視聽震撼與精神激蕩,成功喚起了觀眾的愛國之情,但“執行特殊任務”的人群有限,并無法直擊到大眾的切身生活,而“出行安全”卻是每個普通人都十分注意且必須要面對的話題。所以《中國機長》是在以往新主流大片“家國敘事”的基礎上,進行了“平民化敘事”的創新,體現出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主要發展思想與核心價值觀念。
綜上,《中國機長》對災難這一類型進行了本土化改造,一方面加入了中國集體主義價值觀念,另一方面也融匯了西方個體生命意識認知,在頌揚群體英雄、表贊職業英雄的同時,力圖形構關于“生命共同體”理念的話語主體。
結語
作為國內為數不多改編自重大熱點事件的影片,《中國機長》具有其特殊性。在一定意義上而言,“真實事件”的背景,也就決定了它制作、宣發的特殊性。于此而言,影片的成功,不僅為今后同類題材與類別的電影創作提供了借鑒,更預示著改編過的該類作品,具備強大的票房號召力與深遠的社會文化影響力。毋庸諱言,中國改編真實事件類、災難類電影作品目前數量還較為稀少,如果川航事件沒有轉危為安,其作為故事素材來源改編的可能性也是極小的,這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電影審查制度、國民不喜歡看悲劇的審美偏好等諸多因素有關。電影《中國機長》創作的可行性也是基于此種社會背景。一方面,它具有災難類型的特質,在奇觀化的視覺呈現、英雄成長敘事、緊湊的情節設置等方面,表現出與災難電影的神似性;另一方面,它又根據國民觀眾的審美趣味巧妙地轉變主旨內涵,設置了英雄成長歸來的敘事思路,呈現了“大團圓”“合家歡”式結局,傳達出“敬畏生命、敬畏職責、敬畏規章”的主題,靈活運用災難電影類型的敘事框架,既可以順利通過較為嚴苛的審查制度,又滿足了受眾“奇觀化審美消費”[12](P93-98)的訴求。所以說,《中國機長》是一部智慧之作、創作之作和時代之作。
但是值得注意與反思的是,影片巧妙轉化“災難”內涵,設置大團圓結局,就誠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災難”背后的意義、減少了影片的深度。和國外同類型電影《薩利機長》相比,《中國機長》對于“事件之后”的反思及“事發之因”的探索是缺失的,最后的航空管理局調查員(朱亞文飾)的檢查,也局限于一種例行公事。對于主人公事件之后的心理變化、災難創傷等也沒有深入表達,總體呈現出了一種“為視聽而視聽、為刺激而刺激”的單薄感,造成影片敘事上的縫隙,弱化了電影作品應該具有的人文價值與現實意義。所以毫不避諱地說,《中國機長》是缺乏反思的,它缺少一種直接揭露問題的現實性和關注主人公內心情感、使受眾深入思考的“人文性”。
誠然,反思是創新、發展的開始。一方面,中國災難類型電影相較于好萊塢,在質和量上還有較大差距,尚未形成一個獨立類型;另一方面,在一定意義上而言,災難電影類型應該是我們需要大力呼吁并進行大量創作實踐,而加以完善與形成本土特色的品類,因為它在營造災難奇觀、注重視效呈現的基礎上塑造英雄、謳歌人性,亦在持續傳遞勇敢、奉獻、仁義等主流價值觀念認同的品性精神。[13](P62-77)所以,中國的電影創作者可以經由《中國機長》的成功汲取經驗,對其不足之處加以改進,并在此基礎上,轉變藝術實踐秉承的觀念與方向,力爭推出更多傳播正能量、反思現實問題、呈現人性光輝、頌揚英雄人物的優秀電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