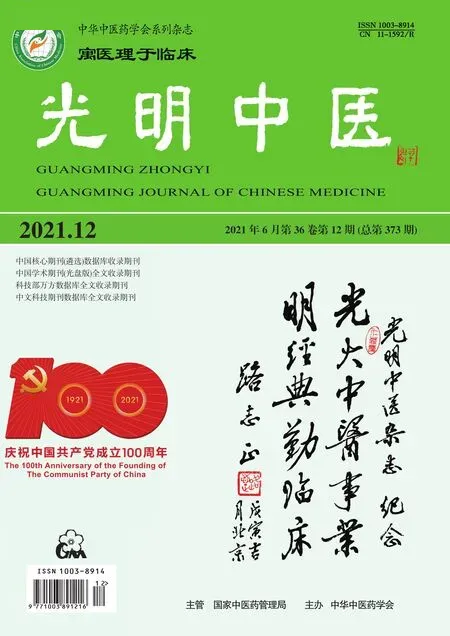李應東教授治療竇性心動過緩臨證經驗及驗案舉隅*
呂婭寧 宿 敏 趙信科 蔣虎剛 李應東△
李應東教授是甘肅省名中醫,博士研究生導師,岐黃學者。從事中西醫臨床、教學與科研工作30余載,對中西醫結合治療心腦血管疾病有豐富的經驗及獨到的見解。在治療疾病中尤其崇尚陰陽、“法于陰陽”,現將其臨證治療竇性心動過緩經驗總結如下。
1 從陰陽立論 心腎同調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明代張景岳《類經圖翼》認為“五行之理,交互無窮,……變雖無窮,總不出乎陰陽”。人體是陰陽協調平衡的統一體,即所謂“人生之本,本于陰陽”,故李教授認為慢性心律失常中醫辨證當首辨陰陽。《素問·六節臟象論》曰:“心者,生之本”,又“心主血脈”,心陽為“心主血脈”的動力源泉,心陽的溫煦和推動作用維持心臟正常搏動。心陽根于腎陽,如《素問·五臟生成論》云: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隨著年齡增長,臟腑機能逐漸衰退,心腎陽氣不足,鼓動無力使血行遲澀脈率減緩,故其病機以心腎陽虛為本,在治療上當以溫補心腎為主。
2 注重安神斂神 形神同治
《素問·靈蘭秘典論》謂:“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靈樞·邪客》謂:“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心有“主血脈”和“藏神”的功能,心陽不振一方面可致心神浮越渙散,進而神不內守,惕惕不安;另一方面,心之陽氣不足運血乏力,可致心神失養,表現出心悸、心神不寧,甚則精神恍惚、健忘,因此在治療中形神同治,常用酸棗仁、合歡皮、首烏藤、龍骨、牡蠣等安神、斂神之藥調養心神。
3 分期論治 標本兼治
李應東教授認為,疾病發展是動態演變過程,治療時也應分期緩慢圖之。心動過緩的病機為心腎陽氣不足,心腎陽虛致水寒內生,不能溫運血脈使血脈凝滯,又心陽虛損,行血無力而血行緩慢,停而為瘀,如《醫林改錯》所載: “元氣即虛,必不能達于血管,血管無氣,必停留而瘀”, 故臨證治療常先扶其陽而后通其瘀滯,標本兼治,以期氣血陰陽平和、互根互用,達到恢復心律之目的。
4 驗案舉隅
歸某,男性,56歲,2020年月2日15初診。患者訴1個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頭暈、全身疲乏、雙下肢酸困無力、活動后氣短、活動耐力下降,遂就診于當地醫院,查常規心電圖示:竇性心律,心率49次/min;動態心電圖示:24 h心搏總數71264次,竇性心動過緩并不齊,平均心率50次/min,最慢35次/min,最快98次/min,房性早搏615個,心率<50次/min占總心率的45.5%。余檢查未見明顯異常。患者臨床癥狀顯著,建議置入起搏器治療,但患者未同意,遂就診于甘肅省名中醫李應東教授處。當下癥見:間斷心悸、心慌,氣短,頭暈,稍活動即加重,面色無華,神疲,倦怠乏力,雙下肢沉重、酸困無力,語聲低微,背部怕冷,飲食及睡眠正常,二便調,舌質淡暗,苔薄白,脈沉遲無力。患者訴既往體健,無其他疾病史。復查心電圖示:竇性心律,心率48次/min,交界性逸搏。脈癥合參,中醫診斷:心悸病,心腎陽虛兼血瘀證。治法為溫陽益氣、和血通脈,給予真武湯合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加減,處方如下:淡附片12 g,白芍20 g,白術10 g,生姜10 g,茯苓20 g,桂枝15 g,龍骨20 g,牡蠣20 g,熟地黃20 g,大棗10 g,淫羊藿15 g,仙茅12 g,丹參30 g,酒黃精15 g,炙黃芪30 g,山萸肉12 g,黨參25 g,炙甘草6 g。配方顆粒7劑,每日1劑,每日2次,開水沖服。
2020年2月22日二診:患者訴心悸、疲乏無力、怕冷較前改善,余癥狀未見緩解,監測心率為45~50次/min,納食及睡眠正常,二便調,舌質淡紅,苔薄白,脈遲。復查心電圖:竇性心律,心率49次/min。在上述方藥基礎上加麻黃3 g,細辛6 g。繼服7劑。
2020年2月29日三診,患者訴上述癥狀明顯改善,心率50~58次/min,稍有下肢酸困,余無不適,舌質淡紅,苔薄白,脈緩。上方去龍骨、牡蠣,加益母草20 g,桃仁10 g,枳實12 g。予14劑繼服。
2020年3月14日四診,復查動態心電圖示:竇性心律,24 h心搏87840次,心率最快89次/min,最慢47次/min,平均61次/min,房性早搏24 h 126次。效不更方,繼續以上述方劑14劑以穩固療效。隨訪2個月,患者未再復發。
按:真武湯出自《傷寒論》,主治少陽病過汗損及腎陽及少陰病邪氣漸深,腎陽日衰、水氣內停之證[1]。李應東教授認為竇性心動過緩的主要病機為心腎陽虛,人身之陽氣以腎陽為本,如“五臟之陽氣,非此不能發”。腎之陽氣不足,心陽亦不足,此病證雖與真武湯證癥狀不一,然病機相同。李教授謹守病機,主方以“真武湯”加減溫補心腎、助陽化氣,合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調和陰陽、安神定悸,以達到形神同治,加活血化瘀之藥標本兼治。《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故用黃芪、黨參、酒黃精合附片、桂枝等溫陽益氣。方中桂枝湯調和營衛,有“損其心者,調其榮衛”之旨,并且桂枝湯加入黃芪,又有黃芪桂枝五物湯之和血通脈之意。研究表明桂枝湯能夠直接興奮心臟從而增強心肌功能,這與桂枝湯中醫理法中具溫經通陽的功效是一致的,且桂枝、甘草配伍能提高心陽虛證大鼠心肌組織能量代謝酶活力[2,3]。心陽不振,恐心神不斂而浮越耗散,因此加龍骨、牡蠣固澀潛鎮浮陽,使神能內守,合大棗安神定悸[4,5]。酌加淫羊藿、仙茅溫補腎陽腎精增強溫陽之力,丹參活血通絡,熟地黃、山萸肉養陰,以陰中求陽,并且山萸肉可制附片之毒。諸藥配伍,有溫陽益氣、養陰活血、安神定悸之效,標本兼治,使氣血陰陽調和,脈氣得復,四肢百骸得養。二診,患者癥狀雖稍有改善,但心腎陽氣仍不足,不能鼓動氣血運行,故加少劑量麻黃、細辛,配附片溫陽驅寒,合桂枝以鼓動心氣心陽,使血行脈通。多項臨床觀察發現麻黃附子細辛湯對各種緩慢性心律失常效果肯定[6-8],藥理研究亦證實附片、細辛均具有強心作用,能使心肌收縮增強,心率增快[9,10]。三診,經前方治療,患者雖心腎陽氣漸復,但血中瘀滯未除,故去龍骨、牡蠣收斂之品,加益母草、桃仁、枳實等以活血通脈、理氣行滯,共達通陽、散寒、行滯之效。四診,患者心腎陽氣基本恢復、血中瘀滯漸除,脈平和,效不更方。本案例體現了李應東教授治療竇性心動過緩心腎同治、形神同調、標本兼治的基本思想,具體治療中以溫補心腎陽氣為主,“溫者,和也,養也”,強調既不能以一派溫燥之藥傷精耗液,也不能過用補益之品助濕生痰,溫陽同時兼益氣、活血、安神,氣血陰陽同調;更強調治療的不同階段、病情演變的不同時期氣血陰陽偏重不同,遣方用藥亦有所不同,謹遵《傷寒論》“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