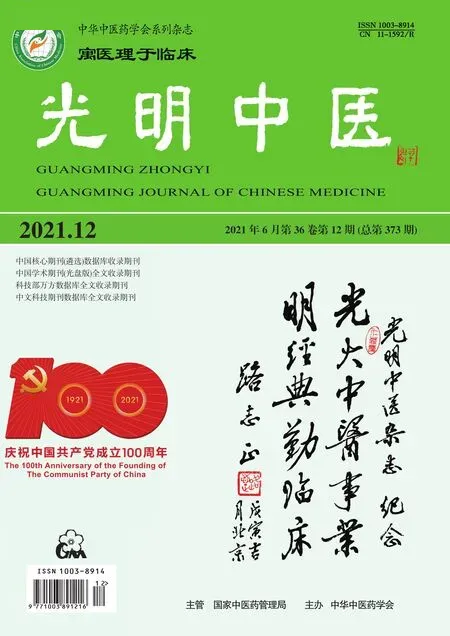何若蘋醫師治療脾虛濕盛證直腸癌經驗淺析*
余文亞 何若蘋 龔文波
何若蘋醫師為國醫大師何任先生學術經驗繼承人,國家級名中醫,第五、六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從事中醫臨床工作近40年,擅長治療內科、腫瘤、婦科疾病及各種疑難雜癥,臨床經驗豐富。筆者有幸跟師隨診,獲益匪淺,現將何師治療直腸癌脾虛濕盛證的臨床經驗總結如下。
1 治療現狀
直腸癌現為我國發病率較高的惡性腫瘤之一,隨著中醫藥事業的不斷發展進步,在腫瘤治療中不斷顯示出獨特的治療優勢,越來越多患者開始在腫瘤的各階段采用中西醫并用的治療方式。長期臨床觀察表明,中醫治療可改善患者預后、提高生活質量、延長存活期、減輕由于放化療帶來的不良反應并抑制腫瘤的復發、轉移。
2 病因病機
在傳統中醫的理論中并不存在直腸癌這一說法,故此病可歸類于“腸覃”“臟毒”“鎖肛痔”等[1]。《黃帝內經》認為“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系,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中醫對于其發病原因大多遵循《黃帝內經》和《難經》中“因虛致疾”的理論,由于臟腑氣血功能失衡,正氣虛弱不能抵御外邪并產生了大量的痰飲、血瘀等病理產物,正虛瘀滯,最終導致腫物形成[2]。
3 脾虛濕盛證
現有研究表明結直腸癌的中醫證型多包含腎陽虛、脾虛濕盛、痰瘀毒聚、氣血虧虛、肝腎陰虛等,無論從文獻還是數據研究都提示大多數的直腸癌患者出現與脾虛有關的臨床表現[3,4]。脾虛濕盛證是在脾虛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主要是由于脾氣虛弱,脾失升清導致水谷運化失司,氣機升降失常,出現濕濁內生,水濕停聚,從而阻遏陽氣,阻滯氣機,郁久而化熱,凝聚成毒,且氣滯則血瘀,痰瘀毒互結,形成“瘜肉”。其主要臨床表現為納少,胃脘滿悶,甚或惡心欲吐,口黏不渴; 肢體倦怠,舌苔厚膩,脈緩等。且根據五行學說,脾胃虛弱則不能耐受肝氣的克伐,可伴有頭暈、噯氣、胸脅脹滿、腹痛泄瀉等表現,若日久脾病及腎,則會導致全身水腫。治法當以燥濕健脾,理氣消腫[5]。何師常用黃芪益氣健脾,太子參養陰生津,合以豬苓、茯苓等利水通淋,并入女貞子、枸杞子等補益肝腎,稍加理氣藥,調暢氣機,達到止痛、散結之效。同時加入貓人參、藤梨根、絞股藍、白花蛇舌草、重樓、三葉青等中藥[6,7],此類中藥經現代藥理研究表明具有提高人體免疫力的作用,從而起到抑制腫瘤細胞的效果[8-10]。
4 醫案舉例
案1患者,女,67歲。2018年12月22日初診。2017年5月22日行直腸癌根治術,同年8月24日作回納手術,曾作子宮及闌尾切除術,有高血壓病史,27日查血糖7.31 mmol/L,三酰甘油3.05 mmol/L,服用降壓西藥(具體不詳)及通便藥。現出現腰背痛,查骨密度,結果為骨質疏松,服西藥。納欠可,肢體倦怠,大便不暢。查體舌下紋黯,苔薄,脈弦。方藥:太子參30 g,豬苓24 g,女貞子12 g,枸杞子15 g,白花蛇舌草30 g,貓人參30 g,黃芪30 g,蒼術15 g,藤梨根40 g,絞股藍30 g,枳殼12 g,決明子30 g,制黃精30 g,瓜蔞仁30 g,鬼箭羽18 g,火麻仁10 g,桑寄生15 g,炒續斷15 g。共14劑,一日2次。
按:患者直腸癌術后,體質狀態不佳,臟腑功能失調,脾胃虛弱,水谷精氣生成減少,營氣不足,脾失升清,氣機運行障礙,導致濕濁停滯,出現肢體倦怠,大便不通暢,納差等表現。證候當為脾虛濕盛。藥用太子參、黃芪補氣健脾,絞股藍、白花蛇舌草、貓人參清熱解毒,蒼術、茯苓健脾祛濕,枳殼寬胸理氣,瓜蔞仁潤腸通便,女貞子、枸杞子補益肝腎。且患者出現大便不通、腰背疼痛、舌下紋黯等癥狀,再入火麻仁、決明子等潤燥滑腸,鬼箭羽降低血糖[11],桑寄生、續斷補肝腎,強筋骨。諸藥相配達到益氣養陰,清熱利濕的效果。
案2患者,男,65歲。2016年9月作直腸癌根治手術,病理示(直腸)潰瘍型中分化腺癌,腸周淋巴結(5/15枚),未見肝癌。拒絕化療。2018年6月b超示:膽泥沙樣結石,胰腺脂肪浸潤。腹部欠舒適,納可。大便次略頻,日行5~8次,舌有瘀點,苔白厚膩,脈細、弦。方藥:太子參20 g,豬苓30 g,茯苓20 g,女貞子 10 g,枸杞子10 g,白花蛇舌草12 g,貓人參30 g,黃芪30 g,藤梨根30 g,蒼術15 g,芡實15 g,山藥 18 g,沉香曲8 g,薏苡仁(另包)30 g,郁金12 g,白芍20 g,炙甘草10 g。共14劑,一日2次。
按:患者術后狀態欠佳,辨證屬脾虛濕盛證,方用參芪苓蛇湯加減,治以益氣健脾,清熱利濕[12,13]。并入郁金活血行氣、利膽退黃,白芍補血柔肝止痛。且患者病程日久累及肝腎,加入女貞子、枸杞子補益肝腎,沉香曲疏肝健脾,芡實補脾止瀉。
案3患者,女,68歲。2017年6月行直腸癌根治手術,已做化療,血脂高,可觸及乳腺及甲狀腺結節,近做體檢提示:高脂血癥,雙側頸動脈內-中膜局限性增厚,納可,大便日2~3次,苔薄,脈細、弦。方藥:太子參30 g,蒼術15 g,黃精30 g,藤梨根40 g,瓜蔞子 10 g,甘草10 g,茯苓15 g,沉香曲6 g,白花蛇舌草 30 g,淡竹葉12 g,炙甘草10 g,大棗10 g,貓人參30 g,重樓9 g,豬苓18 g,絞股藍30 g,制何首烏15 g。共14劑,一日2次。復診時,狀態稍好,述近期體檢查癌胚抗原 12.1 ng/ml,較前略降,神經烯醇化酶17.6 ng/ml。原方加香茶菜30 g。共14劑,一日2次。
按:患者直腸癌根治術后,又行化療,耗氣傷血,導致氣血虧虛,脾胃虛弱,運化失職,痰濕積聚,辨證屬脾虛濕盛證,方用四君子湯加減,治以益氣健脾,清熱利濕[14]。并入豬苓利尿祛濕,抗腫瘤[15],重樓、絞股藍、白花蛇舌草、貓人參清熱解毒,絞股藍益氣健脾,化痰,瓜蔞子潤腸通便,黃精、制何首烏補益肝腎,沉香曲疏肝健脾,香茶菜清熱祛濕、解毒消腫、抗腫瘤活性。諸藥相配起到益氣健脾、清熱利濕的功效。以降低化療不良反應,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大量臨床資料顯示,目前治療大腸癌,殺滅癌細胞不是唯一的目標,而現階段治療的焦點所在是提高生存質量。
5 病后調理
《黃帝內經》有云:“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益精氣,飲食者,人之命脈也”。養生,要從飲食做起。《周禮》中有記載,我國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時代就已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理療體系,醫事制度中已設有負責飲食營養管理的專職人員。當時醫生分為四類,即“食醫”“疾醫”“瘍醫”“獸醫”。而周代的醫療體系又以“食醫”為先,“食醫”的任務是“掌合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饈、百醬、八珍之齊”。即調和食味,確定四時飲食,預防疾病。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最早的“營養醫學”的實踐。
在直腸癌脾虛濕盛證型的病后營養調理中,何師強調要注意顧護脾胃之氣,培養后天之本。何師有廣為流傳的一土方:“用福建浦城的薏苡仁熬粥,再用榨汁機將其打成糊狀,作為早餐食用。”長期服用,有益于直腸癌脾虛濕盛證型病后脾胃之氣的恢復,又能健脾祛濕,清熱排膿,舒筋除痹,功效之廣,令人驚嘆。這也很符合《黃帝內經》中“五谷為養”的學術思想。
6 體會
在癌癥的治療中何師倡導扶正祛邪的治療法則,通過平衡人體陰陽,增強人體正氣,達到正勝邪退的效果。直腸癌的治療往往也需遵循扶正祛邪的原則,隨證治之,且何師認為,在治療中尤其要注意顧護脾胃之氣,培養后天之本。對于直腸癌中的脾虛濕盛證治當健脾燥濕,調和脾胃,脾氣健運則氣血化源充足,正氣強盛。此外在扶正的基礎上還應佐以清熱解毒利濕等祛邪之法,邪去則正安。